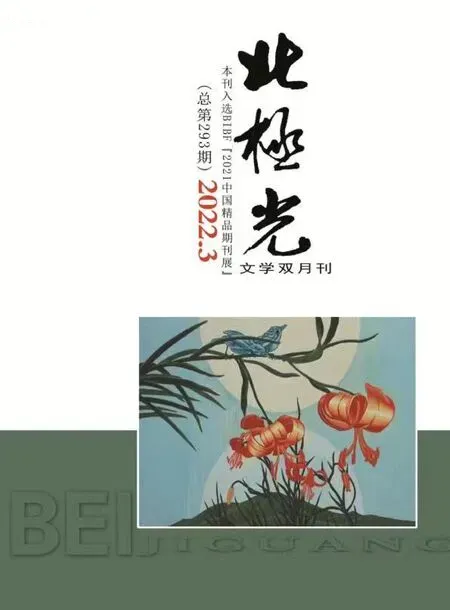胭脂泪
2022-10-21杨玉环
□杨玉环
山头上下来一群清一色的老爷们,说是老爷们,除了鄂伦春族的乌吉之外,他们个顶个没有娶妻生子,倒是山下的妓女过了他们的童子身,把他们变成了老爷们。这群人是李把头带领的金帮兄弟。李把头原本姓白,只因为淘金人忌讳白、黄、吴、梅……这些姓氏,何况他叫着一个跑空的名字——白涛,不就是白掏嘛。他把姓改成李,名元。说姓李的坐过江山,元就是元宝,元宝就是财。
这次进山他们运气不错很走点儿,从按碃(挖坑)到杀青各个环节都很顺当。刚开始往下挖三米,就见到金沙层,然后他们开始掏横洞,一直掏到金线断处。人在横洞里走要猫着腰,借着冒黑烟的松明照亮,一步一挪地把金沙背到胭脂河河床上。等到燕来河开,胭脂河里一下热闹起来,运沙的,摇簸的,清理溜槽的……一片繁忙景象,簸簸闪着金灿灿的光芒,大家一片啧啧,阵阵惊呼。乌吉手里的金簸子越摇越快,好像停不下来的机器,汗水流下来也不舍得停下擦一下。运沙的人浑身是劲儿,一溜小跑,倒掉金沙,还要站在溜槽前享受一番收获的快乐。清理溜槽的魁胜是个闷葫芦,一锹接着一锹挥舞,撮的石子儿擦擦冒着火星子。蹿蹿跶跶的老疙瘩去给李把头报信。孙把头正在竖大拇指,看到李把头趟过花丛走下河床踏上板桥,立即迎上前去说:“大当家的,你真是火眼金睛,一看一个准儿,神了,神了。”接着招呼:“快看,簸簸有黄货。”李把头嘴角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得意,转身走了。
分金子那天晚上,大当家李把头按照老规矩,扣除上缴朝廷和帮里吃喝拉撒的金子,十六人,平均分成十九份。大当家李把头拿三份,二当家拿两份。李把头把事做在面上,弟兄们很服气,没有说三道四的。李把头要打点收金子的朝廷官吏,每次下山还要设宴招待一些小喽啰。孙把头起初不同意多拿一份,说要和弟兄们平分平摊。李把头说“麻溜拿着,你白天和弟兄们一起流血流汗,晚上还要给弟兄们下套撂野物,这是你该得的。”然后目光扫视周遭一圈问:“是不是?”“是”弟兄们语调高高的。李把头轻易不言语,他说话就是圣旨,一口唾沫能砸一个坑。
在这个昏暗的长筒棚子里,霉味儿、烟味儿、汗臭味儿混杂着,可此时这些淘金人完全被兴奋、欲望充斥着。简易的木桌上摆着一圈大海碗,围着一圈黑红汉子,有的光着膀子,有的单脚站立,有的挽着裤腿,黝黑的臭脚丫子蹬在长条木凳上。不等李把头开口,老疙瘩就搬起酒坛子咕咚咕咚倒满一圈酒,李把头示意孙把头讲话。孙把头嗓门大说话有震慑力,他双手把海碗举过头顶又落到胸前说:“弟兄们!咱们这次进山逮着了,咱的土堆高别家一人多,真是山神保佑!
采金男们扛着金镐、金锹,抬着溜槽,提着金簸子、木刷子大步流星地向山下走着,他们精神亢奋到燃烧状态。李把头煞在后面沉思。进山前,金帮搭起了祭台,祭台上供奉着山神爷的牌位,牌位中间摆着猪头两边各放一只全鸡,祭品前正中是香炉,三根香火青烟缭绕,火星炫目,好兆头。这些人齐刷刷跪成一排,破指滴血酒中,虔诚地三叩首,李把头口中念念有词:“山神保佑!保佑金苗旺盛!保佑这次能出金暴子(狗头金)!”然后大家齐呼:“土里求财、黄金自来、以血盟誓、同心协力!”倒掉半杯酒祭神,半杯酒喝下。出发时,李把头、孙把头、按碃的、摇金簸子的共16人,回来还是十六人,李把头很知足。以往进山人员都有损失,有偷金子被打死的,有在金道里塌方被砸死的,像这么全回来的还是第一次。
这里是妓女和嫖客进行交易的地方,有金帮的人、商人、地痞、还有朝廷的官吏等各种人。妓女们排着队煽情地欢迎他们,而当他们走过去又发泄不满。孙把头挑选了玫瑰厅停下脚步,回头看一眼弟兄们,这一眼就是无声的命令,大家随后而入。
大厅里就剩下李把头和一个妓女。这时老鸨花枝乱颤地扭搭过来说:“百合可是我们这里最美的姑娘,睡一宿可是其他姑娘的三倍价钱。”李把头依然没说话,只是瞪了老鸨一眼,老鸨没趣地走了。百合始终低着头,穿着打扮也不同其她妓女,白底蓝花立领的偏襟小褂,靛蓝色缎带滚边,对称的一组组盘扣很精致,下身是海蓝色滚筒长裙,这打扮倒像大家闺秀。这两个人好像用沉默对峙着,李把头伸出中指和食指擎起百合的下巴,立即呆住了,“是你!”百合:“嗯”了一声。
看到这个百合,三个月前的一件事又浮现在李把头眼前。那天大家正在淘金道里干活,在远处撒尿的老疙瘩惊慌失措地提着裤子跑回来,“不好了!不好了!女、女、女人。”李把头问:“在哪里?马上拦住!”老疙瘩说:“已经进沟了。”李把头顿时眼就红了:“把她绑上来!”,“是!”大家应道。老金沟有个“女人不可进沟”的戒律。女人一旦进沟就会破了风水,惹怒山神,金子就会自然消失。正是要出金子的节骨眼儿上,有女人进沟,李把头怎能不急眼?当这个女人被带到他眼前,他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子呦,白得透明干净,像玻璃人碰一下都会破碎似的,一双丹凤眼镶嵌在瓜子脸上,翕动的鼻翼下小嘴像打朵的花骨朵,楚楚可怜的是那双眼睛,瞳仁好像浸在苦水里,那里面藏着说不尽的心酸故事。虽然姑娘穿着粗布衣褂,但依然像埋在雾里的珍珠让人觉得珍贵。李把头顿生惺惺相惜之感,但他为了给弟兄们看,不得不语气强硬地问女子:“你懂不懂这里的规矩?惹怒了山神,是要付出代价的。”女子回答“俺刚来这里不久,不知道什么规矩。”这个“俺”字好像血液里的声音,触动了他心里的软处。李把头沉默半天提了提嗓门:“一个女人进山干什么?不怕狼吃了、黑瞎子舔了?”女子回答说:“找人……”还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李把头说:“女人进沟要砍掉一只脚祭奠山神,否则兄弟们都没饭吃。”女子强硬地说:“你最好把我杀了!”李把头眼睛一闭摆了摆手吩咐手下兄弟:“动手吧!”弟兄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忍心下手,齐刷刷跪了下来:“李把头,还是换个惩罚方式吧!”这也正是他要听到的话,弟兄们求情日后就不会落下埋怨的话柄。李把头唉了一声“算你有造化,看在弟兄的面上,就饶了你。但是你必须留下身上的一样东西祭奠山神。这样吧,头发也是父母血脉之物,你割下一绺头发吧。”一绺头发被放在金道里,女子才被撵出老金沟。
此刻,在这里李把头又逢这女子,真是百感交集。他拥着百合进了房间。李把头没有心急火燎地撩帐上床,他喜欢一点点把灯拨亮,一下下把锅烧开。他命令女子:“把头抬起来!”百合很温驯地照着做了,百合的沉默终于激怒了他,他捧着她的脸,贪婪地盯着她说:“我的小母鹿,不要装可怜,干啥吆喝啥,今天把爷伺候好了,爷亏待不了你。”百合说“别把我想得那么坏。”
似乎这个百合重情重义,李把头对她很满意,接着他收敛了粗鲁又问:“看你是良家女子,为什么沦落到这里?”百合声音低低地说“活命,只有活命才有希望。”她顿了顿,无可奈何地说:“习惯就好了,不干这行也是给人做小,没什么两样,都是下贱的活法,好在采金子的男人个个对俺不薄。”
听了这番话,他露出赞许的表情。她不像其他妓女哭诉一番,找出被逼上这条路的各种理由。“你不是当地人?”李把头又问他。百合点点头,没有作声。“你打哪儿来?”李把头追问。“山东。”百合回答。
李把头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子,就从口音里猜到她可能是山东人。他突然抓紧了她的手,重复着:“山东,山东。”这回俩人好像转换了角色,百合问他:“难道你……”“不错,俺也是山东人。”李把头回答。
百合犹豫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换了一种比较严肃的语气问:“你们采金子的人里有山东胶州来的吗?”“有!”李把头突然很紧张地说。“那你认识白涛吗?你不一定认识,他可能改了名字,你们这里不许姓白。”
李把头猛地顿了一下,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他想再探探百合的语气。“怎么,你认识他?”“不!”百合立刻否定。“这个女人为什么找白涛?”此时李把头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一般。百合又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问:“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老金沟。”李把头肯定地说。
百合电击一样忽地一下子跳起来,然后又犹豫了,喃喃低语:“好,真是太好了!”
李把头望着她,越发感到不安。他很想知道究竟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要找他?”
百合这次像下了决心,哆哆嗦嗦倒了一杯水,然后一口气喝下去,长出一口气。“可以说了吧?”李把头似乎不耐烦了。
百合说:“你要向我保证,不能告诉他你见过我,更不能告诉他这些话在哪里听说的,你必须发誓。”
“我向老天发誓。”李把头很真诚地说。
“好,那你告诉白涛,他爹他娘都死了,弟弟也死了,三个人都是伤寒病死的。”
这时,李把头周身的血液像潮水要冲破血管一般,接着又慢慢降到冰点。过了好一阵子,他也找不出合适的语言回答。他突然起了疑心,问:“你打哪听说的?”
百合用双手抚摸着李把头的肩膀,紧盯着他说:“他是我哥哥!”
李把头的喉咙像被堵塞了一样半天才喊出了她的名字:“兰子”。
百合又紧盯着他看,接着在疯狂的恐怖和恐慌中用低低的,低得几乎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喃喃地说:“哥哥?”
四目相对,都愣住了。
这时,其它房间里传出来的呻吟声、玻璃杯的碰撞声、浪笑声、靡靡调子声混合着、交织着。
李把头感觉自己正在亵渎一个女神,正在侮辱伦理……整个人突然瘫软在地,脸色失血般苍白。
屋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一般,他猛然站起狠狠地抓住百合的肩膀,眼冒凶光厌恶地说:“你怎么能做这个?”
百合眼里噙满泪水,“你说出去淘金子让俺家过上好日子。这一走就是十一年,你走时我才九岁,家里一起死了仨人,天都塌了。俺把自己卖给了人家做姨太太,才葬了爹娘和弟弟。晚上,那老不死的行不成男人之事,就整夜折磨我。我是趁着黑夜逃出来的,一路讨着要着往东北走,后来听说官兵进山给慈禧往返送金子,我就尾随他们进山了。有一天我又渴又饿,就昏倒在河边,被这里的姑娘抬回来,我和这些可怜的姑娘一样当了妓女。”
百合涕流满面,像瀑布冲洗着玉石。
她又说:“我以为你不在人世了!”
李把头说“我根本认不出你来,我离家时你又瘦又小,可现在却长成大姑娘了,那你怎么会认不出我来呢?”
百合无可奈何地说:
“我见过的男人太多了,所有的男人在我眼里是一个样的!”
李把头一直盯着她,心乱如麻,嗓子眼直冒火,很想大哭大叫几声。想想妹妹卖身给亲人送终,还有遭受的磨难。他慢慢把她拉进怀里,越抱越紧,像抱着爹娘和弟弟,他哽咽了,男子汉到动情处也会哽咽的,像潮水一样涌着,涌着。
李把头突然站起来,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出了屋子。他在大厅里大声咒骂,抡起拳头狠命地捶打桌子,酒杯被摔得粉碎。他向前迈几步,摇晃几下,消失在漆黑的夜里。
其它房间的金帮弟兄像从筛子眼儿里露出来一样,踹开百合的门,想看个究竟。
百合蜷缩在地上哭着。
金邦兄弟跑回驻地,发现李把头坐在门前,一口接一口地吸着旱烟袋,眼睛直勾勾一动不动。孙把头摆摆手,其他弟兄都进屋了。孙把头低声细语地问:“当家的,出了什么事?”李把头一点反应没有,整个人处于麻木状态,孙把头不再言语,默默地陪着他。直到月落星稀,李把头才机械地从兜里掏出一袋东西,丢在孙把头面前,天亮了,去赎百合,金子不够,把你的添上。
孙把头正准备安抚大当家的去休息,他好洗把脸去办事。这时乌吉来了,进院就说有个叫百合的妓女跳河了。乌吉根本想不到这是致命的话,孙把头想挡乌吉的话根本不容空,再看李把头好像突遭重创,像发狂的豹子……
李把头疯了。
胭脂河岸传着凄怆的歌声:妹妹,你顺着河走,这是回家的路,爹娘在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