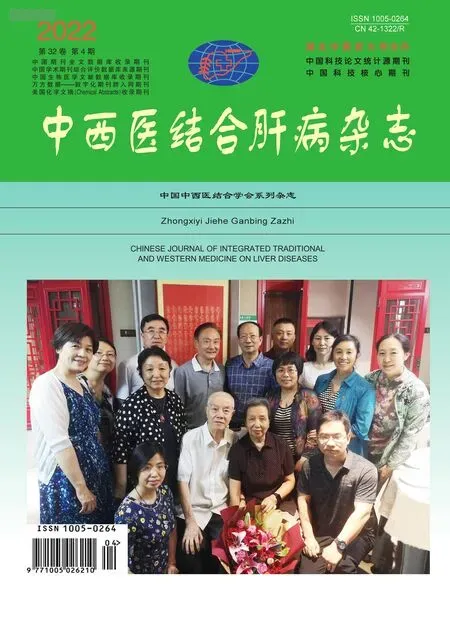龙胆泻肝汤治疗难治性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验案两则
2022-10-15余思雨
龙胆泻肝汤出自《医方集解》,由龙胆草、黄芩、山栀、柴胡、当归、生地黄、木通、车前子、泽泻、甘草十味药组成,具有泻肝胆实火、清肝胆湿热之功,且能兼顾补养肝血,使苦寒不伤阴血
。更有《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称其“妙在泄肝之剂,发作补肝之药,寓有战胜抚绥之义”。我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国家首届岐黄学者季光教授临证加减用其治疗难治性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案疗效满意,现将典型的2则病案介绍如下。
1
PBC
Ci,j(φi+1,j+1-φi,j)-Ci-1,j-1(φi,j-φi,j-1)+Di,j(φi+1,j-1-φi,j)-Di-1,j+1(φi,j-φi-1,j+1)
患者,男,57岁,2020年6月23日以“肝区胀痛伴纳差2周”首诊。患者2017年体检发现肝功能异常,血清M2抗体(++),诊断为PBC,一直服用熊去氧胆酸胶囊(优思弗)治疗,剂量为250 mg,tid po,肝功能基本正常,B超未显示肝硬化。今年以来肝功能持续波动,消瘦明显。查血糖8.0 mmol/L,总胆红素40.1 μmol/L,ALP 321 U/L,GGT 191 U/L,上腹部增强CT示胰头部脂肪浸润。刻下:头汗出,肝区胀痛、纳差、食后腹胀、尿黄、大便粘滞,口苦多饮,舌暗,苔腻,脉弦涩。否认病毒性肝炎病史及其他传染病病史,否认饮酒史,否认糖尿病史及手术外伤史。拟诊胁痛(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龙胆泻肝汤证),予龙胆泻肝汤加味治疗。龙胆草、木香各3 g,炒栀子、制大黄各9 g,黄芩、车前子、泽泻各15 g,柴胡、当归各12 g,生地30 g,厚朴18 g,共21剂。2020年7月14日二诊,患者药后汗出、肝区胀痛、纳差、食后腹胀、口苦诸症缓解,仍尿黄、口气重、苔腻,自测血糖4~6 mmol/L。宗原方予茵陈30 g,藿香9 g,桃仁12 g,共28剂。2020.8.18日三诊,诸症缓,复查肝功能总胆红素21.7 μmol/L,ALP 74 U/L GGT 54 U/L,随访至今病情稳定。
精准扶贫实际上是一个包括“精准识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环节的复杂过程。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首先要遴选好扶贫对象,着力从贫困人口中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促进贫困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脱贫。为此,除了要重点选择地处贫困地区的农业生产企业带头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学生村官、种植养殖大户等作为培育对象以外,还要从贫困地区人口中重点选择青壮年、较高学历者、返乡农民工等人群作为后备培育对象,通过对遴选对象的科学考察,按照技术型人才、经营型人才、服务型人才等不同层次分别加以培育,充分发挥其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的带头与引领作用。
2
AIH
-PBC-
SS
目前,该项竞赛在教育部的组织与指导下已成为参与人数多,影响范围力广,知名度高的全国性学科竞赛之一,深受广大工科院校师生的青睐。
患者西医诊断明确,属UDCA应答不佳的PBC,中医脉证表现为头汗出,肝区胀痛、纳差、食后腹胀、尿黄、大便粘滞、口苦多饮,舌暗,苔腻,脉弦涩。此患者辨治难点在于湿和热之偏重,如热重于湿,当予茵陈蒿汤。《伤寒论》第236条: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本例患者身不发黄但尿黄,头汗出、口苦多饮,符合茵陈蒿汤证表现。但考虑到患者纳差、食后腹胀、大便粘滞,虽苔腻而黄不显,应属湿重于热,予龙胆泻肝汤为稳妥之选。方中龙胆草、栀子、黄芩清肝泄火,柴胡疏肝理气,泽泻、车前子清热利湿,生地、当归养血清热益肝,佐以制大黄、厚朴有通因通用之意,少佐木香芳香醒脾。二诊诸症缓,口苦转为口气较重,仍有尿黄、苔腻,说明瘀热留恋,故仍以龙胆泻肝汤为主,佐以茵陈、藿香加强清热祛湿作用,佐桃仁化瘀不助热;全方兼顾肝、脾、湿、瘀,用药后患者自觉症状减轻自觉良好,肝功能恢复良好,病情稳定至今。
患者,女,58岁,2020年6月22日以“右上腹胀痛3年余”首诊。患者右上腹胀痛3年余,曾于外院诊断为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予熊去氧胆酸胶囊(优思弗)治疗后肝功能异常,遂停止治疗。来诊时患者右上腹胀痛,口干、眼干,时有皮肤瘙痒。胃纳可,二便调,夜寐安,舌红少津,苔薄黄,脉弦细。2020年4月22日检查示:抗SS-A(±),抗M2-3E(+),抗gp210(++),总胆固醇7.7 mmol/L↑,γ球蛋白24.3%↑,ALT 74 U/L,ALP 211 U/L,GGT 114 U/L。CT示:肝内多发低密度灶,左肾中部小囊肿可能,附见右侧心膈角小淋巴结。腮腺活检提示:符合干燥综合征表现。肝组织病理见小叶内肝细胞肿胀、变性,门管区扩大伴中度界面性炎症,以淋巴细胞为主,胆管炎和周围炎易见,部分区域组织增生伴纤维间隔形成,提示:AIH-PBC重叠综合征(G3-S3)。拟诊胁痛(AIH-PBC-SS重叠综合症,龙胆泻肝汤合生脉饮证),西药予泼尼松龙联合硫唑嘌呤方案(硫唑嘌呤100 mg/d,泼尼松龙60 mg/d 1周、40 mg/d 2周),中药予龙胆泻肝汤合生脉饮加减治疗。龙胆草3 g,栀子9 g,黄芩、柴胡、川朴、桃仁各12 g,生地30 g,车前子、党参、麦冬各15 g,五味子6 g,共21剂。2020年7月13日二诊,右上腹胀痛、皮肤瘙痒好转,仍有口干、眼干,胃纳可,二便调,舌红少津,苔薄黄腻,脉弦细。原方去党参、麦冬,加蛇舌草30 g,芦根30 g,共21剂,逐步调减西医治疗方案(停用硫唑嘌呤,泼尼松龙20 mg/d/1周、10 mg/d/1周、5 mg/d/1周逐周递减至3周后停用)。2021年8月10日随访,右上腹胀痛、皮肤瘙痒、口干、眼干诸症均已缓解,连续三次复查肝功能正常(每2月1次,患者拒二次肝穿)。
PBC(旧称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是一种自身免疫性肝病,病理表现为免疫介导的胆道上皮细胞损伤、胆汁淤积和进行性纤维化,最终会进展至胆汁性肝硬化。约90%患者为女性,男性较为少见,发病年龄30~65岁,30%~50%无症状患者通常在常规检查中被发现
。用于治疗PBC的药物包括熊去氧胆酸(UDCA)、奥贝胆酸(OCA)。所有PBC患者的一线药物治疗方法为口服UDCA,剂量为13~15 mg/kg/日,若能耐受,则应终身治疗
。对UDCA不完全应答指的是ALP>1.67×ULN和/或胆红素升高<2×ULN
,未获应答或者不完全应答患者发生终末期肝病的风险明显增加,预期生存率显著低于应答患者,是目前临床治疗的难点。尽管法尼酯衍生物X受体(FXR)激动剂OCA的问世有望改善疾病相关的生化指标,并有可能改善预后
,但目前OCA并未在我国上市,且缺乏对中晚期PBC远期生存获益的真实世界研究结果,因此中医药成为UDCA应答不佳PBC患者的重要补救方法。
杭州市运河片区位于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的交界处,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与东苕溪接壤,东面止于上塘河。该研究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根据杭州气象站资料,研究区2003—2008年多年平均气温17.83℃,多年平均年日照数1 650.03 h,多年平均年降雨量1 158.45 mm,多年平均年降雨天数133 d。研究区占地面积823 km2,涉及上城区、下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江干区和余杭区等6个行政区,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水路交通方便,工农业、旅游业发达,经济发展迅速。
自身免疫性肝病是一种病因不明,与自身免疫有关的慢性肝病,包括AIH、PBC、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
。临床上部分患者可同时具有2种或2种以上疾病重叠发病,称为“重叠综合征”,其中以AIH-PBC重叠综合征最为常见
,在病理组织学上出现碎屑样坏死和破坏性胆管炎特征性改变,是肝硬化、肝功能衰竭和肝移植的主要原因之一
。AIH-PBC-SS重叠综合征临床并不常见,诊断和治疗难度很大。本例患者短短数年间集三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于一身,辗转多家医院最终确诊,赢得了治疗时机。PBC与原发性SS具有类似的发病机制,都是一种自身免疫性上皮细胞炎,表现为上皮细胞的异常凋亡和靶器官炎症
。有报道称约70%的PBC患者可并发SS
。大部分原发性SS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病的患者经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的治疗后病情好转
。
欧洲肝脏研究协会和国际自身免疫性肝炎小组均推荐UDCA与免疫抑制剂联合治疗作为AIH-PBC重叠综合征的首选方案,对于AIH活动相对较轻的患者,建议仅从UDCA开始,如果在3个月内没有获得足够的生化应答,则需添加免疫抑制剂联合治疗
。而糖皮质激素对AIH的治疗效果肯定,但重叠综合征尚无确切的治疗方法
。SS目前尚无根本的治疗方法,临床以局部疗法(替代疗法)、系统疗法(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为主
,中医治疗SS有显著优势,不但可以有效地改善局部症状,还可及时阻断或减缓病情的进展,预后良好
。
患者抗SS-A(±),抗M2-3E(+),抗gp210(++),结合病史,是具有SS、自身免疫性肝病包括AIH、PBC的三重综合征。首选UDCA治疗,但患者UDCA过敏,本案在予泼尼松龙联合硫唑嘌呤方案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中医药治疗起到缩短病程,尽早撤减泼尼松龙用量的目的。《医原》谓:“湿郁则不能布津而化燥”、“燥胜则干”。本例患者合并SS,并有口干、眼干、舌红少津,苔薄黄,脉弦细等阴虚和津液不足之象,予龙胆泻肝汤合生脉饮加减治疗。方中龙胆草泻肝胆之火,以柴胡为肝使,佐以芩、栀、泽、车大利前阴,使诸湿热有所从出也,加桃仁破血散瘀不助热。生脉饮中人参易党参,补益气血而不助火。二诊仍有口干、眼干,舌红少津,苔薄黄腻。原方去党参、麦冬,加蛇舌草、芦根加强清热生津之效。
[1] 赵晓英.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68-69.
[2] 姜小华,仲人前,孔宪涛.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发病机制研究进展[J].中国免疫学杂志,2002,18(8):586-589.
[3] Bowlus CL, Gershwin ME.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J]. Autoimmun Rev,2014,13(4-5):441-444.
[4] Hirschfield GM, Dyson JK, Alexander GJ,
. The British Society of Gastroenterology/UK-PBC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guidelines[J]. Gut, 2018, 67(9):1568-1594.
[5] Cheung AC, Lapointe-Shaw L, Kowgier M,
. Combined ursodeoxy cholic acid (UDCA) and fenofibrate in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patients with incomplete UDCA response may improve outcomes[J]. Aliment Pharmacol Ther,2016,43(2):283-293.
[6] Czaja AJ.Frequency and nature of the variant syndromes of autoimmune liver disease[J]. Hepatology,1998,28(2):360-365.
[7] Rust C,Beuers U. Overlap syndromes among autoimmune liver disease[J]. World J Gastroenterol,2008,14(21):3368-3373.
[8] 袁小燕,孙凌云.干燥综合征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炎的临床分析[J].江苏医药,2005,31(4):310-310.
[9] 陈伟钱,戴晓娜,余叶,等.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2020,52(5):886-891.
[10] 高君,王炳元.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合并干燥综合征患者临床特点分析[J].中国临床医生杂志,2014,42(10):32-34.
[11] 刘晋河,董振华.干燥综合征合并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证候特点[J].中国中医风湿病学杂志,2006,9(3):95-96.
[12]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 EAS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J]. J Hepatol,2017,67(1):145-172.
[13] 刁磊.重叠综合症合并干燥综合征1例[J].安徽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4(1):101-102.
[14] 王静,佘春晖,刘斌.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的研究进展[J].中国药物与临床,2019,19(16):2762-2763.
[15] 苑巨双,王玉盛,董秋梅.中医治疗干燥综合征的临床进展[J].内蒙古中医药,2021,40(6):16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