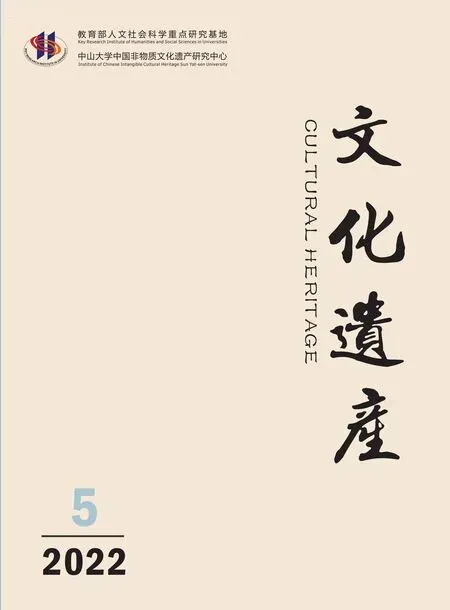“神话中国”观对文明探源的理论意义
2022-10-14叶舒宪
叶舒宪
“神话中国”是文学人类学一派面对西学东渐大背景下形成的流行偏见而提出的针锋相对术语,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选用“神话”作为界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关键词,使之成为“中国”的定语,其理论目标是:突破以“科学”和“哲学”等现代性的、完全西化的词语来界定中国传统的学术偏见和成见,激发对本土文化再自觉的启蒙过程,引导人们走出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认识误区。
就此而言,倡导“神话中国”的观念,是对西学东渐以来造成的张冠李戴和郢书燕说之类流弊现象的公开反抗,其直接的反驳对象,是盲从德国学者雅斯贝斯虚构的学术假象,直接照搬到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普遍流俗。什么是雅斯贝斯营造的学术假象呢?那就是将在古希腊发生的“哲学突破”或“轴心(时代)突破”,横向推演到整个世界,使之成为某种具有人类普世性的思想运动。就好比自然科学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点发挥同样作用那样。中国传统、印度传统、希伯来传统等,居然都和古希腊一样,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内,发生同样的思想观念大突破运动。这样的轴心突破理论,足以让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听起来感到备受鼓舞,但是其遮蔽不同文化真相的负面效果,要远远大于其所能揭示的。
就其根源来说,“轴心时代突破”说在德国学界本身仅是各种各样的理论假说中的一种而已,并没有多少回应和效法者。一旦有美国社会学家看中这种论调并将雅斯贝斯原著翻译为英文,其传播就率先在美国学界打开空间,随即引起美国汉学界的热烈讨论,再通过当代留美学习的中国学者的反馈,输入到中国学界。其理论旅行的三级跳效果,恐怕是其始作俑者和英文译者都始料未及的。眼下,在我国的文科学界,讲到古代思想文化,一般的教科书和学术论著中,已呈现出言必称轴心时代的偏激现象。好像不这样人云亦云或照猫画虎操作,就跟不上时代发展一样!
笔者认为理论工作者有必要针锋相对,开展自我反思和批评讨论。若不能走出此类当代学术偏见,文化自觉就难免沦为空话。既然在中国古代没有发生类似古希腊那样的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依然被某种前科学的思想意识所笼罩、所支配,那么,这是除古希腊之外的全球文化现象,各文明古国或非文明社会皆如此,并不只是中国现象,没有什么需要避讳和掩盖的。
在科学或哲学思维之前的人类观念状态,学界曾有“原始思维”“野性的思维”,诸如此类术语。如今看来这些措辞都不够稳妥,主要因为其中隐含着沙文主义或殖民主义的味道。我们需要重新找到不带价值色彩、不带贬义和文化偏见的中性词语。于是便权衡筛选出“神话”这个通俗易懂的术语。就我国高校的学科分类而言,神话,目前虽然只是民间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常见术语,但这只是非常狭隘化的神话概念。对照国际学界,神话不是附属于文学的小概念,而是统领整个人文的宏大概念。从维柯到卡西尔,早已将“神话”与“思维”两个概念合成一个,即“神话思维”。就此而言,神话不只是民间文学或非遗的对象,也能够代表整个人类的前科学思维传统,这才是更具有普世性意义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其前科学思维传统有一致性,也有文化特殊性,后者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对象。倡导“神话中国”观,将有助于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方面的上述理论误区,重新面对本土文化的真相。
2009年,笔者提出从神话学视角开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室第一次设立重大攻坚项目,于同年发起有关“神话中国”和“神话历史”的学术讨论,并与广东省委协作,启动广东省文化强省项目之“神话历史丛书”(南方日报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迄今出版12部专著,除侧重中国经典研究方面,还包括研究全球最早文明之《苏美尔神话历史》和有关近邻韩国的《韩国神话历史》等。2017举办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第七届年会文集题为《重述神话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谭佳主编的《神话中国》也相继问世(三联书店,2019年)。一个新的本土文化理论体系正在形成,这对于打破西化理论误导下的中国观,聚焦由中国文明发生的独特道路所孕育出的特有文化基因,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范式,以四重证据法为方法论的起点,是融合文史哲艺和宗教、考古等多学科知识的交叉学科范式。原来在单一学科视角无法把握的复杂性对象,将在实证研究与阐释研究互动的文化文本视野中找到确切的定位。就上古史的谱系研究而言,交叉学科范式不纠缠早期历史叙事究竟是神话传说还是客观历史的争辩,并将历史叙事的真伪之争视为某种学术陷阱。古史辨派继承兰克学派的“历史科学”标准,将上古史的三皇五帝谱系乃至夏商历史都判断为层垒堆积而成的“伪史”,殊不知神话历史的叙事模型,具有跨文化跨族群的普世性。每一个族群或民族的早期历史都是民间口传形式而遗留下来的,照例都始于神话叙事。
非神话或解神话的过程,要伴随文明化的进程才会出现。只有柏拉图攻击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神话叙事传统,才有可能给科学和哲学打开大门。换言之,秘索斯与逻各思是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逻各思的权威只在古希腊文明中发生,并未发生在其他文明之中。借用外来的“历史科学”标准去衡量左丘明和司马迁、班固,将本土上古史判定为“伪史”,其结果只能证明古代中国根本没有“历史科学”的观念,犯错的不是司马迁作为国家史官偏要追求什么“究天人之际”,而是将神话与历史分割对立起来的现代研究者自己。司马迁肯定也有伴随文明化进程而来的理性化自觉,但这种理性化的结果只能达到某种有限理性,无法达到科学理性!
历史是延续的,也是断裂的,有些断裂后的链条或环节,就永远找不回来了。历史研究者如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找回失落的历史环节,那将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突破。因为司马迁的有限理性,已经开始切断原有的神话历史的重要因果联系,特别是神话叙事与史前信仰的联系。例如:黄帝的国号有熊,被《史记》保留到后世;但是有熊圣号背后的丰富神话内容与信仰观念,都被司马迁无情地割舍掉了。同样,《楚世家》记载的楚先祖名“穴熊”,其得名故事完整保留在战国古籍《山海经》中,也被司马迁无情地割舍掉了。这导致后人百思不得其解:“颛顼-祝融-穴熊-鬻熊-熊丽-熊狂-熊绎……”的楚王谱系是怎样的由来?楚王族本姓芈,要如此多“熊”号何为?1940年代出土的战国楚帛书讲述以天熊伏羲为首的创世记神话,这样的内容当然为司马迁所不取,因为他只写《五帝本纪》,根本没有写《三皇本纪》。等到司马贞为弥补《史记》的重大缺失而添加《三皇本纪》,时光已到唐朝,先秦时期的伏羲圣号“天熊”,就被司马贞弄丢了。这一丢不要紧,完整无缺的神话历史脉络“天熊-有熊-穴熊-鬻熊”就永远被尘封。
为什么说以皇家史官著述形式流传至今的古史其实是断裂的、残缺不全的?历史又是如何断裂的?近二十年才流行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已简化为“非遗”)观念,为求解问题提供了生动完整的丰富案例:各个无文字民族或族群的口传史诗叙事,一般都承载着的本族社群的原史叙事功能。对无文字民族而言,除此以外别无历史。文史本浑融一体,遵循着一般性的叙事模型: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本族先祖,以本族先祖的降生大地作为人类起源叙事。先祖天降人间,是常见的叙事原型。其起源在于石器时代萨满通神叙事(幻象),体现着史前文化信仰的普遍性特质,从史前部落社会的口传传统,一直延续至文明国家的历史叙事。
汉字的出现提供书写文本取代口传历史叙事的条件。从甲骨文只服务于商代统治者的占卜需要来看,汉字的最初使用语境不是世俗的,而是带有鲜明宗教性特征的。同样,商周青铜器铭文即金文,其使用的语境也同样带有鲜明的宗教特征。金文叙事开篇通常以“王若曰”三字为表达模式,其意思是特指:王者代替附体在其身上的神灵说。一般而言,王若曰模型叙事的发生地是国家宗庙之类。伴随以“王格庙(宫)”之类模式化套语,表明事件发生地点的特殊性——国家级别的神圣场域和仪式性质的认定。换言之,金文叙事关系到统治阶级的政教合一活动,事关权力-财富分配与神圣性青铜器的子孙万代传承,这肯定不同于俗民百姓在篝火边的一般性讲唱行为。既然从甲骨文到金文的叙事全部笼罩在通神语境的神权政治背景之下,这完全符合人间社会最高统治者号称“天子”的神话政治身份。就此而言,文明探源工程岂能完全照搬科学主义的考古实证范式,而缺乏对“神话中国”和“神话历史”的解释学体认功夫。
相对于兰克的“历史科学”范式,维柯《新科学》概括出的历史哲学的三段论范式,倒是更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神的时代——半神半人的英雄时代——人的时代。由于古希腊以外的所有民族都没有发生科学思维的轴心突破,因此所有的历史讲述都从神话叙事开始,而讲述到英雄祖先之后的人的时代,依然要大体遵循神-人互动或天人感应的叙事逻辑。
如果说古人根本没有客观的科学的历史叙事,那就只能是出于主观选择的和神话想象支配的历史叙事。其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以司马迁首创的《五帝本纪》开篇叙事为例: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

黄帝建立社会权威的方式是武力征战,其作战形式却是神话般的野兽大军出阵,以此非凡的征战方式一连三次,终于打败炎帝神农氏,建立第一个强权古国。司马迁记录黄帝率六种猛兽大军征战一事,丝毫没有表示疑惑,说明他是信奉自己所写内容的。这种人兽不分的景象,再度发生在《秦本纪》所记秦人先祖孟戏、中衍二位的形象特征刻画方面:“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能言。”唐张守节《正义》云:“身体是鸟而能人言。又云口及手足似鸟也。”本来,在司马迁之前的战国古书《山海经》中习惯描述人鸟合体或人兽合体的幻想形象,早已屡见不鲜。司马迁对《山海经》的内容明确表示不可信,但是他自己竟然也照样拷贝《山海经》人兽不分的传统神话写法,将这类莫须有的玄幻内容搬进国家正史。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还原整个二十四史以“神话历史”的本土真面目。
不过,司马迁对前代的神话历史内容绝非照抄,他毕竟大大压缩了玄幻场面和纯想象叙事的篇幅和出现频率。但这也只是程度的改变,而非性质的改变。看了黄帝的猛兽大军征战和秦人祖先二位“鸟身能言”,大家都会有所体会。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在这种情况下《五帝本纪》只给黄帝留下576个字的叙事篇幅,即从海量史料信息中择优而精选,标准即是雅驯与否。相信在百家言黄帝的叙事中,有关黄帝死后升天的叙事内容会非常丰富多彩。可是司马迁写黄帝之死却惜墨如金,仅有六个字:“黄帝崩,葬桥山。”仅剩下死亡事件本身和葬地这两个信息,确实非常雅驯。被他删节不用的神话情节是怎样的呢?《五帝本纪》中没有记下的内容,在《封禅书》中却间接叙述出来,那便是齐人公孙卿所言黄帝铸宝鼎升天一事:
“申公,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後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神话中国”观旨在说明:文化文本的元编码没有例外全部是神话编码,这不仅是古史和古书所遵循的编写原则,也是中国大地上无数名目的发生原理。如果你去河南一个名叫“灵宝”的县域去旅行,可能不会想到黄帝铸鼎升天的历史典故。但是当你走到灵宝的铸鼎原,发现还有龙须沟,相传当年黄帝所骑之龙被坠落的龙须之处,当地还有一种草名为龙须草,乃龙须所化。你终于完成一次带入体验式的非遗教育课。民间文学被文学人类学认定为求证历史文化的第三重证据,能够对古书和文物起到双重激活作用。
灵宝铸鼎原的体验之旅表明,神话,特别是原生态神话,能够立即激活被理性化过程所埋没和遗忘的真实历史内容。当年的汉武帝在亲口听闻公孙卿所述黄帝铸鼎升天神话事件之际,也被深深震撼到灵魂。于是出现如下真实的历史场面:

如今的教育制度是历史教育与文学教育完全分开的。二者分属不同的一级学科。这导致历史学博士不用学习神话课程,文学博士也不必读《史记》等史书。我们为什么需要提倡“神话历史”观念?因为,对我国各民族而言,历史与神话不可分割对待。一旦从历史叙事中删除神话内容,历史就会断裂和僵死;神话内容一旦得到复原,历史就复活了。
神话不但能让历史复活,文物也会被重新激活。尤其是鼎和弓这样的常见器物。没有黄帝铸鼎升天的神话想象作为脑洞引导,你去博物馆看一百个鼎,也不一定能有类似汉武帝那样的带入式、穿越性神幻体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