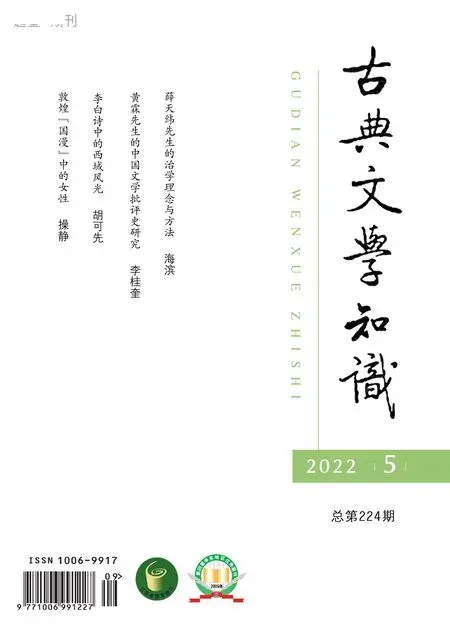《文心雕龙》“宋画吴冶”考释
2022-10-12周兴陆
周兴陆
“龙学”是一门显学,自明清以来,许许多多研究者致心力于对该书的校勘、笺注,文献性研究渐臻完善。近日研读《文心雕龙》,觉得有一则注释似有重新考辨的必要,现斗胆提出来,就正于方家。
《丽辞》篇:
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

夫宋画吴冶,刻刑镂法,乱修曲出。其为微妙,尧、舜之圣不能及。(高诱注:“宋人之画,吴人之冶,刻镂刑法,乱理之文,修饰之功,曲出于不意也。”)
清人黄叔琳的注释,没有引《淮南子·修务训》,而是引用《庄子·田子方》一则著名的故事来注释“宋画”,可谓引入歧途。黄注曰:
宋画:《庄子》: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盘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是古代最为详备的注本,是“龙学”的基石,影响深巨,近人李详、范文澜、杨明照等的校注无不是在黄注本的基础上补苴罅漏,各有新得。范文澜《文心雕龙注》除了吸收黄氏此注外,还采纳了李笠说补注出《淮南子·修务训》文字。范注是现代“龙学”的奠基之作,因此,黄叔琳、范文澜对“宋画”的注释几乎被近现代所有的注释本所因袭,牟世金、詹锳、周勋初、张国庆等所有的注本,凡是解释“宋画”的,都追溯到《淮南子》和《庄子》,几无例外。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文心雕龙》注释者都认为“宋画”一词出自《淮南子》,而《淮南子》的用典是出自《庄子》,所以把两书的原始文字都注释出来。
溯源至《淮南子》是正确的,刘勰这里完全是“因乎旧谈”,用《淮南子》的陈辞。但《文心雕龙》和《淮南子》的“宋画”,跟《庄子》有关系吗?
《庄子·田子方》这则“宋元君画史”的故事,寓意是灭弃世俗礼法,摆脱精神束缚,达到以天合天的境界,才是“真画者”。后代谈艺者多能领悟此意,如明人何良俊《语林》称之为“天机所到”,“遗人以全天”,又说:“苟仅能执绳墨、守途辙而不失者,是工徒之厮役也,曷足以言艺哉!”恽南田《南田画跋》说:“作画须有解衣盘礴、旁若无人意,然后化机在手,元气狼藉,不为先匠所拘,而游于法度之外矣。”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上)曰:“诗文须悟此旨。”用今天的话来说,“宋元君画史”蕴含的是审美超越、艺术自由的道理。
而《淮南子》和《文心雕龙》的文字是“宋画吴冶,刻刑(形)镂法”,《淮南子》还进一步说其刻镂的工巧微妙,尧舜圣人都达不到。显然,其文义的重点是刻镂的工巧,这正好与《庄子》寓言的意思相反。《庄子》寓言强调的是天机自由,《淮南子》用意则在刻镂的工巧微妙。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篇文义重点也在“刻形镂法”即对偶的工巧上。如果说,《淮南子》和《文心雕龙》都用的是《庄子》的典故,那二书随后的“刻刑(形)镂法”四字意思就落空,无法理解了,《庄子》这则寓言显然没有“刻刑(形)镂法”的意思,因此,引用《庄子·田子方》“宋元君画史”来注释《淮南子》和《文心雕龙》的“宋画”,显然是不妥当的。“宋画”一定另有出处。
其实,《淮南子·泰族训》记载了另一则“宋画”的故事:
宋人有以象为其君为楮叶者,三年而成,茎柯豪芒,锋杀颜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呕之而生,吹之而落,岂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数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众,非数之所能领也。故九州不可顷亩也,八极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与四时合信。故圣人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不下庙堂而衍四海,变习易俗,民化而迁善,若性诸己,能以神化也。
这就是著名的“莫辨楮叶”的故事,在当时流传颇为普遍,《列子·说符篇》《韩非子·喻老》都有记载,文字略有异同,现引文于下,以便参照:
宋人有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成,锋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国。子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列子·说符篇》)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导之。因随物之容,故静则建乎德,动则顺乎道。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资而载一人之身,不随道理之数而学一人之智,此皆一叶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丰年大禾,藏获不能恶也。以一人力,则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故曰:“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韩非子·喻老》)
《列子》《韩非子》《淮南子》这三处记载,虽有若干文字差异,当为一事。《列子》所记为源头,《韩非子》《淮南子》在此基础上各有发挥。故事说,宋国有一个人为他的国君用玉(一说象牙)雕刻楮叶(楮是一种落叶乔木),用了三年时间才雕刻成,脉络文理、毫芒色泽都惟妙惟肖,混杂在真楮叶中都辨别不出,假可乱真。这个宋人凭此在宋国获得了俸禄。但列子、韩非子、淮南子对此都不认可,认为“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这样的奇技淫巧,是违背天道自然的。《淮南子·泰族训》这则故事之前谈的是“大巧”,宋人的奇巧正与“大巧”相对。
“莫辨楮叶”故事中所谓“茎柯豪芒,锋杀颜泽”云云,正是《淮南子》“刻刑镂法,乱修曲出”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列子》在故事之后说“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韩非子》以“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加以申述;《淮南子·泰族训》进一步以“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故圣人怀天气,抱天心”加以申论,这些内容正与《淮南子·修务训》“尧、舜之圣不能及”相呼应。把《淮南子·修务训》关于“宋画”的记载与《列子》《韩非子》《淮南子·泰族训》“莫辨楮叶”故事对读,文义之相应,若合符契。可以确信,《淮南子·修务训》的“宋画”典故就是出自“莫辨楮叶”故事。
也许有人说“莫辨楮叶”是雕刻,不是绘画。大约不能这样机械理解,后世论画多引“楮叶”,如陆绍曾《又为吴兴陆谷真题纸扇》“由来楮叶全抛俗,试写梅花逼更真”;叶昌炽《挽吉甫同年熙元叠前韵》“画笥烟云流楮叶,诗龛风月话筒杯”。古人用此典不会计较是绘画还是雕刻。
厘清了《淮南子·修务训》“宋画”典故的源头,就可以理解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篇的“宋画”也是来源于“莫辨楮叶”故事,用宋人以象牙雕刻楮叶惟妙惟肖的故事来形容扬、马、张、蔡等“刻形镂法”,刻意追求对偶的奇巧。《丽辞》篇上文说《诗经》的对偶是“奇偶适变,不劳经营”,到汉代扬雄等人才刻意地追求对偶之巧,这与《淮南子·泰族训》前一则说“大巧”,后一则以“莫辨楮叶”谈人巧一样,是文理顺畅的。后世也有人继续这个话题,如宋末刘克庄《跋徐宝之贡士诗》就以“莫辨楮叶”故事比譬徐氏诗文之工妙。如果像现在大多数“龙学”家那样引用《庄子》的“宋元君画史”,《丽辞》的文意是怎么也解释不通顺的。就浅见所及,在众多的注本里,只有王运熙、周锋译注本注出《淮南子·修务训》,而未引《庄子·田子方》“宋元君画史”。我觉得这是正确的,不过还是应该引出“莫辨楮叶”的故事,意思才彻底清晰。
今人对于“吴冶”的注释也欠妥当。范文澜注引《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这也被当代各种《文心雕龙》注本普遍接受。其实《吴越春秋》这段文字也看不出“刻刑镂法”的意思。范文澜认为吴冶是指干将作剑;其实在《淮南子》那个时代,干将是剑名,还没有转化为人名。王念孙说:“干将、莫邪为剑戟之通称,则非人名可知。故自西汉以前,未有以干将、莫邪为人名者。自《吴越春秋》始以干将为吴人,莫邪为干将之妻。”(《广雅疏证》卷八上)在《淮南子》里干将还是剑名。载有“宋画吴冶”的《修务训》就说:“夫怯夫操利剑,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至勇武攘卷一捣,则折肋伤干。为此弃干将、镆邪而以手战,则悖矣。”显然这里的干将是剑名,至《吴越春秋》干将才是人名,不容相混。吴冶,黄叔琳注:“《吴越春秋》:越王元常使欧冶子造剑五枚。”刘咸炘遵从此注,其他注本则忽略此则黄注,而都依据范文澜注。黄叔琳指出吴冶是欧冶子事,这是正确的。不仅《吴越春秋》这么记载,《淮南子》就多处提到欧冶子:
淳均之剑不可爱也,而欧冶之巧可贵也。(《齐俗训》)
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同上)
故剑工或剑之似莫邪者,唯欧冶能名其种。(《泛论训》)
区冶生而淳钧之剑成。(《览冥训》)
欧冶子为越人,但《越绝书》有“风胡子之吴见欧冶子”的记载,可能是他去了吴国,或者吴越通称,故称“吴冶”。《淮南子》和《文心雕龙》“宋画吴冶”一语,正是把“欧冶之巧”与“莫辨楮叶”之宋人之巧并提,才生出后面“刻刑镂法”一句。如果按现在通行的注释引用“干将作剑,百神临观”注“吴冶”,既与“宋画”龃龉,也与“刻刑镂法”不相干。解释典故,不仅要追溯出处,更要看它是否适合上下文的语境,符合作者的本意。刘勰作文“用人若己,古来无懵”(《文心雕龙·事类》),我们读者也要细心体会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