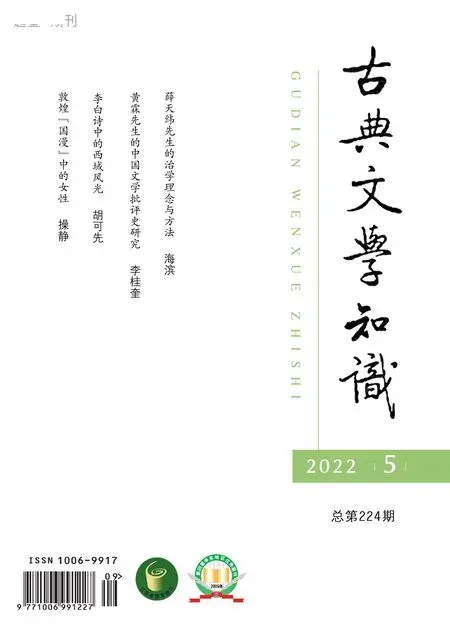魏晋名士的隐逸情怀(上):名士归隐的政治蕴含与思想旨归
——《世说新语》之二十
2022-11-08宁稼雨
宁稼雨
中国文化,是以封建帝王专制和等级制度为核心,以儒、道、释三教为思想基础,以官僚和文人的言行为主要载体的封建式文化。但在看到帝王文化的同时,也要看到与之对立、又相互吸引的隐逸文化。而魏晋时期名士的隐逸生活是中国隐逸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有许多隐逸文化的新亮点和新特色,也是魏晋名士风流画廊中的重要片段之一。
名士归隐的政治内涵
隐士活动的政治内涵,突出表现在他们与皇权的关系上。隐士的形成,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士人的独立意识,即“道”优于“势”的信念;二是皇权所希望的隐士担负的社会使命,即在皇权与社会的矛盾中起到协调作用。这就决定了隐士与皇权间无所不在的紧密关系:皇权一方既要用隐士来装潢门面,又要避免隐逸之风可能产生的不安定因素;隐士一方既要追求独立意识,又不得不承认为人君之臣民的现实,即尽管“道”优于“势”,可又不得不服从“势”的绝对统治。于是,双方如同一对命里注定的欢喜冤家,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吸引。
经过前代的教训,魏晋时期的皇权与士人都开展了对双方关系相处方式的思考。其活的标本,便是“竹林七贤”: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读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人不免要有这样的疑惑:既然七贤是一个亲密无间的隐退群体,为什么嵇康还要把山涛骂得狗血喷头,并且与之绝交呢?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就明白了竹林七贤在隐逸文化史上的真正意义。
魏晋时期皇权与士人处理相互关系时比较务实。在不断地选择和扬弃中,他们逐渐找到了双方不得不接受的相处方式。七贤对皇权的三种不同态度,便是这种选择和扬弃的过程。
第一种为对抗式,只有嵇康一人。嵇康继承了东汉以来逸民隐者的疑君和无君思想,他不仅公开唱出“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论调,还在行为上付诸实施,傲视王侯。这种处世方式的危险性被山林中真正的隐者看得清清楚楚。据《世说新语·栖逸》,一次嵇康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漫游,遇见了道行高深的道教徒孙登,便和他一起交往游乐。临别时,孙登对嵇康说:“你的才能很高,但却缺少保全自身的办法。”《文士传》还记载孙登用火与光的关系来开导嵇康:“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但嵇康并没有听进这些话,继续公开与司马氏政权对抗。直到被捕入狱,嵇康才意识到孙登的先见之明,写诗自责:“昔惭柳下,今愧孙登!”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自己的处世之道。这种方式尽管很崇高,很悲壮,但不现实。
与此相反的第二种方式是投靠式。其中山涛明白得最早。他尽管在竹林与嵇康等人游玩隐逸,但心里早就盘算着什么才是保身之道。四十岁时他便做了赵国相,入晋后又历任要职。所以才遭到嵇康的怒斥。其实山涛的投靠正是隐士与皇权关系中的一种适应,目的是全身,而不是出卖灵魂。所以尽管被嵇康骂得很难堪,但他仍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的后代。嵇康遇难后,山涛仍然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担任秘书丞。嵇绍向山涛咨询是否就任及出世入世的道理,山涛说:“我为你思考很久了。天地四季,尚且有消长盈虚,何况是人呢!”(《世说新语·政事》)山涛的话等于是他的处世宣言,即人的处出要顺应时势,能屈能伸,以保全自己。这种方式也为向秀所效法。嵇康被杀后,向秀拿着本郡的各种文书簿册来到洛阳朝廷,司马昭问他:“听说你有隐居的志向,为什么又来到这里呢?”向秀回答说:“巢父、许由这些拘谨自守的人是不值得效法称羡的。”司马昭听了,大为赞赏(《世说新语· 言语》)。按《庄子·逍遥游》篇“尧让天下于许由”一段郭象注曰:“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尧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许由方明既治,则无所代之,而治实由尧,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寻其所况,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尧也;不治而尧得以治者,许由也。斯失之远矣。夫治之由乎不治,为之出乎无为也。取于尧而足,岂借之许由哉?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者,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途。当途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强调隐逸与为政并无二致。这是对庄子原意的歪曲。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说:“庄生曳尾途中,终身不仕,故称许由而毁尧、舜。郭象注《庄》,号为特会庄生之旨。乃于开卷便调停尧、许之间,不以山林独往者为然,与漆园宗旨大相乖谬,殊为可异。”清人姚范《援鹑堂笔记》认为郭象这段注实取自向秀,他说:“郭象之注,多本向秀。此疑鉴于叔夜菲薄汤、武之言,故称山林、当途之一致,对物自守之偏徇,盖逊避免祸之辞欤?”向秀歪曲庄子原意的动机,与前面故事中所叙他对巢父、许由否定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对传统隐逸理论的重大修正,即隐逸应以服从并迎合皇权的绝对统治为前提。
这种思想在魏晋间并非空谷足音,王昶在诫子书中也说:“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虽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又据《晋书·刘毅传》载,司马昭开始辟刘毅为相国掾时,刘毅以疾而辞,多年不就。后来有人传说刘毅辞官是因为心怀曹魏,刘毅吓得赶忙应命为官。可见这些人的投靠为官,主要是全身之道所致。
第三种方式是矛盾式,以阮籍为代表。阮籍在很多方面与嵇康是一致的。如嵇康提出要“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就干脆提出“无君论”的思想,甚至讲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这种犯忌的话来(阮籍《大人先生传》)。在目无礼法、行为放达方面,二人也是如出一辙。但二人的下场却截然相反,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全身之道。嵇康把心里所想的东西和盘托出,因而招来杀身之祸。而阮籍却善于把对外界的褒贬藏在心里,因而能够得到司马昭的赏识,如李秉在《家诫》中说,他曾经和三位长史觐见司马昭,辞行之前,司马昭问他们:“为官者应当清廉、谨慎、勤勉,做好这三点,还有什么治理不好的?”三人唯唯受命。司马昭又问:“如果实在要在三者当中保留一个,应该保留哪一个?”有人说应当以清廉为本,又来问李秉,李秉回答说:“清廉和谨慎是相辅相成的。必不得已,谨慎才是最重要的。”司马昭表示同意,又问能否举出近来堪称谨慎的典范人物,李秉就举了太尉苟景倩、尚书董仲达、仆射王公仲等人。司马昭说:“这些人每天从早到晚都小心翼翼,确实算是谨慎。但天下之至慎者,非阮籍莫属!每次和他说话,他总是说些云山雾罩的话,也从不评论时事、评价人物。他才是最谨慎的人啊!”在司马昭看来,士人做不做官,做官清不清廉、勤不勤政,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要听话,嘴巴老实。他平日十分注意观察士人,看谁最符合这个标准。他亲自树起的服从典型,便是阮籍。所以,阮籍冒犯礼法的举动,司马昭便视为枝节小事,不足一提。当有人以此为借口,对阮籍落井下石时,司马昭竟能予以保护。如阮籍遭遇母丧的时候,公然在司马昭那里饮酒吃肉。当时司隶也在座,趁机向司马昭进谗言说:“陛下正在提倡以孝治天下,可阮籍却在重丧期间公然在陛下面前饮酒食肉,应该把他流放到海外,以正风教!”司马昭说:“阮籍痛苦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能与他分忧?况且有病的时候饮酒食肉,本来也是符合礼教规定的!”阮籍在旁边照饮照吃不误,神色自若(见《世说新语·任诞》)。司马昭与阮籍之间完成了一笔交易,阮籍付出的是服从和忍耐,换来的是承认和保护。这笔交易在高洁之士看来不免有些肮脏,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笔交易在隐逸文化史上的意义:它以双方自我调节的方式,把皇权与隐士之间的相处方式,调到了最佳位置。司马昭屡次保护了阮籍性命,阮籍也在司马昭上台前夕,受人之托写了劝进表。真是你来我往,互通有无。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说:“阮籍既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闻步兵厨酒美,复求为校尉。史言虽去职,常游府内,朝宴必与。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以吾观之,此正其诡谲,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之士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于杀身?籍何以独得于昭如是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见。”叶氏可谓找到了嵇、阮二人举止相同而下场各异的原因。这一点连嵇康也看到了,“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与山巨源绝交书》)。
说阮籍这种方式矛盾,是指它虽然能保全性命,而且自己也没像向秀、山涛等人那样认真做官,但它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隐士的赤诚、高洁之心。所以阮籍保全生命的代价除了自己的“至慎”外,还有内心极度的痛苦: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隐逸之心未泯,所以才十分在乎自己为保全性命所付出代价的昂贵。他的生命如果受到威胁,可以由司马昭来保护,但由此而产生的内心极度煎熬,却是任何人都无法洞悉、无法分担的:“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魏氏春秋》云:“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与阮籍相似的,还有七贤中的刘伶和阮咸。
竹林七贤像试验田一样,向后人展示了各种与皇权相处的方式。从此便使隐士与皇权关系的调整,进入了自觉的阶段。
皇权一方在隐士不抗拒其统治的前提下,尽量予以优容,甚至亲密无间。这可以晋简文帝司马昱为代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很多他与诸位名士、隐者挥麈谈玄、游弋山水、相濡与共、亲密无间的故事。如果不是帝王的身份,他本人或许就是一位名士或隐者。
在隐士一方,仕隐兼通逐渐成为时髦的风气。在山涛、向秀之后,郭象、张华、石祟、潘岳、陆机,以及东晋时期谢安、戴逵、王羲之、孙绰、谢灵运等人,无不志在轩冕而又栖身江海。《世说新语》中,留下了很多他们或仕或隐的生动故事,其中可以谢安为代表。
谢安从四岁起到弱冠止,就从当时几位地位显赫的大族成员那里得到极高评价。但谢安并没有急不可待地出来表演、做官,他欲仕故隐,待价而沽,先后拒绝了多次征辟,甚至因历年征召不应,被有司奏为禁锢终身。但这些并没有吓住谢安,他继续着自己待价而沽、以隐求仕的游戏。他或者躲在石洞中美滋滋地慨叹:“此去伯夷何远?”或者与王羲之、孙绰等人游弋山水(见《晋书·谢安传》)。一时间,他几乎成了高洁隐士的象征。但是,他仍然逃不过明眼人的眼睛。谢安早年在东山隐居养伎,简文帝司马昱说:“谢安一定会出山。他既然能与人同乐,也不能不与人同忧。”(《世说新语·识鉴》)司马昱已经看出谢安出山的必然,说明皇权对招揽隐士的自信。其实,连谢安自己也偶尔在玩笑中透露出将来未必不出仕的意思。当初谢安在东山隐居的时候,当年还是平民的兄弟有的已经富贵起来,经常是高朋满座,权贵接踵。妻子和谢安开玩笑说:“大丈夫难道不应当如此吗?”谢安捏着鼻子笑着说:“恐怕也免不了吧!”(《世说新语·排调》)这里的“免不了”,除了自己未必不出的意思外,主要还有惮于时势、不得不出的意思。果然,在一代枭雄桓温的压力下,他出任其手下的司马。这不仅意味着对自己隐居生活的否定,也招来很多士人的讽刺、挖苦和揶揄。据《世说新语·排调》,谢安出任桓温手下的司马,上任前要从新亭出发,朝廷官员都来送行。当时有个叫高灵的中丞也来送行,他喝了些酒后就趁着醉态对谢安开玩笑说:“你屡次违抗朝廷命令,高卧东山。大家都经常议论说谢安不肯出来做官,将如何面对百姓?如今百姓又该怎么面对你呢?”谢安笑着不回答(《世说新语·排调》)。
更有甚者,在谢安改变隐居形象、就任桓温司马后,当时有人送给桓温一些草药,其中有一味药叫做“远志”。桓温就把“远志”拿来问谢安:“这种药又叫‘小草’,为什么是同一种东西却有两个名字呢?”谢安没有马上回答,旁边有个叫郝隆的应声答道:“这很好解释。隐处山中就是‘远志’,出了山中就是‘小草’。”谢安听了深感惭愧。桓温看着谢安笑着说:“郝参军的解释的确不坏,也意味深长啊!”(《世说新语·排调》)这种草药的根部称为“远志”,是主要的药用所在,叶部称“小草”。根埋在土中为处,叶生在地上为出,这正象征着谢安先隐后出的所为。郝隆的话语意双关,击中谢安要害,所以令其面有愧色。远志一草二名,是谢安一类仕隐兼通者的形象写照,也说明了隐士文化内涵的修正和扩大。
名士归隐的思想旨归
人们一般把儒、道、释三家视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三大支柱,并以“儒道互补”来概括中国历代文人的常规心理。而隐士的政治态度和社会角色,决定了他们必然倾向于道家一面。魏晋时期的隐士多即名士,他们以庄解儒,崇尚虚无的思想,不仅代表了名士的思想,而且也集中体现了古代隐士的基本思想特征。
庄子的崇尚虚无,主要表现了憎恶文明社会弊端的人对自然的倾倒和回归自然的愿望。魏晋玄学家则运用这一基本的内核,来构建理想的人格本体。
率先将“无”与人的品格相联系的,是魏初时刑名家刘邵。刘邵在《人物志》中,从政治学说的角度出发,特别推崇具有“中庸之德”和“中和之质”的君主,反对那种只具有某一方面才能的“偏至之材”(《人物志·材能》)。因为偏至之材皆一味之美,不能和解和统驭五味;而“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人物志·九征》)。后来的玄学家便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以无为本”的观点。何晏和王弼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王衍传》引)具体来说,他们一方面看到“有”与“无”之间的辩证关系,即有限是无限的表现,无限存在于有限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清醒地估计到无限高于有限的价值。即无限虽不能用来确指某一可名的单个事物,但却可以用一切可能的名称去称呼它。它不受某一确定事物的限定,却可以包罗一切可能的有限事物(何晏《无名论》)。王弼又进一步把无限视为包括“帝王”“圣人”在内的最高人格理想的本体。圣人把握了无限,也就不会失去一切有限(《王弼集·老子指略》)。这样,王弼就在理论上完成了人格理想本体论的建构任务(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贵无”思想的确立,奠定了玄学的理论宗旨。同时,它也深深作用于包括隐士在内的广大士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之中,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如: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强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文学》)
在王弼生活的魏初,人们还常把“有无”作为话题来谈,在此以后,“贵无”便主要渗透在人们的行为过程中。其具体表现,一是推崇具有“中和之质”和“平淡之味”的人物。而隐士的品格正是这样的味道: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世说新语·品藻》)
这位兼有诸人之美的阮裕,即为著名的隐士。《世说新语·栖逸》载他在东山隐居时,经常悠闲自得地把脚捧在怀中。有人问王羲之,王羲之说:“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沈冥,何以过此?”
然而更为潇洒的,还是隐士们在生活中对“贵无”理论的灵活运用和对无限境界的追求。如一次支遁出于隐逸的兴趣和对自然的喜好,打算买下峁山之侧的沃洲小岭,作为幽栖之所。但另一位隐士兼僧人竺法深说:“想幽栖来这儿便罢了,没听说巢父和许由这些古时隐士还要买山而隐。”听了这话,支遁便惭愧地作罢(《世说新语·排调》)。买山是为了隐居,隐居是一种潇洒、旷达的行为,是玄学家和僧人们共同追求的虚无境界。但用金钱买山而隐,却与“虚无”二字大相径庭,是有在无先的表现。又如: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世说新语·言语》)
朱门的有无并不在于它是否存在(有),而在于你是否去感觉它(无)。只要内心虚无了,也就没有朱门与蓬户的区别,在朝在野也就无所谓了。而刘惔问话的失误,就在于他先有二者的区别,反而不符合无在有先的思想。所以《高逸沙门传》也说竺法深虽“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旷达,不异蓬宇也”(据《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
谢安曾评价褚季野(裒)“虽不言,而四时之气皆备”(《世说新语·德行》)。说明四时之气这一无限的精神境界比起有言来要重要得多,所以谢安本人就十分追崇这样的境界。谢安夫人在教育孩子时,有时责备丈夫不管教孩子。谢安的回答是:“我每天都在教育孩子,只是你看不出来就是了。”(《世说新语·德行》)的确,教育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看不出教育的痕迹。这样的教育不仅可以完成教育本身的任务,其本身也是一门优美的艺术。谢安就是这样一位天才。儿子谢玄小时候喜欢把紫罗香囊搭在手上,谢安不喜欢这种做法,却又不肯伤害孩子的自尊,便假装与儿子打赌,赢得后便立即烧掉香囊(《世说新语·假谲》)。谢据曾上屋顶熏鼠,遭到儿子谢朗的嘲笑,并没完没了地逢人便说。谢安知道后就对孙子说:“听说外边有些中伤你爸爸的话,连我也给捎上了。”谢朗听了,十分惭愧,懊恼得竟一个月没出家门(《世说新语·纰漏》)。只有洞晓“有”“无”关系的底蕴,才能达到如此运斤成风、挥洒自如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