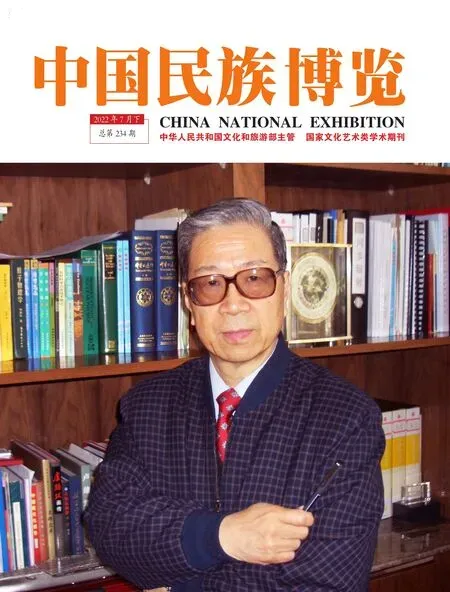萨提亚冰山视域下斯嘉丽的人物形象研究
——以《飘》中斯嘉丽与母亲埃伦的亲子关系为例
2022-10-11叶锦熹
叶锦熹
(西交利物浦大学,江苏 苏州 215028)
引言
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创作的经典文学作品《飘》以其细腻生动的笔触、意蕴深刻的省思向世界展现了19世纪下半叶美国南部诸州(以佐治亚州为主)广阔的社会画卷。作品跟随女主人公斯嘉丽的活动轨迹,丰满翔实地描绘了美国南北战争战前、战中以及战后重建时期人民生活变迁的面貌;更通过情节活动的展开推进,在文学艺术层面上塑造了极具个性、立体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为19世纪沉重压抑的女性个性解放发出历史的先声。
书中女主人公斯嘉丽的形象极富张力,一方面她自私虚荣、轻率任性,惯用手段达成目的;另一方面她独立顽强、胆识过人,绽放出个体生命饱满的热情。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斯嘉丽的母亲埃伦。这位母亲温雅亲和、乐于助人,秉持仁慈奉献的美德,是书中旧南方模范女性的典型代表,尽管作为配角点缀也难掩其丰采神韵。在以母亲埃伦为代表的家庭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斯嘉丽,其性格特质却呈现出迥异的面貌。斯嘉丽最终性格的形成与其所受家庭教育究竟有无联结,又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深层肌理塑造了她如此矛盾又极富魅力的性格特质,这些深层因素又是如何支持和影响着她的行动及应对方式……这些问题都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同各学科与文学之间的交流互释、碰撞融合有着密切的联系。伴随着当代层次丰富的心理学理论在其领域的进一步的开拓与广泛认可,心理学理论也逐步融入文学作品的分析解读,成为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从近现代发达的心理学理论的视角重新看待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形象,不仅有助于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及其变化,还能从崭新的视角了解作者人文心理体察的能力和心理描写的真实性、创造性。
本文以此新颖的视角作为切入点,采纳“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五位治疗师之一”维吉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1916—1988)所开创的“萨提亚冰山理论模式”对斯嘉丽的性格形成进行深层的分析阐释。通过家庭系统文学解读在一定的语境中探讨斯嘉丽行为的深层动因,将人物与情节、历史社会环境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在解读文学叙事中的关系模式上,探讨个体心理、家庭关系、社会结构、历史变迁、文明流变等层面上层层作用、错综复杂的联系。
一、萨提亚冰山理论
维吉尼亚·萨提亚,既是闻名世界的心理治疗师,也是家庭治疗模式的开创者与探索者。作为一名具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工作者,她深入探索了当时流行心理学治疗惯例以外的多重领域,在批判性反思亚里士多德单一因果论、线性思考模型的基础上,鼓励提倡阿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路德维希·贝塔朗菲以及葛瑞利·贝特生等的系统性的思考方式。并且在基于海德格尔、克尔凯戈尔、马丁·布伯等建立发展的积极存在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发展阐明正是如此积极的生命的力量将人们功能不全的应对方式转化为高自尊情境下高水平的自我关怀。
萨提亚模式为心理学界注入了积极的能量,也给治疗界带来了新的希望。本课题所关注的“萨提亚冰山理论”也是她丰饶理论体系中的一枚硕果。她所提出的冰山理论,实际是一个生动的隐喻,即认为个体的“自我”如同一座浮出海底的冰山,并由此自然划分出海平面以上和以下两个部分。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活动、行为内容以及应对方式等对应着个体冰山裸露在海平面以上的部分,也称为“个体冰山的外部”;而个体内心世界所暗藏的自我、渴望、期待、观点、感受等层次,自下而上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内在体系,作为个体冰山的内部,为外部提供着源源不断、难以察觉的动力支持。
在冰山理论视域下,家庭教育显然对个体冰山的形成以及冰山的内部运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每一个成员的不断成长与变化,整个家庭和适应过程,个体的发展既可能像一首与生命和谐一致的交响乐一样美好,也可能发展成为一场令人绝望的斗争。个体成长的关键节点极有可能在暗藏的巨大冰山内部留下痕迹。而储存在此的难以察觉、难以消弭的能量将伴随个体成长过程潜在地塑造冰山的表征。
二、浮冰之上的斯嘉丽
对我们文章的主人公斯嘉丽而言,她顽强生命力的最终形成既是残酷战争所磨砺的结果,也与早期家庭教育下个体冰山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结,逐步揭开七层冰山的神秘面纱,我们从中探索人物魅力的细节亮点。
(一)行为层级:矛盾冲突的光彩
萨提亚冰山理论中的行为层,是冰山的最顶层。它对应着人物可直观接触的外在表现,其实际是内心复杂作用后的投射。换言之,行为是个体自尊的一种外部反映。
出身于南方庄园主阶层的斯嘉丽,在以母亲为代表的南方奴隶制上流阶层的精心教养下长大,富裕无忧、备受宠爱的生活,令人自恃的美貌,前赴后继的追求者……这些因素无一例外都雕琢了她极高的自尊心,促成其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处事原则。这里我们可以简要列举一些斯嘉丽在面对周围环境时的行为进行分析参考:少女时期,初闻心上人艾希礼即将订婚的消息,“斯嘉丽脸不变色,只是嘴唇发白……她直愣愣地瞪着斯图尔特”这是她流露的震惊与呆滞;她在向心上人大胆表露心意并遭遇拒绝之后,感受到强烈的愤怒羞耻“就在这时,她用尽全力对他脸上掴了一巴掌……忽然间,她的暴怒消退了,只剩下满腹凄凉”;偷听到艾希礼妹妹霍尼与梅兰妮等的私密谈话后,她“捏紧拳头捶打着身旁高高的白色廊柱,恨不得自己变成大力海士参孙,把整个十二橡树拉坍,把里面的人通通压死”,并在不久后为了满足自我虚荣心,她赌气轻率地夺走了霍尼的未婚夫查尔斯,而后又为金钱夺走亲妹妹苏埃伦的未婚夫弗兰克,并不顾此番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的伤害痛苦。
南北战争时期,面对义卖舞会上白瑞德离经叛道、荒诞唐突的邀请,她可以轻松卸下虚伪麻木的“寡妇”面具,将旧南方传统伦理置之脑后,大胆而响亮地回答“我肯的”;在监牢中面对白瑞德的调笑,她为了金钱甚至主动以情爱为诱饵;在亚特兰大危在旦夕之际,面对即将临盆的昔日情敌梅兰妮,她却尽力承担起了毫无经验的接生工作,并设法将梅兰妮母子平安带回塔拉;战后重建时期,面对满目疮痍、一派萧条的故土,她同当时的仆奴一同下田劳作,想尽一切办法让一家人免于饥荒。
斯嘉丽的种种行为显然呈现出矛盾冲突的特点,在她身上,相当高傲的自尊表现,以自我为中心、自私冷漠、贪婪虚荣和富有责任心、勇敢大胆、坚韧坚定都渐次从不同的方面展现得淋漓尽致、百折不回。而正是这样夸张复杂、富有戏剧性的外在表现构建了她矛盾对立的性格特质,为她的人格魅力赋予了特殊的光彩,也让读者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物形象的吸引力。
(二)应对方式层级:姿态成长的魅力
在萨提亚冰山理论中,应对方式层居于行为层之下,同样是裸露在外的冰山层级。萨提亚在她的理论中阐释:人们为了以一种夸张的形式表现出对自我价值的内心感受,通常会采取生存姿态来保证自己的生存,即取悦他人。这样的生存姿态大致可分为五个类型:讨好型、责备型、超理智型、打岔型以及表里一致型(最理想的状态)。如果个体被生存姿态操纵和控制,那么就不得不在试图获得接纳的同时隐藏渴望与人联结的强烈需求。

图1 讨好型

图2 责备型

图3 超理智型

图4 打岔型
回到文学作品中,我们或许不能准确地为斯嘉丽的生存姿态下一个定义,但在诸多细微之处都可以窥见责备型应对方式的痕迹。责备型姿态的显著特点就是“绝不可以软弱”,它表现为我们应当维护自己的权利,不接受来自任何人的借口、麻烦或是辱骂。
比如,斯嘉丽在面对心上人的拒绝之后一段经典的描述:“她不觉产生了新的愤怒,对她自己,对艾希礼,对全世界。因为她恨她自己,所以也就恨所有的人。”又如,当她向白瑞德借钱失败后的心理活动:“她真希望他们真的把他绞死,今后她永远也不要见到他。其实如果他存心给她钱,她当然有办法把钱拿到手的。”责备型具有爆发性的特点,在责别他人时,个体常常表现出敌意、专制甚至是暴虐的,这往往会导致亲密关系的疏远或断绝。由于高自尊的心灵难以承认自己的脆弱,斯嘉丽从来都是挺直脊背,只有单独一人时才愿意卸下防备。个体应对方式并没有高低之分,每种生存姿态都包含着达到完善的种子,在责备的姿态方式中就隐藏着决断的种子,这也在斯嘉丽的成长中得以体现。
在文学作品中,读者以上帝视角参与文学阅读、感受人物魅力。斯嘉丽责备型的生存姿态并不完美,却相当契合她在早期环境下养成的优越感,所以不显突兀;并且,随着南北战事的推移,斯嘉丽的应对方式也在经历的艰难困苦中得到巨大的锤炼,逐步发展成接近理想形态的表里一致型:为梅兰妮助产、护送梅兰妮母子回乡;在荒芜的处境面前重新撑起塔拉庄园的门楣;甚至在最后由对艾希礼的情感执念回归到对白瑞德的情感认知,发现爱的本质……都能够让人感受到斯嘉丽由内心的空虚寄托转变为对自我的确认、对他人的接纳的一个过程。尽管人物的性格底色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斯嘉丽越发成熟的现实性思维和应对方式却呈现出一种成长模式,这让读者可以透过斯嘉丽的成长窥见人物背后战争的摧残与社会历史的流变,对读者具有启迪性的意义。
三、冰体之下的埃伦
(一)感受、观点、期望与渴望层级:昔日依恋的重塑
冰山理论的第五个层级即为感受,我们的应对方式就产生于我们对自己的感受。感受强烈地依赖于过去的经验基础,即使此刻的感受是由此刻的事件所激发,我们也会下意识地调动自己长期积累的感受来进行反应。而这种长期积累的感受,也被称为“反应性感受”,即我们对自己的感受所表现出的反应——是建立在我们的认知和期待基础上的;观点,也被认为是一个人的认知、知觉、信念、价值观等,作为冰山理论的第四个层级,通常会在幼年时期形成个体独特的模型。而期待,或者说预期,则是萨提亚冰山理论中的第三个层级。它主要由对自己的期望、对他人的期望和来自他人的期望三个部分构成。个体基本的渴望往往就通过期望表现出来;渴望,作为冰山理论的第二层级,是人类所共有的、对被爱、被接纳、被确认、被肯定的渴求。在个体成长的早期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尝试、验证,每个个体都形成了自己的定义。综合上述,冰体内部的层级,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在个体冰山中占据巨大空间的内生动力其实都与个体成长早期所受的家庭教育紧密相连。
法国著名哲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及心理分析师伊里加蕾曾强调:“母女关系作为社会伦理的一个课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斯嘉丽的早期家庭教育对她个体冰山中的渴望、期待、观点、感受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聚焦于斯嘉丽的母亲埃伦·奥哈拉。
埃伦作为旧南方女性的代表,她的形象同样是标志性的。甫一出场,其形象就显得生动:“屋子里飘来了斯嘉丽的母亲埃伦·奥哈拉轻柔的声音……那是埃伦去给干活回来的人发放食物。”“她从不厉声斥责孩子,差遣下人,但是在塔拉庄园,谁听见她的声音都会毫不迟疑地照着去做。”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母亲埃伦作为庄园女主人的魅力所在,感受到她所传达出的公正平等、温和包容、乐于助人等关于“美”的精神。而在这“美”的背后,也隐含作者对南方旧文明随风而逝的怀念与隐痛。在这样令人如沐春风的感受下,是斯嘉丽对母亲的依恋和憧憬:“斯嘉丽本是强忍着泪水,此刻她接触到母亲的永恒的魅力,闻到母亲丝绸衣衫上香袋里散发出来的枸橼香味,又引起她身上一阵震颤。斯嘉丽觉得,埃伦·奥哈拉身上有一种惊人的力量,也是家里的一个奇迹,而且可以使她敬畏,使她陶醉,使她心安。”埃伦让斯嘉丽能够心安,她将母亲视为“超越人类的某种圣洁的东西”,她甚至会因为埃伦责备的眼光而羞愧不已。这值得深思——因为在书中,斯嘉丽几乎与所有女性角色产生过矛盾,唯有对母亲埃伦,像是对待“美”的雕塑一般的存在,依恋憧憬的同时却保持着分寸与距离。而这样的依恋憧憬也在早期一度构建了斯嘉丽的认知与观点:成为像母亲一样的人。她在情感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对艾希礼的执着渴望也可以在这个层面上进行探讨:艾希礼与母亲埃伦同为旧南方文明的代表人物,他们具有相似的特质:温雅、正义、仁慈——就某种层面上来讲,斯嘉丽对自我虚构出的艾希礼的幻象的爱的渴求,实际上也是在以疏离崇敬为主导的母女关系中,对被爱、被接纳、被确认、被肯定的冰山内部渴求。
时代是发展的,旧南方文明也要在阵痛中走入新时代。在饱经战火后,斯嘉丽惊愕地发现“母亲对她的教诲如今是绝对没有任何价值了,斯嘉丽伤心透了,并陷入了迷茫……埃伦那个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世界已经随风飘逝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残忍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是非标准、价值观念都已经变化。”母亲的离世是全书情节的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斯嘉丽信仰体系的崩塌和重塑——斯嘉丽的应对方式和行为活动都开始发生转变;它同时标记着一个特殊意义的时代,投射出文明进程的更迭与不可逆转。
(二)自我层:抗争的生命与美的象征
在萨提亚冰山理论中,自我境界是生命最高的境界,作为个体内心体验的源泉,它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居于冰山的最底层。这其中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丰美的创造力,它关于精神,关于灵性,关于个体的核心与本质——并且与冰山的其他六个层级有机整合构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整体。
埃伦的角色塑造实际上与斯嘉丽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书中第三章曾提到埃伦的旧事:“当时,那眼睛明亮可爱、行为放荡不羁的菲利普离开萨凡纳一去不回,也带走了埃伦燃烧的火焰和她的青春,只留下一只徒有温柔躯壳的新娘。”相比于斯嘉丽最后醒悟爱情真谛的不畏失败、坚定追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埃伦的爱情悲剧让她选择了妥协,这也是一种蜕变,但这种蜕变是向男性妥协,向旧制度妥协——埃伦的真实自我实际上已经封闭,只留下温柔贤惠的躯壳。“埃伦的生活并不轻松,也不幸福。她本不指望通过轻松的日子。要说不幸福,那是女人的本分。世界是属于男人的,她认定自己命该如此。”而在这样家庭整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斯嘉丽其实也一直在向读者提问:为什么如此高雅的母亲却选择了并不相配的丈夫——而斯嘉丽也通过奋斗成为一个新社会秩序(资本主义)下的精明女商人,展示出对当时女性低微妥协以及对旧社会礼教旗帜鲜明地挑战与抗争。
纵观全书,斯嘉丽一系列活动都在围绕着“抗争”展开:对爱情受挫的抗争,对男女不平等的抗争、对新旧时代更替的抗争……无论是她性格的阴暗面,还是始终留存的美好品质,都伴随她的成长有机地整合形成一个完满的个体——站在文学审美的角度,斯嘉丽这一人物形象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抗争的生命与美的象征,不完美,但足够鲜明立体、动人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