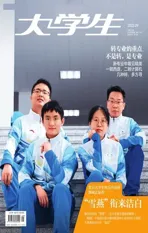绘本中:“她”好,“他”能
2022-10-09惠一蘅蔡静远李新艺颜珂中国人民大学
文/惠一蘅 蔡静远 李新艺 颜珂(中国人民大学)
图/彭美琪 杜天舒 李映雪 李霞 张子涵 童祎航 刘奕婷 单子郁(中国人民大学)
今年,我们走进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的绘本区,以书架的一个分格为单位,按照“一格一本”原则进行抽样,选取主要角色具有明确性别取向的绘本,最终得到218册有效样本。我们以不同性别为对照,编码分析故事的作者及其笔下角色的身份与行动,进一步呈现出我们目之所及的、真实的绘本世界。据此,我们想要看清在广阔的儿童绘本世界中,性别观念是如何被描绘和解释的。

图 1

图 2

图 3
纸页之外:创作者的选择
“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单元,是反复出现于文本中的相同或相似的要素,能够反映出不同故事之间的共性,我们首先分析了218册绘本的叙事母题。
成长母题是儿童绘本世界的主旋律,在218册绘本中出现了107次,占总体的49%。在绘本故事中,成长母题一般表现为主人公在其他人物的引导下,改正错误、解决问题、管理情绪、分担家务等,从而获得社会规范化的成长。比如在法国的经典成长绘本《红帽子艾米莉》中,4岁的艾米莉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学着如何面对第一次尿床、第一次上幼儿园等成长中必须经历的环节。
对抗母题则讲述主人公在与自然、他人、社会甚至自我的冲突中生存并发展,如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的绘本《花木兰》着重展现了花木兰如何与敌人斗争,最终解救出了皇帝。
寻找母题则侧重于对外界世界的探寻与感知,小主角往往会离开熟悉的家,去外面的世界探寻,与心中的期待相遇。例如《母鸡罗塔:好想念亲爱的奶奶》中的小母鸡在奶奶离世后,相信奶奶一定变成了星星,于是她出发去寻找“星星”奶奶。
在常见的友情、亲情母题中,则侧重描绘小主角如何解决与朋友、家人在相处中的矛盾、困难,最终感知到友情与亲情。
我们将218册绘本的作者与主角性别进行编码分析后发现,创作者在母题选择上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向。同时,作者与故事内主人公的男女性别数量比均接近1:1,呈现出一个均衡的、由两性共同搭建的绘本世界。
然而,当进一步分析作者性别与主角性别的交叉关系时,我们发现,后者比例的“均衡”恰恰来自两性作者创作倾向的“不均衡”。
我们构建了一项“相同性别偏向程度”指标来衡量这种倾向:0%表示作者在主角性别选择上没有偏向,创作出的男女主角数量相当;100%则表示作者只创作与自己性别相同的角色,即男作者笔下均为男角色、女作者笔下均为女角色。
如图2所示,在218册绘本中,96位男性作者的平均“相同性别偏向程度”是17.53%,102位女性作者的偏向程度是21.57%(其余样本因为作者信息缺失而未计入)。无论是男性作者还是女性作者,都或多或少会倾向将自己的性别赋予笔下的主角。
整体数据的样貌无法展现出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我们选取了样本中绘本数量最多的3个国家中国、美国和日本进行分析,发现3国均存在作者性别分布不均衡情况,各国的性别偏向程度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分。
如在中国的绘本中,女性作者占据主导,其数量是对应男性作者数量的1.81倍。不过,由于大多数作者在选择主角性别时,性别偏向程度并不强烈(集中在10%-20%左右),使得孩子们最终看到的,仍然是男女角色数量相当的世界。
其中,相较于中美两国,日本的情况最为特殊。在日本,女性作者数量仅为男性作者数量一半左右。与此同时,男性作者的性别偏好程度达到了68.42%,大大高于总体男性作者的偏好程度;而女性作者对女性主角的偏好程度则只有9.09%,明显低于总体女性作者的偏好程度。在日本,无论男性作者还是女性作者,都更倾向于将男性作为主角。
世界之中:怎样的他们
在绘本世界中,“她”和“他”有着什么样的人格轮廓?又是怎样推动着故事齿轮的旋转?
我们对故事中人物的性格特点进行提取,除了善良、友善这些男女共有的特点,女生更多是温柔、勤劳和体贴,男生则是友善、调皮或邪恶的。
为了深入剖析人物在故事情节中的作用,我们把绘本中的人物按功能分为5大类:承载者、指引者、捐助者、破坏者及对情节无推动作用的纽带角色、陪衬角色。
承载者一般为主人公,故事的叙事都围绕其行动而展开,是剧中最主要情节的推动器。正面积极的承载者往往表现出美好的品质,是胜利果实的享有者,在样本角色中的数量最多;而最终无法通过道德和人性的考验、沦为“反面教材”或经历悲惨的主角,被视为负面消极的承载者,他们在发挥功能的样本角色中占比最少。
指引者往往能引导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助其实现自身的价值。如在绘本《红帽子艾米莉》里,妈妈作为孩子的指引者,教导孩子解决矛盾。
为了避免因主人公陷入困境而导致的叙述中断,捐助者角色同样不可缺少,绘本《钧瓷娃娃》中的公主便作为捐助者帮助主人公小男孩击退破坏者巫婆。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破坏者的男性远高于女性。绘本世界中,那些显示出明确男性特征的梦魇怪、差点撞倒别人的车夫等,之所以“能够成为”破坏者,归根结底是——至少在作出伤害的那一刻——他们拥有比被害者更强的超能力、更大的灵活性或更丰厚的物质条件。
比“破坏者形象多为男性”更令人担忧的,是男性破坏者与女性负面承载者的组合。无意识的性别预设可能在种下积极思想的同时埋下消极观念的种子。
职业身份:缺席与复位
性格特质之外,绘本中的人物身份展现着他们如何在社会中锚定、与世界联结,是一个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维度。
绘本的受众通常为0-6岁的儿童,在这个年龄段,家庭是儿童最熟悉、心理距离最近的空间。与此对应,无论男性和女性,家庭相关的角色如父母、孩子、其他长辈,都是绘本中最常出现的人物身份。
根据全国妇联在2021年调查发布的《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全国主要数据报告》,在业女性与男性的占比,分别为43.5%和56.5%。而当我们将图5的左右部分并置观察可以发现,“家庭”模块通常与母亲、妻子、姨妈等母职角色绑定,而社会化群体则主要由男性组成,故事中“男主外,女主内”的身份设定无论对女性还是男性都是一种枷锁。

图 4

图 5
与此同时,男性职业角色的种类数量几乎是女性的两倍,显示出更大的丰富度,也使男性拥有了众多“专属”身份,如官员、画家、科学家、医生、博士等。两性虽然均有动物化的形象,但其中掌控群体最高权力的“动物王”(如狮子王)大多由男性扮演。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在护士、保姆这类传统意义上以女性为主体的职业之外,侦探、宇航员也开始多次成为绘本女主角的身份。从现实看,女性的智慧并未在现实中缺席,绘本等文化媒介所要做的便是去积极挖掘、客观呈现“她”的参与。
结语
相比文学作品,儿童绘本在性别叙事上的障碍在于:精简的情节难以尽述复杂丰满的人性,鲜明的角色性格在缺乏展开与解释的情景下,不经意便会落进扁平与刻板的陷阱。
在“回归儿童本位”成为童书出版共识的今天,如何打破性别规约,为孩子提供多元、自由的想象空间和成长可能,是出版人应该深思的重要题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