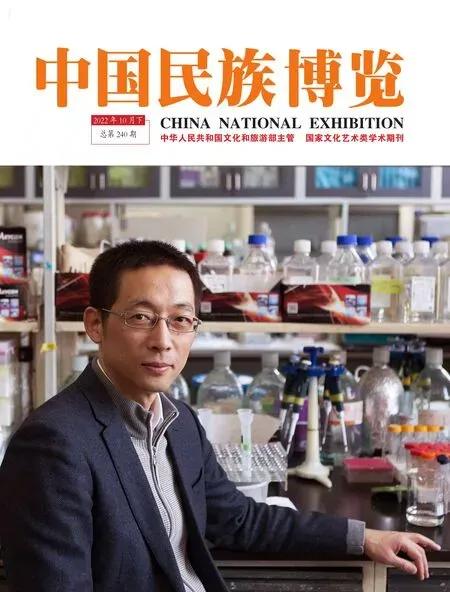自我的悲歌
——荣格精神分析视角下的《洪堡的礼物》
2022-10-08江凤
江 凤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47)
《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是二十世纪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的中期代表作,于1975 年以小说形式出版。著名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贝娄“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小说家,而《洪堡的礼物》是他最优秀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Harold Bloom:1)在《洪堡的礼物》中,贝娄描写了美国犹太作家查理·西特林(Charlie Citrine)和他的恩师洪堡·弗莱谢尔(Humboldt Fleisher)的不同命运。小说以西特林为叙述者,回忆了他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大半生经历,讲述了他与恩师洪堡、前妻丹尼丝、情人莱娜达、黑手党坎特拜尔、哥哥朱利叶斯等人之间发生的故事。诗人洪堡虽有渊博的知识及卓越的才华,却因执着地追求艺术的真、善、美,不肯与现实社会同流合污,最终贫困潦倒,在小旅馆中郁郁而终。西特林最初靠推销牙刷为生,在洪堡的提携下,逐渐在文艺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因以洪堡为原型创作的戏剧取得了成功从而名利双收。他曾有一个时期在思想上与洪堡渐行渐远。当他在纽约混迹于名流之中时,遇上了穷困落魄的洪堡,但他避而不认。洪堡死后,西特林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在他深陷困境之时,用洪堡生前馈赠的一个电影提纲改写成剧本,走出了困境。西特林最后重新厚葬了洪堡。在小说结束之时,西特林和孟纳沙安葬了洪堡的遗骨后,发现一朵小红花。孟纳沙问:“这是什么,查理?一朵春天的花吗?” 西特林答道:“是的。我想这终归会发生的。”(贝娄:606)
故事寓意式的结局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基于这些颇具象征意义的文字,许多读者和评论家倍感安慰,普遍认同《洪堡的礼物》反映了贝娄的乐观主义思想,认为贝娄摆脱了先前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愤世嫉俗的讽喻基调。评论家布拉德伯里就根据故事的结局,将《洪堡的礼物》定位为喜剧,认为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精神超越的故事。(Bradbury:85)国内学者周南翼则进一步指出西特林在最终“实现了灵魂的自我拯救,精神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周南翼:248)然而,通过对文本的仔细研读发现,故事的结局其实只是一种浪漫主义手法,作家贝娄并没有真正地给小说中的西铁林的未来指明方向,他的理想难以实现,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恰如空中楼阁,只不过是虚幻缥缈的乌托邦。本文以“自我”作为视角,从小说中的人物西铁林与现实生活中的贝娄的双重纬度,分析了人物的主观自我与现实环境的冲突,不仅仅展示了美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更意图揭示“美国梦”面具下的物质主义实质。
一、西铁林与贝娄的犹太自我
自我是什么?西方传统的哲学家们,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把自己凌驾于众人之上,为人类编织生活的“语录本”,推崇“纯粹精神”与“理想人格”,教导人们不要信任肉身、情感与激情,意图以人的部分代替整体,以理性和虚幻指导现实中的人们生活。德国哲学家尼采改变了这一观念,他在《悲剧的起源》中指出,人是精神性与肉体性的整合统一,因而要像古希腊酒神祭那样,在醉境中释放人的本能,解放精神对肉身的禁锢。尼采号召人们努力发现自我,追求自身的价值。(Nietzsche:187)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则认为:“自我是构成意识场域的中心,是所有个人意识的主体。”并指出:“自我是我们生命的目标,是那种我们称之为个性的命中注定的组合的最完整的表现”。“一切人格的最终目标,便是自我实现”。(荣格:98)古典哲学中的“自我”尊崇理性,忽略个体的要求,尼采以来西方世界的“自我”则是人本主义的“自我”,关注人的本能,突出人的自身价值,赞同人的自我实现。
根据荣格的研究,仪式以及古老民族的特性能够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在他们的后代中延续下来,构成他们人格意识,也就是“自我”的一部分。荣格曾经在埃尔贡山区部落探索宗教观念与仪式的痕迹,他发现当地的土著人每天清晨太阳升起之时,都要在手心吐口唾沫,把手举向太阳。然而他们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潜意识的行为。其实这是土著人祖先的太阳祭献仪式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在其后代的延传。
古代犹太神秘主义哲学认为,宇宙划分为低层级的物质和高层级的精神(知识)两个领域,低层级的物质领域是公众经验到的有形世界中的事物,带有暂时性或偶然性,从认识论上来看是一种“或然的”“可能的”属性反映。高层级的精神领域,是指居于有形世界之上的、作为抽象观念存在的灵魂世界,包括科学、哲学、智慧等内容。灵魂以理想的形式停留于精神领域,在那里,通过精神的追求和神意的启示,灵魂可以到达终极真理。(施炎平:68)而在现实生活的教育活动中,犹太人在教育儿童之时,常常在书页上涂上蜂蜜,以让孩子从小就能感觉到知识的甜蜜。在传统的犹太家庭中,男人每天都埋头研究经书,不问俗事,无需操心经济收入,学问上的成就是他们的骄傲,也是全家人的骄傲。重视精神(知识)、勤劳、上进构成了犹太民族的特性。
作为俄国犹太移民的儿子,西特林生活在美国,已经远离他的祖先源地耶路撒冷,然而,犹太人的民族特性在他身上却很好地延续了下来。西特林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在大学时期“昼思夜想的只有文学”,(Bellow:1)他的人生追求屡遇困境,但他并不气馁。他大学毕业后流落于芝加哥,最初以推销牙刷为业,生活困顿。然而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在文学界出人头地。他在为生活奔波之余经常去拜见当时已是著名诗人的洪堡,并靠着洪堡的提携与自己的努力步入文坛,终于成为颇有声誉的剧作家。西特林积极上进、勤奋踏实,有着崇高的人生理想及精神追求的犹太民族典型特质,构成了他的“自我”的一部分。
然而,西特林的“自我”却屡遇挫折。在历经艰辛之后,他以洪堡的个性为素材创作的剧本在百老汇上演终于取得了成功,名誉、金钱、地位、女人接踵而至。西特林吸取了洪堡遭受拜金主义围堵失败的教训,努力在文学创作与物质主义之间寻求平衡,他放弃了批判工业主义境况下人的精神“厌烦”的著作的写作,转而为当时的政治人物撰写传记,以博取政治人物的青睐。然而,西特林的努力仍然难逃失败的命运。实用主义与文艺追求代表着物质与精神的两个极点,从来就是格格不入,步入了实用主义道路的他即使冥思苦想也难以获得创作的灵感,再也没有能力推出新的著作,文学梦难以为继。最后,西特林破产了,曾经围绕在他周围的人纷纷离他而去,心怀文学理想的他只得住在马德里三等膳宿公寓后面的宿舍里写一本导游手册。虽则最后他意外得到洪堡遗赠给他的礼物:两部剧本提纲,并凭借着洪堡的礼物摆脱了困境,然而遭受了物质与精神双重打击的他对人生的态度及理想的信仰完全改变了。不管怎样努力,艺术家都无法改变在物质至上的美国的命运。
多位评论家认为,西特林其实就是贝娄的影子,他的人生历程与贝娄几近相似。(Hyland:80)同样也是犹太人后裔的贝娄在骨子里有着犹太民族的积极追求、勤劳肯干的精神。贝娄在他的人生选择上与西特林一样,他选择了遭受家族鄙视的文学道路,开始了执着的追求过程。贝娄在文学追求上历经磨难,在他选择文学作为理想之时,遭到了家人的极力反对,父亲不愿见他,哥哥对他冷嘲热讽。他的初期创作活动还屡遇挫折,寄出的小说常常受到出版社的拒绝,使得他只能在经济窘迫状态中生活。然而,贝娄从不轻易放弃,他不断地努力,终于在出版了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后,在文学界渐渐地建立起自己的声望。1972 年,贝娄出版了《洪堡的礼物》,并因其于1976 年获得了普利策图书奖。同年,贝娄又因“对当代美国文化进行了富有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登上了世界文学的巅峰。
无疑,世界给予作家的荣誉证明了他的成功。然而,若从贝娄所追求的创作目的的实现上来看,则远远还未实现他的自我,他的努力远未达到目标。贝娄认为“艺术的作用在于真实的展现世界,在于对世界的抗争”。(周南翼:32)他在一系列小说中都展露这一主题。例如《晃来晃去的人》中的主人公约瑟夫虽处于孤立无援、与人隔阂的状态,却拒绝被周围的物质主义同化,坚持不懈的追求自己的理想。又如《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始终坚持文化治世的思想,在周围的市侩主义中踽踽独行。然而,现实是令作家失望的,美国奉行物质主义、实用主义至上的现实不但没有丝毫的改观,反而有加剧之势。
贝娄与西铁林一样,都想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但是,具有犹太人自我的他们,注定是不能完全获得美国社会接受的。小说中的西铁林在成名之后,曾想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以实用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周旋于政界名人之中,沉湎于物质享受。然而现实中的他并不快乐,并最终因洪堡的死亡深感愧疚,改变了实用主义的信仰。因为犹太身份的问题,贝娄在美国社会历尽艰辛,常常受到歧视与打击。贝娄的小说主人公大都是处于苦难之中的犹太人,与其说他在多部小说中描绘了犹太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倒不如说贝娄是用自己的笔尖向世人倾诉作为犹太人的自己的艰辛与不幸。
二、西铁林与贝娄的知识分子自我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娄的个人属性绝不会仅仅狭隘地局限于他的民族特性当中。西特林与贝娄不仅仅是犹太人,他们都还是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的思维根植于内心。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呢?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论,认为“知识分子并不局限于少数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而是包括各个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只要进入某种精神活动,进入社会关系,善于表达意见,作出自己的文化选择,这样的人都是“知识分子”。(萨义德:12)而卡尔·曼海姆在1929 年发表的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提出来了“自由漂游的知识分子”这一理论,他认为由于知识分子自由飘游的属性,他们可以超越狭隘的特定阶级意识或阶层的局部利益,进而达到普遍的、公正的判断和标准,成为意识形态谎言的揭露者、思想的相对主义者和批判者、各种世界观的审视者。(曼海姆:108)萨义德的“业余知识分子理论”与卡尔·曼海姆有相似之处,他认为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市民社会的集中化,大公司、财团、基金会、利益集团等雇佣并控制了知识分子的研究和计划,知识成为了商业和政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对社会现实表达不满和进行批判。(萨义德:71)西方学者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虽然至今缺乏统一的定论,但却都不否认一点,那就是知识分子是“具有社会良知的人,是人类基本价值例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423)
西特林便是具有这样知识分子自我的人。他在年轻时获得洪堡的青睐与提携,逐渐走上了成功之路。与洪堡相比,他曾经尝试着去做一个识时务者,他迎合政界名人,按美国主流社会价值标准生活。然而,洪堡的死亡对他的心灵产生了震动,具有知识分子良知本能的他逐渐厌恶了实用主义的生活方式,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反思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走上了与实用主义背道而驰的道路。也就是从他放下实用主义的那时起,西特林的好运戛然而止,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与实用主义冲突的后果就是西特林逐渐被现实社会遗弃,厄运不断降临,成功离他越来越远。
在社会良知及批判性这一方面,贝娄比起西特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一系列作品都反映了美国的金钱社会本质。在《只争朝夕》中,贝娄以主人公威尔赫姆的一生经历表明在美国社会,金钱是评价一个人的唯一尺度,物质上的失败就意味着个人的失败。评论家莱斯利·菲德勒认为,尽管小说里的威尔赫姆是一个犹太人,使它已经超越了犹太人的范畴,反映了美国的社会实质和贝娄的社会良知。(周南翼:141)而《洪堡的礼物》毫无疑问表达了贝娄对于美国拜金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表达了贝娄对于公众冷漠心灵的谴责。无论小说中的西特林,还是现实生活中的贝娄,他们知识分子的自我都不可能实现。西特林只能流落于西班牙,贝娄改变美国物质主义的愿望也只能是一腔热情。在实用主义面前,文学诗歌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西特林与贝娄的自我挫折自是理所当然。
三、西铁林与贝娄的自我悲歌
荣格在他的精神分析著作《未发现的自我》的第一章“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困境”中指出:现代社会的个人已被拉平化、均等化,群体规模越来越大,个人变得越来越渺小。个人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已不再存在于个性的发展之中,而是存在于国家的政策和社会的群体信仰之中。个人只有将自己淹没在群体信仰的洪流之中,他才能获得群体的认可,反之,他将受到群体的遗弃,处于孤独的境地。(荣格:13)
贝娄与西特林的人生境遇反映了他们的个人自我与美国社会群体信仰的冲突。美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决定了物质主义至上的观念过去是并将始终是美国的群体信仰之一。另一方面,战后美国社会在信仰和价值观念方面经历了严重危机。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扫荡了西方人的一切价值观念。现代人虽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科技和文明,但随着人道主义的丧失,人的精神世界变得一无所有,成为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人的存在失去了意义,没有了归宿感,信仰迷失下的人们怀疑一切,不相信未来,因而极力追求物质的享受,追求暂时的感官刺激,推崇及时行乐。在文化艺术被边缘化的社会背景下,小说中的洪堡和西特林努力追求精神价值,想跻身上流社会,融入美国主流文化,自然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在强大的群体信仰——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面前,洪堡与西特林的自我实现的理想被撕扯得体无完肤、支离破碎。
反观现实生活中的贝娄,理想自我与社会现实碰撞的结果使得他的心灵伤痕累累。执着的贝娄在婚姻、工作生活中屡遇困境,他不得不多次转向于超验学说。饱受现实生活折磨的贝娄甚至多次去看过心理医生。跟《洪堡的礼物》当中的西特林一样,贝娄相信斯坦纳人智学,认为人们可以跟死去的亡灵交流,并且通过灵魂的净化达到自我拯救。其实,对于像贝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竟然要选择非理性的方式来摆脱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嘲弄。在《洪堡的礼物》结尾,西特林看见了一朵春天的小红花,然而,这象征着什么呢?是预示着西特林将继续沿着洪堡的追求知识,追求真、善、美的道路前进吗?显然,贝娄的用意在于表明西特林从实用主义完全摆脱了出来,实现了灵魂的自我拯救,然而,曾经走过这条路的洪堡已然证明在美国这个实用主义的物质社会,文艺济世的道路是不可能成功的。西特林该向何方而去?贝娄并没有对西特林未来的道路作出任何新的设想,只是用浪漫主义设置了一个超验的结局。
贝娄用西铁林无法实现的自我展现了人道主义缺失、文化精神沦落的美国社会现状,表达了作家对于物质主义统治下艺术家命运的担忧,其实也是对作为其中一员的自己的命运的担忧。美国历来自诩为“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1932 年,作家詹姆斯·洛亚当斯在其著作《美国史诗》中提出了“美国梦”一说,认为“在美国,只要努力奋斗,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现实中的美国虽也不乏优越之处,但远非想象中的五彩斑斓,而是一个种族歧视严重、信仰缺失的社会;是一个文化贬值的、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的金钱社会。那里也许是政治家及金融寡头的天堂,却有可能是知识分子的地狱。20 世纪20 年代,同样怀惴美国梦的贝娄的父亲带着一家人来到了这个梦想中的国度,50 多年后,作家贝娄却在这样的境况中迷茫忧思: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前途在何方?人类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洪堡的礼物》虽似乎呈现出些许乐观主义的迹象,但并不能印证西方知识分子的前途已是一片光明,小说内外知识分子的多舛命运,不啻为对西方大肆宣扬的所谓的“美国梦”的绝妙讽刺,同时也让人看清了美国的拜金主义社会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