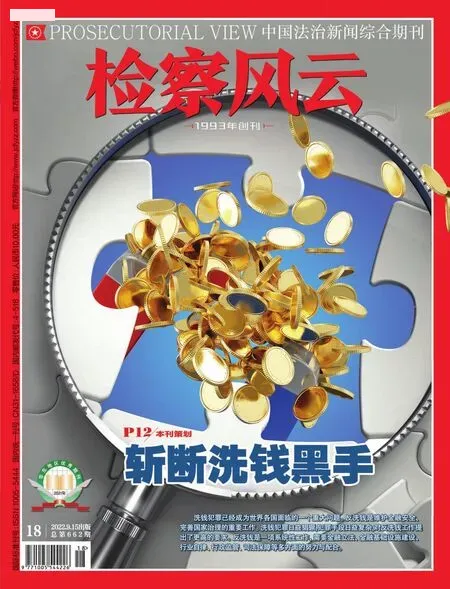完刑人困境与社会集体无意识
2022-09-27林朴
文·图/林朴

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屡获各类奖项的日本影片《美好的世界》,讲述前黑社会分子三上正夫(役所广司饰演),因杀人罪被判入狱,服刑13年后重返社会,努力融入社会但处处碰壁、找不到出路的故事。
这是一部颇具观赏性的作品。摄影、叙事、表演都有独到之处,细细观赏,当然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好电影。但回到电影的主题上,不免令人觉得,好的电影技巧浪费在了一个自我禁锢的范式内。这里所谓自我禁锢的范式是:社会大众对有前科的社会人员,太过严苛,不论是就业还是融入社会,都过于排斥,使他们在回归社会的过程中,受到了较为难堪的境遇。有些人走投无路再次犯罪;有些极端者,甚至选择一死了之。三上正夫的结局正是后者。当只有一部电影讲述这样的故事,在认知上它是独特的;但当一大堆电影讲述同类的故事,我们便称之为“范式”。在数量庞大的同类作品中,《美好的世界》没有创新的表达,没有打破范式,这算是笔者对新作品特有的苛责。
英语世界里有这样一句名言,“Everybody deserves a second chance”(每个人都应该有重来的机会)。这句话也常被用于服完刑回归社会的人。他们应该有回到社会被平等对待的权利。但现实不是这样,甚至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对有前科的人,人们大多持警惕、排斥的态度,他们回归社会可谓困难重重。这个应然和实然的冲突,构成了这类电影的表达范式。
刑罚是法律体系对犯罪事实应受惩罚定性定量的判定和执行。那么,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他就洗清了所有犯过的罪孽,变成一个和没有前科的人一样的社会人了吗?在法律体系看来,的确如此。然而,现实生活中,社会大众很大程度上似乎并不认同这一点。层出不穷、不论拍多少不同个体的完刑人回归社会的电影故事,全都像在同一个范式中不断重复,并且指向同一个困境。
社会大众是由各行各业、年龄和身份极为离散的人构成的。世俗社会中,他们往往不约而同地对完刑人予以集体无意识地排斥。翻拍同类故事的制作人或创作者意识到了这种冲突,抓住了曾经的罪犯在这种集体无意识面前孱弱的一面,在艺术上形成了近乎流水线作业的悲剧满足感反差;甚至,无一例外地将悲剧性结果归咎于社会大众的冷漠与偏见。
笔者以为,这差不多是谬论。当几乎没有镜头和故事对准受害者遭受苦难后的境遇,无视社会大众对犯罪的担忧,似乎只能让观众随着编剧和导演们一起陷于无法突破的社会困境,寻求乌托邦式的解决路径。人们依旧在不停地追问(难道大众没有权利责问),犯罪的后果被完全纠正了吗?完刑人再犯的风险被降低到了最低吗?他们真心忏悔,跟过去(犯罪)完全切割了吗?如此种种,却往往忽略了出狱者成为累犯,还有一部分原因恰恰源自社会大众对他们的歧视和排斥。
当然,社会大众的反应是真实的,他们在以群体无意识的方式,通过暴力机构的威慑某种意义上把罪犯的刑期变长,令罪罚变得超出法律体系的认定。这不是冷漠和偏见,而是社会大众对犯罪行为的深层抑制本能。
艺术工作者正在尝试的,是用作品告诉观众:世界并非那么美好,犯罪行为除了受法律体系惩罚之外,还会在更长时间内受到来自社会大众的软性惩罚。这是一个客观现象,并非仅仅出于冷漠与偏见,甚至并非只针对完刑人,而是整个社会大众的一种自我惕厉——不要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