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到底有多深
2022-09-16◎叶子
◎叶 子
1
肖德贵死了,认识他的人不多,几个来补鞋的老主顾提着鞋,站在巷口摇头说不相信。那么小心的一个人,平时见着蚂蚁绕开走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说死就死呢。但肖德贵的确死了,搭了灵棚,棚子整天响着哀乐,棚顶挂一张微笑着的脸。有人问秀芳,德贵不会水啊?秀芳嘴唇抖动几下,没出声。难不成真淹死会水的?秀芳半天接不上个句子,末了说,水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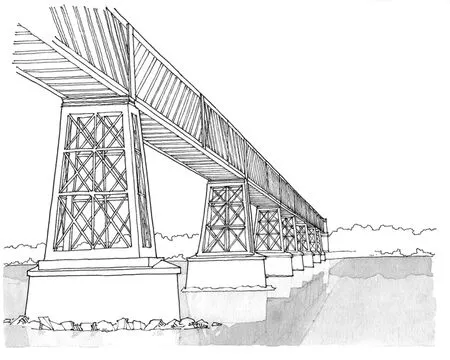
肖德贵是我舅,我去上香的时候他还在笑。我凑近看,发现肖德贵的像是画的,饱满的脸上刻意多了几条皱纹,有点儿失真。我想起昨天下午舅妈面前的照片,大概是请人照着画的。我印象中舅舅永远土着一张脸,近乎泥巴随便被人捏了几下。他是那么高,人堆里容易找着,佝偻着腰的准是。他不喜欢人堆,见有人靠近,他立马走开。我舅右手残疾,臂膀从肱二头肌那个地方断掉,长成一个走着蓝色血管的肉瘤,动起来很奇怪。我见过一次,感觉那条断臂莫名其妙的低幼化。那天舅舅来幼儿园接我,平时都是我妈接,她把所有白班调成夜班,为的就是接我。那天我妈头疼去了医院。我喊了声舅,他伸出左手,手掌笔直竖着,后来我在过马路时看见交警用这个手势,是停止的意思。舅舅站不直,腰以上的部分向前栽着,加上一件宽大的上衣,看起来滑稽。舅舅将右手插在裤兜里,准确点说将右边的衣袖插在裤兜里。一路上他在前边走,步子不大但急,我在后面小跑才能跟上。我喊肖德贵你奔三根桩啊?这是我外婆的口头禅,三根桩是火葬场,刚好建在国道的三公里处。肖德贵刹住脚,竟然没有往前栽倒。他环视周边,说校门口全是你同学。他牵着我,不急着往家走,带我到和平路吃酸辣粉。我问,舅舅你真当过兵?他不置可否,仰着脸盘子望天,我顺着望天,傍晚时分的天空什么也没有。好半天他问,你知道天上的样子吗?不等我回答,他说绝不是在地上看天的样子,了解天得从天上看。那时候我们就像一朵云飘在空中,想在空中待着就待着,想飘哪里飘哪里。说完递给我一个五角星,我没要,我盒子里的五角星满得装不下,偏偏我想要子弹壳,他又没有。显然舅舅有些失望,说,跟你舅妈一路货色。你是伞兵?我撇了撇嘴,表示不相信。他有些急,把我拉到僻静处,右臂使劲向上,袖子一下子褪到腋下,断臂露了出来,他说,证据。我看见的其实不是手臂,是一截短小丑陋的肉棒。我紧张得有些闭气,舅舅好像无所谓。我问过外婆,舅舅的手臂怎么断的?外婆拍我一巴掌,什么怎么断的,再乱说撕你的嘴。
我们吃完酸辣粉往家走,一路上舅舅叽叽咕咕背诵诗歌,关于天空的,我听不懂。回到家舅妈堵在门口,正指责我妈,说你这个当妹妹的当到家了,你哥上得台面吗,啊?接着指着墙上的挂钟,冲着舅舅喊,四个点了,一张脸兜得捡不起来了不是?我赶紧躲开。舅妈挺着肚子,那里装着我表弟肖军。舅舅像我上课打瞌睡一样犯了错,低着头踅进屋子。
我问坐夜的肖军,舅的相片是画的?肖军眼里空空的,眼底血丝发散,点点头。我说舅舅也算是勇救落水老人,没啥遗憾的。肖军闭着嘴。看得出,婚礼上的酒精还未散尽,整个人蔫不拉几的样儿。
2
就在舅舅接我后不久,肖军爬出了舅妈肚子。不得不说,肖军天生读书的料。我们班有个自诩为学神的家伙,有天背《出师表》,到“故五月渡泸”处断了篇儿,肖军当时读小学三年级,在我家坝子里逗蚂蚁玩,接了句“深入不毛”,举座皆惊。学神拿出大白兔奶糖,说背完给你。肖军当即一字不漏背完。那以后,学神再也没有到过我家,也不再提学神的话。我妈似乎发现了肖军的天赋,拉着就去找舅妈。舅妈到处翻来一本发黄的书,念给肖军听,是一个叫鲁迅的人写的《伤逝》,念完肖军竟然能够复述个大概,我妈让我复述,我支支吾吾连主人公都没有记住。舅妈抹了一把脸,满手的泪,颠几步拍着铁门喊,肖德贵,老天待你不薄啊。舅舅从二楼下来,扶在铁门柱上听舅妈颠三倒四的叙述,舅妈叙述时偶尔看我妈一眼,我妈跟着点头。舅舅木着脸,摇摇头,没有言语。舅妈拧了鸡毛掸子敲着桌子,说,从现在开始,肖军读书的事儿是头等大事。然后一挥手,佐着话语下决定,有点像列宁在十月。外婆当晚夹了捆黄表纸去了河边,给外公烧了点儿钱过去。不到一周,舅妈给肖军请来了家庭教师。我家院坝的蚂蚁,每天自顾自地来去。我问我妈,舅妈家哪来钱请家教?我妈怜悯地看我一眼,说老天爷匀给舅舅的保命钱呢。
舅妈那年怀身大肚,在朝天门码头接过舅舅的右手,准确说是衣袖,向送舅舅的两个战友鞠躬,勾不了腰,只得欠着身子说给首长添麻烦了。其中一个黑膛短脸的敦实个子给舅妈敬了个礼,说我是肖德贵同志的班长,他受伤我有责任,嫂子,先安心保胎,等段时间我来看老肖。然后递给舅妈一个信封,说这是组织上的关怀,给德贵同志治病。肖德贵斜嘴吊眼一乐,右手刚要舞动起来,被舅妈揿贴住身子。肖德贵只得吐掉嘴里的烟蒂,用左手向战友敬了个礼,站在码头目送轮船离开,才跟着回了家。
舅舅一直没摆过断臂的原因,舅妈也是三缄其口。在此之前,全家得到消息是肖德贵受伤,但没有想到是缺了一条胳臂。外婆天天去华严寺吃斋念佛。肖军上学不远,两条马路过去的人民小学,舅妈每天接送,既不让外婆接送,也不让舅舅接送。舅舅对此有些看法,说无论如何得送送孩子,然后朝肖军挤眉弄眼。肖军不说话,只点头。舅舅拉着肖军准备出门,舅妈拦在门口,肖德贵,你跟我来。肖军就伫门外等。舅舅跟着舅妈进了卧室,舅妈问肖德贵,你觉得你送军军去上学方便吗?方便啊。我是说你用哪只手牵孩子?舅舅一时急促,扬起左手说不比正常人差。是,关键是肖军的同学怎么看?怎么看?舅妈坐到床沿上,耐着性子说肖军是接受你的,是吗?是,不然他不会让我送。但是,肖军的同学接受你吗?同学的家长接受你吗?要他们接受干吗?就你瞎,肖军期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好多人眼睛都红出血了,这下倒好,你帮着去出口气。舅舅绕不过来。舅舅的班长说他当时胳臂摔断了,醒来不认人,眼里空的。后来医生会诊,轻微脑震荡,只要安心养,不受刺激,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经过舅妈这几问,舅舅脑子跟不上,短路,突然人往后仰,跌翻在地,全身僵直,脸青面玄,口吐白沫,蜷曲抽搐,把舅妈吓得半死,扯了张毯子盖住舅舅,蜡黄着脸喊外婆,让肖军喊我妈。等我妈赶到,舅舅早醒了,在毯子下蜷成一团。外婆把舅舅捧到怀里,浅着勺子喂葡萄糖水。舅舅身子虚弱,像刚跑步登过一座山。他说,我头疼,军军你怎么不去上学?我睡地上干吗?翻着身子起来,地上渍一摊秽物。
舅舅从此吃卡马西平片儿,一日两次,一次两片。医生说这属于脑部异常放电,不能停药,脑子的放电捉摸不定,维护好情绪,轻重断不了根儿。药瓶放在左边掩襟口袋里,一走动就能听见药粒嘁嘁喳喳的声响。
从此我很少看见肖军笑,每天捧着大部头的书,冷着脸看,跟全世界欠了他钱似的。有同学问肖军,你爸是伞兵?肖军不答,被问急了,怼一句:你爸才是伞兵,你全家是伞兵。把问的人弄得一愣一愣的。
3
舅舅的朋友不多,几个内亲内戚轮流坐夜。肖军白天睡会儿,晚上抱着火炉子当孝子。在第三天下午,舅舅的灵棚前来了一个陌生人,我和肖军都不认识。当时我正给长明灯续菜籽油,那人在棚口晃晃过去了,然后又退回来,望着照片上微笑的舅舅,嘴唇抖动,提着的黄布挎包落在脚下,问,是肖德贵?我偏着颈子问,找肖德贵?那人短黑的脸膛拼命挤了个笑,瞬间又消失了,有点儿像风吹了那么一下子,然后说,狗日的走了?他捡起挎包走进来,肖军递给他三炷香,他挡开了,在微笑的舅舅面前敬礼,鞠躬。然后从挎包里摸出个盒子,盒子黑油油起了包浆,并列在舅舅的骨灰盒旁。
舅妈被肖军叫了过来,舅妈喊了声“班长”,带着班长去了屋里。屋里红色的“囍”字全都撤了,贴上的“奠”字糨糊还未干,但堂屋中间的彩灯没来得及撤,一开灯,跟着一闪一闪亮晶晶,气氛迷离。舅妈赶紧揿灭开关。班长坐下,我将茶水递过去,班长喉结滚动,喉咙轰鸣,看来赶了很远的路。班长环视了一眼屋子,盯着楼梯口的铁门看了半天,脸色黯然,说,苦了老肖。班长说他早退役了,在贵州山区务农。班长说最近一睡觉准梦见肖德贵,大鸟一样悬在空中,虚着眼,头发飘拂,他大声喊肖德贵,肖德贵充耳不闻。天大的风,他哪能听见,你说?舅妈勉强笑笑,没有说。我上去就是几脚,吼他,为啥不开降落伞为啥不戴面罩,呃?他回头一看是我,吓得煞白脸,一收翅膀,直线坠到地上,还弹了几弹。龟儿子跟现实版差不离。班长喝了口茶,张合着漱几下,吞了,把茶缸递给我,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久。老肖侄儿。舅妈说。我估计老肖念我,就摸着赶过来了。班长摸出旱烟,一小捆用报纸卷的,抽出一只,伸出舌头准备舔着封口,看到我和舅妈惊异的眼神,赧颜放下,说,嫂子,撤销德贵的处分决定在盒子里,退伍时我想亲自送过来,回贵州后就没走开,牵牵扯扯过了二十多年,真对不住老肖。舅妈说,别,对德贵没大用处。班长停了一会儿,将手里的烟展开,排烟丝,挤着裹紧,然后问,怎么去的德贵?淹死的。德贵不会水?舅妈松了口气,像是最后一个人提这个问题,顺手把一包朝天门递过去,说,水深。大概班长觉得一会儿就把话说完了,屁股还没热乎,尬坐着,这时肖军进来上卫生间,班长逮到一个话题,侄儿在哪儿上班?上海。啧啧啧,这身板,随他爸,高,不当兵可惜了。说完讪讪地笑,盯着楼梯口的铁门,黑得发暗的铁门上,挂着把金色的铜锁,问,老肖乱跑?
有段时间舅妈严禁舅舅出门,舅妈家住一栋两层楼的老砖房,她在楼梯口安了铁门,该吃饭的时候拍一下锁,铁门“哐哐”响,我家住在隔壁,我妈就会说该弄饭了。那个时刻舅舅寸着脚一阶阶下楼,从铁柱间接过饭盒,席地坐在台阶上,膝盖头并着搁饭盒,栽着头一顿猛吃,吃相腌臜。外婆有些不忍,说放娃子下楼,这样下去怕是胖得过不了铁门。舅舅确实胖了不少,白净了不少。舅妈背过脸去,把钥匙递给外婆。
我们家对舅妈的宽容让我吃惊,特别是外婆和我妈,舅舅是她儿子,我妈是舅舅的亲妹妹。我说放舅舅出来,不然要憋死的。我妈竟然笑出声来,笑得泪水长流。我问妈你是在哭还是在笑?我妈马上抡起手背抹了眼泪,说命,都是命。
舅舅下楼那天,我们像举行什么盛大的仪式,围一圈儿在一楼等他。事实上,肖军打开铁门,舅舅迟疑良久,脚没下地就反身上楼。我喊舅舅,舅舅背着我们扬了扬左手,说你小子别喊,数学题一团糟。我立即闭了嘴。
4
有天我在家里写作业,突然铅笔下有个亮点跳动,顺着光源望,舅舅在天楼拿镜子跟我打招呼,他朝我咧嘴,示意我把作业本竖起来。我竖起作业本,他架起望远镜,调着焦,大体看了有几分钟,然后摇摇头,左手在空中打了个大叉。毫无疑问,第二天我的数学老师也给画了个大叉。从此,我做完作业,就用镜片晃天楼,舅舅从某个地方冒出来,架起望远镜,像扫视战场的将军,看完,他在天楼上来回奔跑,舞着左手,给我打对钩或者打叉。
周末一个人无聊。作业做完,父母加班,肖军补课,和舅舅玩了一会儿镜子对晃,抓起游泳圈,去了瑞河,游泳。水发黑,光斑像绸缎打上的高光,缓缓移动。以前游的人多,自从上游建了水泥厂,游的人少了,差不多只剩我这种无聊的学生娃。我一个猛子扎下去,触底,有些遗憾,站起来,水淹在我肚脐眼。我甩掉游泳圈,放平身子,躺在水上,朝天空泚尿,尿落到肚皮上,热乎乎发烫。天上东一块西一块的云朵,丝绒样,半天不动,云后面是深不见底的蓝。我突然想起舅舅望天空的样子,鼻子酸热。十五岁的我第一次想写诗,第一句是“瑞河掩不住一个少年的寂寞”,自己觉得还行,想第二句,半天挤不出来,作罢。现在想起来可惜,要是那时坚持想,说不定现在诗坛多了一个诗人。眯上眼,眼里红彤彤的,像淌血。因为想不出句子,闭气下沉,搬开水底的石头,右手一薅,一只螃蟹在手,正蜕壳,从脚到身子全软,我摆弄了阵子,放水里,螃蟹吐着泡子,旋一圈不见了。
没有我的日子舅舅也很无聊,每天在天楼嗨嗨嗨一阵,说是练气功。我爸妈双双下岗,我爸用买断工龄的钱买了辆建设125,跑摩的,昏天黑地跑。我妈一早推着稀饭白糕去人民小学门口卖,我妈说经常看见肖军进出,喊他吃白糕,他像没听见一样。
很少见到肖军,我妈也不允许我打扰他,我妈说肖军是肖家的根。那我是什么?我妈乜我一眼,说落叶。我不在乎根啊叶的,我只在乎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样子。只是每次见到肖军,我竟无从开口,感觉怪怪的。
肖军不负众望,保送进了本市重点中学。小学毕业学校搞一次亲子活动,肖军皱着眉头把参赛表格带回家。那天舅妈不在,外婆在另一个小区打川牌。肖军过来找我时吓我一跳,他把表格放在我面前,问,我该不该填他?我瞅见亲子活动是家庭乒乓球友谊赛,下面有参赛成员表。我望了望天楼,空的。我问,为啥不跟舅舅商量?于是我陪着肖军喊舅舅,估计舅舅刚睡醒,眼珠在眵目糊中滑来滑去。我们隔着铁门,舅舅在台阶上坐着,用衣袖揩眼,老远我们闻到一股臭鸡蛋味儿。我说舅舅真臭。舅舅嘿嘿一笑,渥了两腋痱子,楼上热。肖军将表格递过去,舅舅看了半天,突然兴奋起来,说,老子从小霸台子,水泥台子哟,放心,准赢。
可是,乒乓球得双手。
舅舅猛地黯然,屋里跟着暗了。隔了一会儿他说我左手灭他们。
肖军翻翻白眼。舅舅急了,摇得铁门哐哐响,说我练的左手,左手发球,左手挥拍。这段时间再稍稍练练,就回来了技术。舅舅突然从衣兜里捏出一枚石子,一扔,飞进门边的靴子里。又摸出一张扑克牌,三根指头卡住,一弹,扑克在屋子里旋一圈儿,稳稳当当回到舅舅左手上。我和肖军被唬得一愣一愣的。
舅妈是晚上知道这事儿的,她在参赛表中看到了“肖德贵”几个字,像被烫着了样,打开铁门,上二楼,二楼没人,上天楼。舅舅正挥着拍子与墙对练,全身精湿。事实上,舅舅左手打乒乓球的动作说有多拙就有多拙,看起来有点儿像球在打他。舅妈问,肖德贵,孩子不懂事,你跟着不懂?不等舅舅反应过来,舅妈亮出那张表格,舅舅双眼亮晶晶地说,准赢。舅妈压低声音咆哮,军军好不容易保送。比赛关保送什么事儿?我左手一样打。打你个头啊。舅妈彻底生气,说脑壳真进水了。
舅舅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下午,他迷糊了好半天才想起今天有个友谊赛。于是赶紧下楼,铁门锁着。他用镜片照我,那天偏偏没有阳光。他在天楼急得团团转,估计跟饿狼找不着鸡的感觉差不多。我看到时,他竟然撑起太阳伞,从天楼跳了下来。刚开始人在空中悠悠地旋了一圈儿,突然加速下落,卡在一人高的花椒树上,像只大鸟悬着,刺得号娘,动弹不得。
外婆戴了老花眼镜,给舅舅取了半天毛刺,抹了明矾水,再上紫药水,舅舅斑斑点点像动物园恹疲的豹子。
5
我们送舅舅去三根桩火化,外婆没去,她说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忍心。肖军一路扔着纸钱。舅舅化妆时,我仰头望高高的烟囱,冰冰凉耸入蓝天。我想,舅舅不是常常念叨天上吗?舅妈花钱掐了个时辰,我们坐在石栏杆边等着喊号。
殡仪馆人多,一潮一潮像赶集,生死都匆匆。喊到我们时已接近中午,我们好像没有来时那般忧戚。我们为舅舅准备了全套送别仪式,好多人投来赞许的目光,工作人员举着拇指说善终。我们跟在乐队后面,先是礼炮九响,绕着花坛进大厅告别,舅舅躺在白菊环绕的棺内,整个人容光焕发。乐队将太平棺送到过道中间,工作人员说最后告个别,我竟一下没有认出舅舅,估计其他人也有这种感觉,舅舅胖胖的脸上浮着一层红晕。舅妈试探着问,可不可以将舅舅擦皮鞋的家什一起烧,工作人员摇着头说那样得付两个人的钱。我妈上前想说点什么,没等开口,工作人员过来喊时间到,仰着脖子吼:极乐世界九千九,通天大路莫回头。
舅妈说的家什是舅舅亲手做的。那时肖军读高三,住读,舅妈一分钱掰成两半使,一个人掰成两个用,里里外外一把手。我流落江湖,靠卖文为生,美其名曰作家,每周借看望我妈为由,狂蹭两顿大餐。有天我去看外婆,她躺在一楼的大床上,见我进去竟然喊了一声军军,我知道老人家的脑子不好使。我嗯嗯。舅舅坐在楼梯口,突然说他得学着打棺材,听着起鸡皮疙瘩。舅妈给肖军送鸡汤去了,食堂有很多高三父母拎着保温桶等孩子下课。我爸爸已经卖掉了建设125,买了木工家什,学了半年跟工程队跑。家什搁在外婆家天楼。建筑业一路高歌猛进,木工工资水涨船高。我顺口说舅舅你可以的。没想到以后的每天,他在自家天楼,将木棒锯成木板,木板割成木条,木条截成四方小块。他挥汗如雨,刨花飞溅,左手越来越灵巧。不到一个月,棺材没有做出来,倒做了个擦鞋的工具箱。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爱因斯坦小时候还做过小板凳,这个比小板凳复杂。然后他缠着舅妈要出去自力更生。舅妈不能分心,她目前心里只放得下肖军。她说把药带上,不要在近处摆摊,走远点儿。我敢说那段时光是舅舅最快乐的时光,他找到我,问远点儿的地方有哪些。我想起公司楼下巷子里有人擦皮鞋,于是带着他坐两站轻轨。舅舅非得要感谢我,按住我,擦我的皮鞋。每天我都会加班,为的是等舅舅擦完最后一双鞋。有天舅舅让我拍张肖军的照片给他,我进不了学校,在围墙的围栏缝隙拍了张课间跑步的照片,侧面,舅舅说随他,不当兵可惜了。
舅舅的骨灰很少,肖军捧着骨灰出来,乐队来送。我妈将擦皮鞋的家什扔进了花圈焚烧炉。舅妈赶紧对着炉子念叨几句。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是肖军毕业后,舅妈一下子无事可做,好比马拉松运动跑完后的慢走,没了目的。舅舅也似乎比同龄人老得快些,脸瘦成一溜腊肉,背佝得像焗虾。三个人像抽了筋,整天活无生气。肖军是他们的筋。肖军在上海上完大学留在了上海。舅妈开始信这信那,她不是专门信菩萨或者耶稣,对着一碗水一棵树,或者肖军的一件衬衣,也可以念叨半天。
6
肖军结婚的消息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我妈不让人告诉我,怕我受刺激。最后隐瞒不住,外婆在床上嚷要去上海,我问去干吗?她说参加军军的婚礼。我盯着老太太肃穆的脸,确定这话不是脑袋打滑的诳语,于是回家问我妈。我妈嗤一声,说还好意思问。我说,连舅舅都知道为什么不让我知道?那得去问你舅妈。不过你也不用问,军军回来还要办次酒。
肖军带着新媳妇回来了,说是十里洋场的千金。但新娘子当天下午就得回上海,没假期。小两口住在酒店。酒席就在酒店办。舅妈给所有认识的人都递了帖子,连乡下几十年没走动的远房亲戚都通知到了,电话里聊着多少钱的酒席,有哪些硬菜。我妈撇撇嘴,对我爸说扎场子不是这个扎法,又不是打人命。我爸说上海的房价贵。
当天中午,非常热闹,肖军从小到大的老师都到了场。班主任们都发了言,当然,我妈也发了言。肖军挺着西装,挽着新娘子,优雅地敬着酒,低声说着话。我有些恍然,像在参加十八世纪巴黎上流社会的聚会。我环顾四周,找不着舅舅。肖军偶尔也环顾一眼,然后他望向我,我摇摇头。酒喝到半下午,肖军送新娘子去机场,我去找舅舅。还在院门外,老远就看见舅妈跪在堂屋。走近看见她面前搁着舅舅的照片,当兵时的。舅妈没察觉我,我闪到一边,听舅妈念叨些什么。舅妈说,德贵啊,我有罪啊。我感到好笑,有罪是上帝管,舅舅不管。舅妈继续念,我包容你,承认你,军军包容你,承认你,我们全家都承认你。但他们包容你吗?承认你吗?我看见铜锁挂在铁门上。舅妈继续念,我有罪,我忏悔,今生不够,来世来凑。我感觉自己笑了一下,但却笑不起来。军军小学六年级,我怕你去打友谊赛,给你加了安定。给自己的男客下药,我毒啊,比潘金莲还毒,我有罪。我感觉胸口发堵,堵着团湿棉花。舅妈继续念叨,德贵啊,今天是最后一次,军军回上海,我就向天下人宣布,你肖德贵是我男人,肖军的亲生父亲。我憋不住哭出了声,舅妈缓缓转身来望着我,张着嘴好半天,才说,我有罪。
舅舅醒过来时已接近傍晚,看来舅妈放的剂量大。听说酒席办过了,舅舅打了自己一耳刮子。舅妈上去抱住他,倒把他吓一跳,他推开舅妈,挎上工具箱走出院门。
我们是在晚饭时接到派出所电话的。中午吃的还未消化,晚饭没心思吃。突然电话遽然响起,全家人都没反应过来,肖军已经喝高了,沉沉睡着。还是舅妈去接了,接着接着人筛糠一样抖,然后顺着柜子滑下去,瘫软在地。
后来我和肖军去派出所,查看了报警记录。舅舅没有去擦皮鞋,而是去了河边。报警人看着一个擦皮鞋的坐在岸边,有些奇怪,就多带了个眼睛,捡几块石头敲他一下。恰巧有个老女人在河边捞浮财,捡垃圾的,报警人经常看见。老女人捞着捞着人跟着河水跑了,他惊呼救人。鞋匠猛甩掉工具箱,顺着河岸跑了几十米,斜着冲进水中,扎猛子到处找。报警人赶紧报了警。
派出所的人对肖军说,你爸应该没找到那个老人,也许精力不济吧。我们捞上来时,你爸的左手死死插在裤兜里。奇了怪了。
我们来到医院太平间认尸,舅舅泡成了婴儿脸。
7
肖军回上海前来找我,让我带他去游泳。我看他不像开玩笑。想起来也是,肖军对瑞河的记忆,大体止于那个背《出师表》的下午。我妈要阻止我,我说没事儿,淹不死人。话出口感觉不对,咳了几声说,好久了我也想游游。我带他到瑞河,淹死舅舅的地方前几天还拉着警戒线,现在撤了。河水黑得发亮,大块大块移动。对岸的雾气还未散尽,山峦静卧,偶尔会有一只大鸟从水面飞过,不见倒影。这个时间还有点儿早,水凉凉的,漫过脚踝时像蚂蟥在爬。我和肖军往前走了一截,水始终没有淹过肚脐眼儿。脚下全是沙,沙子从趾缝中溜出来,又沉下来,水发浑,泛起刺鼻的气味。肖军嘀咕怎么这样子,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水还是什么,没接话。他在头里往前蹿,水哗哗响。我说要不去河中央,那边深点儿。突然肖军停住身子,望着瑞河的双眼发空,他蹲下来。我以为他冷,说要不上岸,味太大。肖军蜡黄着脸,一下将整个人埋进水里,半天没有出来。我也将头浸入水里,将眼睛虚开,我看见一个老人瘦弱的身子,衣衫单薄,微笑凝视,脖子上勒着一双手,那双眼睛疲惫却闪着亮点。他用晃荡的衣袖跟我打招呼,左手紧紧插在裤兜里,任由身子匍匐河底。我认出老人是舅舅,想对舅舅喊抽出左手,却被呛了一口水,我站起来,肖军还在水中。刚要过去拉他,他像一只蓄势已久的大鹏,冲出水面,水流披离,恍惚整条瑞河被他带离河床。他甩动身子,水珠四散,锐声喊:爸啊——
第一回,我听见肖军喊肖德贵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