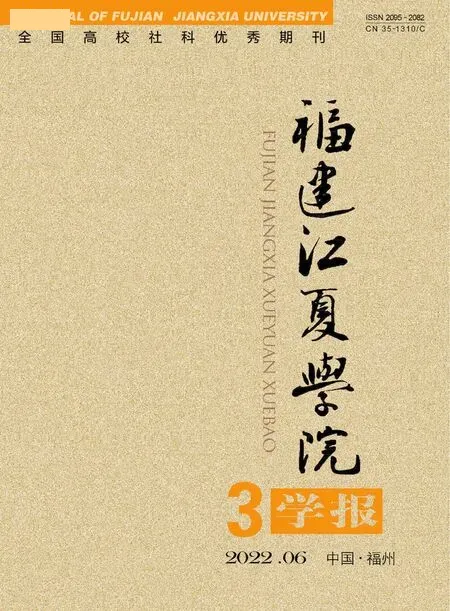余氏刊本《列女传》插图及其女性叙事探析
2022-09-09胡小梅
胡小梅
(福建江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建安余氏勤有堂本《新刊古列女传》(简称“余氏刊本《列女传》”)为现今所知最早的图文版《列女传》刊本。余氏原刊本今已不可见,仅在刘承幹编《嘉业堂善本书影》存有二叶(四幅)书影,幸有清道光年间扬州阮福小琅嬛仙馆覆刻全本(后收入“文选楼丛书”)。阮氏覆刻本,据书末《摹刊宋本列女传跋》,系“全摹宋式,丝豪(按:毫)不改”,故能“存宋本之旧,不失其真”,以致于过去“常有用旧纸刷印,冒充宋版以欺人的”[1]19。本文据日本公文书馆藏阮氏覆刻本(索书号为290-0061)探析余氏刊本插图面貌并分析其插图如何展开女性叙事。
一、插图概况
(一)插图数量
余氏刊本《列女传》全书共有8卷、124篇。其中前七卷为《列女传》,104篇,传、颂、图齐备;第八卷为《续列女传》,20篇,有传、图而无颂。以往的研究一直认为每篇有1幅插图,共有123篇、123幅插图①参见王伯敏著《中国版画通史》(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郭味蕖著《中国版画史略》(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周心慧著《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徐小蛮、王福康著《中国古代插图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等。。虽然部分藏本可能因为有缺页而不足,但经详细检视发现,“每篇(节、则)一图”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全书实有插图125幅,除卷一《齐女傅母》(见图1、图2)外,其他每篇有1幅插图。《齐女傅母》讲述了齐国公主、卫庄公夫人庄姜刚嫁到卫国时,重衣饰而轻操行,其傅母及时对她进行规劝,勉励她注意身份、修养身心,庄姜“感而自修”②参见西汉刘向编撰《列女传》卷一《齐女傅母》篇,清代阮氏覆刻余氏勤有堂刊本,日本公文书馆藏本。下文凡引用《列女传》原文均据此藏本,不另注。的故事。图1和图2的画面并不相接,一绘使者向卫庄公报告的场景(从图1左侧二名男子上方的榜题为“交好使者”判断使者报告的可能是关于聘娶庄姜的事),一绘傅母规劝庄姜之事,二者在文本中属于不同时空的两个情节。图1、图2当视为2幅插图,因此全书的插图数量应为125幅。

图1 《 齐女傅母》插图之一

图2 《齐女傅母》插图之二
(二)插图形式
此本的插图形式为上图下文,每半叶(即1个页面)的插图栏和文字栏大致相等,各占页面的1/2。所有插图的高度一样,即为版框高度的一半,但宽度不同。按照插图是否跨页,可以分为单面形式和双面合页连式2种,其中单面18幅,双面合页连式107幅。双面合页连式的插图横跨二个半叶,阮福《摹刊宋本列女传跋》称此本“旧为蝴蝶装”“册页作两翼相合对之形”,书页打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完整的插图。阮氏覆刻本改蝴蝶装为线装,二个页面相背、插图亦相背,不便于读者欣赏。双面合页连式的插图,一般占二个半叶上栏的位置,但有一部分插图(共23幅)并未占据二个半叶上栏的全部,这些插图的上栏有若干行刻的是文字(见图3)。

图3 《鲁臧孙母》图文书影
(三)插图风格
此本插图风格古雅朴素,绘刻质朴而生动。人物主要采用白描手法,有榜题用以标注人物身份。环境背景丰赡,宫殿亭台等建筑主要以阳刻凸版的方式镂刻,使画面具有明显的黑白对比。构图匀称优美,画面规整有序。由于采用方形(单面)和长方形(双面合页连式)的插图版面,以及善于运用线条的交叉、转折等,画面具有很强的纵深感。但间或存在人、物大小比例不协调的情况,如卷八《严延年母》插图中的“严延年”这一人物较围墙高出许多,比例失衡。有的插图构图颇见匠心。如卷七《孽嬖传》的《夏桀末喜》和《殷纣妲己》都有关于“酒池”这一历史典故的叙述,《殷纣妲己》另有关于“肉林”的叙述,为了不显重复,插图创作者以“酒池”作为《夏桀末喜》插图(见图4)表现的内容,“肉林”则为《殷纣妲己》的插图(见图5)表现对象。在线装的阮氏覆刻本中,“酒池”与“肉林”的插图前后相接、并排而列(见图6),当读者翻到第七卷的第二页时,“酒池”“肉林”一起赫然映入眼帘,加深了感观印象。另外,就图中人物与景物的位置和方向而言,图4右半部和图5左半部的人物遥相呼应,构成一种形式上的互文关系,别具匠心地阐释了“孽嬖”的主题。

图4 《夏桀末喜》插图

图5 《殷纣妲己》插图

图6 “酒池”“肉林”插图
二、插图与《列女传》的文本形态
《列女》图源远流长,是重要的传统绘画题材,在西汉刘向《列女传》成书之前就有“讲述古代女子善恶故事的‘女图’存在”[2]。刘向编成《列女传》之后,依传文的七个类别③即余氏刊本的前七卷内容,第八卷《续列女传》为后人续补。,绘制了配套的列女图,此事在《七略·别录》中有记载:“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3]一般认为将《列女》图绘于屏风者不是刘向本人,而是宫廷画工所为。汉代以来,各代均有《列女》图传世。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可以发现东汉、六朝时期的墓葬中有大量《列女》图的画像石、画像砖及屏风,如山东嘉祥县武梁祠就有8幅《列女传》画像[4],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屏风绘有一组16幅列女传人物故事漆画(部分仅存残片)[5]。历代画家也创作了大量的《列女》图,比较知名的有西晋卫协、东晋顾恺之及北宋李公麟等。余氏刊本《列女传》延续了历史悠久的《列女》图传统,以图为重,为每篇故事都配上插图。其卷首目录赫然宣称此本的插图是“晋大司马参军顾凯之图画”,阮氏覆刻本扉页亦题“顾虎头画列女传”。
从图像所占页面亦能看出余氏刊本对插图的重视。提及建安版上图下文式插图,论者常将此本同元代建安虞氏的“新刊全相平话五种”相提并论。但在1个页面中,“新刊全相平话五种”的图像只占1/3,此本则占1/2。图、文各占页面1/2的这种形式在宋代福建刊本《纂图互注周礼》《纂图互注礼记》《纂图互注荀子》中也使用过。但宋代福建“纂图本”的上图下文式插图数量很少,一幅插图只占一个页面的上栏。而此本插图数量众多,从不同形式插图的数量看,铺满二个页面上栏的双面合页连式插图居多(有84幅,见图4、图5),这样的插图相当于占一个完整的页面。插图数量多,所占页面比例大,刊刻者对插图的重视可见一斑。
此本的刊刻者偶尔会提醒读者注意插图。这类提醒全本共有7处,分别在卷一《邹孟轲母》、卷三《晋羊叔姬》、卷五《楚昭越姬》、卷六《齐威虞姬》和《齐钟离春》、卷七《晋献骊姬》及卷八《班婕妤》的文末。这7篇的文末都标注有“图见(同∕在)前”的字样,这在其他书籍插图本中是极少见的。这些字样同刊本的文本并无关系,刊刻者何以要在这些地方标注类似于旁白的字样、提醒读者注意插图的位置呢?这可能与《列女传》独特的文本形态有关系。《列女传》的文字文本包括传文和颂辞(《列女颂》)。一般认为,传文与《列女图》产生的时间早于《列女颂》,前引《七略·别录》载刘向与刘歆校完《列女传》之后,“画之于屏风四堵”,至于《列女颂》,有研究者认为是刘歆受西汉扬雄为赵充国作颂的启发、依《图》作《颂》而产生④关于《列女传》(传文)、《列女图》和《列女颂》的作者及创作时间先后、彼此关系问题,可参看陈丽平著《刘向〈列女传〉研究》的相关章节和张朋兵《列女〈传〉〈颂〉〈图〉关系考论》(《文学与文化》2019年第3期)。。《列女颂》包括“大序一篇,小序七章,颂一百单五章”⑤参见刘向编撰,顾凯之画图《古列女传》卷首目录“母仪传”下双行小注,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原独立为一卷,与《列女传》(传文)是分开的。至南宋嘉定七年(1214),蔡骥对其进行改编,“将颂义大序列于目录前,小序七篇散见目录中间,颂见各人传后”⑥参见刘向编撰,顾凯之画图《古列女传》卷首蔡骥《颂》,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也就是把原来独立为一个整体的《列女颂》分散开来,大序移到目录之前,7篇小序归到目录中每一类篇名之下,每个人物的颂辞放在相应的传文之后。余氏刊本的文字文本排列情况与蔡骥所述相同,只是缺了目录前的“大序”和第一卷“母仪传”中的一篇颂辞(当还有对应的传文),可见是据蔡骥改编本刊刻的,再加上插图,形成了“一传一颂一图的《列女传》文本文献形态”[6]。颂与图关系密切,汉代以来看图作颂的风气久盛不衰,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例如明末建阳雄飞馆刊本《二刻英雄谱》就使用了一图一赞(颂)的形式。刘歆依(列女)图作(列女)颂,因此历史上曾出现过图、颂结合的《列女传》文本形态,此本卷首北宋嘉祐八年(1063)王回序中曾提到当时有人见到“江南人家”所藏的《列女传》“各题其颂像侧”⑦参见刘向编撰,顾凯之画图《古列女传》卷首王回《古列女传序》,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传为顾恺之所绘的《列女仁智图》每段之后都有颂辞(见图7)。《列女传》各篇传文字数多寡不一,少者不足100字,多者近1400字;颂辞字数则相对固定,基本为四言八句,加上“颂曰”二字,共34字。此本的插图占据1~2个页面的上栏,颂辞分散到各篇传文之后,当传文字数较少时,或是传、颂、图位于同1个页面,或是传文和插图跨2个页面、而颂辞在第二个页面,无论哪种情况,颂与图都在同一页面。但当文字较多时,所需页面亦较多(最多为4个页面),就有若干纯文字的页面,位于传文之后的颂辞与插图也就不在同一个页面,为了提醒读者回看前面的插图、以便进行图、颂对照,刊刻者在颂文旁边标注了“图见(同∕在)前”的字样。简单的标注可见出刊刻者对于插图的重视,更是对依图作颂、图颂结合这一悠久传统的回应。

图7 顾恺之《列女仁智图·晋伯宗妻》(宋摹本,局部)
三、角色、空间、姿势:插图女性叙事的展开
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刘向《列女传》第一次“大规模全方位多层次而且集中地展现和描写女性群像”[7],书中主要以讲故事的方式对帝王进行道德劝诫⑧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载刘向著此书的宗旨为:“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次序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因此在每一篇中都围绕女性传主的言行叙述一个或多个故事,这些故事在余氏刊本中成为插图描摹、创作的对象。插图和文字,是插图本书籍中具有互文关系的两种不同类型文本,关于二者的关系,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讨论,不复赘述。在此要关注的是,余氏刊本《列女传》插图的男性创作主体(画工、刻工)⑨尽管明代曾有“建阳故书肆,妇人女子咸工剞劂”(见明代方日升《古今韵会举要小补》万历三十四年周士显刊本卷首李维桢撰《韵会小补再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的记载,但从现存古籍插图的画工和刻工资料看,古代书籍版画插图的画工和刻工一般为男性。是如何在这部“集中地展现和描写女性群像”书籍的插图中表现女性、展开女性叙事的。
(一)插图表现内容的选择
《列女传》各篇字数多寡不一。一般文字较少者只叙一个故事,这唯一的故事自然就成为插图表现的内容。但文字较长、所叙故事不止一个的篇章,则存在选择哪个故事进行图像化的问题。例如《邹孟轲母》,不足千字的文本叙述了孟轲母的4个故事:一是三择其舍、为孟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二是断杼教子、勉励孟子刻苦向学,三是谆谆教导、让孟子明白夫妇相处之道,四是晓以大义、解除孟子远游的后顾之忧。应该说,在文字这一“时间性媒介”⑩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一书中认为:诗(文字)摹仿的是“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适于表现“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绘画(图像)摹仿的则是“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更适于表现“在空中并列的事物”。详见莱辛著、朱光潜译:《拉奥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中,4个故事都很精彩,共同构成丰富而立体的孟母形象。但在图像这一更适合表现“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的“空间性媒介”中,由于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8],第一、第三和第四个故事因为具有明显的持续性特征,都不适于以图像尤其是单幅的插图进行表现。断杼教子则不同,这个故事叙事性很强,有确定的物体(织机、织线、剪刀)和易于摹仿的动作(“以刀断其织”),因此插图创作者选择了孟母引刀向前、准备剪断织线这样一个处于情节高潮来临之前、“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进行描绘(见图8)。《列女传》的故事情节中有很多紧张激烈的冲突,余氏刊本一般都不选择冲突的顶点即高潮,而是选择情节高潮到来之前的“顷刻” 进行绘图。如卷四《梁寡高行》插图描绘的是传主举刀准备割下自己的鼻子,卷五《盖将之妻》刻画传主盖将之妻持刀奔出准备自杀,卷五《京师节女》则是以节女丈夫的仇人持刀前来准备杀死替丈夫赴死的节女为插图表现内容,卷四《宋恭伯姬》刻绘大火烧至宋恭伯姬所住宫殿,《楚昭贞姜》刻绘大水淹至贞姜所在的渐台……这些都是表现“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其他刊本并不像余氏刊本的插图密集地表现情节高潮到来之前的“顷刻”,以《京师节女》为例,明清刊本一般不选择节女即将被杀的“顷刻”绘图,如明代金陵富春堂刊本《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插图表现的是节女被杀、仇人手持头颅的情景,题为明代仇英绘、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鲍氏知不足斋重印本,《列女传》则是以仇人抓走节女父亲以此要挟她的内容绘图,均不同于余氏刊本。

图8 《邹孟轲母》插图
图8还有值得一提之处,其左边画面绘有“书院”(此榜题与故事时代不符,依文字文本应为“学宫”)和俎豆作为插图的环境背景之一,其实是将第一个故事中孟母“复徙舍学宫之旁。其(按:指孟子)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嵌入第二个故事的图像之中,图8看起来更像是蒙学读物《三字经》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直接图像化。一般认为《三字经》成书于南宋时期,其精炼而通俗的表达很好地扩大了孟母故事的民间传播,余氏刊本《列女传》的刊刻时间为南宋或稍晚的元代,其插图的画工和刻工对《三字经》应该是熟悉的,是不是在创作时不自觉地将从小接受的《三字经》进行图像化?亦未可知。孟母断杼教子的图像相对固定,一般描绘一个女子引刀准备割断织机上的织线(或布匹)、一个孩童立于旁边。在余氏刊本之前的各类图像如此,余氏刊本之后,明清时期深受其影响的各种《列女传》刊本插图,如明代富春堂刊本、徽州黄嘉育刊本《刘向古列女传》,以及清代鲍氏知不足斋重印本《列女传》等,亦是如此,图8因此成为孟母断杼教子图像中很独特的一幅。
余氏刊本将断杼教子的故事作为《邹孟轲母》插图的表现对象,除了该故事适于图像化之外,更是以纺织这一古代“妇功”的重要内容来体现孟母的性别特征。蚕桑纺织是古代女性性别分工的主要内容之一,《列女传》中有多个篇章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邹孟轲母》外,还有卷二《晋文齐姜》和《鲁季敬姜》、卷四《楚白贞姬》和《鲁寡陶婴》、卷五《鲁秋洁妇》、卷六《齐宿瘤女》和《齐女徐吾》、卷八《陈辩女》等。孟母断杼教子的故事较早见于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被写入刘向《列女传·母仪传》之后,树立了孟母作为慈母的典型,也成为此后各种图像的常见题材。在汉代就有画像石摹刻这一题材,《中国画像石全集》卷二收有东汉晚期山东枣庄山亭区桑村镇西户口村祠堂壁画中的“孟母教子”图;两晋以后的文人绘画也常以此为创作题材;明清以来的版画、雕塑等民间图像中更是频繁出现。[9]图8以纺织突出了孟母的女性身份和慈母角色,并借由“断杼”这一即将发生的动作实现了与文字文本相似的儒家伦理教化功能。母亲是女性的主要角色之一,抚育教养子女因此也成为女性社会分工的另一重要内容,《列女传》卷一《母仪传》,对十数位女性的描写多数是以母亲教育子女(主要是儿子)的故事展开。如《弃母姜嫄》这一篇,更为读者熟知并感兴趣的当是姜嫄“履巨人迹”而有孕,并因此视其所生孩子为不详、屡次弃之而不死的故事,但余氏刊本却是选择了“及弃长,而教之种树桑麻”的内容进行绘图。正是因为作为母亲的姜嫄“好种稼穑”,并给予弃“种树桑麻”方面的教导,弃长大后才能担任稷官(农官)并号称“后稷”。可见余氏刊本对内容的取舍。其他如《启母涂山》《晋伯宗妻》《魏节乳母》等篇,余氏刊本的插图都描绘传主怀抱婴孩,虽然就艺术性而言这些插图略嫌模式化,但却是对传主母亲角色的突出与强调。
(二)插图中传主空间位置的安排
除了选择能够凸显女性特征的内容进行绘图之外,余氏刊本《列女传》的插图还通过对画面空间位置的安排进行女性叙事,具体体现在内外区隔、传主与其他人物的位置关系等方面。
首先是内外区隔。儒家传统的性别伦理观念提倡男女有别、男外女内,刘向以儒家学者身份编纂的《列女传》深深浸透着这一伦理思想,在《鲁季敬姜》中,他曾借敬姜之口提出“寝门之内,妇女治其职焉”,这一表述意味着男女的内外区隔不仅体现在职责方面,如上述纺织、抚育子女等都是女性很重要的职责,还体现在身体所处的空间位置,女性身体的空间位置主要在“寝门之内”。那么,余氏刊本的插图是如何在画面中体现这种内外区隔的?此本上图下文、多数为双面合页连式的插图方式使得插图呈横向长方形状,图中人物常按性别分置于画面左右两边,客观上产生一种类似于区隔的效果。如卷一《有虞二妃》的插图中,男性人物(舜帝、瞽叟)位于画面的右半,而女性人物(娥皇、女英、舜母)则位于左半,中间有张矮几隔开。在“旧为蝴蝶装”的余氏原刊本中,左右两边的画面同时展开在读者面前,画面中间的矮几起到区隔的作用。阮氏覆刻本改为线装,读者在阅读时首先看到的是画面右半的舜帝和瞽叟,翻过页才看到位于下一页上栏(其实为画面左半)的三位女性人物,线装的方式客观上加强了区隔的效果。再如《晋伯宗妻》的插图(见图9),画面右半绘伯宗妻怀抱孩子,属于“内”的范畴,左半所绘伯宗与毕羊交谈则属于“外”的范畴,左右分隔,内外有别。

图9 《晋伯宗妻》插图
其次是传主与他人的位置关系。图像中人物身体位置的高低代表着尊卑高下,按照传统的儒家文化观念,男女在价值定位上是男尊女卑,在图像中通常表现为男高女低。但细观余氏刊本《列女传》的插图,则会发现并非完全如此,有多幅插图表现出一般图像少见的女高男低。如卷一《周室三母》(见图10),插图画面右半绘第一代的太姜、太王夫妇和两个儿子,右半绘第二代的太任及其子文王、第三代的太姒及其子武王,从视觉效果上看,图中坐着的三位女性比站立的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等四位男性高(太王则与太姜等高)。这四位男性均蓄须、戴冠,表示他们均已成年,正常的情况应该是男性高于女性。这里女高男低的位置安排代表着女尊男卑。再如《鲁季敬姜》,图中敬姜坐在高出地面一个台阶的室内,其子文伯立于室外地面,从位置上看,同样是女高男低。类似的情况还有《楚子发母》等。余氏刊本将这些插图中的人物位置处理成女高男低、女尊男卑或是为了突出传主的母亲身份和长幼有序的人伦孝道。“女性在儒家这里……当为人妻妇生儿育女成为母亲后却受到极大的敬重与孝顺”,“很少有文化像儒家这般有如此悠久和深厚的爱母、遵母、敬母、孝母的观念以及礼俗的积淀”。[10]余氏刊本的刊刻地建阳是南宋儒学大师朱熹成长并长期生活、著述讲学、终老长眠的所在之处,刊刻者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通过对插图中人物位置高低的着意安排强调推崇母仪母范。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明清刊本《列女传》的插图中得到承续。⑪已有研究者对明代黄嘉育刊本插图中女性人物的位置高低作出分析,参见许剑桥《放大、整容、去势——观看黄嘉育刊本〈古列女传〉插图中的女性“神话”造像术》(高柏园、曹顺庆主编:《古典与现代的交会——海峡两岸社会与文化学术会议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327-349页)。

图10 《周室三母》插图
(三)人物动作姿势的设计
如果以二分法对《列女传》的人物进行简单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成“好女人”和“坏女人”二类。在文字文本的叙述中,列女孰好孰坏,清楚明白,但在图像中则有较大局限,例如明代黄嘉育刊本第七卷第一篇《夏桀末喜》的插图描绘的是一个女子乘船游于山水之间,单看插图,很难看出图绘内容与末喜有何关系,只有结合文字,才知道插图创作者想表达的是末喜纵情声色、恣意享乐,行游于酒池之中。⑫许剑桥《放大、整容、去势——观看黄嘉育刊本〈古列女传〉插图中的女性“神话”造像术》对此本有详细的分析。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插图都如此疏离于文字。在余氏刊本《列女传》中,插图创作者通过图中人物动作姿势等造型的设计,帮助读者判别图中人物归属哪一类,并借此表露创作者的价值判断。
从动作姿势看,此本插图中的人物主要有站(或立)姿与坐姿两种。经统计,有坐姿人物的插图约53幅,其中28幅图中坐姿人物为女性传主。这28幅中,有10幅很特殊,其传主都属于“孽嬖”类别,分别是卷七《夏桀末喜》《殷纣妲己》《周幽褒姒》《鲁桓文姜》《晋献骊姬》《陈女夏姬》《齐灵声姬》《赵灵吴女》和卷八的《赵飞燕姊娣》《更始韩夫人》的插图。而这10幅插图中有7幅都是描绘孽嬖即宠妾与国君同坐,或同观牛饮者醉而溺死于酒池(《夏桀末喜》,见图4),或共赏男女嬉戏于肉林(《殷纣妲己》,见图5),或戏看烽火(《周幽褒姒》),或沉溺酒中(《更始韩夫人》)……如此种种,不仅是对孽嬖及昏君荒诞奢淫的直接揭露,更是对“逾礼制”者的有力批判。虽然儒家早期的性别观念中是承认“妻与夫齐”⑬班固《白虎通义》有“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至庶人其义一也”的说法。的,但也仅限于妻,身为奴仆的妾是不具备与男性丈夫(主人)平起平坐的资格。但在余氏刊本的这7幅插图中,宠妾不仅以坐姿出现,更是以和国君(男性、主人)并肩共坐的姿态赫然出现在读者眼前。反观“孽嬖”之外的其他可以归入“好女人”类别的传主,极少被绘成和男性同坐的姿势,仅有的2幅是《卫灵夫人》和《齐威虞姬》。《卫灵夫人》图绘夫人酌酒拜贺卫灵公多得贤臣,图中卫灵公正面朝向读者坐于主位之上,夫人则背向读者、侧面朝向宫外,主次分明。《齐威虞姬》图中虞姬和齐威王分别在画面的右半和左半,内外有别。“孽嬖”类的《晋献骊姬》和《陈女夏姬》插图中的骊姬(见图11)、夏姬也呈坐姿,不过其坐姿非常独特,都是双臂架在椅子的扶手之上(与二女所处时代不符),左脚盘于椅子,这一坐姿与女性身份完全不相称,不仅未见于刊本中其他女性传主的插图中,亦未见于插图中男性人物的造型。《列女传》的文字虽未直接描述骊姬的容貌如何,但她是作为晋献公攻打骊戎的战利品被带回晋国并深受宠爱的,容貌自然非同一般;至于夏姬,刘向以“其状美好无比”来描述,并叙述她“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同样是绝佳美人。插图创作者并没有赋予这两个绝色女子婀娜多姿的画面形象,而是为她们设计了这样一个粗俗、野蛮的动作姿势,以反差极大的人物造型突出对“淫妒荧惑”“指是为非”、色美德薄、“终被祸败”(《孽嬖传》小序)者的揭露与鞭挞,与刘向“戒天子”的编纂目的是一致的。

图11 《晋献骊姬》插图
四、余论
关于余氏刊本《列女传》此本插图,尚有两个问题可作分析,在此略谈一二。
其一,此本插图题署顾恺之绘,究竟是否出自顾恺之呢?对于这个问题,清代人即持有正反两种看法。此本覆刻者阮福坚持其插图出自顾恺之,清末藏书家叶德辉则认为“其题‘顾恺之图画’亦无根据”[11]207-209。今人亦多认为此本插图非顾恺之所作。王伯敏在《中国版画通史》中将传为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与此本插图进行比较,得出“除了个别的人物造型有一点点相同之外,全是后人之风”的结论。[12]将传为顾恺之画的《列女仁智图》北宋摹本残卷⑭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存十段、二十八人,涉及《仁智传》的“楚武邓曼”“许穆夫人”“曹僖氏妻”“孙叔敖母”“晋宗伯妻”“卫灵夫人”“齐灵仲子”(不完整)、“鲁漆室女”“晋羊叔姬”“晋范氏母”(不完整)等十则内容。与此本相应的插图对比发现,除了人物位置关系和部分人物动作、姿势以外,二者大相径庭。比如人物的衣冠服饰,《列女仁智图》的人物服饰以宽衣大袖为主,衣袂飘逸,衣褶密集繁复近乎夸张,此本则要简单得多。再者此本插图有丰赡的环境背景、《列女仁智图》是传统的人物画、全无背景。所以,比较大的可能是,建安余氏在刊刻此本时,参考了传为顾恺之绘的《列女仁智图》长卷,按照其中的人物位置关系创作了《新刊古列女传》的整套插图,为了凸显插图的分量,径直署上顾恺之的大名。假托名画家作品的做法在明代的书籍插图中相当多见,若往前追溯,余氏刊本《列女传》是较早的一种。
其二,此本插图颇负盛名,是否名实相符?“绣象书籍,以宋椠《列女传》为最精……人物车马极古拙”[13]“镌刻极工”[14]“甚为精美”[1]19,备受赞誉。但细观插图发现有明显不足,包括插图大小不一、文字行款多样,榜题错讹多见等。插图或占一个页面、或占超过一个但不足二个页面、或占二个页面的上栏。下栏文字的行款参差不齐,半叶字数最少者为100字(十行、行十字),最多的者为270字(十五行、行十八字)。之所以会出现插图大小不一、文字行款多样这类与书籍“标准化”⑮美国何谷理在《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刘诗秋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三章探讨了印刷书籍的标准化问题,包括印刷字体的标准化、整体页面布局和风格的趋同等,文字格式(行款)的相对一致也是其表现之一。“标准化”有助于提高书籍生产的速度。生产相悖逆的情况,当是刊刻者为减少纸张、压缩成本所作的调整。另外,全本插图榜题错讹多达12处。如卷三《曹僖氏妻》插图榜题为“曹僖”,传主是一位曹国大夫的妻子,其丈夫姓僖名负羁,榜题误将曹当作姓、僖当作名。此榜题在《列女仁智图》北宋摹本残卷中为“曹僖负羁”,并无误,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此本插图并非出自顾恺之。诸如此类的错漏讹误,反映出余氏刊本《列女传》插图绘、刻的草率粗疏,也说明其插图的画工和刻工可能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手工艺人。他们理解能力有限,对《列女传》的故事也许并不熟悉,在绘刻插图时未能仔细推敲、理解透彻之后再进行创作,仅仅掌握故事大意就将之付诸于图,虽然插图的内容大致无误,但却在标注榜题时屡屡出错。余氏刊本《列女传》的插图质量自有其可取之处,但图中存在诸多不足,同样是客观事实,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