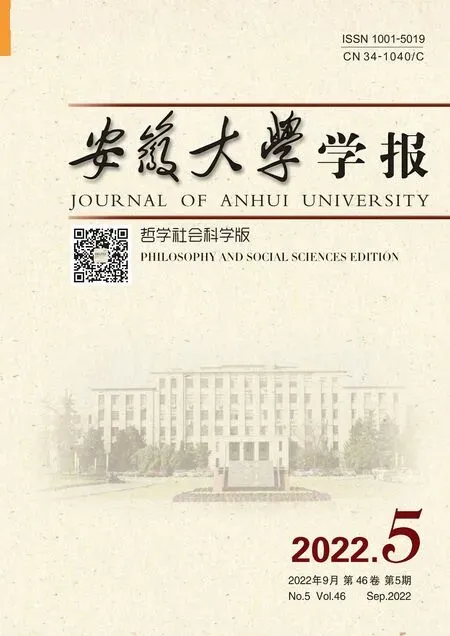明代徽州民间赋役合同的形成与流行
2022-09-02黄忠鑫
黄忠鑫
明代国家赋役财政的基础在于“户役”,即以“户”为赋役编制单位,把人户编为若干役种,设立相应役籍,如民户、军户、匠户、灶户等,并编排为里甲等联户组织,轮流应役。这种役法源于元朝的“诸色户计”并在明代得以全面推行(1)王毓铨:《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刘志伟还指出,“户役是明朝国家制度最根本的基础,明王朝的整个国家就建立在户役制或说配户当差制度之上”。参见甘阳、侯旭东主编《新雅中国史八讲》第七讲《白银与明代国家转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226页。。“户役”既有官府自上而下地按“户”点派差役,也有家户内的集体协商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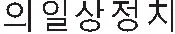
一、明初户役与合同文书之出现
关于民间协商户役之合同,目前所见最早的是元朝泰定三年(1326)祁门县十都谢智甫三兄弟等所立的两份文书(6)这两件文书原藏于安徽省博物馆,学者们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和命名方式。刘和惠命名为“析税文书”(《元代文书二种引证》,《江汉论坛》1984年第6期);张传玺定名为“分家文书”(《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68~670页);李春园认为应是“分户文书”(《社会视角的元代户籍与税役——基于徽州谢氏分户文书的初步讨论》,未刊稿);李翼恒称为“赋役合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元代徽州文书考释》,《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2页)。。一份立于十一月二十日,另一份则立于同月二十四日,并标注前份文书“不再行用”,且文末还出现了“合同”半字字样,应是得到正式签署,属于赋役合同的范畴。其内容是谢氏兄弟将一个总户头析分为民户、金户和弓手户,将相应的户籍、税钱“照数”分割,重新分配到各户,并约定以发卖杉木的价钱作为弓手户津贴。这里“户”之规模不同于一般认识的核心家庭,而是具有家族色彩。但该合同没能反映出此前的承役情况,只是一个片段,却表明在明代以前民间已对户役事务自行协商应对方案。至于家户协商的文本形式缘何采用合同而不是其他契约类型,以至于被前人误认为是分家书,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明前期对元朝的赋役户籍制度有所承袭,但也重新登记了人口,户帖、黄册的相继推行,说明纳赋应役的单元得以重新确立,作为赋役单元的“户”之内涵再次回归到家庭。此时,民间文书中关于户役事务协商亦留下少许零星记录。徽州府祁门县北乡六都善和里(今六都村)程氏家族的《窦山公家议》是一份宗族管理手册(7)关于祁门县善和程氏家族的研究,主要有:周绍泉《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族产研究》,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编:《谱牒学研究》第2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刘淼《清代徽州的“会”与“会祭”——以祁门善和里程氏为中心》,《江淮论坛》1995年第4期;颜军《明清时期徽州族产经济初探——以祁门善和程氏为例》,《明史研究》第5辑,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61~67页;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第二章《徽州社会变迁个案剖析:祁门六都的社会变迁》,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44页;卞利《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沈昕《明清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康健《祁门善和程氏承海派考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详细记录了该家族应对军户之役的情形以及协商文本形式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了解户役合同的形成过程。
善和程氏发迹于元末明初的程弥寿(字德坚,号仁山)。他曾辅佐朱元璋,授枢密院都事,镇守浮梁景德镇(8)《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善和程氏始迁谱图》,周绍泉、赵亚光:《窦山公家议校注》,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239页。。仁山公生有三子,长子程佐被祁门县佥为吏役。洪武二十年(1387),“时法网严密,犯者连坐。适有他处闲吏抵法,乃概将同时闲吏尽发充军”(9)《窦山公家议》卷8《东西军业议》,周绍泉、赵亚光:《窦山公家议校注》,第127页。,程佐被发配到辽东卫所,此为善和程氏列入军籍之缘由。程佐充军不久便病故,洪武二十二年勾取户丁补充,当时次子程仪和三子程仕也已经“身故”,只得以次孙程庭春前去充役。至永乐三年(1405),庭春也病故。
面对繁重的军役,程弥寿在晚年连续订立四份批文,收入《窦山公家议》时都被命名为“高祖仁山公遗嘱军役文书”(10)周绍泉、赵亚光:《窦山公家议校注》,第136~137页。。第一份是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元年,1399)六月初十日,主要指出两点:其一,军役是“众家户役”。除了三子程仕已出继别户当差外,程佐、程仪两支必须“轮流前去军前补充军役”。“众家”说明这里的“户”已经类似于前述元代合同中的情形,是一个大家庭的规模。其二,对于承担军役者,应当给予盘缠、军装等补贴。程弥寿将家户中尚未分家之部分田亩,“批扒付当军分内收租,略办盘缠,送至辽东军前,付应役之人支用。众家或亲人去,或雇人去,共出工雇路费,务要作急赍送”。第二份文书在洪武三十三年(即建文二年,1400)十一月十八日订立,同样以祖父的名义批出,将除了军装田之外的田地“日后并行均分”。十一月二十五日又立一件新文书,似乎是专门交给三孙程新春(即窦山公)的,其文曰:“有孙还春、新春,我百年之后,二孙务要和义,不许争论。应有事务,长孙还春毋得恃尊凌卑,递相争论。如违,仰新春将此文告官,准不孝论。”最后一份文书是在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所立,几乎将前述文书的内容重复了一遍,更像是前份文书的正式版,文末同样提及“仰新春将此文告官”,同时也强调“子孙并依此文为准”。
至于为何反复要求长孙不得恃尊凌卑,第四份批文提到一个关键细节:“因洪武二十二年,蒙军前文书到县,取户内人丁补役。彼时长孙还春身有病患,不能前去充补军役,德坚就令次孙庭春前去补役。”军役本由长子程佐一支(其有二子庭春、新春)充当,而程还春虽是次子程仪之子,出生却早于庭春、新春,是这个不能分家的军户家庭之长孙。前述文书语境中,应由长孙还春首先应役,方符合共同户役的本意。但可以想见,还春虽然宣称患病无法服役,而更可能的情况是,他并不愿意承担程佐家庭的军役,遂以长孙之身份表现出“恃尊凌卑”之态。权宜之下,程佐长子庭春先赴辽东补役。而程弥寿也希望给予一定保障,不仅将田产拨出作为军装田,还专门授予程新春可以告官之文字凭据。可见,子孙存在矛盾时,家长通过立批文的形式予以协调,达到了户内按照一定规则应役、降低赋役风险之目的。
尽管第二份文书自称“今立合同文书贰纸,与各孙照证”,但文末署名是“祖父程德坚批”,仍属批文。因此,这四份文书均以“批”的形式订立。徽州文书中的“批契”,主要是亲族内财产转移的文书类型,通常是长辈批产给晚辈,体现立批人的个人意志,采取的是单契形式(11)阿风:《明代批契的法律意义》,《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程弥寿的文书大体符合这样的判断,但第二份批文却是一式两份的合同,主要是分与两位孙子作为凭证,同样采取了批契之口吻。所以,这批文书无论是作为批文,抑或被后人视作“遗嘱”收入《窦山公家议》,都没有经过家庭的商议(此时年龄最小的孙子程新春也已经二十岁出头),而由仁山公一人确定户役的应对方式。
随着仁山公和远在辽东的程庭春相继病故,业已成年的还春和新春需要主持户役运行。他们签订了一份“窦山公同兄还春公申明祖父仁山公遗嘱轮流充补军役合同”(12)《窦山公家议》卷8《东西军业议》,周绍泉、赵亚光:《窦山公家议校注》,第137~138页。,将“遗嘱”以合同形式表达出来,并添加了新的内容:
六都程还春,有伯程佐,与父程仪同户,蒙本县点伯充吏。至洪武二十年间,取闲吏赴京,转发辽东充军,病故。后至洪武二十二年间,勾取户丁补役,彼时将弟庭春起送前去应役。至永乐三年,蒙本卫文书到县,称说病故,勾取户丁补役。今同众谪议,将祖父存日乞养到本都凌寄保在户为义子,均出盘缠支用,起送前去补役。一次系伯佐分内庭春前去补役,二次同众将寄保前去补役,三次系轮该程仪分内前去补役,四次又轮该程佐分内前去补役,所是累次盘缠,并系二分均出。在后二分照前轮当。五次又轮该程仪分,六次又轮该程佐分,七次又轮该程仪分,八次又轮该程佐分,九次又轮该程仪分,十次又轮该程佐分。在后各分子孙,照依此文轮流充当。自立合同文书之后,二分各无言说。如违,将此文赴官陈告,仍依此文为准。今恐无凭,立此合同文书为用。
永乐三年三月初三日程还春书
见立文书人程友信 程敬宗 程潮宗 程丕烈
合同与批文的差别在于,批文中有立批人的自我陈述“今已年老,心思百年之后,诚恐不行依时赍送盘缠”之语,而合同主要建立在“同众谪议”的基础上。从程氏应役文书的形成过程来看,明初以家庭为“户”的背景下,家长可直接决定后辈中的应役人选,批文体现了家长的意愿。只有在家长权威减弱的情形下,合同的形式才被采纳,成为体现户内各家庭平等订约、共同应役的文本依据。上揭合同复述了程弥寿批文关于程仪、程佐两房轮流补役顺序和共同摊派盘缠费用等内容,体现的是上轮不愿应役的程还春对共同应役之保证。签署也仅有还春书写,未见共同参与的程新春之画押,尚不具有合同的完整样式。众人协商的轮役顺序基本上还是遵照仁山公确立的规则,呈现出主导者“首唱”和众人“唱和”之色彩(13)日本学者寺田浩明认为乡村社会围绕合约形成的集团、组织“并不是事前就具有共识的人们经过对等的讨论就能达成的结果,而是某个主体的首唱和众人对其唱和的过程”。参见氏著《明清时期法秩序中“约”的性质》,载《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王亚新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符合民间合约的内在特征。所以,该文书显示了从批文到合同的过渡形态,也彰显出家户订约的基本目的是确定轮充顺序、人选及其应役津贴。
虽然众人协商合约共役,但在以后的程氏家族规约中,仅强调由此演化出来的东、西二房不得将共有田产分析变卖。军装田的管理几乎成为唯一重视的内容,而不在意由何房充役(14)《窦山公家议》卷8《东西军业议》,周绍泉、赵亚光:《窦山公家议校注》,第127页、135页。。如合同所载,永乐三年时,程氏兄弟并没亲身应役,而是在“同众谪议”后委派“义男”代为充任。此后,军役似乎不再困扰程氏家族,而窦山公等人转而经营田地垦殖、科举考试,生计面貌焕然一新(15)此案例也印证了于志嘉的判断,“从世系图可以知道,明初一名军役在有明一代能衍生出多少军籍子孙,而实际赴卫执行军役的又有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军役对军户所造成的实际负担,不论就在家族整体赋役中所占的比重,或就其对所有家族成员羁绊程度而言,都较明初时大大的减轻。若族中有军资田专供军费,‘军籍’对军户成员的影响将更形降低”。参见氏著《再论族谱中所见的明代军户——几个个案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3分,1993年。。那么,协商订约的意义还在于改变了亲身远赴卫所的方式,对家户摆脱军役负担、发展壮大有深远影响。
另外,善和程氏属于谪发充军之例。对于“三户垛一”为代表的垛集征兵,从一开始就存在正户、贴户之别,不同姓氏人群的组合,以及互帮应役的方式。正、贴户对于轮充军役的先后次序和帮贴费用,应该存在某些协议(16)于志嘉:《论明代垛集军户的军役更代》,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5页。。垛集法下的军户,有强烈的合作应役之需求,极有可能在确立之初即已订立合同文约,但目前尚未得见,故不做讨论。
二、家户扩大与合同文书的流行
民间社会在应对户役的过程中,有诸多私自协议,乃至舞弊手段,如民户可以通过分家析户的办法降低户等,整体规避赋役负担,采取分家文书的形式即可;或串通胥吏“飞洒诡寄”“花分子户”,将自身变为下户,主要是不成文的约定。由于不得分家的制度限定,军、匠户家庭可以迅速膨胀为人口较多的家族与应役共同体,较之民户更容易促成户役合同的出现。纵观明代,徽州人口有较为显著的增长,家户规模亦呈扩大之势。从明前期到后期,各县人口大体呈现出增加趋势。例如,休宁在1502—1602的百年间,从200个里增加到216个;歙县从弘治年间的228个里,到万历三十年(1602)增加为282个(17)[韩]权仁溶:《明代徽州里的编制与增减》,《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里数的增加,与人口数量增长有直接关联,承担赋役的家户规模也大为扩充,推动了协商的频繁和合同文书的流行。以下利用三件弘治、嘉靖时期的民户户役合同,显示家户规模扩大后的赋役协商情况。
民间社会形成通过土地转让和帮贴等策略,应对人口迁移与里甲赋役的矛盾。弘治十六年(1503)十月祁门县三四都凌友宗的拨田供解税粮文约,记载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家族内部对户役私相交换之协议:
三四都凌友宗,今因家中屋宇狭窄,人众难以住歇,前往本府婺源县迁居。今本家系应门户,官差捕户,浩大繁多,兄侄不从。自情愿将承祖开垦得荒田一备,坐落本都七保土名梅树坞坑,所有亩步四至照本保经理为始。其田与本都王迩安、黄从善、凌明德、宗富等相共,内友宗该得分籍,尽数约内拨与胜宗侄文敬等名下,前去耕种收租管业,供解门户差役税粮等项。日后友宗即不可妄生异志,私卖他人,亦不许胜宗等子侄设计变卖。如甲首差费户门等项,租谷供解,如使用不敷,友宗自行均贴,亦不许胜宗等子侄越外设计科友宗财物。友宗子孙倘有回宗,听照管业,同管门户。自今立文之后,各无悔违。如悔者,听自守文之人陈理,甘罚白银五钱公用,仍依此文为准。今恐人心无凭,立此文为照。
再批:今有住基前后竹山并山地,本家与十二都胡安五等相共,友宗该得分籍,亦拨与胜宗同侄文敬等交租管业。又,小塘坞、方七坞、南山坞、叶家源,共业坟山四号,尽行与胜宗、文敬管顾,日后过生,听自安葬,不许阻当,亦不许变卖,如违,以准不孝论之罚。又,有标祀众田租塘,听自仝众共耕收租管业标祀,日后友宗子孙亦无争竞变卖,倘有回宗,前项一并照旧管业无词。立此文文约为照。
弘治十六年十月初七日 立此文约人凌友宗,中见人凌敬达、敬顺、敬学,依口代书人廖克明(18)《嘉庆祁门凌氏誊契簿》,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11,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80~481页。
因为“家中屋宇狭窄,人众难以住歇”,凌友宗一家决意迁居邻县婺源。这一举动可视作有计划的移民,显然要带走一众人丁。以“画地为牢”方式控制人户的里甲制度下,人口变动对户役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留在当地的兄侄反对凌友宗迁移。为得到谅解,他将多处田山、坟山转让给兄长凌胜宗及其子凌文敬。至于本户的“甲首差费”等项,如果租谷供应不足,凌友宗还承诺“自行均贴”。因此,凌胜宗父子继续承担户役,并对迁户的土地产业合法占有;凌友宗则放弃了所有土地,迁居他乡。由此人口流动与土地转让在家族内部达成平衡,也保证了户役运行。
为保证户役的持续运行,家族对承役人选的继承协商也频见于合同之中。利用万历休宁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的研究表明,异姓承继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包括义父在内的直系亲属继承不到一半。如此便可以采用旁系亲属的承继策略应对前户主死亡这样的突发事件,从而有余地地选出适龄新户主(19)周绍泉、落合惠美子、侯杨方:《明代黄册底籍中的人口与家庭——以万历徽州黄册底籍为中心》,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55~256页。。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月祁门十西都李、汪二姓家族所订立的合同亦显示异姓承继与户役维持有着复杂的关联:
拾西都李兴户原有户丁李四保,于上年间出继同都汪周付为婿,以为养老,原立摘继文书。今因李四保生子云寄,又摘李兴户丁李法。本年大造,是李兴户内人朦胧,又将云寄名目填注李兴首状内。四保岳母细囝讦告本县,蒙批里老查处,李兴、四保不愿繁官,遵奉县爷教录,凭中立文,云寄仍承汪周付户籍奉祀继产当差,李法仍承李兴户役,各自管办。所有李兴将云寄名目收入首状,李兴自行改正,云寄仍在汪户当差。自立合同之后,二家各毋悔异,如违,听自呈官治理无词,仍依此文为始。今恐无凭,立此合同文书为照。
嘉靖四十一年十月初八日立合同人户丁李长互(押),同立文人李夏(押)、李四保(押)、汪三春(押),里长谢锯(押)、谢公春(押),代书中见人李满(押)(20)《嘉靖四十一年祁门李长互等确定李云寄等承继合同》,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2,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20页。
如合同所言,李兴户下男丁较多,原有一个名为“李四保”的户丁,在此前过继(“摘继”)到同都汪周付户下为婿,“以为养老”,通过异姓承继维持汪姓的户役。但李四保既有亲生儿子李云寄,又将李法过继到自己名下。在新一轮黄册造册登记时,“云寄名目填注李兴首状内”,造成“李兴户内人朦胧”。因为李云寄本该在汪周付户下承役登记,如果又回到李兴户下,则汪姓户役又将后继无人了。而李四保父子则有可能利用黄册登记的漏洞,同时继承两户的财产。故而李四保的岳母细囝报官。最终,李氏方面自认理屈,“不愿繁官”,通过里老查处和中人立约(21)合同签订者中,“里长”有谢锯、谢公春两人。但十西都仅编有一里,应该只有一位里长,因此笔者判断谢公春可能是老人。,从而恢复了里甲黄册秩序,李云寄仍在汪周付户当差,李法则继续在李兴户下登记(22)此外,家户承役合同中还有故意牵扯他人的行径,引发纠纷,重新订立合同。如,万历十年十二月祁门县十西都谢权合同便称:“西都谢权,原系十甲下甲首文明户丁,因谢用义承顶三甲谢汝敬户下甲首黄保户,合同内着权名目,权不愿顶,托凭亲族胡才、谢大生重立合同,权仍在文明户内供差,是侄谢用义顶黄保户差役,两不相累。前合文内顶户事情,与权无干。”(《顺治谢氏誊契簿》,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书号:000123)崇祯十年十一月休宁二十六都三图六甲里役合同也载明:“廿六都三图六甲里长巴正有,轮充现年里役。因家贫,告扳七甲甲首亲人朱贞,蒙署县事张大爷着令朋充,因朱贞只身不愿承当,今凭十排公议,果实不能充当,仍议巴正有充当前役,催办钱粮等项完官,并不干涉朱贞之事。其至册年审图,照原巴正有承当,并不再扳生情。如若生情再扳,以凭排年呈明甘罪。”(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4《顺治休宁朱氏〈祖遗契录〉》,第296~297页)。
嘉靖四十五年七月,祁门县查湾村(一名龙源)汪于祚同弟汪于祜、汪于衽和侄子汪必晟订立合同,希望通过分家,“各便解纳”,改变因“户役重叠,家事纷纭”造成“难累一人支持”的困局。他们托凭亲族胡时、饶学礼、汪璨等人,“将嘉靖三十一年自父蛟潭公故后起,至四十五年本月止,于内有因户役支费等项揭借家外并众己银两,逐一清算明白”。除了保留一定规模的公产外,“其余本都一保、二保、三保、四保、五保并十三都四保、五保、八保仍存田地、山塘、苗木、庄基、铺店,俱作四股均分,并无异言,所有税粮各扒供解”(23)《嘉靖四十五年汪于祚户分业合同》,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2,第385页。。在人口、土地产业繁多的情况下,家族内也没有一位有力的管理者,只能将户分小,降低各家应对户役的风险。但分家之后的四股,应该是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大家庭。
上述三件合同所呈现的例子都以户役为中心,皆提到家户内已是人口众多(“人众难以住歇”、有足够男丁过继承嗣等)。这些“户”不再是明初以家庭为应役单元之情形,相当于《窦山公家议》中未分家军户之情势,家族形态愈发显著。“户”规模扩大,可降低应役风险,也就需要集体协商,保证户役的运转。家户内协商的内容,主要围绕确定应役人、以土地为中心补偿分摊策略两个方面展开。而龙源汪氏的案例则显示,“户”的规模增大并不都是有利条件,在缺乏家户首领的情况下,将“户”的规模适当减小也可以保证户役的应对。
明中后期,徽州民间赋役合同的若干原则性规定还上升为族规家法,与“宗族乡约化”的进程大体同步。常建华发现范氏祠规等休宁地方家族的规约都有“赋役当供”条目,具体内容一致,是在宣讲圣谕影响下制定的,当有共同来源。他推测“母本大约产生于嘉靖万历之际,有可能是休宁县地方官或著名士大夫制定的,然后由地方宗族各自在具体内容上斟酌损益,加以推行”(24)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3~314页。徐彬亦指出,嘉万时期徽州族谱新出现的内容之一是家法族规(《明清乡村绅权建构与社会认同研究——以徽州士绅修谱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92页)。嘉万之际章潢所著《图书编》卷92《圣训释目》中,“毋作非为”条下也有“毋拖欠税粮”的内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97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88~789页)。。祁门县武溪陈族在天顺元年(1457)制定“家谱定规”,提到“吾门粮差,各有定规”,说明该家族早已订有户役合同。“定规”明确了若干规约,其中有族长“提督”族内“违误拖欠”之事;而“凡秋收催趱,预先完之”的族人,便可称为“保家之士”(25)《明天顺祁门县武溪陈氏宗族家谱定规》,卞利编著:《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641页。。可见,这些内容是在官府赋役要求和民间户役合同基础上提取若干规定,并发展为族规家法中常见的“赋役当供”“早完国课”等条目。家族势力认同“早完国课”之义务,在里甲户役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绩溪城北周氏家族在万历戊戌年(二十六年,1598)将“条编事例”写入宗训:“今之条编事例,依期完纳,免累身家,乃为良民也。吾族子孙,或同甲朋户,秉公均派,则上不紊官府,下不贻累一人,方为尚义人家也。勉之,勉之。”(26)《周氏宗规序》,卞利编著:《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第387页。此条“输赋税”的训约,既有当时族谱家规流行的“赋役当供”“早完国课”条目之表述方式,又结合了新颁的“条编事例”,其背后当有具体的合约条款作为支撑。这也折射出一条鞭法改革后钱粮催征愈加严厉之社会环境。如何在新的赋役制度下有效地规避应役风险,正是徽州民间社会颇为重视的问题。
三、洪武九年里甲合同辨伪
在家户之上,还有里甲为主要代表的编户组织。既然家户规模扩大,需要订立合同确定赋役责任,那么里甲组织是否也有集体订约?笔者发现一份洪武九年《一图津贴二图约迎接办公合墨(禀案批附)》,收在婺源县清华东园胡氏族谱所载的诉讼案卷之中(27)《清华东园胡氏勋贤总谱》卷30《杂录》,1916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全文移录如下:
立议墨人胡汝明、吴天五、胡国珍、戴有信、姚文祥等,今为卜居清华,文风彩丽,市省通衢,往来关津,靡不有济。余辈忝在名区,英贤俊拔,襄成乐义。所虑民图周阔,而人烟稠密,散居僻处。是我辈爰集本图各姓数人,建居街市,规立一、二、三图。而一图有隐居东园者,亦有居于大坞者,并居沱口等处,人烟涣散,难以枚举,且有官府往来,办公不及。忝在雅谊,绵绵相好。将一图地方五人一并竭诚遵领,其地方街下以上至姚家巷及大坞、金家园、高奢、双河等处一并所贴二图举领资费纹银廿二两正,其银是身二图五人收领,以为生息,防备日后办公之用。倘后官府往来迎接一切私差外费,不得波累一图。如有,是身五人硬当,决无翻悔。自议之后,二图永不得生情异说,恐后无凭,立此议墨一样二张,各执一张,永远存照。
议墨一样二张,各执一张,永远存照。 系两幅歧缝字,本图得右幅
洪武九年二月十二日立议墨人 胡汝明 吴天五 胡国珍 戴有信 姚文祥
胡尚斌 胡尚文 江元勋 江依槐 汪能鹄
书见 汪世忠
清华是婺源县的大型聚落,隶属十八都。明代在该都之下立有五里,而清华即占三里。但该合同存在诸多违背事实之处。
首先,洪武三年小黄册之法“每百家画为一图”,有里长和甲首轮役之建置(28)《永乐大典》卷2277《湖州府三·田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6~892页。。直到洪武十四年正式推行里甲制度后,每个图(里)中应有110户,每年有里长1人和甲首10人应役。通过“不尽畸零”的协调手段,里甲编排兼顾村落空间与人户数量,是就近村落的人户组合。但在洪武九年时,徽州是否存在小黄册及相应基层组织,限于史料匮乏,未有定论,合同所载的里(图)甲组织与小黄册之法和里甲制相去甚远:同在一“图”之下的各姓散居多处,亦不似初编成的里甲形态;作为两个图的协议,仅有10人参与。这些内容都脱离了明初基层赋役组织编制的实际。
其次,里甲正役的主要职能是“催征钱粮,勾摄公事”,且明初正役事务是比较简单的。明中期以后大小衙门和官吏逐渐将人力物力取办于里甲(29)刘志伟:《关于明初徭役制度的两点商榷》,《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遂成里甲的沉重负担。合同所谓“官府往来迎接一切私差外费”这样的“支应”事项,并不是明初里甲的任务。
再次,田赋折银的最早记载在洪武九年四月,但只是临时措施,所折物品除银子外还有钱钞(30)《明太祖实录》卷105,洪武九年四月己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1962年,第1756页。明前期徽州契约文书中对白银的记载,多属于以银议价,以宝钞、谷物支付的情况。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洪武八年则颁行“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之令(31)《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第1670页。。这份合同恰好介于这两个时点之间,却宣称以“纹银”作为差役交易的货币,亦异于常理。宣德、正统以后,随着金花银改革的推行,才有“纹银”之名,亦可证明该合同细节之伪。
最后,合同开头过于铺陈渲染之表述,也与一般的赋役合同之语句和格式不符。
再考察这份合同的流传。据族谱所附说明文字信息来看,该合同是清代才被胡氏家族所重视,“此合同原存本图胡学济家内。乾隆三十一年,图内用银十两付贴胡学济,将议墨交众。又用办东道银七钱七分”。原来包议墨纸内还附一纸:“此合同因高儿年幼,仅交十龄,与二图胡宗显之子同窗,将此议墨一张、寨山文契一道并大坞社坞口升公乡贤坟图一张窃出,与窗友存训嬉戏,易换鸟雏。后查出,大究理论,凭亲劝谕,将本家已租南市八月白三秤赎回,幸甚。后日子孙,视如珍宝,宜珍藏之,不可轻入匪人。”此合同在清代以前的流传并没有什么踪迹线索。
之所以需要全图集资购买,并被家族珍藏、抄入族谱,正是因为此合同在清初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华胡氏对此有逐条的记录,并注明“其底细详十排老簿”。尽管疑点重重,此合同在地方社会的实际效用却是不容置疑的。清初徭役征派也认可前朝的民间规约,一图得以避免重负。在雍正朝保长报充时,本着按照图甲的原则,一图又成功免除保甲之役。此后,二图企图勒索保正经费,又因为此合同的规条约定,官府认可其自行商议处置。在这几次纠纷中,二图是否质疑合同真实性?纠纷的解决机制如何?由于“十排老簿”未能得见,更多的细节无法考察,仅能知晓的结果是官府对此合同颇为认可,并多次保障一图的赋役利益。
揆诸事实,明初里甲制度的运行以编排家户、轮流承役为主,皆以黄册记载为准。粮长、里长作为法定的官府代理人,兼具地方势力背景,直接承担大宗赋役。因此,团体赋役负担体系与有力之户承役的直接性,是明初赋役制度的重要特点。即便《大诰续编》有“议让纳粮”的条目,却是比较少见的用词,仅限于解运环节中的民众评选送纳税粮代表(32)[日]岩井茂树:《赋役负担团体的里甲与村》,[日]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周绍泉、栾成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68页、170~171页。。
基层赋役运作中,粮、里长手握大权,佥点家户、征收赋税、摊派徭役、制定轮役顺序等,均由其全权负责,具有“二次派差”的意味,也相当于家户中主持户役的家长。但是,他们对于集体赋役事务的协商,必须征得官府的同意以获得权威和约束力,表现为调整方案的呈报。例如,宣德九年(1434)常熟县里老们联名呈状,提出各里按照统一额度预征米粮,支办军需物料的方案(33)况钟:《况太守集》卷9《兴革利弊奏·请建立义役仓奏》,《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66页。。物料派征面向全县530个里,具有不确定性。里长们协商的应对方案,以每甲出米50石作为办纳物料的基金,带有民间协商分担赋役负担的合约色彩。因此,这是在粮里阶层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围绕物料措办的核算体系和册籍(34)申斌:《赋役全书的形成——明清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预算基础》,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36页。,反映的是“民征民解”阶段粮、里长们向官府提交赋役调整方案并征得同意,不同于此后的“官征官解”“自封投柜”阶段各色中间代理人(里长户、册书等)自行签订的合同文约,无需官府批准。还有学者指出,这条史料是宋元义役在明代恢复的起点,但官府的最终推广实施也与里老的设计有很大差别(35)李园:《从义役看明代江南重役地区的应役实态——以苏州府模式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4期。。而宋元义役的民间结合方式是依靠个别核心人物,难于长期维持,反而强化了官府的控制(36)[日]伊藤正彦:《宋元鄉村社會史論——明初里甲体制の形成過程》,东京:汲古书院,2010年,第97页。。置于义役的演变脉络来看,粮里长协议的自主性依旧很低。所以在明初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下,里与里之间订立合同,私相授受,转移徭役负担是无法实现的。
综合以上分析,尽管这份所谓洪武九年合同在清初成功地成为地方家族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被族谱收录并流传后世,但无论从里甲组织和白银使用等细节推断,还是结合明初的制度背景,该文书当属明清之际的伪造品,不能视作明初赋役合同。
四、里甲组织的赋役合同
明初里甲赋役环境具有“事简里均”之特征。所谓“事简”,是指里甲负担的基本任务(“里甲正役”)比较简单,仅“催办钱粮”和“勾摄公事”两方面(37)[日]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付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8页。。梁方仲认为,“催征本里的钱粮,及拘传本里本县的民事罪犯和案件,这就是明初里甲的两大基本任务”(38)梁方仲:《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梁方仲文集·明代赋役制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468页。。而“里均”表现在政府开支不太大,里甲编制和人户财产的登记比较认真,赋役科派比较均平,各里负担也较均平,十甲轮年的方式可以行得通。不过,随着各处衙门纷纷索取人财物力的支应,里甲的负担超出了前述两大力役范围,引发了均平法等改革。在里甲组织层面,商讨如何应对不时需索也愈加频繁,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惯例。
里甲勾摄公事包括清理军匠(39)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2页。,但不属于明初的里甲之责。正统以后,新的清军系统确立后,粮里、长解等基层人员实际担当勾军、解军的工作,目的是取代卫所派出的勾军官旗(40)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71页。。其中,长距离解送军士的“解军”之役被视作“重差”,或在里甲组织中较早形成了相应的规例。万历十二年八月,休宁九都一图十排年所立的解军合同就声称“先年立有合同,管解本图军伍”(41)《康熙陈氏置产簿》,清代抄本,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簿册文书,书号:000132。。次年九月,同县五都四图里排的轮流解军合同则称,由于甲首沈润之在浙江嘉兴府私自贩盐,“犯问充军,行牌前来本县,关提排年,到彼管解”,但“本图原无军、匠,未有规例,无人认肯”,故而十排年会集商议,“遵照别都图定例”确定了解军的基本程序和津贴标准(42)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散件文书,书号000059。。两份合同约定的原则大体相似,包括每次解军都须由“两甲管解”,其余八甲共同津贴;按照路程距离津贴路费等,而轮充顺序和津贴标准则是根据各图甲实际情况而定。因此,里甲组织应对解军任务的方式,便体现在合同的签订和相互影响上。
明代后期,临时增派的税收名目接踵而至,如矿税、辽饷等。里甲组织往往以土地税粮为基准摊派并订约。万历二十九年五月休宁十二都一图分派矿税合同称:
十二都一图十甲里排朱仲堡、汪文新、汪文谏、何玘、朱仲坦、邵元勋、邵钟相、吴万、邵元、朱尚德等,为谦议纳矿税、公举便民事。奉本府太爷沈行掌县事,回太爷明示,里分三等,身等祁、黟比邻,地瘠民贫,耕种营生,少涉商贾。所有矿税银两,行派六县,本里敢梗化坐视不行,输纳又无殷实可报,切思本图株守田产,今十排从公确议,将本图矿税俱照本图粮数多寡分派输纳,众轻易举,苦乐均受。倘矿税不免,可为久规,庶毋偏累之患。册后粮有出入,俱照本图实在粮数缴纳无辞。十甲中如有抗拒不遵成议者,十排公同具呈,开[闻]官究治。今恐人心无凭,立此合同一样十张,各执一张,永远存照。
万历二十九年五月 日立合同里排 朱仲堡、汪文新、汪文谏、何玘、朱仲坦、邵元勋、邵钟相、吴万、邵元、朱尚德(43)《明万历汪氏合同簿》,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书号:000027。
根据该图的协议,新增的矿税名目,依据各户实在钱粮多寡进行摊派。现存的万历三十年税票载,休宁县五都四图需上纳矿税银共计九两八钱六分六厘六毫六丝○忽四微(44)《明万历三十年七月初三休宁县矿税票》,周向华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崇祯五年六月许成儒寄税许六户合同亦称,许成儒新置买的田产一亩六分七厘,计粮八升九合三勺四抄五撮,推入本族“许六德富名下供解”,“所有递年编粮、辽饷,照依官则由票并加耗上官,议定递年清明交付本管许世兴上纳,不致迟误”(45)《崇祯五年许德富等供解田税合同》,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4,第321页。。同样是依据钱粮比例摊派辽饷和条编。
里长还不时替官府购置米谷,显然就是临时差事。《应星日记》就有万历四十五年和崇祯八年九月绩溪县衙要求“大户”领银代买官谷的记录(46)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日记的整理与研究》下编《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至清顺治九年(1652年)曹应星日记》,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69页、172页。。早在万历十九年三月,休宁县十四都十图里排的合同就有这样的记录:“今奉本县祝爷发银与现年买谷备济,原例铺户,今差里长,犹恐苦乐不均。”原先由铺户承担的差役,改由里甲承担。该图十甲共同商议,由每位排年出银三钱,交给现年里长作为购买米谷之津贴,“但遇后差,照此旧规津贴,毋得推延拗众”(47)《明万历十九年三月休宁县十四都十图洪法、洪伯善等议立排年里长合同》,卞利编著:《徽州民间规约文献精编·村规民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223页。。可知此后官府将差派对象从铺户转向里甲,《应星日记》所言“大户”也应主要指里长户。
除了官府不时需索之加增外,里甲组织也针对地方管理事务订立一些私约。管见所及,徽州文书群中现存最早的里甲合同是弘治四年订立的。其文曰:
拾西都排年里甲李本宏等,承奉上司明文,为清理田山事。今蒙本府委官同知大人甘,案临催并解切。缘图下各户,田土坐落各处,都保星散,一时难以查考。只得虚提字号、条段、亩步、四至,朦胧选官造册,答应回申。中间字号四至多有差错,或语报他人字号四至者有之,或捏故冒占愚懦小民者有之,或开报未尽者有之。思得此册,实为民患。众议写立合同,各收为照。日后排年里甲人等各户事产,只照青册经理契字买业开耕为准,不以此册为拘。如有刁诈狡猾之徒,指以此册为由,颠倒是非,冒心违文,设词争竞者,听受害人赍此告理,追罚白银五十两公用,仍依此文为始。(48)《明弘治四年(一四九一年)祁门县李本宏等排年里甲合同》,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18页。按,笔者对句读有所改动。
祁门县十西都的里甲排年奉命清理田山、整理册籍,当属临时任务。但是,都保田土分散,“一时难以查考”。在同知官下乡急催的情况下,里甲呈报的土地信息多有讹误。应付官府差事、编造清查册之后,众人担忧册上所载内容会造成今后产权秩序的混乱,故而订立合同,约定只承认黄册底籍或鱼鳞册(“青册经理”)、土地买卖契约(“契字买业”)等作为确权之凭据,不以此次清查册为准。共有18人参与订约并签署,包括谢、李、胡三个姓氏,“各收一纸为照”。显然,这是一份没有呈报官府的民间协议,由里甲集体私下共同约定相关规则。
祁门县十西都里甲排年为“条立乡约、敦笃风化”,在嘉靖四十一年订立一份条款较为全面的合同(49)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散件文书,书号000057。,大致有以下五方面的私约:第一,强调了里甲的基本任务,对钱粮催征“间有恃贻累当年赔”之困境,约定“依时称付完官”;对于“排年讼事,体勘供结”之事务,则要求当年应役的里长“毋得需索”。第二,应对“近因上司例行借办均徭”之事,禁止现年“攘夺包纳”,以及大户、小户关系和甲首津贴等。第三,改变公山庵的管理方式,另召僧徒供奉香火,禁止各排年“放债入庵”以及“闲人久占庵居、找敷钱谷”等。第四,对于申明亭、社坛、店铺等“空闲官地”,由里甲集体“召赁输租”,并将所得租金作为应付各项公事的备用经费。第五,加强公共山场管理,“编甲巡视”,禁止外来人户侵夺。
上述五条,前两条属于里甲供纳赋役的事务,后三条是里甲集体对当地公共土地的控制。里甲组织往往依托寺庵,将其作为公共活动空间和集资机构,上述公山庵便是如此。此外还有一些里甲集资维护修理庙宇的记录,如一件万历二十七年的合同载曰:“八甲吴高元同弟三元,原于万历元年是父志达领到众排庙舍银一两二钱零二厘,又于隆庆元年父收到四甲方烈原领庙舍本利银六钱一分八厘,向未付舍。”此后正式修庙,吴高元和吴三元二人立约,“情愿立约听四甲、十甲银算利多寡均派”,每人承担一半(50)《吴高元等立修庙摊派合约(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初六)》,陈琪、倪清华主编:《明代徽州文书集萃》第9册,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034页。。山场利益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更为巨大。不独十西都立有禁约,嘉靖三十五年十东都一、二图排年也签订了禁革山场合同,其文曰:“本都山多田寡,各家户役因赖山利以供解,近被无耻刁徒不时入山侵害。”山林面积广大,登记粗疏且课以轻税,反而成为祁门地方社会应对徭役的重要经济来源。山林经济的发达,造成偷盗杉木等行为屡禁不绝。因此,全都排年订约,划定禁革山场范围,“将本都上孚溪起至孚溪口,外至石坑口,无分各姓山场,在山杉、松、竹、木概行禁革。自立禁约之后,毋许仍前窃盗,肆害如故。犯者,盗木壹根,罚银壹钱公用。若本犯恃强鲠众不服,邀同在会立文人等呈官理治。凡在禁约之家,毋许偏私曲互,以弛众议。所有各家地佃、伴仆人等,讨柴烧炭,俱不许戕害杉松苗木,若损木壹根,无分大小,罚银似前。烧炭务宜谨守,毋许纵火延误”(51)《嘉靖三十五年祁门张祖等护山禁约》,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2,第242页。。山林收益可补助国家赋税和日常生计,除了家族势力的重视外,以里甲的名义可以联合各家族力量,更能提升山林保护的权威度。
综之,里甲合同的出现,应与里甲基本职责不断增加,应付官府不时需索有密切关联;也反映出里甲组织通过乡规民约的制定,强化了办理地方事务、维护土地产业的权力。
五、结 语
赋役是王朝国家实现资源调配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合同则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反映人们在书面化协议机制中如何进入、维持并终止交换关系(52)[美]曾小萍等编:《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李超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页。。通过上文考察可以看出,作为赋役制度和合同文书结合点的赋役合同,呈现了基层社会纳赋应役的策略,称得上是明代赋役体制变动的一个缩影。民间应对赋役的单元有家户和联户的里甲组织两个层次,相应地,赋役合同之产生与流行机制也是不同的。
明代户役制度下,户的内涵有很大的转变。明初登记人口形成的“户”,主要对应的是家庭,应役人选和津贴的商量亦只限于家庭之内,家长裁断经常显得尤为重要。但随着户从家庭转变为家族、规模扩大,户内的人群构成变得复杂,合作应役和津贴需要多方协商,反映出民间对赋役风险的规避,家户内的赋役合同由此得以流行。
就现有留存的徽州文书来看,明初赋役合同的签订只局限于家户之内。更大范围的赋役协商(如粮、里长群体)是存在的,但自主性很低,需依赖官府的同意,因而应役集体独立订立合同、自我约束的条件尚不具备。有的家族档案中虽有洪武时期的赋役合同,但并不符合明初实际情况。随着明中期官府不时需索愈加频繁,里甲职能增加和公产管理之需求等多方面因素,推动了里甲集体签订合同之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