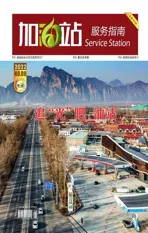我的童年梦想
2022-09-01段明钊
文/段明钊
雨越下越大,但还能看到马路对面一栋建设时间不久的新楼已经快要封顶了。看着、看着,我不禁哑然失笑。一旁的妻子问我:“笑什么?”我说:“你知道我儿时曾经的一个理想是什么吗?”妻子说:“不知道。”
6 岁时,我的理想是做个打墼的。
那时,为了让两个叔叔有房子结婚、早日成家,父亲和母亲商量,把祖屋留给他们,自己在村子西头另盖房子。但家里穷,盖不起砖房,只能建那种用石头建地基、用土墼垒墙的土坯房。
建房前一年的冬天,父亲请人去村北的山上开凿了许多青石运到新家,当时还是长满荒草的空地。作为建设新房的基石,又去集市上买回檩杆、梁,拵屋用的麦秸、和泥用的麦穰也和亲戚邻居打了招呼,都给提前攒着。
跟大多数人家一样,那时几乎顿顿吃煎饼咸菜,来客人时才能炒个白菜、芹菜,但没有肉,鸡蛋也很少。偶尔村里有来卖豆腐的,母亲就会换个一斤两斤的(因为没钱买,只好用豆子易货交易),就算开荤了。
我记得很清楚,父母为了招待那些请来打墼的师傅,每顿晚饭都有白菜炖豆腐,中午饭还用一咬就流油的肥肉炒芹菜、芸豆,即便是咸菜也要滴了香油再端上桌,闻着就让人流口水!
更让我眼馋的是每天上午10 点左右,都要给打墼的师傅吃“贴赏”(就是给这些从事重体力活的人加餐),每人好几根油条呢!我实在馋得不行了,就央求母亲给我一根油条吃。平时对我百依百顺的母亲,此时板着脸:“不行,油条就这么多,还要给打墼师傅做贴赏!”言外之意,我不是打墼的没资格吃。
于是,我只能躲在门后、眼巴巴地看着打墼师傅大口大口地嚼着每一根油条,耳朵里充满了打墼师傅咀嚼油条脆脆的“咔嚓”声,自己的肚子不争气地发出“咕咕”声、喉咙里无法控制地发出“咕咚、咕咚”的吞咽口水声。
吃完“贴赏”,师傅就来到打墼的地方。我尾随其后,看他们干活。打墼都是两人一组,分大工、小工。打墼时,小工先用刮板刮去打墼平板(约有20 多厘米厚、表面平整的一块大青石)上的余土,将墼模(木质,高度约10 厘米)放置在平板上,扣上揽头棒子(固定墼模的装置)后,在墼模底部均匀地撒上草木灰,用煤矿上那种铲煤块的大铁锨,将刚刚挖出、依然鲜湿的细土(选的是当地纯净的黏土)倒满墼模,再在隆出墼模的鲜土上撒一把草木灰。
然后,大工上场。只见他精神抖擞、稳稳当当地踏上墼模,气定神闲地用脚步均匀踩实黏土。因为有了打墼平板及墼模的高度,打墼师傅此时就有了些“登泰山而小鲁”的气势。
随后,他将40 斤重的杵头稳稳握在手里,轻轻一提,就势碰一下揽头棒子(检查揽头棒子是否牢固),高高抬起,借助杵头自身重量,看似只是轻盈几下,就将墼模中的黏土夯得平整溜光。然后,他恰如舞台上的舞者,将身体优美地做四次侧倾,杵头的下楞就在墼模的四个角留下了月牙状的“眼”,虽然每次都以为杵头要落在墼模上,但杵头每次落下的位置,几乎都在离墼模大约1 厘米处。
最后,仿佛舞者一曲舞罢的谢幕,打墼师傅弯腰将杵头放回原处,轻盈的用脚蹬开揽头棒子,双脚又稳稳当当地踏回打墼平板下的平地,一块平整结实的墼就打好了。
此时,微风轻拂,蓝蓝的天上飘着白白的云,打墼师傅脚穿一双洗得发白的胶鞋,身着草绿色军裤,脖子上搭着一条干净的白毛巾,粗壮有力的双臂黝黑发亮,身上透出淡淡的烟草香气。

◇供图/视觉中国
看着他,我小小的身体里似乎充满了无穷力量。我立志,长大后也做一名打墼师傅:那样,我就能吃上香喷喷、流油酥脆的油条“贴赏”了。
我正沉浸在“励志”的激动中,突然听到有人喊我乳名,抬头一看,原来是赶来帮忙的表哥正颤悠颤悠地挑了一担河水走过来。“快!给你捞了一条大鱼!”我赶紧跑过去,趴在水桶上一看,哈!一条足有20 厘米长的鲢子鱼在水桶里游动。闻讯赶来的父亲掩饰不住内心兴奋:“好兆头!好兆头!年年有鱼(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