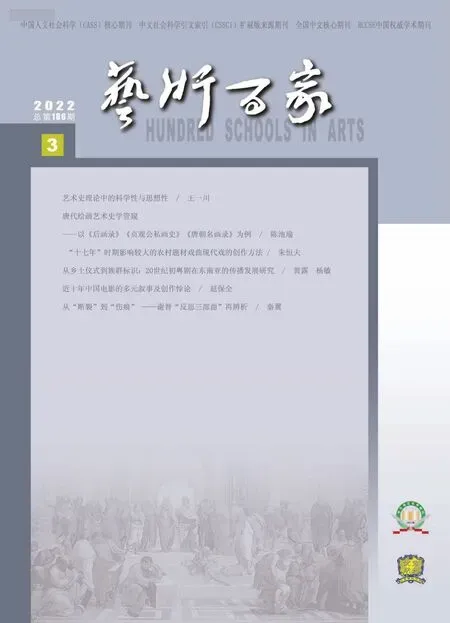雅俗的分界*
——《长物志》中的儒家审美观
2022-08-31张琛琛胡筱
张琛琛,胡筱
(1.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2.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 201620)
晚明是一个商品经济急速发展、城市文化极度繁荣、市民思想多元开放,但政治形势却十分险峻复杂的时代,“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雅与俗的界限变得模糊……”[1]3这种文化生活的多样性与心学思潮的流行休戚相关。因此,一方面是伴随经济成长而到来的市民阶层所要求的人文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反映着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这二者共同形成了晚明社会追求物欲和尚奇的美学特质。在居于社会上层的文化精英们看来,这样的审美变化实则是对两千年来儒家温柔敦厚美学观念的一种冲击。
于是他们一方面对自我修养提出了要求——君子不应拘泥于事物的具体方面,而应去思考事物背后的道之所在;另一方面对器物之用作出了规定:器物作为载道的工具,应将儒家审美观由精神层面转向具体生活方案的落实。出于这样的目的,文震亨所著的《长物志》一书为文人生活中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的雅俗厘定了正统,书中内容是对传统文士生活方式的系统总结,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文化精英们的审美趣味。从书中文氏对器物的雅俗划分中,人们可以看到他所追求的是传统儒家的中和之美,是理想生活的本质之美。
一、儒家审美中的“雅”“俗”关系考
“雅”在先秦时代是一个价值评判词,它主要用于音声方面的表述,具有正式、正规之义,如“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2]94中的“雅言”即是正音之义,原指西周王畿的语音,经过士大夫对其标准化后,而成为当时的国语。[3]131因此《毛诗序》中有“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4]5这样的解释。《荀子·荣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5]34此处“雅”与“夏”是相通的,此处的“夏”是中原地区,它代表的是区别于地方的一种属于统治阶层及士大夫的“标准”。而语言在其“标准化”的同时亦开始“文雅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雅”才在文士阶层中发展成为一个与“俗”相对立的概念,随后伴着文士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加强,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审美概念。
“俗”的早期意义一般指乡土社会中长期形成的约定和习惯,在周代时具有浓厚的政教意义。《周礼》中提出大宰之职应“以八则治都鄙”[6]30,其中,“六曰礼俗,以驭其民”[6]30;大司徒之职要根据不同地形所形成的人民生活习惯施行十二种不同的教育,其中,“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6]216。这两处的“俗”所表达的意思都是指乡土习俗。《礼记·王制》中“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7]153的“俗”与“宜”指的也是风俗和习惯。《荀子·乐论篇》中有“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5]250和“移风易俗”[5]250之说,李斯在《谏逐客书》中也有关于“俗”的论述:“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8]237这几处“俗”字所表达的思都是一致的,因此,“俗”在先秦时代所指代的都是当地的风俗习惯。
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士”阶层是肯定审美和艺术的,孔子的观点是:“审美和艺术在人们为达到‘仁’的精神境界而进行的主观修养中能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9]43审美和艺术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是孔子美学的出发点和中心。因此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91,就是以道为方向,以德为立脚点,以仁为根本,以六艺为涵养之境。而“士”阶层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持一种批判态度,由此逐渐将原始的“雅”与“俗”的意义抽象为一种社会的普通存在。东汉以来,雅俗的对立逐渐形成,其后随着士大夫阶层文人意识的觉醒,雅俗作为对立的审美概念趋于成熟,而学者士大夫出于对儒家道统秩序的追求,逐渐将儒家思想中的审美态度作为判断事物雅俗的标准,这一观念在以理学作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宋明两代得以巩固。
从《长物志》中对“雅”与“俗”的划分标准来看,文氏将周正合理、自然质朴、适度致用的器物归为“雅”,将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器物一律斥之为“俗”。文氏通过“雅”“俗”这一对概念在《长物志》中对器物进行了审美价值的判断,从而揭示出晚明传统文人在对生活本质美的追求中所内含的儒家思想。明代中后期社会主流思想由理学转向心学,文士们要么从具体事物中求理,要么从自身心中求理。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由具体之物出发去把握自然规律,通过选择和使用器物阐发其人生态度逐渐成为很多文人求理致道的方法。
《长物志》一书中多次出现“雅”“俗”对举和以“雅”“俗”为审美判断的句式,如照壁:“得文木如豆瓣楠之类为之,华而复雅……有以夹纱窗或细格代之者,俱称俗品。”[10]25文具:“以豆瓣楠、瘿木及赤水、椤木为雅,他如紫檀、花梨等木,皆俗。”[10]316-317帐有冬月与夏月之分,“有以画绢为之,有写山水墨梅于上者,此皆欲雅反俗”[10]335。全书十二卷中,文氏频繁使用这样雅俗判定的语句对器物的选择、使用和内涵进行标准的划分。从广度上,该书涉及了文氏理想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深度上,则通过对器物的材质、形制及其精神内涵的把握阐明了晚明文人内心世界中“雅”与“俗”的分界。
综上所述,文震亨作为晚明儒家审美的实践者,他将“雅”与“俗”的概念截然划分,作为规定日常器物选择、使用以及鉴赏的标准,实则是将个人的生命追求寄托于对现世的具体日用生活之中。以前文所阐释的“雅”“俗”概念作为衡量器物的标准,通过物质层面的心理愉悦促使精神的向上探索,这是晚明文人对圣人之学的向往,人们将这种对器物的审美融入圣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2]91的精神追求中,希望通过这种从容涵泳的生活态度达到更为高远的人生境界。
二、《长物志》择物的标准:自然古朴为雅,刻意巧饰为俗
器物的选择亦是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个人心性修养的外在表现。晚明文士通过对器物的选择与鉴赏来构建理想人格,将对自我人格的要求转化到择物、赏物的标准当中,甚至将二者融为一体。文氏在室庐卷末总结道:“总之,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10]40他对于物的选择,自有一套标准:样式上欣赏“宁古无时”[10]40,材质上要求“宁朴无巧”[10]40,方式上要做到“宁俭无俗”[10]40。
《长物志》中“宁古无时”[10]40的观念来自儒家思想中的尚古传统。作者在书中多以“古雅”“古意”“古风”“古朴”“古拙”“最古”等词作为器物的品鉴标准。如几榻卷和器具卷均谈到古人制器物如何,并对其作了具体描述,如:“琴为古乐,虽不能操,亦须壁悬一床。以古琴历年既久,漆光褪尽,纹如梅花,黯如乌木,弹之声不沉者为贵。”[10]299他认为古器精良高贵。《长物志》中多处流露出这样的尚古观点,若将这些观点置于传统儒家的思想之河中进行考察,可上溯至先秦儒家思想中对古代圣王和西周礼乐统治下全盛时期的向往,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华夏文明的祖先崇拜与儒家传统中的孝道思想。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2]90《大戴礼记》有云:“文王治以俟时,汤治以伐乱;禹治以移众,众服,以立天下;尧贵以乐治时,举舜;舜治以德使力……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11]184这表明中国文人在儒家思想的源头上早已接受了这种尚古、崇古的观念,那么文氏在书中对器物审美上的要求实则来自先秦儒家思想对三代之治的向往与追求。
《长物志》中“宁朴无巧”“宁俭无俗”[10]40的观念来自儒家“道本器末”[12]792的思想。在器具卷中,文氏认为器物首先在装饰内容上应有所选择,在题材上,那些与自然相近的内容才可以称为雅,在材质和形式上则以古朴简约为雅,反对刻意的装饰内容和手法。他认为尧峰石“正以不玲珑,故佳”[10]115,认为香筒“中雕花鸟、竹石,略以古简为贵。若太涉脂粉,或雕镂故事、人物,便称俗品……”[10]258-259还写道:“有倭人鏒金双桃银叶为纽,虽极工致,亦非雅物。又有中透一窍,内藏刀锥之属者,尤为俗制。”[10]270他认为镜子当中的“秦陀:黑漆古、光背、质厚无文者为上”[10]278。他在器具卷中认为雕刻本身的妙处在于刀法圆熟、藏锋不露,而“俗子辄论金银胎,最为可笑”[10]325。他还列举了有些人本想对器物有所装饰,得到“雅”的效果,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如“有以画绢为之,有写山水、墨梅于上者,此皆欲雅反俗”[10]335。因此在器物的选择上,他的看法是“本色者最雅”[10]333。仔细品味,他的这些观点与儒家审美中“道本器末”[12]792“重道轻器”[12]792的思想相契合,孔子曾多次赞许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2]85可见,“谋道不谋食”[2]156“忧道不忧贫”[2]156正是孔子的明确主张。与此相应,在器物选择的层面上,“朴”与“简”正是一种安贫乐道的审美态度。
总之,道是“本”,器是“末”,道是根本,器作为从属,只是道的外在表现。那些注重高远、追求根本的文人雅士,在事物的选择上必然是追求其本质,而非巧饰。与此相应,文震亨对器物的刻意巧饰亦加以否定,提倡简朴为上,认为在器物的选择上“虽极人工之巧,终是恶道”[10]325。可见,他所提倡的器物之美是在于为使用而存在的器物本身,而非贵重的稀有材质和人工的刻意装饰。
三、《长物志》用物的态度:适度致用为雅,跟风附势为俗
《长物志》在卷一即总结道:“古人最重题壁,今即使顾、陆点染,钟、王濡笔,俱不如素壁为佳。”[10]136这里开宗明义,明确地表达了文氏对器物的使用态度是“随方制象,各有所宜”[10]40。因此,器物在使用上并不存在既定范式,人作为使用器物的主体,应以适度致用为上。他在位置卷中对悬挂书法、香炉、花瓶等的大小疏密位置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位置之法,繁简不同,寒暑各异。”[10]347室内的书画不应随意悬挂,而要与时令相应:正月初一宜挂宋代福神及古代圣贤;正月、二月宜挂春游仕女及时令花卉……总之,“皆随时悬挂,以见岁时节序”[10]223。使用古铜花瓶养花也不仅仅是因为“古色可玩”,更主要的是“古铜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10]287。对于苏州地区将扇面装订成册以供赏玩的风气,他认为这样做很是俗气,反而不如四川的扇子方便适用。[10]296舟车卷中,他认为舟车的功用在于“用之祖远饯近,以畅离情;用之登山临水,以宣幽思;用之访雪载月,以写高韻”[10]341。总之,器物的使用应当随时随用变换,不可迂腐地一致对待,更不可盲目追随一时的风尚。文氏这种使用器物的态度表达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同时也描画出了晚明文人以心感物、以物喻志的心理状态。
文震亨在器物的使用上,并不在意器物本身的华丽奢侈或者当下的潮流趋势。当他谈到对器具陈设的追求时,批评时下风气不分雅俗,一味追求雕琢装饰,取悦俗世风尚,指出真正的风雅之士并不注重铭刻题记等手法的华丽,而是以实用精良为佳。如:“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又坐卧依凭,无不便适。”[10]226可以“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簟,何施不可?”[10]227尤其在衣饰卷中,文氏特别强调了与时、与地相宜的重要性,指出每一个时代有其穿着的规制,应当按其时代规制穿着,打扮上不可一味追求富贵华丽,而应当根据季节和所处的环境有所变化区分。[10]328此类观点在器物卷中也有所涉及,例如谈到魏晋名士清谈所用的尘麈时,他认为“古人用以清谈,今若对客挥麈,便见之欲呕矣”[10]284。他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庸俗做法,但将其悬挂壁上,也不失为一种雅致的收藏。总之,要以致用为上,并且要合时宜,不可盲目地崇古、尚古。
《长物志》中所表达的适度致用的用物态度是儒家入世哲学的具体表现。文氏虽对器物的选择、使用和理解作了详细的规定,但他却反对教条性地对他的文本进行理解,他认为器物应当为人所用,要因时、因地制宜,不可照搬照抄,否则仍会落入俗套。因此他在禽鱼卷末指出:“余所以列此者,实以备清玩一种,若必按图而索,亦为板俗。”[10]134这种反对刻板的儒家实用主义态度贯穿于全书的各卷内容。春秋末年,孔子学说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改变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恢复西周礼乐统治下的社会秩序。因此,传统儒学本身是一种入世哲学,这种入世哲学反映的是以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它要求知识分子以“格物”“致知”而达“诚意”“正心”,进而达到“修身”之本,由此而致“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2]135孔子在这里通过“授之以政而不达”“使于四方而不对”批评了不以致用为目的的死读书,即是对刻板意识的否定。因此,儒家思想自其产生之初,就具有明显的入世致用倾向,并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人生信念。这样的致用思想反映在文人用物的态度上,即是一种具有中庸意味的实用主义态度。
四、《长物志》观物的内涵:文质相符为雅,崇奇尚怪为俗
在文震亨所处的晚明时期,一方面是市民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剧变,另一方面是明王朝倾覆所带来的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当时的文人们出于对内心不安情绪的排解需求,通过对奇人、奇物的追捧而获得心灵上的自由与满足。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晚明文人产生了崇奇尚怪的审美特点。文震亨在书画卷中,认为“书画原为雅道”[10]143,因此书画作品的价值应来源其本身所具有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作者的名声以及绘画的技巧等表面形式,他对当时那些“心无真赏,以耳为目,手执卷轴,口论贵贱”[10]137的书画收藏者提出了批判。他强调书画的内容应作为书画价值的首要评判标准,因此“一作牛鬼蛇神,不可诘识,无论古今名手,俱落第二”[10]143。他进一步反对晚明崇奇尚怪的社会风气,将不符合温柔敦厚传统审美的器物,一律斥之为俗。他在书中多处表达了对当时社会一般审美的反感,如花木卷中他认为芙蓉(荷花)作为水生花卉,自然是种植于水中岸边,最能反映本然之美态,然而却有人植于他处,将其染色,认为这种做法“甚无谓”[10]61。器物卷中“有以老树根枝,蟠曲万状,或为龙形,爪牙俱备者,此俱最忌,不可用”[10]260。在水石卷中又写道:“斧劈以大而顽者为雅。若直立一片,亦最可厌。”[10]117
文震亨所例举的这些时代审美风气往往只追求器物外在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忽略了器物内容上的饱满充实。他书中对器物内涵的观照,是对当时的一些流行审美风气的背离,他欣赏器物所立足的理念与先秦儒家的美学观点遥相呼应。为了使艺术与审美在社会生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孔子强调艺术美需要达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因此提出“尽善尽美”这一美学命题:“子谓《韶》: 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2]68孔子认为韶乐是尽善尽美的,因为它既有浑厚的道德基础(内容),又能完美地进行表达(形式),而武乐不如韶乐,主要是因为它没有足够的道德基础,在内容上未能尽善。也就是说,如果能将艺术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那就是“尽善尽美”。进而孔子又提出“文”与“质”要相统一,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86,这是对君子修养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君子的道德品质与文饰要相统一。对此,余英时先生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论述中也认为朴实的本性要和文化教养相结合,才能够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子标准。①即形式与内容二者的统一不可偏颇,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君子标准”,才能进一步达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2]156,即中和的审美标准。《论语》中多次表达了孔子对“文质相符”这一概念的肯定,这使历代的美学家都十分注重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质”与“文”的统一。《论语·八佾》:“子曰:‘绘事后素’……‘始可与言《诗》已矣。’”[2]63孔子用绘画与素底比喻礼和仁的关系,朱子对此的注释是礼仪是以忠信作为其本质内容的,这就如同绘画首先要有洁白的画纸一样。在《论语·先进》中,孔子与弟子们言志,子路、冉求和公西华谈论的都是如何治理国家,曾点却回答:“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2]124曾点所回答的只是普通人的闲暇生活,却得到了孔子的赞许,因为曾点描述的是孔子所追求的中正平和的世界。程颐认为:“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2]124朱子认为其他三子规规于事之末,只有曾点“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2]124。因此孔子才会赞许他的回答,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所认同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匹配。
综上可以看出,文氏对器物的欣赏标准是明确的,即要具备“雅”的内涵,而这种“雅”的内涵是来自形式与内容的相符,同时包含了一种“心物相契”的体悟。在书的序文中,沈氏谈到这些寒不可衣、饥不可食的闲事长物是古今清华美妙之气,是天地琐杂碎细之物,只有那些具有真韵、真才、真情之人才能赏识其中的妙趣,而很多人只是追逐这种看似高雅的形式,对器物真正的内涵一无所知,是令人叹息的。
五、结语
首先,文震亨作为明代书画四大家之一文徵明的曾孙,是晚明苏州地区文人的典型代表,他针对晚明士绅阶层注重物欲、追时尚奇的社会审美倾向,为日常器物的选择、使用及内涵的方方面面厘定了标准,进行了雅俗的区分,将文人的精神追求诉诸对器物的审美标准,以器物审美比拟个人精神修养的雅俗。他通过器物审美描述了对生活本质之美的追求,并客观而理性地描绘出中国古代史上最具艺术气息的世俗生活,同时重新注解了那个转型时代的儒家美学观。
其次,文震亨认为黄金珍珠产于山渊,取之不尽,尚且为世人所珍爱,而那些古代的书画作品,皆出于“不能复生”[10]137的名士之手,而更应当珍惜。通过他在这本书中的总结,我们可看出文氏所珍视的不仅仅是出于名士之手的书画作品,更包含了一切经由人类智慧所创造的美好器物。他的好友沈春泽为其所作序中更直言文震亨此书的“用意深矣”[10]8,即在于防止后人忘却这些美好器物的来源和技艺。《长物志》全书所言虽器物,却始终贯穿着儒家思想中对人的关注,相对于物质美的判断,文震亨更注重人对器物的创造之美,而这种美正是宇宙天地间独一无二的。
再者,《长物志》一书涉及园林建筑、家具器物、书画收藏、花木饮食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集中反映了晚明文人通过对日常器物的审美要求所表达出的对理想人格的向往与追求,因此它不仅是基于园林、器物等的研究文本,亦是晚明江南地区文人价值观的写照。沈春泽在序中认为“删繁去奢”[10]8四字可作为全书的概括,表明文震亨在书中所撰写的内容深受儒家“以心御物”[7]13“重道轻器”[12]792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对当代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而言,该书为构建中国传统的审美和儒家生活范式提供了一套较为可行的方案,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审美观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而在当今这个经济快速发展、人心愈发焦虑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凡事追求高效率、快节奏,并把物质的丰裕作为幸福生活的衡量,最终导致人们的心态趋于失衡。文震亨在书中所阐发的这种审美思想起到了让人回归本心、重构生活本质的作用,他通过将生活日用之物归类总结,对人的物质追求和心灵需求作了一次全新的审视,为儒家审美观在当代的阐释与实践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本。
① “此处的‘文’字涵义较广,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教养”,在当时即所谓‘礼乐’,但其中也包括了学习诗书六艺之文。‘质’则指人的朴实本性。如果人但依其朴实的本性而行,虽然也很好,但不通过文化教养终不免会流于‘粗野’(道家的‘返璞归真’,魏晋人的‘率性而行’即是此一路)。”见于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