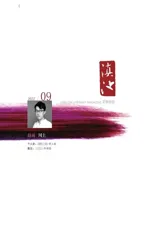隐忍(外一篇)
2022-08-30散文诺尔乌萨
散文 诺尔乌萨
毫无疑问,对于孩子母亲来说,这是一次鬼使神差的遭遇。
孩子母亲下班后,骑上电瓶车,刚出校门不久,不幸撞在一辆出租车上,人已被司机及时送往医院。
接到这个自称是司机的陌生男人电话的那瞬间,我被吓呆了,脑子一片空白。
慌乱中,我三步并作两步,恍恍惚惚地穿过两条街,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急忙赶到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5号观察室。
一进门,看见她已经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输上了液体,面目看来没有什么损伤,一路悬着的心这才落下。
有白褂天使进出。
来到病床旁,我立马就问,痛不痛?撞在哪里?严不严重?是怎么撞的?见我受了惊吓和气急败坏的样子,她轻轻抬起右手,移开身上的被盖,勉强撑起上身,指着旁边的一个陌生男人说,下午回来的路上,就是这个人的出租车行驶在她的前面。在没有打左转灯,没有任何迹象中,出租车突然在她前面来了个向左转,一阵身不由己的惯性中,她连人带电瓶车,“砰”的一声撞在出租车上,人翻过车的顶棚,摔在另一边的水泥路面,两只脚的膝盖骨先栽在地上。
她说,还好,没有什么大碍,就是头晕,两只膝盖疼痛得比较厉害。
听孩子母亲说完后,坐在床前独凳上的这个陌生男人说,的确是这样,娘娘没有说错。
我问,你是?
他说,他是司机,刚才的电话是他打的。
我暂不想理他。
我给孩子母亲说,什么叫没有什么大碍,我看您连命都差点没有了,那是多么危险的一幕啊!她没有说话了。
司机说,他和娘娘非亲非故,可事发后,娘娘没有愤怒,也没有表露出任何一点责怪他的意思,老师就是不一样。
我觉得,他分明是在阿谀奉承和宽慰我的孩子母亲。
那瞬间,我顾及不了什么,毫不客气地直接对眼前这位司机说,是你开的车?他说是,替车主开车,他开工钱。我问他,你是咋个开车的?处于对孩子母亲本能的疼爱和怜悯促成了我心中一时的怒火,那会儿我的情绪有些激动,甚至愤怒,我的语气有些重。他说,那瞬间,自己仿佛是着了魔,恍惚了一下,就岀事了,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
说完,他看看我的孩子母亲,又看看我,然后低下头,像是深深陷入了自责、懊悔和后怕中。对自己的过错表现出十分诚恳知错的态度。
听孩子母亲说没有什么大碍,看见她完好的样子,我想是不幸中的万幸!我这才稍稍冷静下来,转念一想,或许他也不是故意的,对他来说,可能这也是一次意外。我变冷静后,渐渐消气了,内心里的怒火才慢慢熄灭。渐渐,还宽恕和原谅了他。
眼前这位司机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满脸被高原紫外线辐射成黝黑。穿作寒碜。说话吞吞吐吐,一看是个憨实的老农,模样倒是让人觉得怪可怜的。
还处在忍受疼痛中的孩子母亲以摇头的方式在向我示意,不要责骂司机。
我领会了孩子母亲的示意,以平和的语气对司机说,事情岀都岀了,重要的是直面现实和自己的过错,把病人服侍好,治疗好,让她早日康复。他站起来,双手合十,谦恭地说,好的,好的,谢谢!
看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找到主管医生,吩咐了一些话,然后离开了医院,回家做饭。
晚上七点过,正准备岀门送饭,不料门被突然打开,原来是孩子母亲。她右手撑起腰部,满脸痛苦的样子,一拐一瘸地进来。
我原以为她会在医院里至少住上十天半月了,万万想不到这么快就回来。我感到十分意外。
我说,我正准备去给你送饭,不在医院住院输液治疗,跑回来干啥?她说,她不好意思。我说为什么,她说,被车子撞了,在住院,万一被亲戚朋友知道,觉得自己丟了脸面,没有面子了。我说,司机呢,她说她让他回家了。你留下他的姓名,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没有,她说没有留下。
原来,她置自己性命于不顾,去担心的是自己的面子。我说,面子重要,还是你的生命重要?你那个面子值多少钱?可当饭吃,当衣穿?我有些生气了。她没有开腔。
我边说,边轻轻扶着她坐在沙发上。过了一阵,她才说,看样子司机是个可怜兮兮的老农,她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说她假借此事,赖在医院里,骗人家的钱。她是在担心别人说她的坏话,戳她的脊梁骨。
其实,过了一阵,我也在内心里想,孩子母亲的担心也并非空穴来风。
此前,我曾听说,在街上,有老妇人被摩托车、电瓶车或自行车轻轻碰一下,对方立马倒地,假装重伤,趁机在医院里住上十天半月。还听说有车经过一些偏僻集镇时,一不小心碾到一条猪仔或一只鸡,主人家硬向驾驶员漫天要价的事。人们对猪鸡的主人和老妇人的鄙视和痛恨是不言而喻。还有一种是专门从事碰瓷的人,更是令人恶心。
孩子母亲是害怕无意中自己被人视为这种人。
但我还是说,管他是农民,还是城里人,这不是个身份或可不可怜的问题,是两码事儿。他突然在你前面调头,是违规,还把你撞成这个样子,他该负岀代价,该为自己闯下的祸买单。
孩子母亲还是没有开腔。
我说,你现在不在医院里把双膝治愈,这么匆忙回来,将来万一留下后遗症,怎么办?她说,那也算是自己倒霉了。她是个有些固执,又极爱面子,爱名誉的人。
其实,细想起来,世上哪个人不爱面子,不爱名誉呢?只是爱的程度不同而已。而我们周围的人,有些把面子和名誉看得轻一些;有些把它看得重一些,这也许是事实。
比如在面临生死考验的战场上,有人以冲锋在前为荣,以临阵逃脱为耻。也有人到了生死关头,总是会选择逃命,这与他个人有不有胆识,英不英勇和爱不爱面子有关。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倾其所有,忍嘴待客,也是看重面子。邻里间,朋友间,同事间,不管发生什么吵架闹架,不得轻易骂重话,骂粗话,甚至是讨厌岀言不逊的人。
顾及面子和文明兼而有之。
平时人与人之间的误解,纠纷甚至是矛盾,许多是来自彼此间缺乏沟通与交流,包容,关心理解与尊重,甚至是因为不顾及面子造成的。
从前,在祖国大西南这片古老的崇山峻岭间,不同民族间彼此隔陌,利益冲突,互不忍让,日积月累,形成了彼此间的隔阂。而现在,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的素质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学会了相互理解,包容,尊重,给彼此留面子,不计较个人得失,于是出现了眼下各民族间,或是一个民族的内部,翻天覆地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和睦成一家的社会局面,真是来之不易。
想起这些,我逐渐理解了孩子母亲的用心良苦。
夜里,我坐在她的旁边,用右手轻轻地揉捏她的两边膝盖骨,她说,人活名声,狼活一张皮,这事就这样算了。孩子母亲怕我对此有些固执,反而用谚语来劝导我。我没有开腔,内心里倒是在想,万一留下后遗症,以后受苦的是你自己啊!
第二天,一家人正在吃午饭,出租车司机提着一个塑料口袋,站在门口,敲着开着的铁门,我说请进。他进屋后,我们请他一起吃饭,他说他已吃过。我请他往沙发上坐。他把手里的塑料袋递给我,觉得沉甸甸的,我问是啥?他说是一份凉拌猪耳朵。我说,你买这些东西来干啥?他说是来道歉。提一份凉拌猪耳朵来道歉,我收下也不是,不收也不是,感到十分为难。
也许一份凉拌猪耳朵对眼前这位乡下人十分重要,可在他的眼里和我的眼里,一份凉拌猪耳朵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而我觉得他主动登门拜访来看望一下伤者,这个远比几份凉拌猪耳朵,甚至是十份凉拌猪耳朵都还要重要得多,或许这就是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区别所在,这也让我想起了孩子母亲先前说的话:司机是个可怜兮兮的老农。
我说没有这个必要,下不为例。他说好。接着,我还从做人做事和小心、安全开车的角度,认真教育了他一番,他一直在认真听,其间,嗯,嗯地不断点头,最后是感动得眼里包着泪花离开了我们家。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孩子母亲被车撞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两天后的中午,家里突然冒进来一帮熟悉的年轻人,他们是来做说客的,动员孩子母亲去住院。他们说,这事不能就这样轻易饶了司机,至少也得让他赔个三五万元才行。我们夫妻俩一直在说,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况他是个可伶巴巴的农民。怎么也说不动,觉得我俩顽固不化,最后这帮年轻人失望地离去了。
就这样,孩子母亲的膝盖骨在家调养了整整一年后才好一些。
事后有一段时间,司机还是经常打电话来过问孩子母亲的伤势。后来,他的电话越来越少,最后是连人连电话消失在时间里。
这是十五年前的事。
那以后,我俩都没有在意和留意过这件事。
五年前的一天晚饭后,孩子母亲与院子里的几个女人散步走路,走着走着,觉得自己的膝盖骨不对劲,有些疼。自从那天,只要每次稍走远一点的路,她的双膝就觉得隐痛。
前年初,这样的疼痛越发严重。上下楼梯,散步,起身落坐很困难,甚至看见她抬腿都十分艰难、吃力、痛苦的样子,我感到怜悯,心疼,于心不忍。带她去打针,贴膏药,带护膝,服药,收效甚微。到州一医院骨科去检查,医生问她,以前膝关节受损过没有?她把十五年前的事如实告诉了医生,医生说需要做CT图片检查。做了CT图片检查,等来的结果是:创伤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膝关节软组织萎缩。
医生说,是明显的后遗症。
看了CT图片和医生的确诊,我俩都无语了。或许她这才想到了当初我的提醒。我讥讽她,当初叫你好好治疗,你不听,自作自受。但她还是没有一句后悔的话,甚至没有一丝后悔的表情。
拿到检查报告单,慢慢回家的路上,我跟在孩子母亲后面,见她走路轻脚瘸柺的样子,想起她对待此事一直所持的态度:宽容,大度,善解人意,有悲悯情怀,反而觉得自己成了心胸狭窄,显得自私和冷漠的人。
我又一次敬佩起我的孩子母亲。
这倒是让我俩十分看重了一件事,那就是急于想搬到底楼去住或想拥有一套电梯公寓,以此来缓解一下她上下五楼时膝盖疼痛的痛苦。
除此之外,她一直是默默地隐忍着疼痛。我俩都不愿意去想这件事的源由,也淡忘了那个肇事者的名字。
越来越远
接到远房奶奶不幸去世的噩耗,匆忙赶到西昌城北郊区的殡仪馆,她老人家的遗体已被静静地安放在15号大厅里的灵柩上。
瞻仰她的遗容,想起她的音容笑貌,想起她为自己的儿女们含辛茹苦的一生和生前对待亲戚朋友的热情、大方与和蔼,想起她从此告别她的所有亲人们,走向遥远的另一个世界,我的内心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悲痛,泪雨淅沥。
此景此情,我想放开嗓子,按彝族人哭丧的方式,大哭一场,想用许多话语表达对这位老人的敬重和失去她的悲伤。可我环视四周,众亲里,竟然没有一个亲人为眼前这位老人哭丧,只有少数几个人脸上表现出一点悲痛,更多的人没有把这当回事,无动于衷。我想,只有自己独自在这里哭叫,又觉得不合适宜,甚至有些别扭和尴尬,只好强忍了内心里的悲伤。
作为儿女,自己的母亲已离开了人世,已经静静地躺在灵柩上。想起她是自己的亲生母亲,骨肉相连,想起她一生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从今以后天各一方。此时,他们几兄妹也许已经是难抑心中的悲痛。
从小在机关院子里长大的几兄妹,早已远离了只有在乡下人身上还有体现的朴实善良与语言,生活习惯和思想情感,即使不能用母语哭岀一番震撼人心,感人流泪的丧歌,至少也该是抱着母亲“妈啊妈啊!”地放声大哭一场吧。我站在旁边想。
也许是因为内心强大,男儿有泪不轻弹,爱母爱在骨髓里。我看见眼前远房奶奶的几个儿女,个个除了表现出一副忧伤的面孔,丧着脸,没有一滴眼泪流岀来。一个个进进出出,忙于用手机发微信,发短信,打电话,甚至发视频,告诉各自的亲戚朋友圈和同事:母亲不幸去世的噩耗。
他们几兄妹各自手机里的电话、微信、短信倒是一直在忙,响个不停。
我们在忙,忙于布置灵堂,租用桌子板凳,安排人买烟买酒,买瓜子花生,忙接待好客人。
岀殡送葬要择吉日。卦卜先生扳起指头,简单地择算了一下日子,说是第三天好。这意味着她老人家的遗体必须在殡仪馆停放和祭奠两天两夜,守灵两天两夜。有的老人去世后,择算的吉日不合适,要祭奠七天七夜。两天两夜不算长。
接到噩耗,城里的亲戚朋友和远房奶奶的几个儿女们的同事有的赶公交、有的打的、有的是三五个人一起走路来,很快有人陆陆续续前来奔丧。
有抱着啤酒来的,有怀揣礼金来的,有送花圈来的。就是没有听到一句哭丧。
这其中,第一拨到的人,固然是在州级部门和西昌市级机关工作的十来个亲戚。
到了门口,他们几兄妹急忙上去与前来奔丧的亲人们握手,端板凳,斟酒敬酒。
这些前来赶丧的亲人与他们几兄妹寒暄几句话,表示痛惜与节哀,证明了自己已到。
我注意到,才坐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侄儿一边敬酒一边在说:“我还有事,还要赶回去。”他显得有些匆忙。我问他,你难道还要立马返回不成?他说:“最近单位的确是事多,中午还要赶回去加班,只有露个面,表表心意了。”话音刚落,他还没有走进灵堂,还没有去看一下自己婶娘的遗容,人就匆忙离开殡仪馆,往回走了。
剩下的几个同路而来的亲人礼节性地进入了灵堂,看了一眼老人家的遗容,在几个堂兄妹面前晃悠一下,也只是在灵堂的亲人群里露了个面,然后转过身,拿起酒杯,走岀灵堂,加入到门前的人群里。
门前倒是比起灵堂里热闹得多。
这里有说有笑,是另一个世界,三五个坐成一堆,嗑花生瓜子,喝酒,摆龙门阵。
我随便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所摆的内容大致是一些与眼前这位老人的去世和前来奔丧不太靠谱的事:比如是相互问候,询问彼此的健康状况,推进脱贫攻坚情况,最近哪个人又升官了,哪个领导因受贿又被弄进去了,娃娃读书或考工作的事,天南海北地闲聊。
间或,还摆一点国际囯内时事热点……这时候,不管是讲话的人,还是听讲的人,个个都显得津津有味,喜欢这些聊资,到这里来的目的,仿佛就是在一起这样漫无边际的聊天。
灵堂里反而是空空荡荡,冷冷清清。除了摆放在两边的花圈,只有奶奶的几个儿女们守候在她老人家的身边。
后面陆续到来的城里亲戚朋友和同事也如出一辙,一种风格,同样是打一头,露露面,彼此见个面,你好我好地问候两三句话,打一声招呼,也就纷纷离去。
剩下的,越到后面,愈发稀少。
白天还是热热闹闹的场面,到了晚饭前就变得稀稀拉拉。
外面呢?门前多半的人早已经回家。留下的啤酒箱、空酒瓶、一次性纸杯、花生瓜子壳,等待我们去收拾。
前来奔丧的这些城里人,仿佛是山野上的一些鸟群,黑压压的一大群,铺天盖地而来,飞落到不远处的草地上,蜻蜓点水,眨眼间,又是一轰而起,飞走了,飞得无影无踪。目光里只留下一方空寞。
就在这时,一阵雷鸣般的哭丧声从殡仪馆的大门外响起,而且是迅速地向我们滚来。
这是来自山里的亲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男女老少皆有之。有的甚至哭得声嘶力竭。哭声响彻整个殡仪馆。
这是一条长长的、黑色的河流。
走进了,也看清了面孔。其中,有些是她老人家的亲弟妹,有些是她的侄儿侄女和孙儿孙女,有些是她的外侄儿外侄女或生前友好。
他们翻山越岭而来,费了几番周折而来,恍恍惚惚而来,怀着悲痛而来。
有的年轻人还牵着牛,有的牵着羊来奔丧。
黑色的河流涌至眼前,门前的人群猛然掀动,纷纷让岀一条过道,一个个以惊讶的目光,看着这条长长的、黑色的河流涌入灵堂,把老人的遗体罩得密不透风。
此时,整个灵堂变成了另一番场面,哭丧声震天,响彻灵堂,要掀飞屋顶。泪雨横飞,仿佛在平静的水面上掷进了一块石头,引起了层层涟漪。
此时,一个人的生命意义被人世间爱的哭声和泪水升华了,感天动地。
眼前动人的场面,从心底里勾起了所有此前在场的人的悲痛与泪水,也许是从灵魂深处也把老人家的几个儿女们感动了。他们这才表现出悲痛的样子,也这才开始呜咽地低声哭泣。
这时候,自己的泪水又一次禁不住夺眶而出。
已经是筋疲力尽的这些山里亲戚,女人们个个一直依在灵柩旁,守护着远房奶奶;男人们从灵柩旁退出来,一个个向其他前来奔丧的人递烟,敬酒,给人找座位,与人聊话。他们的主动与热情,让前来的人无不感到温暖,洋溢成一片浓浓的情意。
我看得十分清楚,从昨天到今早,远房奶奶的几个儿女们更多的时候在忙于敬酒,招呼应酬,安排来人的膳食。唯有来自山里的亲戚们一直是寸步不离地守护在老人的身边,直到天亮。
今天是齐人。自古以来,彝族人的祭奠仪式,齐人这天是高潮。
这些来自山寨,具有奔丧传统久远历史的亲人们,男女老少,一早就换上了自己随身带来的盛装,整整齐齐地排在路口,迎接姻亲家族和所有前来者。
到了夜里,有人通宵守灵;有人在哭丧。
这时候,所有在场的人在大厅里突然围成了两堆厚厚的人群,经过一番费力,挤进其中一堆,原来是有人把亲人们组织起来,排成长长的横形队列,由一个人领唱丧歌,就是唱送魂歌仪式,我们叫“策格”,边唱边左右摇摆,像是摇荡的波浪,舒缓,悠然,直到通宵。用歌声把老人的灵魂送回古老的祖居地。听得懂那些唱词的人,觉得无比动人。
夜深人静,遥远的天幕上唯有星星在闪烁,大地一片宁静,睡梦中听到悠悠远远地飘来这样的唱词,哪怕只有一两句,让人蚀骨销魂,甚至令人忧伤而流泪。
而另一堆人里,则分成两人一组,主人和姻亲家族两个阵营,进行格言谚语诵唱比赛,我们叫“物子勒”。这些格言谚语大都出自我们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其内容包括了天地演变史和百科知识。这样的比赛一问一答。类似于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的知识竞赛和答辩会。比赛采取淘汰制,看是谁懂得多,对答如流,诵唱铿锵有力,咄咄逼人,把对方说得问得言尽词穷,无言以对,谁就是属于最后的夺冠者。
摘去冠军者,在场的众亲们还会纷纷拿出钱,以三五百不等的奖金给予奖励,从此还会名声远播。
他日在这样的祭奠场合,有人会打听着前来聘请。
婚丧嫁娶的场合,无论是唱还是诵,山里的男人们每个多多少少都会露一手,甚至有的女人也有这样的爱好与本领。
“策格”还是“物子勒”都磁石般吸引了城里的亲人们,他们会被围成密不透风,身上堆满了城里人羡慕不已的目光。
换成山里,当东方露出鱼肚白,第一束阳光洒下大地,开始出殡送葬。
满地坐着黑压压的人群,静静地等候主人家分发属于绿色食品的祭牲牛肉,彝语叫“古次”,就是葬礼上的丧席。一会儿,一筐一筐的祭牲牛肉坨,热气腾腾地被年轻人们抬到人群中,每个人三五坨不等,外加一块馒头或一块荞粑什么的,很快分发到他们手中,这个老人的祭奠才算圆满告终。
可到了今早为远房奶奶出殡送葬时,看看周围这些送葬的人群,就像是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达到陕北的人变少了。坚守到最后,能坚持到今天早晨的亲人们稀稀拉拉,少之又少。也许这些才是亲戚中的亲戚,是精华。
人被抬去火化,这位老人身后,只有山里亲戚们荡气回肠的哀泣声,没有前扶后拥的亲戚前来为她告别送葬。
目送老人归天的亲人们,正站在原地,个个在心中疑惑,今天到底还举不举行“古此”仪式呢?
恰好这时,一个来自山村的亲戚问道:“今天还举行‘古此’仪式吗?”
“现在城里不太时兴这些了。”站在旁边的一位城里亲戚说,“照此下去,今后你们山上的寨子里有亲戚去世也会是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山村亲戚有点失望,自言自语,“我们这些亲戚,从小在外面读书,在城里工作和安家,条件越来越好,令人羡慕,但也离我们越走越远了!”
我想,山村亲戚说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中的“我们”指的是语言,传统习俗和思想情感的朴实与否吧。
旁边另一个山里亲戚接着说了一句“尔比(格言谚语)”译文是:“山上长什么样的草,羊就食什么。世上出什么样的规章,人们就用什么。”其喻意不言而喻。
随着火化房上冒出一阵滚滚浓烟,远房奶奶已化成了青烟,飘入天堂。
远房奶奶的亲人们都各自散去了。来自山里的亲戚们,离开了火葬地,走出大门时,一个个三步一回头,看似心欠欠的,仿佛有什么东西落在了殡仪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