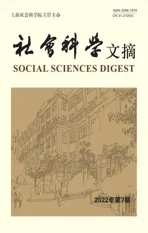担纲者的“类型学”:中国革命研究的新视野
2022-08-30孟庆延
文/孟庆延
问题的提出
马克斯·韦伯与陈寅恪尽管归属的“学科”不同,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各自的知识体系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各自研究都呈现出对在制度演化与文明演进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担纲者”群体的深切关照。
韦伯对古印度教展开研究时曾指出:古印度教的担纲者是一个具备文书教养的世袭性种姓阶层。他们并不出任官职,而是担负起作为个人及群体之礼仪、灵魂司牧者的功能。他们形成一个以阶层分化为取向的稳固中心,并形塑出社会秩序。只有具备吠陀经典教养的婆罗门——作为传统的担纲者,才是被认为具有宗教身份的团体成员。
同样,陈寅恪在对隋唐政治集团展开分析时,曾这样概括“关陇集团”:“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统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有同出一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是能内安反侧,外御强敌,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
韦伯与陈寅恪在研究中对“担纲者”的深入考察,对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就韦伯而言,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本质上乃是一种“比较文明研究”——他对古印度教、古犹太教、伊斯兰教、儒教及它们的具体担纲者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这些不同宗教的“神义”是如何在“担纲者”群体的精神气质与伦理人格上加以呈现的,借此讨论了诸文明缘何会衍生出不同的历史与制度形态。就陈寅恪而言,其总体问题意识在于理解从魏晋到隋唐的中古时期,中华文明应对外来宗教文化(佛教对儒家)和周边军事威胁(游牧尚武胡族)的双重冲击,不仅成功地保存和发展了中国文化,同时还在隋唐之际从分裂走向了统一。在这个问题意识之下,陈寅恪具体展开其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就是“社会集团”,无论是对“山东豪杰集团”的分析,还是对关陇集团的分析,实质都是对文明演进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担纲者的社会集团展开深入讨论,真正理解“制度”与“政治”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演化方向与运动趋势。
韦伯与陈寅恪在其研究中所呈现出的“担纲者”的研究思路,是他们留下的重要学术遗产。在历史社会学的理论视域下,就笔者所从事的“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这一研究主题而言,这一思路对突破目前研究中的碎片化与抽象化困境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将围绕下述问题展开具体论述。
其一,前文所述韦伯与陈寅恪研究传统中的“担纲者”其实质内涵是什么?如何理解这些经典研究中呈现出这样一种共通性的研究进路与研究风格?
其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碎片化”与“抽象化”的解释困境的本质是什么?“担纲者”的研究思路对突破这一阐释困境有何意义?
其三,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为什么要去识别关键的“制度担纲者”?这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构成中国革命研究的“新视野”?
被遗忘的“担纲者”:经典理论资源的当代意义
(一)“担纲者”、身份群体与类型比较:韦伯的历史社会学遗产
韦伯对个体社会行动意义的探究,构成了其比较文明研究的基础,并通过对有着共同精神气质的“担纲者”群体的考察实现的。例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勾勒出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新教徒的典型精神气质。在韦伯笔下,正是这样一群“担纲者”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承载者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担纲者”——清教徒努力挣钱这个行为的意义并不在于享乐,而在于践行“天职”的宗教神义。
在韦伯笔下,“担纲者”所具有的行动意义构成了群体性的精神气质,并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构成了“选择性亲和”的关联。韦伯的分析思路贯穿于他对世界诸文明的分析。例如在分析中国文明时,他将儒家理解为一种宗教形态,而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体系中的官僚士大夫,则构成了这一“宗教”的重要“担纲者”。韦伯认为“士人”阶层的精神气质与群体人格实质上对于理解中国文明及其历史演进趋势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个阶层的宗教的等级伦理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个阶层本身,它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韦伯所谓的“担纲者”乃是一种具有独特伦理人格与生活样式的“身份群体”。在韦伯的社会学传统中,“身份群体”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概念,它是不同于“阶级”概念的存在,因为阶级乃是指“处于同样阶级状况中的所有人”;所谓“身份群体”,其形成基础既包括某一群体所特有的职业类型与生活方式,也和他们所具有某种世袭的血统和身份有关,亦和这一群体所受到的教育与经验式的训练有关。综上,韦伯在其比较文明研究中所涉及的“担纲者”恰恰就是在“身份群体”这样的基础性概念之上产生的,它是一种叠合了宗教信仰、生活样式以及受教育经历等诸多要素的复合概念体系。
(二)“担纲者”、社会集团与源流研究:陈寅恪的历史社会学启发
陈寅恪的社会集团概念,首先涉及民族(胡汉)与血缘世系,进而以此为基础呈现某一社会集团所具有的“民族性”与群体特质。这一点在他对关陇集团的分析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陈寅恪认为,关陇集团是理解隋唐政治变化的关键,而所谓关陇集团,乃是于南北朝时期宇文氏建立北周之后开始的“关陇本位政策”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集团。南北朝时期,宇文氏为了对内巩固自身在关陇这一胡汉杂糅的区域维持有效统治,对外可以集中胡汉两族中精干力量形成军事优势而采取的政策,此政策形成了一个超越单纯种族与地域的“关陇集团”,李唐皇室以及唐中期之前的主要文官武将皆起源于这一集团。因此,它是一个胡汉杂糅,以胡人文化为主,同时吸纳了汉人部分文化的社会集团。
陈怀宇曾经指出,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受到了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因此我们看到,在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中,“社会集团”具有了“身份群体”的概念内涵:这一地域—血缘—民族—习俗的社会集团概念,最终是以“生活样式”以及整个社会集团的性情倾向将精神气质呈现出来。
综上,无论是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传统,抑或是陈寅恪的史学研究脉络,都对于“担纲者”和“社会集团”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它们尽管不尽相同,但是内在意涵是一致的:无论是“身份群体”还是“社会集团”,都构成了理解文明演进与社会变迁的关键“担纲者”群体。由此,我们才能看到韦伯笔下不同文明的演进路向,也才能理解在胡汉融合、佛儒交汇、中原板荡的历史情境下,隋唐时期的华夏文明究竟是如何在具有不同精神气质的“担纲者”的实践中,渐渐生成新的文明性格与文化气象的。他们的研究在不断提示我们,在回应制度、文明的生发、演化此类问题的时候,要充分注意那些起到关键作用的“担纲者”,这恰恰是目前有关中国革命研究所面对的核心问题。
“担纲者”:具有总体史意义的行动者
无论是韦伯还是陈寅恪,他们对“行动者”的选取并不是随机性的,而是带有明确的“指向性”——这个指向性并非意味着研究者的个人好恶,而是建立在对“担纲者”所具有的“总体性”的判断上。具体到本文的讨论主题而言,这里所谓的“总体史意义”就是指中国革命的研究,需要研究者不断通过对史料的细致爬梳,去识别那些在历史演进、制度发生变化的进程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担纲者”群体,并通过对他们精神气质的勾勒与描摹,理解这些“担纲者”本身所具有的性情倾向、实践方式与总体制度变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应星等学者近年来以中央苏区时期的政党革命实践为主要聚焦议题,以“制度源流”为核心问题意识的一系列研究,内在蕴含着“担纲者”的理论视角。
(一)组织形态的承载者
应星近年来的研究,集中在对民主集中制的发生学问题上。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政党,在建党初期就开始从苏联的革命实践进程中不断汲取经验,将俄共(布)的民主集中制作为自身的组织制度,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结合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做出调整,进而在复杂而漫长的革命实践进程中完成了制度的创设、调整与定型。由此,他集中对中央苏区时期的万安暴动等事件展开了历史社会学分析。而苏区时期的江西,乃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最初付诸革命斗争实践,并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分化机制与传统社会结构相结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构成了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形态的发生学情境。
应星通过对万安暴动的事件社会学分析,实质上揭示了以曾天宇为代表的一类地方干部典型的精神气质,由此去理解他们具体的革命实践形态。这一分析路径,突破了“权力—利益”的阐释困境——他所揭示的具体历史情境下的一系列张力关系,恰恰是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完善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制度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作为地方干部的“担纲者”曾天宇,对于理解民主集中制的发生学,也就具有了“总体史”的意义。
(二)国家与社会的联结者
中国共产党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做出具体的调整与创新,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与当时的苏联社会有着诸多结构性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不像苏联那样,已经有了相对成熟和强大的产业及工人队伍,在当时工业化程度较低的中国社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构成了建党之初党的骨干力量。由此,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在建党初期和革命年代通过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这个主要“担纲者”群体将马列主义思想传播到基层社会大众层面的?他们自身的群体特征又如何影响了政党最初的组织形态构建?
应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其有关江西早期党组织发展的研究中提出了下述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学校成为革命的策源地?又是什么样的学生成为当地最早的革命者?这些学校和学生是如何构建起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网络的?他充分结合地方社会史的相关材料,分别以当时的南昌二中及其改造社、南昌一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两个不同类型学校的研究,揭示了在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群体在不同学校就读建立基层组织时所呈现出来的组织方式与组织形态上的差异,进而揭示了这种差异又和不同“担纲者”的“精神气质”的差异有着怎样的关联。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寻找关键的“担纲者”群体,对于理解组织形态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涵。
(三)政治传统的缔造者
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中,颠覆不合理的阶级结构与社会结构,亦是革命的重要目标与内容,而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下,这一目标与内容又集中在体现土地革命的进程中。近年来有研究者围绕土地革命中的“阶级划分”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政治传统的发生学研究。
首先,笔者曾经在研究中指出,“阶级”并非传统中国社会内生性的社会分化机制,在以血缘、地缘和土客关系为核心分化机制的传统中国社会中,阶级理论亦是作为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的。那么,这样一种外在的理论知识又是如何演化为在实践中作用于地方社会的政策的?何种类型的革命干部在阶级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呢?笔者通过对以王观澜等为代表的早期技术干部的生命史与精神气质的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回应。此外,强调激发群众主观情绪的动员方式,亦非无本之木,它是在彭湃所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形成的,这与以彭湃为代表的早期从事农民运动的干部的思想倾向和实践方式又有着密切关联。最终,上述两种不同的组织动员机制在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历史实践中汇聚起来,最终构成了毛泽东农村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革命政党推进土地革命的重要组织机制。笔者通过对“技术干部”与“农运干部”这两类“担纲者”群体的精神气质的系统考察,揭示了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思想资源、实践方式与组织动员机制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对“制度”与“制度担纲者”的发生史进行了重新书写。
总结与讨论
笔者强调将经典研究传统中的“担纲者”概念带回来,对下述研究主题做系统回应:作为“制度担纲者”而存在的那些关键行动者与制度精神、制度实践形态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内在关联,以此拓展对中国革命这一宏大议题的理解深度。最后,笔者尝试围绕“担纲者”这一理论概念的实质意涵及其实践可能做简要的讨论:
其一,作为“担纲者”的行动者,是理解制度发生的关键切入视角。制度如何生成,又为何在某些关键的事件节点出现某种“突变”,在这背后,究竟是何种类型的行动者在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这样一种从制度发生学角度出发的问题意识长久以来处于被忽视的状态。由此,重启“担纲者”视角,有助于我们更为整全性地认识制度的发生学过程。
其二,作为“制度担纲者”的行动者,是在“群体气质”与“制度精神”之间建立关联的重要中介机制。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在不断地提醒我们,社会学所追求的,乃是对行动背后的意义的阐释;而“担纲者”作为理解文明形态载体的重要“介质”,其精神气质与生活样式恰恰构成了意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同时也是已经高度组织化了的社会行动,其内在蕴含的意义系统又体现在经由革命而创生出的新制度的“制度精神”之中,若要理解制度内在蕴含的理念形态,我们必须重视对关键“担纲者”的精神气质展开深入分析与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