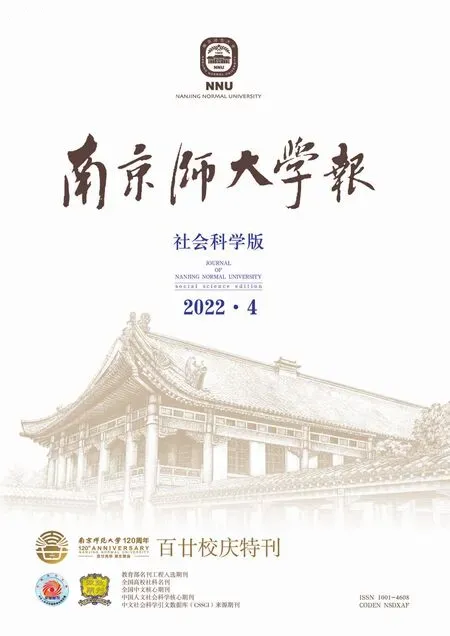论汉字神话学
2022-08-29骆冬青
骆冬青
“文心雕龙”,此名何意?不妨像读“武松打虎”一样来读,那就是“(文)心”(主语)雕龙(谓语)。(1)按:关于《文心雕龙》书名,有种种说法。此处,强调的是“龙”,认为此名之落脚点是神话中既有形而又无形的“形而上”的神龙。英译中,往往作并列结构“文心和雕龙”,译作: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杨宪益、戴乃迭译作:Carving a Dragon at the Core of Literature。俄译者理解的《文心雕龙》,为“在文字的心中雕刻龙”“在词语心中雕刻的龙”“文学思想的雕刻的龙”“文雅词语的心与雕刻的龙”。(见[俄]玛丽娜·克拉夫佐娃、李逸津:《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心雕龙〉词条译释》,《语文学刊》2019年第3期。)“虎”是实有的动物,打“虎”,是人对于动物的应急暴力反抗——虽然,大多数人,在力量上,是无法抗衡虎的。雕“龙”,何为“龙”?一种神话中想象的动物,是灵物,是神灵,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2)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99页。所谓“古来文章”,其实针对的乃是当时的“以雕缛成体”的观念,在此语中,却是让步,却是否定的对象;“岂取”,古人所不取,乃作者所必取:是“驺奭之群言‘雕龙’也”。与“雕虫”的“雕缛”不同,是“(文心)雕龙”!重点落在“龙”,那个想象的、抽象的、灵性的、华夏图腾的“龍”。故书名《文心雕龙》,乃在于构建一个心灵世界,那是像“龍”一样生活灵动的“文”,那是心灵中刻画(雕)的龍!什么是“文”?“雕龙”之“文”,那是“物象之本”,是“错画也”,是图象;在“文心”中,指的是“连属文字,亦谓之文”,(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3页。是“文字”之连缀所成。刘勰曰:“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4)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下册),第1898页。是以“汉字图象”之“心”去刻画那个想象中的神性的龙。
“龙”这个汉字图象,才真正刻画了华夏文化中的那种神性的灵物。汉字与神话,由此紧密相连。由此字即可见,汉字与华夏神话,均和上古史、考古学、艺术学以及古生物学、古天文学、古地理学等等相关,但是,神话时期的精神形态,却是以汉字图象的形式凝聚在文字中。现代文字学之一大契机,得益于一大奇迹,那就是甲骨文的发现,甲骨文正是与神灵对话的文字。现当代学者中,已有一些关注到汉字与神话的关系。从王国维到闻一多、丁山、吴其昌、陈梦家等,均有论及;日本学者白川静、美国学者艾兰、法国学者汪德迈等,也多有论述。这些学者,对神话与古文字的关系,均有所悟,在研究中也有一些发现和发明,取得许多成果。但是,却未曾提升为一种强烈的意识,那就是,文字创生于神话时代,乃至文字创生本身也依托神话,文字乃神性活动的重要构成部分;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金文,以及战国文字,均与神话有着深刻的亲缘关系。因此,汉字研究中,需要彰显神话学意识。如此,将令“说文解字”拥有更为深广的原初语境,汉字哲学、美学可开辟新的智慧境域,汉字研究或可具有更为博大的思维背景,而中国神话学亦将发现更为高远的汉字学空间。在前汉字时代产生的神性意识和神性叙事(“话”),存在于汉字的创造中,让我们可以寻回失去的世界。汉字神话学,其落脚点在于汉字,在于汉字如何被历史学(训诂)、哲学(经学、小学)所驯服,失去了灵性神性。可是,从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中、从考古发掘的文物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回那个漫天神灵的世界,因为,正是在汉字中,一切端倪和轨迹均班班可考。那时的人类与神类、万类的一切,均成为远古化石,凝固在汉字之中。如何从中唤醒那些活灵活现的幻象和心象?汉字的初文,是否可以寻觅?
由此更可以思考:汉字创生,是否依靠神性思维的逻辑?“六书”之前,汉字图象的构造,依循什么原则?华夏文明中的文字谱系,与华夏神话中的神谱有何关系?如此等等,均应在汉字神话学的思考中逐步显明。
一、 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神灵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5)[德]马克思:《马克思博士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贺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马克思的这一名言,将神话纳入了哲学,将神变成了人——却是具有崇高人格的“圣者”、“殉道者”。也将神话写进了“日历”,普罗米修斯神话于是标记在人类历史的历书上,成为不朽的哲学事件、美学事件。而“普罗米修斯”这一名字,也凝为概念,成为电子芯片般集合着诸多意念的存在。马克思给出了对神话智慧的哲学理解。
“禹是一条虫”(6)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9—66页。。顾颉刚之论断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神话的尊严,剥离古史中神话的冲动竟然是从文字训诂获得灵感,清除中国文化中神话英雄的历史存在,将禹从神、人降为虫,是否消解了华夏精神的历书中同样堪称“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意义?
司马迁撰著首部中国通史《史记》,首先面临的史学难题,无疑是上古历史中的神话传说如何书写。“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那种“野性的思维”,那种“邃古之初,谁传道之”,在经学、神学业已成形的汉代,更是从“天问”永久的怀疑,变成了理性上“难言之”的内容。不得不说,司马迁乃“疑古”学派的最为重要的思想根源。被《史记》“隐去”的、删削的“不雅驯”的东西,其中当有许多神话传说。历史的日历,哲学的日历,与美学、艺术的日历,就这样错开了道路。有“层累的古史”,其实更有久经失去的“层累地消失”的古史——自《尚书》“重黎绝地天通”,来自“天”神的世界只留下了恍恍惚惚的幽灵,如何寻回那逝去的“民神杂糅”的世界?尤其中国文化中神话历史化的过程,将神话作理性重释,要寻回神性世界,更需别辟蹊径。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灵悟:“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神灵”(7)[法]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1页。按:此处采取于坚译。。我想,从汉字寻回神性世界,乃重要途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8)陈寅恪:《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72页。“文化史”中,却无论如何不可缺失“神话史”:神话所描述的历史,和神话本身的历史,以及成为“文化”起始处——其核心乃是哲学——的神话史。也就是说,神话先于“文化”,是文化的基因,“文化”将神话“化”在自身中并逐渐降低其地位,乃观念的变迁使然。所以,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神灵,比每个汉字都是一部文化史,具有更为本原、本质的意义。“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4页。童年时代,总是有着记忆混沌模糊却异常温馨、异常蛮野、异常光怪陆离,却又生机勃勃的朝霞绽放的光景,更是精神活力“最完美的地方”。人类童年时代,乃神话阶段,或曰神性时代,正是永不复返却又无法忘却的具有“永久的魅力”的时光。其印迹,不仅蕴藏在考古文物和文献中,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更体现在汉字这一最珍贵的活化石中。历史、文化在积累的同时,也常常在失去。其中,有意识形态、王朝更迭的原因。而前文字时代,神性时代,则是因为缺少纪事的媒介,而在之后的文字中刻镂下一些痕迹。
找回失去的世界!——柏拉图的理念论(相论),说“知识即回忆”,假定“相”是先天存在,可以通过“学习”来“回忆”,将“相”寻找回来。“相”或译“理念”、“理型”、“理式”,无疑具有视觉隐喻,与汉字作为“文”字有某种相契。对于那个神性世界,毕竟,“普罗米修斯”需要“写”到“哲学历书”上,书写的文字,尤其是汉字对神性世界、对神话的特殊书写,包孕着无穷奥秘。语言与文字是如何产生的,是难解甚至无解的问题;但是,在语言中“叫”出“神”,甚至以文字“写”下“神”名,无疑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对着某种崇高的、超验的力量,喊出一声“天啦”,虽然不会“石破天惊”、“异想天开”,但是,却让我们与那种神奇的力量蓦然对接。若是“写”下这个“字”,则无疑具有了开天辟地的神圣力量。
确实,汉字“天雨粟,鬼夜哭”的神话,需要将汉字本身放回那个远古的神性世界中,或可“望文生义”——从汉字之“文”、“字”,审察其原初意义。
有意思的是,顾颉刚论“禹是一条虫”,所得到的一个反驳,便是被指责为“望文生义”:“最奇妙的是先生因《说文》禹字训虫便以为禹不是人类,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这般望文生义的解释,如何叫人信服呢?”(10)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第94页。有人指其根柢在于:“这种《说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会,真是奇得骇人了。”(11)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疑问》,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第87页。柳诒徵在《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中说:“比有某君,谓古无夏禹其人,诸书所言之禹,皆属子虚乌有。……以《说文》证经考史,必先明《说文》之谊例,不明《说文》之谊例,刺取一语,辄肆论断,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12)柳诒徵:《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6—69页。一说顾颉刚是《说文》迷,一说顾颉刚“不明《说文》之谊例”,《说文解字》乃讨论的一个核心。但是,文字学以及古文字,却往往在讨论中被置为并不重要的地位,其要义,乃在古史观,乃在古史与神话的关系。
“古史辨”,“辨”字表明,顾颉刚先生要从古史中剥离神话的意识。这种意识却是通过文字学而彰明较著。在论述“禹的演化史”时说:“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13)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页。着眼于古史,着眼于理性的历史,必然要将“禹”从历史中还原,或排除。这与当时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尧舜抹杀”论也有相似的思路。“茫茫禹迹,画(划)为九州”,走遍九州的禹迹,竟然是蹂地的“兽足”,无论如何,却是令人骇怪。
从传统观念看,“禹是一条虫”这个似乎荒诞的论点,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令科学的历史理性更加清醒。顾颉刚是一个历史学家,在重审古史时,强调剥离“层累的古史”中的神话,是有其卓见的。另一方面,“古史辨”中,却也显示出他具有的神话意识,乃至神话研究的鲜明意识,将神话(故事)与古史切分,反而让他重视神话传说。但是,古史与神话在“民神杂糅”时代,其实有着无法剥离的血肉联系,正如即使现代社会,也无法剥离神话,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也会被神话。所以,顾颉刚的这种论述,又难免执着于两分。顾颉刚云:“言禹为虫,就是言禹为动物。看古代的中原民族对于南方民族称为‘闽’称为‘蛮’可见当时看人作虫原无足奇。禹既是神话中的人物,则其形状特异自在意内,例如《山海经》所说‘其神鸟身龙首’,‘其神人面牛身’都是想象神为怪物的表征。这些话用了我们的理性看固然要觉得很可怪诧,但是顺了神话的性质看原是极平常的。”(14)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225页。顾氏在文中对禹的性质下了一个假定:“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社神(后土)。其神职全在土地上,故其神迹从全体上说,为铺地,陈列山川,治洪水;从农事上说,为治沟洫,事耕稼。”“又因当时神人的界限不甚分清,禹又与周族的祖先并称,故禹的传说渐渐倾向于‘人王’方面,而与神话脱离。”“《周颂》三十一篇没有‘禹’的一字,那时人竟没有禹的伟大功绩的观念;一到穆王末年的《吕刑》,禹就出现了;到西周后期,社祀也举行了,《大、小雅》及《商、鲁颂》屡屡把禹提起,看得他在古史中的地位是最重要的了。”(15)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114、114、127页。冀朝鼎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文论著中,对顾氏的见解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和很高的评价:“对于禹的问题,顾颉刚的见解是,禹是在大约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殷、周期间,流传于长江流域民间神话中的一个神。而这个传说,看来先是集中在现在的浙江省被称为绍兴会稽一带发生的。越人崇拜禹,把禹作为他们的祖先,并认为他的墓地就在会稽。这个传说由会稽传到安徽省的涂山,并认为禹曾在涂山召集过诸部落的首领开过会。后来,又由涂山传到楚(今湖北省),由楚传到中国北部”(16)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朱诗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0页。。冀朝鼎对顾颉刚的肯定,得到了后来地质学、地学史、第四纪学、考古学等学科的证明。现在,良渚文明的发现,对证明顾颉刚的说法也有帮助。但是,禹毕竟是个神话人物,“中原的汉族虽然把这位越族传说中的伟大人物据为己有,但是他们显然留有余地,设法在这种传说中添枝加叶,尽量布置一个结局,让这位从越族中硬拉过来的人物,最后仍然回到越族中去。这就是权威的史书《史记·夏本纪》中所说的:‘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史记·越世家》又说:‘越王勾践,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17)陈桥驿:《吴越文化和中日两国的史前交流》,《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这又赋予了这个神话以历史性和科学性。



那么,这个禹,或者正是神话中的句龙,亦即禹龙。在此字中,即凝缩着一些神话,如《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归藏·启筮篇》“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之类。鲧作为鱼族,鱼化龙,乃《庄子·逍遥游》中首出意象。这个像生命精子般如蛇如龙的精灵,却也隐喻着汉字创生的奥秘。
大禹作为中国文化中“最高尚的圣者”和“王者”,亦如普罗米修斯一样,以名字留存于万世。不过,不一样的是,在“禹”字本身的汉字图象中,即芯片般集聚了神话,集聚着神话所凝集的精神意识乃至集体无意识。
“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神灵”,不过,她是以图象方式活灵活现地生活着的神灵。这些神灵有着自己的谱系,有着自己的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但其根柢在于汉字图象。
二、 形象、宪象、法象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已经是哲学化的思想。“道”置“名”前,就哲思而言,或许合适;但就人类原初智慧而言,则对于神灵的意识,或神灵的呼唤,必在“道”前。甚至,这种呼唤所依凭的“名”“字”,乃是最为根本的。“道”之为“名”,即如是也!
所以,“名可名,非常名”,最初的“非常”,乃神也。名可名,神命名;名可名,神之名!从“可名”,到“有名”,这是一个伟大的飞跃。《圣经》神话中,是耶和华给万事万物命名。那么,在“命名”之前,语言何在?这是永恒之谜。人类只能归之于神类。说出“要有光”的毕竟是创世的神灵。似乎,在有“言”之前,神天然具有语言能力。最初的“以言行事”,是以神灵之“口”出的语言而行事。这一创世事件,同时也是一个“语言事件”,语言创世!看似荒谬,却将语言与神灵同样视作超验存在,将一种介质,那一伟大的“命名”工作,赋予一种制序的神秘。而“历史便被看做是命名的完成”(22)[德]汉斯·布鲁门伯格:《神话研究》,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页。,神话所开启的原始的命名起源的故事,到了人类历史叙事中,成为一种确定的事实。
可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神话,均从混沌中,忽见“仿佛若有光”,然后,才有了人类本身的创生。世界各地神话中,有着不同的源头。在最终成形的关于语言的神话中,可以分作两种模式:一是西方模式,德里达所谓“声音逻各斯”;一是象形文字模式,或曰中国模式,乃“图象逻各斯”。图象逻各斯以视觉思维为主导,声音逻各斯则凭借听觉;光速远高于声速,闪电先于雷声。图象模式中,“要有光”,令人类语言从声音外开辟了新境。汉字的图象思维,将其精神追抵复杂的生存根源——混沌着一切感觉,却又有了某种意象,是先于语言和逻辑的存在,是人类在生存境域中以形象为核心的现象学直观。正如伊利亚德所说:“形象、符号、神话并非一些与心理无关的字眼,它们满足了某种需要也完成了一定的使命:揭露最隐秘的存在形态。”(23)[罗]米尔恰·伊利亚德:《形象与象征》,沈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年,第5页。须知,在汉字中,形象、符号和神话,均是极为重要的构成元素。形象将神话转变为符号(Symbol),成为深层意义上的象征(Symbol)。在人类远古,诗、乐、舞三者本为一体,均是为“神”而“作”,凝定为文字的“诗”为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经”。当然,在其他文化中同样如此,不过,其记录却未必相同。海德格尔说:“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绝不是任意的道说,而是那种首先让万物进入敞开域的道说,我们进而就在日常语言中谈论和处理所有这些事物。所以,诗从来不是把语言当作一种现成的材料来接受,相反,是诗本身才使语言成为可能。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Ursprache)。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反过来要从诗的本质那里来理解语言的本质。”(24)[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6页。“诗”即源于混沌、包含混沌的道说,但是,斫破混沌却仍然靠“诗”,靠神性的言说。故海德格尔说:“作诗是对诸神的源始命名。”(25)[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49页。那么,汉字是如何为“神”原始命名的呢?

“图象先于声音”(28)骆冬青:《图象先于声音》,《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以此忽然一道电光闪耀,在天空被电光撕裂,诘诎伸展之际,古人忽自天象中悟到了神灵境界。神之无形以抽象的形状显示,而此抽象之形状,却具有极大的意义张力。与人体之屈伸无关?却似乎相关,甚至可以从中审视出舞蹈之象。电闪雷鸣,闪电刹那即逝,更增神奇。以“申”为天干地支,则是古人仰观天象所得天“文”的铭刻。故“天神引出万物”,虽然是后来的追认,却道出了集体无意识的遗存。而这是汉字图象述说的神话。所以,语言,不仅与声音有关,更与图象有密切联系。象形文字,或曰图象文字,看似为语言的辅助,语言的另一种表述,却具有了另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在神性世界,被推为超验的存在。法国汉学家汪德迈认为:“中国文化的心是‘文’。”(29)[法]汪德迈:《跨文化中国学》(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第154页。我认为,此“文”即许慎《说文解字序》所指出的“文者,物象之本”,是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孳乳浸多的“字”之生长基因。总之,是天文、地文、人文,更是其总源头——“神文”。这些后世以为乃仰观俯察远近摄取而垂为“宪象”的“文”,其原初却是神示的“神文”。“一个完整的神话记录在我们的语言之中。”(30)[奥]维特根斯坦:《哲学语法》,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03页。所以,可以反观“我们的语言形式中的神话。”(31)[奥]维特根斯坦:《哲学语法》,第302页。不过,在汉字中,却是以汉字图象和语言图象记录了文字形式的神话。西方哲学重视的语言,在中国哲学中,则更应当重视“文”,其本义即“汉字图象”这一中国文化之“心”。
最初的神性记忆,仍是以汉字图象的形式记录下来的。那么,如何确定神话时代与传说时代的分野,是一个颇为困难的问题。“殷商传说时代的历史,似乎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自‘契居蕃’起至示壬示癸止,神话多而史实少,也可称为‘神话时代’;后期自成汤居亳至盘庚迁于北蒙止,有传说的史实未获得地下文字直接的证明,与武丁居商以后的文物之盛,截然有辨,所以名之为传说时代。”(32)丁山:《商周史料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9页。我想,在良渚文明、三星堆文明考古已发现相当丰富成果的当下,丁山的结论或许需要改写。但是,对于史料、考古与神话的相互印证,却是颇为重要的思路。
现代科学以光年量度天文距离。远古的时光,竟然可以从天上的星光中遥遥感应。神话时代并未远去,不仅那些思维方式、精神意蕴仍然在人类意识深处起着重要作用,而且那种原初的、无羁的创造精神,更是永远激荡着人类的想象。中国文化中,有着“河图洛书”神话,将图象意识推至先天、先验乃至超验的维度。确实,相对于天地自然,人类的历史渺不足道。这是神性意识最初的源起。在这一意识中,华夏文明最初的重要发现,便是“文”,便是“形象”、“宪象”,便是“法象”。
“神”字的产生,或许即来自电光石火之间的顿悟,那是来自天上的灵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又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於地”。法、象取自《系辞》,“法”即朱子所谓“造化之详密可见者”,“象”即“造化之至微无形者”。(33)朱熹:《周易本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29页。后世概括的“法象”,已经具有浓厚的哲学意味。许慎《说文解字序》中的仓颉:“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而神话中的仓颉,自是以《淮南子》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最为著名。纬书《春秋元命苞》中,仓颉“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两个仓颉,一个似乎是哲学家,另一个似乎是天神。维柯《新科学》以“三条真理”解说语言和文字的起源:“(1)既已证明了最初各异教民族在开始时全都是哑口无言的,他们表达自己的方式就必然凭一些和他们心中观念有自然联系的某种姿势或具体事物。(2)他们必然用过符号来固定他们的地产的疆界,并作为他们的权利的持久见证。(3)他们必然都用过钱币”,为此,“我们在这里必须推翻某些埃及人所持有的那种错误见解,认为象形文字是由哲学家们发明的,用来把他们的高明的玄奥智慧隐蔽起来”。(34)[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18页。维柯的《新科学》中,关注到“中国人至今仍用象形文字书写”(35)[意]维柯:《新科学》,第220页。。最初的文字所写,是诗性的语言,先由神的和英雄的两种字母构成,后来用土俗语言表达,最后用土俗字母书写。维柯的思想中,仍是“声音逻各斯”占据主位。但是,他关于单音词的理论,关于语言从象声、惊叹、代名词、小品词,到逐渐形成名词、动词的理论,均蕴涵着深刻的见解,似可在某种意义上解决汉字单音节的问题。尤其是,维柯所谓“心头词典”(Mental Dictionary)说法,将语言中的“心头”与“外头”,似乎共有的“神”——“思想”、“精神”、“观念”——联系为一。“每种语言都各用和自己同时发展起来的字母或文字,不过三种语言开始时就有很大的差别:神的语言是几乎无声的,或只稍微发点声音;英雄的语言开始时是有声与无声的平均混合,因此就是土语和英雄们用来书写的文字——即荷马称之为semata[符号]的二者的混合;至于人的语言则几乎全是发音的,只是有时发音较轻或是哑口的。”(36)[意]维柯:《新科学》,第229页。希腊神话中,是卡德茂斯神把字母带给了希腊人。神,教会人写“字”。

“天文”乃象,象即“造化之至微无形者”;“地文”乃“形”,形即“造化之详密可见者”。庖羲氏却能够仰观俯察,“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宪象”即“法象”。被理性化、“哲学”化的文化英雄,褪去了神性、诗性,宪象、法象、形象之中的灵魂——“神”,却并未消逝,仍然是汉字图象作为表“意”文字的精神创造的根柢。
三、 神话赛博格
天象无形,且多变易。在无边的黑夜中,天空给人神奇的想象,正如在白天大地万物呈现出“适我无非新”的万千形态。“天阙象纬逼”,似自逼近的交错星象中,感觉到上天的某种无言的语言。这正是维科所谓“神的语言”。“文”与“语”建立的“不二”关系,正应由此感悟。“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其实,天上“人”之无声“语”,最初惊动“天下人”的,或许乃是“星象”。
闻一多解《易·乾卦》“龙”(龍)曰:“《乾卦》言龙者六,(内九四‘或跃在渊’虽未明言龙,而实指龙。)皆谓东方苍龙之星,故《彖传》曰‘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史记·封禅书正义》引《汉旧仪》‘龙星右角为天田’。九二‘见龙在田’,田即天田也。《说文》‘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亦谓龙星。九五‘飞龙在天’,春分之龙也,初九‘潜龙勿用’,九四‘或跃在渊’秋分之龙也。《史记·天官书》:‘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星,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是龙欲曲不欲直,曲则吉,直则凶也。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亢有直义,亢龙犹直龙也。群读为卷,群龙即卷龙,《诗·九罭传》‘衮衣,卷龙也’,《说文》‘衮,天子享先王,卷龙绣于下幅,一龙蟠阿上乡’。卜辞龙字或尾交于首,屈身如环,殆所谓卷龙欤。卷龙其状如环无端,不辨首尾,故曰无首,言不见首耳。龙欲卷曲,不欲亢直,故亢龙则有悔,见群(卷)龙无首则吉也。《易》义与《天官书》相会。《乾卦》所言皆天象,所谓‘仰则观象于天’者是矣。”(37)闻一多:《古典新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92页。朱芳圃曰:“按闻说精确不移。古人察星之形,详星之势,与物彷佛,即以其物名之。东方七宿合为一象,因角为龙角,心为龙心,尾为龙尾,故曰苍龙。后人不瞭龙为神化之巴,又混星宿取象之苍龙为一谈,因而徜彷迷离,成为神化莫测之物矣。”(38)朱芳圃:《朱芳圃文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30页。
不过,说甲骨文与苍龙星宿是“象形”,倒是有些疑问:苍龙星宿的“形”乃极度抽象,是以“意”连缀起来的天“象”,是只有星星点灯般闪耀着的“造化之至微无形者”,将其连缀为“龙”的,本身已经是心中有“象”,故能够将上天的星星以无形的线条相连。也就是说,这一“天象”,只有来自神性的心灵,才可“看”出来。能够看出变幻莫测的“神龙”之后,不变的“龙”之图象,只能是某种神性的灵悟的眼睛。
“在天成象”的神灵,赋予人类仰观天文的眼睛。这种目光,是可以划破天幕,在天空进行几何学连缀、思考的神性的精神。本来“至微无形”,却因为成“象”而得彰显。这是汉字图象由图——星图——而成为“象”(星象)的心灵历程。这一历程,乃是人类在神话时代的某种“科学”研究的领悟。“仰则观象于天”的“观象”,投射了多少精神意象的思索和观念的凝结,正是从神话中,方可得到审视。
其实,“天象”所启示的图象抽象能力,在“六书”所谓“象形”乃根本能力,是“六书”结构汉字图象之“神”。“依类象形”也好,“物象之本”也罢,均需要有“类”“本”的精神意向作根柢。“在天成象”的“龍”,却“在地成形”,需要充实为肉身。也就是说,将天幕上点状分布的星星,凭空连上虚线,连缀成为苍龙,是一种特异的“表象”能力,这种能力无以名之,最初只能归于“神”性。而人类如何“表象”那些“神物”?于是,从“在地成形”的地球引力,赋予其肉身;但是,毕竟是“神物”,既有肉身,又要飞升,所以,这只肉虫,又有“夗转飞动之皃”。不过,仍然是文字图象,是“夗转飞动之皃”,取其“神”态的手段,还是“象”,另一种抽象。
康德哲学中,认为“空间是一个必然的先天表象,是一切外部表象的根据。我们决不能形成一个表象,认为没有空间,虽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其中没有任何对象”(41)[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73页。。又曰:“在空间方面,一切关于空间的概念都以一个先天的直观(不是经验的)为基础。因此,一切几何学原则,例如三角形的两条边加起来大于第三边之类,也决不是从线和三角形的总概念推导出来的,而是从先天的、具有必定确实性的直观引出的。”(42)[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74页。在远古,这种先天直观,无疑是神性的能力。“在天成象”的几何学表象能力,必加上“在地成形”的生动活泼的肉身化,由此,“龍”才能够具有“形象”,成为“法象”,定为“图象”。此“龍”之两种字形,一是极具抽象变化的“星象”,经由“心象”,又有了某种可以感触的形态,夭矫变易,恍恍惚惚,见首不见尾,成为“神物”。“龍”正体现出卡西尔所说的神话仿佛具有的一副双重面目:“一方面它向我们展示一个概念的结构,另一方面则又展示一个感性的结构。”(43)[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我以为,概念结构,展示其神性;感性结构,展示其人性。康德的概念与直观、先验感知与感性经验的结合,在卡西尔这里,成为神话的重要特点。但“结构”一词,则以“图象”概括了“龍”这一汉字的超越性。
于是,虫、星、龙,以几何学直观与感性经验的统一,而成为一种具有神话逻辑的交合。神性思维中蕴含着科学思维的基因。汉字图象中,包含着超越语言的内容,那是原始时代天文与神话的有些模糊的面庞,透过光年向着我们投以感性的魅惑。卡西尔说:“语言与神话乃是近亲。在人类文化的早期阶段,它们二者的联系是如此密切,它们的协作是如此明显,以致几乎不可能把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它们乃是同根而生的两股分枝。不管在哪里,只要我们发现了人,我们也就发现他具有言语的能力并且受着神话创作功能的影响。因此,把这两种人类独具的特性归之于同一渊源,对于哲学人类学来说,是颇有诱惑力的。”(44)[德]卡西尔:《人论》,第172页。语言与神话归于的同一渊源,我以为,乃是“象”。“龍”这一汉字图象,恰好将语言与神话归为一体。“禹”是一条虫,还是一条“龍”?姑且放下,但“禹”字却是一个神话中的“神物”。
汉语中,植物、动物、人物、神物,似乎都是“物”,都是有着生灵的器物。《周易》曰“观象制器”,“制器尚象”,均将“象”与“器”相连。原始的刻画符号,原始图案、图纹,似乎均是“物象之本”的极其抽象的“文”。制器,乃几何学思维与技术思维的结合,但其冲动却来自神性的直观。远古器物中,事神的,或神之用器——神器,乃大宗。即使后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仍然以事神为第一要义。汉字图象,本身既是“神事”的重要部分,是天书的神示、神识,是神使……是神指向人的传媒,又是永久的铭刻书写。最重要的,汉字图象与“器”,有着深刻联系,诚如刘熙《释名序》所谓“自古造化,制器立象”,制器与立象并称,恰体悟到其中的相通。以一“物”字概括动植物和人、神,或许,正是某种几何学精神的展示。根据器物形状所成之汉字图象,在汉字中有许多,推其原,则均与神性的生活相关。在近年又有发掘的良渚文明、三星堆文明中,有着颇为充分的体现。
神话中的科学意识,最根本地,体现为技术。天地神人,在神话中,均由技术之“神”与“物”贯通。神器,则是最能体现那种几何学直观的神性的表象。世界上所有神话中,最初的“神”,许多都是与“制器”相关的英雄。重要的神性符号,如古埃及、古印度的几何图形,乃是非感官的精神的象征;植物、动物、人物、神明,万“物”之中,似乎都有一道技术的光亮透过。这种神话思维,以最新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赛博格”。
“赛博格”本是一个属于工程学范畴的专有名词,赛博格(Cyborg),此词由控制论(Cybernetic)与有机体(Organism)结合而成。从科学角度看,人类运用技术可以将不同物种相嫁接,从而在当代科技中,创造出“植物人”“动物人”“超人”。神话中的神,其实许多即是动物、神灵和人相结合的赛博格。神器的神乎其技的“技术”,往往是其核心——“技术”的神话,在现代社会是某种科学乌托邦,但在神话中,却是指向无限的能力。神话中的“控制论”,指向的控制着时空的“神”,不仅具有身体的超人性,精神的超人,更指向无羁无尽的创造。

因此,汉字图象的神话“赛博格”,就体现了“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神灵”,体现出汉字之“文”心,是那种“雕龙”的精神,即创造一种本不存在的图象,却能够神奇地表达人类精神的精深微妙。这条赛博格的虫、星、神的合体,正是汉字图象的神话意象的象征。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神灵,是哪一个,却无法认定。
神话中汉字图象之“龍”,就这样夭矫变化、活灵活现、神气灵动于中国文化的“天人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