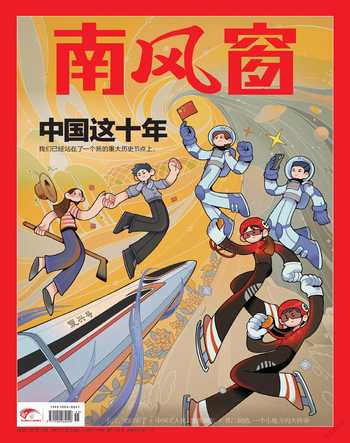理想政治与理性治理
2022-08-18李少威
李少威

今天,一个人如果在街上乱倒垃圾,会受到何种处罚?首先清理,而后批评,最后罚款。大规模倾倒商业垃圾,如建筑废物,还可能被拘留。
但在商朝,“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乱倒垃圾者,砍手。
这是韩非子介绍的,真伪难征。韩非子接着说,对此子贡不赞成,孔子却不反感。孔子说,“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
韩非子介绍的“孔子话语”,是极为典型的法家逻辑。一个小恶不加以严厉禁止,就会衍生大恶。严刑峻法以禁小恶,人们既很容易守法,又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那么大恶就不作,大乱就不生。在法家看来,法律就是用来防微杜渐、恐吓社会,令人不敢为奸。
这种观点绝对不会出自孔子。孔子的办法一定是居上位者以身作则,以道德教化百姓,使得人们打心里就不想往街上倒垃圾,“城市是我家,清洁靠大家”。孔子从不赞成用严苛的刑法去对待老百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令刑法的约束,治标不治本,人们可能因为害怕而不敢犯法,但并非发自本心。只有德政、礼治,才能让人真心服膺。
这个例子表现了儒家和法家在政治理念上的根本差别。
儒家理想,憧憬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人是政治的目的,治理只是手段,政治体的存在只是为了实现人的福祉。
而法家治理,认定每一个人本质上都是坏人,如果不用严厉的法律权威加以威吓,人就一定会做坏事。只有严格限制人的行为,才能防止对政治体的破坏。政治体的存在,是共同利益实现的根本,或者说,政治体就是共同利益本身。
以严刑峻法整合社会,塑造出一个强悍的军事机器,在其中,人渺小到了蝼蚁的地步,读《商君书》,脊背发凉。
儒家理想在道义上很难被反驳,但它的先天不足在于缺乏实现方法,就像一个人无法提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放到高处去。反复尝试依然无果,人以及后人就会去造梯子,爬上去。法家就是那个造梯子的后人,只是反动过甚,把梯子当成了目的本身,而对人的处境不再关心。
法家出自儒家,宗师是孔子的得意弟子子夏,姓卜名商。他的弟子李悝、吴起是魏国变法、强军的领导者,也是早期法家代表。李悝又教出来一个商鞅,商鞅幾乎完全抛弃儒家道德,以严刑峻法整合社会,塑造出一个强悍的军事机器,在其中,人渺小到了蝼蚁的地步,读《商君书》,脊背发凉。
孔子对子夏说过,“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担心这个得意弟子从君子的浩然之气中滑出,走向术与法的层面,可谓有先见之明。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很不客气地把他的前辈子夏称为“贱儒”,谋食不谋道,令人齿冷。然而,荀子同样教出来两个法家徒弟—韩非和李斯,韩非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而李斯是秦国残酷治理“最后的疯狂”的主要操盘手。
于是我们看到,《汉书·五行志》中记载:“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 乱倒垃圾虽然不用砍手,但要在脸上刺字。无情之法,致使秦朝在统一之后十五载而亡,这个结果,从思想嬗变的角度,可以追溯数百年。
一种宏大的理想诞生,令人如沐春风,驱使有信念的人们为之赴汤蹈火,但到最后,往往容易因为理想难以实现而出现一个反动过程,现实走向反面,走向极端,观照中西历史,莫不如斯。西史如法国大革命,便是如此。
理性的治理,应当用政治理想来约束现实政治,使之相得益彰。政治的目的是人,而实现的手段是情与法并行,政治体本身,是一种调和理想与现实的工具,其存续之根基,在人,不在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