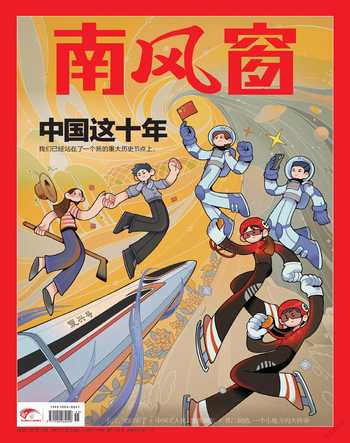“成年孤儿”:失去父母以后
2022-08-18朱秋雨黄泽敏
朱秋雨 黄泽敏

妈妈和爸爸在一年内接连离世时,黄溪30岁。
黄溪说,爸爸在2022年春节离开,她以为解放了,感到很久未有的轻松。她去商场做了美甲、美容、健身,花了过去一年没敢花的很多钱。
摆脱了癌症家属的身份,黄溪过上了三天舒服的日子。
但她逐渐发现,时间并不是治疗心灵的药。与父母相处的细节,总会在不经意的瞬间涌来,记忆越来越沉重。有时候在路上开车,她会望着前方忍不住喊,爸爸,妈妈。
时间的流逝提醒她,自己是一个失去双亲的人,要孑然一人活在世上。
美国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李维写过一本名为《成年孤儿》的书,讲述的正是像黄溪一样,丧父丧母、失去亲人的成年人。
他在书里写“:成年丧亲,其实是极普遍的现象,那种失去归属的感觉,需要受重视、受疼惜,却往往被社會避而不谈。”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成年人成为孤儿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们采访了一些“成年孤儿”。他们都还年轻,却过上了真正意义上一个人的生活。
这不是只有眼泪的故事。这是关于人怎么从孤独、哀伤、失去靠山的绝望中喘口气的故事。黄溪说,成为孤儿半年以来,她的感悟是:“我们要接受,人注定会和孤独、无常共处。”
这些情感都将化成身体的一部分,“人要学会共处”。
手 术
郑州人黄溪曾以为,父母会陪伴她很多年。
没有疾病的时候,他们住在同一个小区、不同的房子,生活像两条平行线。父亲母亲有自己的小日子:钓鱼、煮饭、外出旅游。独生女黄溪则整天忙工作。
平静的生活在2021年3月被打破。父亲感到左腿疼痛,走路开始一瘸一拐。医生最初判断,可能是椎管狭窄,做个手术就能改善。
黄溪放下了悬着的心。在她认知里,这不是大问题。她清晰地记得,手术前,她开车送父母去医院,阳光洒落在车窗。到了停车场,父亲和母亲一起下了车。
两人有说有笑,还拥有健康的体魄。
但是,脊椎手术做完,父亲的腿依旧没好转。
随后的一个月,黄溪经历了大起大落。前往不同医院做检查时,医生给的说法都不一样,有人说是神经炎导致,有医生判断是脑胶质瘤。
判断为后者的医生越来越多。黄溪查了查,这是一种大脑和脊髓胶质细胞癌变产生的疾病,具有复发性高、死亡率高的特点。但这时,她仍觉得前方充满希望。
她为父亲办了住院。主治医生的说法也模棱两可。他对家属解释,这颗瘤长在了复杂的脑部运动神经附近,不好穿刺取样,目前只能依据影像学判断。
他接着抛出了问题:“要不要考虑手术?”
黄溪全家的第一反应,“做!”一颗瘤子就像定时炸弹,人随时可能被击穿。他们不想活得如此被动。
与医生多次接触后,她与母亲听出了其言外之意:手术风险大,不建议做。想做手术的只剩下父亲一人。
但最终,是否做手术的决定还是遂了本人的意。黄溪记得,她和母亲提出不做手术时,父亲心情呈肉眼可见的低落。他开始每晚睡不着觉,半夜跑到医院大楼门口坐着。他不甘心,想赌一把,全家人都看得出来。
他欺哄母亲道:“医生说手术挺成功的。你加油努力,快点好起来。”
再次与主治医生商量后,黄溪决定,支持爸爸,赌一次。
让她感到幸运的是,2021年5月,她等来了“手术成功”的消息。尽管医生加了后缀:由于瘤长在脑部很深的位置,未能完全清除。
但此刻,一家人已经满心欢喜地念想:“手术成功了,生活肯定要好了。”她把父亲接出了医院,顺便辞了过去不顺心的工作。
与黄溪相似,2016年,李克俭也是突如其来地接到坏消息:妈妈得了胃癌。
不同的是,医生直接宣布,是晚期。
李克俭在读高二,对于那时的他而言,离开母亲,等于他失去了世上所有的连结。
自他出生以来,相近的长辈接连离世,先是外婆外公、爷爷奶奶;亲生父亲也在他刚记事时,与母亲离婚。
8岁时,母亲将他从四川的老家接到工作地广东珠海,还顺便介绍了自己的新伴侣,一个让李克俭叫继父的澳门男人。李克俭很快意识到,这个男人不仅不帮他交学费,还会在房间里一包接一包地抽烟,常因琐事对母亲大呼小叫。
这样的家庭没给过他温存。活着的动力,李克俭说,过去一直是为了母亲。
但医生很快宣布,母亲第一次手术失败。恢复的可能性不大。
对着还抱有希望的母亲,他没忍心告诉真相。
他欺哄母亲道:“医生说手术挺成功的。你加油努力,快点好起来。”
恶 化
手术出院后,黄溪的父亲像变了一个人。这是脑部手术过后的正常反应。切除瘤块的“动静”会影响脑部其余功能,人将变得暴躁、易怒,无法控制情绪。
父亲的左腿也未如意料中恢复。母亲开始变得低沉,经常把“我不想活了”挂在嘴边。
但这不代表希望的丧失。黄溪记得,父亲满心盼望着左腿的恢复,坚持找康复医院做复健治疗。
那段时间,她经常半夜接到母亲的电话。
“你父亲又摔跤了。”两人再一起把他往医院送。
持续的努力拗不过扎在身上的病。一个多月后,脑部切片检查结果出炉,父亲的病被确诊为脑胶质瘤三期,是恶性肿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