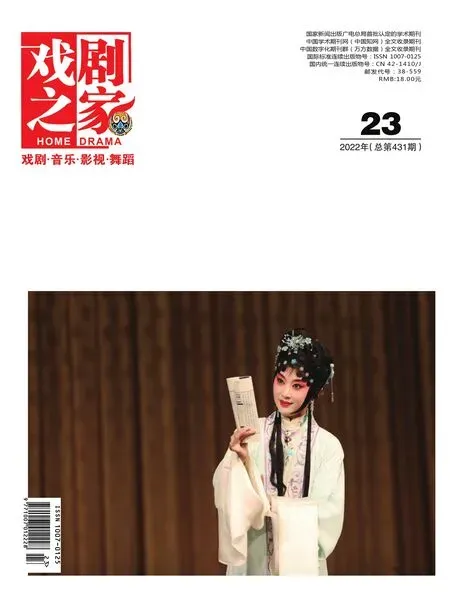峄县“清官独杆轿”研究
2022-08-17张峻珲
张峻珲
(枣庄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山东 枣庄 277100)
“独杆轿”也叫“清官独杆轿”,起源于古峄县(现为枣庄市峄城区),后广泛流传于鲁南和苏北地区。史载,“清官独杆轿”是民间百姓为纪念清乾隆年间(1711 年—1799 年)峄县清官张玉树(张玉树,字德润,号荫堂,陕西武功人,进士,曾任清平知县、峄县知县、胶州知州、济宁知府、云南临安知府)而发明的,随后在峄地民间流传。峄县“独杆轿”因表现形式独特,于2009 年被申报为“山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项目。
一、历史源流
峄县为旧县名,最早为秦置,地处今山东南部地区,包含枣庄市市中区、峄城、台儿庄全部及薛城东部、山亭南部、苍山西南三镇、微山县韩庄镇,以及徐州市北境部分乡镇,后于1960 年改为枣庄市峄城区。“独杆轿”的首次出现是在1774 年,峄县时任地方官张玉树为官清廉,提倡“与民同乐”,峄县人们为了纪念张玉树,由当地举人孙蓉衫、副贡张兰坡等知名文人、艺人和商人集体联手创作了清官独杆轿。“张玉树待士民如师友,为峄县人民做好事、实事数以千计”,因此,每到大年初一,峄县人民便抬着独杆轿和狮子龙灯一起到县衙门给清官拜年,以示感恩。此后,“独杆轿”随原有节庆表演狮子龙灯队一起,每年到县衙门拜年,并成为春节与节庆日子里的“看家戏”。此后,这项民间活动历经风霜后断断续续地沿袭下来,在1949 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 多年间,经民间艺人和当地政府的努力保存与弘扬,“独杆轿”以城镇街道为主要活动场所持续发展。因表演的功能指向比较明确,峄县“独杆轿”主要用于民间节庆,未曾用于民间信仰的民俗祭祀。
新中国成立后的20 世纪50 年代,随着秧歌竹马、狮子龙灯的复兴,独杆轿再度露面,十年“文革”期间,民间艺术跌入低谷。1984 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地方文化站与干部群众在老艺人的帮助下恢复了民间传统艺术,峄县清官独杆轿又和观众见面。1995 年,山东卫视专门录制了以清官轿为主,以狮子龙灯为辅的专题民间艺术节目——《峄县社火》,节目在中央电视台转播后,进入国际电视文化视野。2009 年,枣庄市文化局和峄城区文体局把《峄县清官独杆轿》申报为“山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项目。
二、“清官独杆轿”的表演形式
“独杆轿”舞蹈表演时用唢呐乐队伴奏,表演时三人一组,两人抬着一根一丈多长的竹竿,一人坐于竹竿上,三人配合唢呐声与锣鼓点,协调一致向前走。在动作上,轿夫、旗手起落有致,顷刻悬至半空,顷刻落于地面,表现出上岗、下坡、快进、慢行等形象,在队伍中穿插行进。竹竿上的演员随着音乐节奏和竹竿频率的变化做不同幅度的颤动,从而在上下两层空间舞动转化,在大起大落间带给观众感官上的刺激,所以,“清官独杆轿”是在行走间进行表演的一种民间舞蹈。
(一)道具制作与使用
峄县“独杆轿”的主要道具是一根一丈多长的杆子,以独杆为轿,有两位轿夫抬轿,县官坐轿与民众交流,这是该舞蹈的主要表演形式。在游走过程中,为表现演出的技艺效果和高低两度空间的使用,左右横移是独杆的主要使用方式。“独杆轿”中的独杆所用材质为毛竹,毛竹主要生长于中国南方,并非鲁南苏北地区的特产,其重量较轻、柔韧性强,因此成了独杆道具的首选。在“清官”的命题下,“独杆轿”的表演形式相对固定,民间艺人为了传承与弘扬对清官张玉树的怀念与尊敬,对“独杆轿”的表演形式进行了较为完整的保留,在传承过程中较少改动,基本保留了其历史原貌。县官的身份由“官印”来表现,“官印”由黄布包裹,由县官持于手中,“官印”表现了“独杆轿”产生之初官员“与民同乐”的理念。代表县官身份的“官印”被“县官”从衙门中拿出,同县官一道游乐在民众之中。由于“县官”在进行表演的同时还需一手持官印,加大了独杆上“县官”演员的表演难度。“仪仗”是“独杆轿”的另外一种道具,“官印”“仪仗”为旗帜两面,分别书“一身正气”与“两袖清风”,代表着峄县人民对县官张玉树的怀念。
(二)动作花式
“独杆轿”的舞蹈动作要点在“平衡”上,要求饰演县官的演员始终保持身体“中正”,在坐轿过程中既要安然自若,又要同民众相呼应,与民同乐。“轿夫”在抬轿过程中需要做出上岗、下坡、快进、慢行、队伍穿插变转等动作,并且,两位“轿夫”还要与“旗手”步调一致,相互“徘徊”。整支表演队伍的主要表演步伐是“一步一颤”,其中,“快进”与“慢行”是轿夫根据乐队伴奏在“一步一颤”基础上所作的节奏变化,并随演出队伍整体作出相应的步伐节奏调整。此外,“起轿”与“落轿”为演员上、下独杆动作,无特殊样式变化。
(三)服饰装扮
“独杆轿”的表演队伍共8人:县官1人、轿夫2人、举旗2 人、乐队3 人。县官轿前有两名旗牌手,两个旗牌各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字样。县官戴纱帽、穿官衣,手捧大印。官轿后常有2~3 个组,均与轿并行伴随演出,其扮相多为舞狮和挑夫,着戏装。轿后若为舞狮,则为2 人,执球者1 名;轿后若为挑夫,则为4 人,扁担内挑着高度放大的五谷、苹果及鱼鳖图案。“县官”头戴乌纱帽,面带黑色长须,身着红色官袍,腰系红色绣云带,脚穿乌纱朝靴,与京剧“包公”形象相似,左手执黄布包裹的官印,坐于独杆之上。“轿夫”头戴红色头巾、黄色内衬、红色外褂,胸前有一“轿”字,下身着黄色灯笼裤,脚穿薄底黑靴或黑圆口布鞋,腰系黄色绸带,帮助抬轿时腰腹部要收紧发力。“独杆轿”演员的服装是根据演员角色制定的,观众根据演员服装可以明确定位演员的人物形象,
这也是“独杆轿”简洁、明了的服装特征。
(四)伴奏乐器
“独杆轿”在表演时主要有唢呐乐队伴奏,主奏乐器——唢呐音色雄壮浑厚,穿透力强,与乐队中的小锣、小镲相呼应,时而高亢明亮,时而悠远绵长,营造出欢快、热烈的节日气氛。演出时,乐队走在队伍最前面鸣锣奏乐,后面是两位举旗人,两个轿夫抬着县官紧跟其后,伴随着《秧歌调》《步步高》等传统曲目,形成“一条龙”之态。
三、“独杆轿”传承现状中的问题与思考
民间文娱活动的丰富、网络互通的普及和社会主体力量的经济因素转移,使“独杆轿”的传承与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传承现状与问题
“独杆轿”自公元1776 年形成至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虽然历经了社会变革和时代变化,但一直传承至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独杆轿”在党的方针政策引导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从文献和记忆里再次出现在峄县地区的街坊、巷子中,并逐步走向书本与课堂。1984 年,在峄城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镇文化站和北关工农街、西关徐楼村干部群众恢复了民间传统艺术。“峄县清官独杆轿”趁此机会在老艺人的帮助下再度出现在峄县的土地上,并在当地政府保护下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峄城区的“看家戏”。“独杆轿”虽然被评为省级“非遗”,但由于其独特的技术要求,其在传承与保护上渠道狭窄,活动场所以社区、街道、展演等为主,虽然“独杆轿”也开始了培训班的技艺传授工作,但是,由于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不够,保护意识不强,导致“峄县独杆轿”处于青黄不接的传承状态,当地政府对此一直保持关注。“峄县清官独杆轿”作为一种民间表演娱乐活动,经常出现在枣庄市的街巷与展演活动之中,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作品,没有搬到舞台上,而是始终保持着一种原生的舞蹈形态,这也构成了“峄县清官独杆轿”独有的朴拙特色。
笔者对《峄县清官独杆轿》的调研从2018 年开始,笔者在枣庄市峄城区仙坛苑广场前后多次观摩了“独杆轿”的表演,并通过现场采访传承人与民间参演艺人的方式,收集了一些与峄县“独杆轿”相关的传承与发展资料,并了解了其在当下传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目前的《峄县清官独杆轿》传承处于后继无人的状态。首先,道具的使用限制。由于“独杆轿”以“独杆”为道具,道具重量限制了使用群体,所以,能够接受传承的多为年轻男子,而大部分本地年轻人都忙于生计,或去外地务工,很难放下生活问题潜心学习“独杆轿”;其次,活动场地与时间的限制。“独杆轿”道具较大,对活动场地的条件要求较高,因此,仅适宜表演于街道广场,再加上以节庆日为主的演出时间,使得“独杆轿”与民众接触较少,民众对地方“非遗”的认知不够;再次,“独杆轿”目前尚没有舞台表演作品,这也反映了当前的艺术工作者对该舞的关注度较低,同时,这也是“独杆轿”苛刻的演出条件限制的结果;最后,在对“独杆轿”进行调研时笔者还发现,当地虽然鼓励、支持并保护“非遗”舞蹈的发展,但是,当地对影像资料的保存并不完整,有关“独杆轿”的历史影像资源并不完善,这也使研究者在对“独杆轿”的表演形式进行研究时没有可靠的依据。
(二)对传承现状的思考
“清官独杆轿”发展至今已有二百余年历史,其强大的生命力来源于当地文化土壤的滋润和本身经久不衰的活力,但是,面对当下剧烈的社会变革,其传承和发展仍然面对诸多挑战。在当下,“独杆轿”虽然依旧拥有大量受众以及政府部门的支持,但传承人和参演人员的减少与老龄化,使其在保存上难以为继。此外,其传承中还存在以下四种现象需要研究者认真思考:
第一,继续完善补充“清官独杆轿”的文献整理,对“清官独杆轿”的演出活动予以高度关注,并做好组织宣传,提高民众对该民间文艺活动的重视程度,鼓励全民参与、全民欣赏、全民推广。通过活动宣传引起民众的重视,提升民众对“清官独杆轿”的认知,将地方“非遗”普及到民众的生活中。
第二,“独杆轿”的道具是其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之一。从道具的样式来看,竹竿长一丈有余,质地为毛竹,有较高的韧性和密度,比普通竹类稍重,因此,其表演对使用道具的“轿夫”人选有特殊要求。“轿夫”不仅需要将“独杆”扛起,还需计算“轿”上县官的重量,所以,“轿夫”的工作在整个演出团队里是个“体力活”,在选择“轿夫”时需要考虑演员的体力、身高、耐力、身体素质等多方面因素,而符合要求的主要群体是社会中的青壮年。在枣庄地区,社会中的大部分青壮年要么为了生活在外地务工,要么需要工作没时间参与,又或者能够欣赏却不愿意参加演出活动等,这是限制“独杆轿”传承发展的根本问题。
第三,“清官独杆轿”作为民间娱乐活动,具有群体性、娱乐性、聚集性等特点,需要较大的演出场地;另一方面,因其群体性和聚集性,也需要一定数量的民众参与并观赏,这要求“独杆轿”的演出时间多在节庆日里,这在时间与空间上限制了“清官独杆轿”的发展。与民众互动的减少直接降低了民众对该民间“非遗”的认知与了解,使其从“我”文化演变为“他”文化。
第四,有关部门对“清官独杆轿”的支持与发展虽有一定力度,但在具体落实上仍有不足,当下的“清官独杆轿”并没有发展出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基本保持着民间的原生状态。传承人年龄较高,参与者老龄化严重,使“独杆轿”缺失了民间舞蹈文化与时代同步的革新步伐。在没有创新发展和舞台作品的当下,“独杆轿”作为一种民间“非遗”,较难为更大的群体所接受,所以,当下的“独杆轿”发展应当更加注重对原生“独杆轿”的创新与创作,即双创精神指导下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知识构成、思想意识、审美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于“独杆轿”这种具有民族与地域文化特色的“非遗”舞蹈而言,既是冲击也是挑战,怎样寻找继任者,如何推广“独杆轿”,如何在发展中传承与创新,是“独杆轿”未来发展需要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