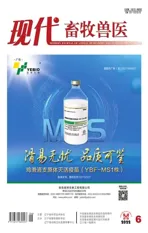畜间炭疽的流行与防控思考
2022-08-16曾秀玲毛以智
周 标,张 霞,罗 意,曾秀玲,皮 泉,毛以智,李 涛*
(1.贵州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省六盘水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贵州 六盘水 553000;3.贵州福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贵州 贵阳 550002)
炭疽(anthrax)是由炭疽芽孢杆菌(Bacillus anthracis)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败血性的人畜共患病和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因其典型症状是引起皮肤等组织发生黑炭状坏死而得名[1]。炭疽芽孢杆菌影响包括皮肤、肾、肠、结膜、脑膜、淋巴等组织器官,几乎所有热血动物均可感染,且以草食动物最易感。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炭疽列为必须要报告的动物疫病,我国将该病列为二类动物疫病进行管理,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炭疽芽孢杆菌繁殖体自身存活力不强[2],但当其暴露于空气中则易形成芽孢;物理、化学因素的消毒方式无法完全消灭芽孢,被芽孢所污染的场地用具、土壤、水源等可成为持久的疫源地[3]。目前,关于人间炭疽的统计报告相对较多,本文整理分析了近年来发布的人间、畜间炭疽发生情况,并提出了畜间炭疽的防控建议,以期为相关研究和防控工作提供参考。
1 炭疽流行形势分析
炭疽一般呈散发或地方性流行,世界各地均有分布,在雨水多、洪水泛滥、吸血昆虫活动频繁的季节多发,具有一定的季节性[4]。
由表1可知,国内每年均有畜间炭疽疫情散在发生和局部地区暴发流行。整理农业农村部《兽医公报》中炭疽疫情数据可知,2017年至2021年9月全国发生炭疽疫情68起,发病动物466头,年均13.6起,年均发病数93.2头,每起疫情平均发病数为6.85头;主要分布于青海、云南、内蒙古、黑龙江、宁夏等省(自治区)[5]。

表1 2017年—2021年9月国内各省份(自治区)畜间疫情省份统计Tab.1 Statistics of domestic animal epidemic provinces(autonomous region)from 2017 to September 2021
近年来,我国畜间炭疽疫情发生和危害逐步降低,但2021年有所抬头,十年无炭疽疫情数的西藏一年内发生了7起疫情。本次统计疫情均为兽医公报上公布的疫情数,部分畜间疫情是在引起人感染炭疽发病后报道。从国内2021年疫情数远超2020年的流行形势来看,未引发人感染的畜间炭疽病例预估不低于统计数。人间炭疽与畜间炭疽呈正相关,发病高峰期一般为7月至10月,多为接触含有孢子的病死牲畜或动物产品时被感染,兽医、牲畜生产者、农业工人或屠夫均属于密接高危人群[6]。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国炭疽疫情开始呈下降趋势;从2006年开始,人间炭疽例每年报告不足500例[7]。
由表2可知,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历年年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2021年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显示,2017年至2021年,我国炭疽发病总人数为1 581例,死亡人数9例,年均发病人数316例,病死率0.57%。尽管近年来国内人间炭疽总体呈下降趋势,但2021年发病率有所回升,河北、山西、北京、山东等地陆续出现,全国共报告人间炭疽病例406例,比2020年多182例,特别是往年没有病例或偶有散发病例的山东、安徽、山西等省份出现聚集性炭疽疫情报道[8]。

表2 2017年—2021年国内人间炭疽发病情况Tab.2 Incidenceof human anthrax in Chinafrom 2017 to 2021
2 流行原因与分析
近年来国内畜间炭疽的报告数逐年降低,但2021年人间炭疽和畜间炭疽的报告数均出现了反弹升高的情况,对兽医及卫生工作者而言,这一反常现象不容忽视。针对这一流行情况,原因可能包括以下3个方面。
(1)随着我国养殖业规模、密度和流通半径的不断增大,国内动物及其产品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增加了炭疽疫情传播和扩散风险,引种和购进活体动物等导致的输入性疫情增多。
(2)随着温室效应不断加剧,全球极端天气频发,尤其是洪涝及干旱灾害的发生导致土壤和环境中的炭疽孢子暴露,加剧了老疫区疫情的发生。
(3)2020年底,国内生产、消费和运输等恢复迅速,污染的畜产品(如骨粉肥料、皮毛、羊毛或污染的精饲料、饲草)随之传入新的地区。
虽然我国总体已基本控制了炭疽病的流行,但自然疫源地环境中的炭疽芽孢难以根除,且2021年的疫情报告数已出现反弹,畜间炭疽防控任务仍然艰巨。
3 畜间炭疽临床与诊断
3.1 临床症状
畜间炭疽的潜伏期通常为3~7 d,最长可达20 d,多为急性经过,往往以突然倒地死亡、尸僵不全、天然孔出血为特征。畜间炭疽主要包括4种典型症状:最急性型(中风型)、急性型、亚急性型和慢性型[9]。
最急性型病畜突然昏迷倒地,周身摇摆战栗,心跳过速、极度呼吸困难,可视黏膜发绀,暗色血液从天然孔流出,病程持续几分钟到数小时[10]。急性型多见于牛、马[11],体温高达42℃,吼叫、兴奋且具攻击性,之后精神沉郁、肌肉震颤、步态不稳、黏膜发绀、呼吸困难,反刍、食欲、泌乳逐渐减少至停止;起初便秘,而后腹泻,便血,尿暗红,乳汁带血,还可引起妊娠牛流产,病程持续1~2 d直至死亡。
亚急性型类似急性型,除急性热性相同的病症之外,往往在病畜皮肤、直肠或口腔黏膜等局部出现炭疽痈,初期有热痛感且质地比较硬,之后变冷且无痛感,有溃疡或发生坏死,病程持续数日至1周以上。慢性型病例通常呈慢性经过,基本不表现出临床症状,常见于猪[12],多为局限性变化,通常在宰后发现病变。
3.2 病理变化
严禁在非生物安全条件下剖检疑似患炭疽动物的尸体。患病动物尸体尸僵不全[13],主要病理变化表现为可视黏膜发绀、出血,局部出现浆液性渗出及出血,黏稠且凝固不全,呈暗紫红色煤焦样。淋巴结肿大、充血,切面潮红。脾脏肿胀数倍,脾髓呈黑紫色,胸、腹腔及心包中有红色混浊液体。
3.3 诊断
畜间炭疽的诊断以流行病学、临床症状以及实验室检查为主。生产实践中如遇到家畜无征兆突然倒地死亡时首先要怀疑是炭疽,若病死家畜的自然孔渗出血水更需要特别警惕是炭疽的可能。严禁解剖死于炭疽的病畜尸体,确定需要采样时只能够从耳根部采血液样本,必要时通过切开肋间或穿刺采脾脏样本[14]。必须在相应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实验室病原学诊断,主要包括免疫学诊断、细菌学诊断、分子生物学诊断等。
对新鲜病料可直接涂片染色镜检,常见染色方法有碱性美蓝染色、瑞氏染色或吉姆萨染色,镜检发现荚膜节状大杆菌可进行初步诊断。免疫学诊断主要包括沉淀反应(Ascoli反应)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分子生物学诊断则广泛以PCR技术为主,反应灵敏、快速,特异性强,还具有可区分炭疽强毒、弱毒等优点[15]。
4 畜间炭疽防治措施
坚持“预防为主,免疫和治疗相结合”为原则,以“加强宣传、依靠科学、群防群控、果断处置”为方针开展畜间炭疽的防控工作,采取“早、快、严、小”的措施,早发现疑似病例,及时上报,阻止疫情扩大[16]。必要时专业人员在严格防护下对病畜进行隔离治疗。
4.1 控制传染源
炭疽的主要传染源是因炭疽而死亡的动物尸体和患病动物以及受到污染的用具、饲料、草地、土壤、水等,炭疽芽孢污染的场地用具、土壤、水源等则成为疫源地。因此,应加强监测预测,对畜间炭疽疫情进行风险评估,严格按照20020066—Q—326《畜禽产地检疫规范》和《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实施检疫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及时发现患病家畜并隔离治疗,严重时按相关规定实施应急处置并做好无害化处理,才能够实现有效地控制传染源[17]。
考虑远离人居、水源等因素,因地制宜,通常采取就地彻底焚烧尸体及污染粪肥、垫料、饲料等手段。采用5%福尔马林对需移动的尸体和污染地(土壤)、渗出物(血)、房屋、厩舍等进行数次喷洒浸渍消毒,密闭空间、工具、器具采用熏蒸消毒[18]。采取检疫、监测、隔离、治疗、淘汰等有效措施,净化污染群。
4.2 切断传播途径
炭疽的传播途径包括通过皮肤黏膜、摄入、吸入和注射等,其中全世界大多数(95%)病例通过皮肤传播,家畜通常因摄入炭疽芽孢或被吸食过感染炭疽动物(尸体)的吸血昆虫叮咬后引起感染[19]。因此,严禁在发生炭疽的疫点疫区、江河流域附近以及炭疽病死畜填埋场周边、洪水侵袭过的牧地草场、地势低洼地带等容易被炭疽芽孢污染区域放牧[20]。严格实施产地检疫、屠宰检疫工作,对新老疫区执行定期消毒制度,雨季要重点消毒。对皮、毛也要严格进行消毒,加强饮水、饲料的管理,以防受到污染。生产生活中从事兽医实验室诊断、动物防疫检疫以及养殖、畜产品和皮张加工等工作的密接人员要加强自身防护,炭疽疫情处理的参与人员必须严格穿戴防护装备。
4.3 保护易感动物
炭疽在人和各种家畜、野生动物中均具有易感性,其中草食动物易感性大于杂食动物,杂食动物易感性大于肉食动物,家禽一般不感染[21]。畜间炭疽与饲养方式和畜群结构密切相关,加强饲养管理,建立并执行严格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保证家畜营养和养殖环境舒适卫生,合理设置饲养密度等可有效保护易感动物。通过调查摸底疫区及受威胁区易感动物养殖数量、分布等情况,进行足量的防疫物资储备。
各地根据当地炭疽流行情况、抗体水平、生产需要等确定免疫接种对象和范围,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使用国家批准的炭疽疫苗定期实施免疫接种。在每年春秋两防集中免疫时使用Ⅱ号炭疽芽孢杆菌苗免疫[22],免疫密度达90%以上。连续接种3年未发生炭疽疫情可停止接种,但停止接种后应实行长期监测[23]。
4.4 治疗措施
炭疽传染性较强,病畜进行治疗时,需专业人员在严格防护下进行。一般情况下,最急性病程短促,患病动物尚未来得及治疗便倒地死亡;急性和亚急性的病畜若治疗及时则可治愈[24]。
畜间炭疽的治疗可分为血清疗法和药物治疗[25],其中抗炭疽血清是治疗特效药物,一般病初皮下或静脉注射同种动物血清效果显著。药物治疗则以磺胺类、抗生素类药物肌肉注射效果良好,其中磺胺嘧啶、青霉素G有特效,疗程2~3周,同时采取对症疗法和支持疗法[26]。
5 畜间炭疽防控思考
5.1 建立部门联防联控机制
高效的联防联控机制是炭疽防控的关键,建立健全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调沟通机制[27],及时沟通、定期会商,通过开展防控督导、调研、联合执法等方式,形成合力才能够有效防控炭疽。严格落实各项防控工作的同时,要不断强化“人病兽防、源头治理”的理念,积极向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沟通汇报,严厉打击买卖、运输、加工病死动物的违规行为。
5.2 建立炭疽疫情监测排查体系
在多部门的协调沟通机制基础上,建立人间、畜间炭疽疫情监测排查联动体系,提高畜间炭疽采样检测频次,动态监测历年炭疽疫点环境污染情况。应加大炭疽排查普查力度,全面摸清炭疽分布状况,完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要时期的炭疽疫情报告机制,科学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疫情。
5.3 广泛宣传发动,形成群防群控合力
强化社会宣传教育工作,多形式宣传炭疽的危害性和防治知识,提高密接人群自我防护意识和防控能力。重点强化炭疽防治技术规范和培训,提升基层防疫人员“早发现、快反应、严处置”的能力和水平。强化舆情引导,广泛动员全社会人员,营造群防群控氛围。同时加大执法力度,震慑违法行为。
5.4 及时妥善处置疫情
炭疽疫情处置由当地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炭疽防治技术规范》和应急管理办法等严格组织实施,划定疫情疫点、疫区、受威胁区,并实施严密的封锁。严格执行无血扑杀、无害化处理、封锁、消毒、紧急免疫、停止易感动物交易和放牧等措施,防止污染水源和环境。同时做好洪涝等灾后防疫工作[28],及时打捞、收集、无害化处理畜禽尸体,加强媒介生物控制和消杀等。
6 结论
目前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情况下,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对炭疽、布病和禽流感等人畜共患病的防控工作也不容松懈。炭疽流行因素明确,可防可控。因此,在饲养、生产、经营、屠宰各环节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同时要建立严格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严格实施产地检疫、屠宰检疫工作,对新老疫区执行定期消毒制度,雨季则要重点消毒。生产生活中的密接人群注意个人防护,参与疫情处理的有关人员要严格穿戴防护装备,做好自身防护。落实人病兽防,科学、全面、合理地开展炭疽防治活动,炭疽有望在我国被控制乃至净化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