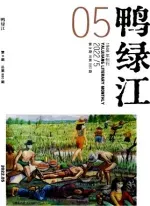那像诗的呼吸
2022-08-15刘恩波
刘恩波
“你坐在窗口/天在下雪——/你的头发雪白/还有你的双手——”这是内利·萨克斯的诗句。我读到它,是在1992 年的某一天。飘着雪花的北方冬日里,我和妻子栖居的一间朝北的房间,只有下午才能望见斜阳。
那个时候,她失业在家,无事可做。我的单位也属于自由闲散的性质,平素许多时候也要窝在家里办公。我们那么年轻,过着拮据艰难的日子。所幸还有文学和艺术的照耀,如一道光亮倾泻、点染在这间小屋,为两个小人物带去了惊喜、慰藉、期盼和感动。
“在你的雪里入睡/带着在人世的火的气息……”而从前那个遥远的夏天,“土地,让牧野升到不可见的世界——饲水场,让缥缈的小鹿过夜。”萨克斯的诗美得就像傍晚窗外闪现的雪花。我们一起诵读许许多多哀伤的、温婉的、幻灭的、凄楚的文字,仿佛雪夜天然融入了眼前的黑暗和幽光。
内利·萨克斯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66 年),可她在自己人生的中途碰上了希特勒当政、残酷迫害犹太人的历史时期。后来她侥幸逃亡去了瑞典,然而,伤痛的记忆虽结疤脱落,但烙印仍在,凝固于她雕塑一般硬朗执拗的诗行。
她写哭墙,写受难的约伯,写黑夜,写星光沉寂时的冷雪……读她的诗,你会感到压抑的哭喊,感到血脉像波浪一样起伏,冲撞、敲击人的头盖骨!你会读到信仰跌落之际一个人内在的挣扎与超升。
最初,我对内利的偏爱,是缘于她的诗总是在绝望的灰烬里埋藏希望的胚胎和幼芽。“望着这个大地,不让任何人未尝过爱情就离去”“在天体的音乐声中/从哪儿传来你们的音响?”“约伯,你哭了每个通宵/可是有一天你的血的星宿/会使一切升起的太阳黯然失色”……内利置身于“痛苦的中心”,用自己的哀叹和叫喊控诉历史与时代的乖戾和残暴,并依旧信奉《旧约》里的伊甸和神的信仰。诗人作为雅各的后裔,作为精神救赎的象征而发育完全——《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二十八章讲到,雅各抱着一块石头睡觉,“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内利在诗中写道:“让空中天使的梯子/像旋花花圃的卷须一样发芽”。换言之,有了信仰的依托,人的迷航总会升起一抹微弱的光亮。于是诗人用“软化的心”“星光的葡萄酒”“吹满气息的混合体”一类字眼表达了生命扔掉绸蝴蝶的永劫,“会因一吻而苏醒”的永恒美丽、饱含柔情的呼吸和爱的存在。
倾心阅读内利·萨克斯的日子,正值北方冬天落雪时节,吟诵着她的诗句——“在你的雪里入睡/带着在人世的火的气息里的一切痛苦/而你那像温柔的百合花的头/已经沉入大海的黑夜/投向新的诞生”,就感觉到苦涩和哀婉深处尚存的几许安慰、温度与生机。
我们的日子还是小米粥就咸菜、苞米面饼子、炖土豆白菜汤,半个月能吃到一回肉,买来咸鸭蛋也要两个人互相推让着吃,可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无比富有和充实。
《世界抒情诗选》《孤独的玫瑰》《史蒂文斯诗集》《野草》《四个四重奏》……那些圣火般点亮内心希望与慰藉的书卷,让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那度日如年的人生竟然有了艺术的底色、情感的归属和灵性的坐标。
妻子喜欢上了索德格朗、阿赫玛托娃、狄金森等许多女诗人的作品。她在一个紫色的本子上抄写了不少诗歌。月白风清之夜,雪色迷离的早晨,或是阴郁着浓厚雾气的下午,她都在我们不大的炕桌上用心地记录那些梦境一样美妙的诗行。
《世界抒情诗选》包括正本和续编,一共两册,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它印制精美,所选作品荟萃了那个年月中国翻译界的精英们从异域采撷到的各种奇花异草,闻之令人心旷神怡,斗室生春。
我和妻子那时候人手一册,将书视为瑰宝,捧在手里,不忍释卷。
然而看什么,其实还是受到天地时令、心态机缘的影响。什么境况下愿意看什么样的诗,好像暗合一点玄妙。
早春时节,春光乍现,继而蠕动着万物生长的气息。小草渐渐露出嫩芽,树木逐一抽出清新的枝条,风变得柔和舒卷了,日子一派盎然之机。这会儿适合浏览索德格朗,适宜看小林一茶。
小林一茶的作品以俳句传世,有人说他“自嘲自笑,不是乐天,不是厌世,逸气超然”。
他生涯孤苦,三岁丧母,父亲再娶,十四岁即离开家门流浪,数十年后结束了漂泊,娶妻生子。可惜好景不长,子女纷纷夭折,患难妻子也英年早逝。一场大梦忽觉,老来,他依旧孑然一身。
取名一茶,想来有“一碗茶即是人生,一碗茶里可见天道”之意。喜乐哀伤,人性之常。先生饱受人生颠簸、情感幻灭之苦,却能转身洞察其中幽微,看透生命浮沉,在达观和乐观里静静品咂自然和心境的万千变化。
俳句虽小,却足以装下他的天和地、冷与暖、悲和欢。
林林翻译的俳句,在《世界抒情诗选》续编只有12 首,可是毕竟让我们觉察、体味到了小林一茶的诙谐、豁达和自得其乐的风范。
“元旦寂寥,不止我是只无巢鸟。”语出戏谑,近乎天然。
“西山啊!哪朵云霞乘了我?”物我混沌,处处生机。
“撒把米也是罪过啊!让鸡斗起来。”此句果真富有理趣,辣味尽藏其中。
至于“到我这里来玩哟!没有爹娘的麻雀”,语含辛酸,故作笑谈,将儿时悲哀、痛痒剪接到诗语里,出之于放浪讥诮,反倒平添生命的妩媚与可爱。
由于早年即离开故乡流浪在外,诗人的心意里总是有一份故乡情难以割舍。
说实在的,小林一茶最令我感念的就是他写故乡时的款款绵延的口吻和气息,像是经过了岁月打磨、时间洗礼后的情感结晶散发出来的一种别致的幽情。
“我生的故乡,那儿的草,可以做饼哩!”有人说,故乡就在舌蕾之际,信焉。
儿时的吃法和味道,到人老了时,依然是心里面的宝。
“做饼的草,长青了哩,长青了哩!”翻译者林林对此有旁注,曰:“可以看到天真的童心,发出惊奇的叹声。”
写童年故乡,最宜于老去了才写,才想。打开往事的是心灵记忆的钥匙。儿时乐事,历尽沧桑而转眼成空,即便是小儿女的欢态也成了隔世的凭吊。
像“女儿看啊,正被卖身去的萤火虫”这样的诗句,林林注说,夏天有钱人买萤火虫,装在纱袋里,悬在室内,或放在院子里飞翔,以供玩乐。
小林一茶的子女都夭折,可他心里装着他们的影儿,时不时迸发在字里行间。心痛的哀婉,用萤火虫的动感体态冲淡了,而那骨子里的伤却表现得如此淡然、怡然。
过来人的追忆有着不胜愁思的美,这在东方美学中称得上心领神会的妙谛。
许多年后,当我走进松尾芭蕉的世界,看他的和歌、俳句还有散文,意外地接续上了如小林一茶的哀婉与淡淡的忧伤情态,譬如这句“手捧慈母遗发白,儿泪热浸秋霜消”,两者相比,一茶的调子似乎更和缓一些,冲淡一些,但骨子里其实是一样的。
大概,对故乡拥有深深思念和依恋的人,都是常年在外的漂泊者。他们怀揣着故乡到处流浪。而他们眼里的故乡也不一定就是完全静态的美好,也许还有动态的缺憾。
小林一茶写道:“故乡呀,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花。”由此可知,诗人对故乡既有思慕的一面,也有些许不满。总之,感情是复杂的,如同我们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抱持两面性或者多面性。
漂泊的诗心从来萍踪无定,“我这颗星,何处寄宿啊?银河。”
一茶似乎离空间的家园越来越远,但在心理的时间距离上遥相呼应,故乡就在梦中,在眼前咫尺之间忽闪。
直到有一天,他五十岁了,返身故里,“十二月二十四日入故乡/这终老居住地/哦,雪五尺!”五尺深的雪,让半辈子跋涉的诗人暂获一处落脚之地。
诗的奇妙,是心灵的交感与愈合,是重塑、再造彼此。
就在我忘情小林一茶的时候,妻子迷上了索德格朗、阿赫玛托娃、狄金森等诗歌领地里交相辉映的女诗人。
1993 年的早春,微风拂面,还有些许冷意。那个皂角园在小河沿附近,对面是动物园。我们常常光顾此地,在恰到好处的幽静里簇拥着活泼跃动的蓬勃诗情。
索德格朗是穷苦的,省下买香水的钱,购得纸张和笔,写着她荡气回肠的诗。她体弱多病,身心不堪重负,仅仅在世上活了31 个年头。
应该说,在那些阳光露出红彤彤的额头、地气悄然回温的春天早晨,阅读索德格朗的人有福了。
我看见了她眼睛里笼罩的憧憬、不安、惶惑、激动、沉迷、幽怨……后来,她告诉我,她很心疼索德格朗。她说,女人写诗,是唤醒自己的本能和记忆。她说索德格朗的诗就像受伤的小鹿饮着生命的泉水,洗礼着神秘、高贵和圣洁。当然,绝望、幻灭、悲哀的色彩也都在……
“是我——我自己的囚徒——这样说:生活不是春天,尽管穿着淡青色的天鹅绒衣服”“生活是限制我们行动的狭小的圈子,我们从未越过那无形的圆周”“生活是置自己于不顾/无声无息地躺在深深的井底/任头顶上的太阳/像金色的鸟在天空盘旋”“生活是短促地挥手告别,然后回家睡觉……”(索德格朗《生活》)
她说:“你瞧,索德格朗把生活和命运看得多么通透,可是又多么美啊!她谛听着,想象着,挥霍着,好像每一天都如一辈子那么长,一辈子也像每一天那么短。”
我微笑地看着她倾诉,那儿超越了她自己的局限和遗憾。失业的危机感、生存的困惑以及寻找的苦涩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诗歌的救赎力量。
妻子带着点调皮的神色望着我,说《期待着灵魂》要是自己写的就好了。我让她读给我听,她答应着,用满是感激和憧憬的口吻念诵出那美妙的诗句——“我独自在湖滨的树林里漫步/我活着,同湖畔的老树结友/同一切柔弱的花草交谊/我独自躺在那里等待着/没有一个人走过,一个也没有/硕大的花朵从挺拔的枝茎上向我俯首/不知疲倦的藤蔓一直爬进我的怀里/我对一切都报以一个感情,那就是:爱。”
从畅游索德格朗的世界回到眼前的现实,我们发现皂角园里各式各样的树木正在偷偷释放生命的天然气息。早春的沛然生机从花色草籽嫩芽上面一拱而出,裸露着大地的肤色,佩戴着阳光铠甲般的光晕。几只麻雀欢快地叫嚷,好像在对人们发出诚挚的召唤。快来看春天的脚步啊,快来!水池子里的泉水汩汩地从石头缝隙中溅出好看的泡沫,假山上瘦硬的石块给天光映照得宛如水墨画里的色块、线条。这不是索德格朗笔下冰雕木刻一样的《北欧之春》的造影,而是沈阳这个古城盎然春意下几许春天走来的擦痕样片。
在这书里,我随手翻到了大冈信《为了春天》那首,我跃跃欲试,想给她读。
她说:“我们还是一起吧,读那春天的诗。”
多年之后,我又一次打开诗选,隔着三十年的时光,老去的记忆重新撒上了最初的光、最初的盐分和蜜的滋养。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早晨,我和她一起朗诵大冈信的诗,在春色里,在春风里。
“从沙滩上掘起瞌睡的春天/用它来装扮头发/你笑了/将一片笑泡如波纹在天空抛洒/大海静静地温暖在草色的阳光下/你的手放在我的手中/你投的石子飞在我的天空……”“门在春风中敞开/无数手臂向绿荫和我们摇摆/崭新的道路躺在柔软的大地/你的手在泉水中流溢着光彩/于是我们的睫毛下沐浴着阳光/静静地开始成熟/果实与海。”
年轻那会儿,虽沮丧但还有憧憬,虽落魄但还有信心。我们在皂角园里散步、漫行,听风的絮语,看云的卷动,遐想诗的流淌与自由。
今天想来,那会儿是我们纯真、踏实、历练而又无畏的时光。将诗歌置于世俗之上,把每一个今日和当下视为永恒的、属于心灵的朝拜和祭奠。
我们睁开好奇的眼睛看世界,人类精神艺术的圣火生生不息,照亮了两个诗歌热爱者的内在生活。
《孤独的玫瑰》由《外国文艺》编辑部编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蓝色封面打底,一朵红玫瑰上面点缀着夜的繁星。
书何以如此命名?是因为编者嗅到了诗歌日益边缘化、诗人日益贫困化的气息。“现在一切都必须变成娱乐,都必须是消费品。在这种压力下,艺术沉沦了,蜕变成商业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感叹,道出一个历史时期中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沉沦和危机征兆。
但是,在“写诗不足以维持生计的地方”,还是有多少诗人在讴歌。“在那喧嚣繁华但又干涸荒漠的土地上,他们的诗歌像孤独的玫瑰,绚丽馥郁,引人注目。”
而作为饥渴的阅读者,我们的阅读盛宴又一次开始了。
那一年的夏天,让人带着感激和幸福,带着希望和诱惑,在享受诗歌的天籁中陷落于精神无比丰足的浸润与洗礼。
妻子是从阿赫玛托娃的诗找到了奇异神秘的沟通和共鸣。
我是从埃利蒂斯、博尔赫斯还有史蒂文斯那里发现了诗意存在的另一种光影和面目。
当然,无论我还是她,都受惠于《孤独的玫瑰》书卷里每一位诗人星星般的照耀和接引。可以说,众多的星光汇聚成了诗歌夜空的共同璀璨。
不过,偏爱总是有的,偏爱来自甄别和比照,来自寻觅和探求中的取舍,还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
戴骢翻译的阿赫玛托娃,看上第一眼,就征服了她。她告诉我,比索德格朗还好。
在此之前,她看的是吴劳译出的普拉斯的作品。她说太震撼了。她指着眼前的书页,念叨着“每个死孩蜷着身子,像条白蛇,每人趴在一小罐牛奶前”“爹爹,爹爹,你这狗杂种,我一了百了啦”“我披着一头红发升起,我吃男人就像呼吸空气”……她说这女的疯魔了,中邪了,但还是盛开着,让人跟着着魔。
她对阿赫玛托娃的评价是安静、诚挚、朴素、有分寸感,如沉香散发出经久的味道。
也许个人气质决定了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情感认同。
读阿赫玛托娃,是往内心更深处走。其实,这位俄罗斯女诗人骨子里也有很冲动、很强烈的东西,就像这样的诗句:“请你把沉沉的夜色织成殓尸的丧布/覆盖住这柔肠寸断了的陨灭的身体/再唤来瓦蓝色的氤氲的迷雾/给我唪读安魂的祷文,把我吊祭……”它足以将人引领到绝望的地狱之门或是幻灭的炼狱的入口,但决绝飞扬的本色无疑更属于她的同胞、另一位诗歌女祭司茨维塔耶娃。那是若干年之后我们的分享,最初还根本无缘触碰到呢。
妻子倒是更痴迷阿赫玛托娃温情柔和细腻的口气中布下的娓娓道来的语调,从早期《无题》的“雪原上滑雪板留下的那道长长的痕迹/仿佛让我忆起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年代”,到后期《回声》的“通向往事的道路早已湮没”“那边是什么?是沾有血迹的石板,是进入墓穴的栏门/或者是至今不肯沉寂的回声”,都是诗人在这萧条、开阔、荒凉、原始的地带铺设的通往人心灵密度与温度的桥。
索德格朗与阿赫玛托娃,包括狄金森在内,无疑都是生命的朝拜者,亦是诗性精神的皈依者,阅读她们堪称一生的功课。庆幸我们很早就走进这诗歌课堂的某个小角落,听到那些灵魂微步的跫音。“它来时,山水谛听——阴影——屏息/它走时,就像死神脸上的迷离。”狄金森那咏叹调般的碎语沉吟,至今还引领着千千万万读者越过心灵的荒原,怡然奔往朝圣的路。
当然,就文学阅读而言,无论多么亲密地交接或融合,到一定节点,也总会引发自我的内在骚动和叛乱。
“我渴望一间小屋/或是属于我的小岛/白天看风的行走/夜晚听山鸡的鸣唱/不要纸/不要笔/更不要别人的诗章/让思想顺水而流/让生命渐渐消亡”,这是我妻子当时的告白——读索德格朗她们读痴迷了,然后想着挣脱,重获身心自由的某种宣泄。大概这也是物极必反的交接、相遇和纠结,里面是深深的依恋和忘情,还有不能自拔的告别之恸。说到底,人还得走自己的路,学着写自己的诗。你的样板再强大,他们(她们)也都成了过往和历史,不会代替你生存于世。
不读诗,苦闷;读诗,更苦闷。这就是青春的迷惘与苦涩,如同药和酒,非得调和在一处,也只能调和在一处,才见格外的甘洌香醇。
当然,无论小屋还是小岛,既是实体,也是想象中的存在。那是灵性栖居的家。
我们住的那个小屋处于阴面,下午才有阳光。它是不是妻子心目中的“小岛”另当别论。反正它是我们的窝,我们的乐园。
尊贵的客人常常在茶余饭后被邀请出来,他们从书本上探出头,带着爱琴海的风浪、潘帕斯草原的一轮落日,或是来自拜占庭文明的精致的手工艺品……
“我活到一定的年岁,诗来找我。”聂鲁达的这番话,多像我们诗性阅读的开场白啊!
是的,在这间小屋里,我们读叶芝,读埃利蒂斯,读米沃什,读博尔赫斯,读史蒂文斯,读拉金……这些诗歌的至尊者将他们的微笑、谈吐、机智、风趣、幽默、抒情、理性……一股脑融进了空气、微风、水、粮食,还有梦境。
夏天多雨,阴面的屋子更显得潮湿。墙皮斑驳,似乎有绿毛状苔藓微微渗出。偶尔有查水表的、查煤气的,敲门声挺大,仿佛是对寄人篱下者的无端轻蔑。
妻子终于找到点活儿干,到一家不太正规的民营报社帮着编辑版面,但是一连好几个月都没有工钱,只是发了点生活零用品权当报酬。沮丧和不甘是有的,冷清和寂寥更不匮缺。然而,这憋闷压抑的小窝,只要主人眉头舒展,言笑晏晏,那就是诵读文学的时刻光临了!
有一天,好像赶上什么节日,她很早就下班了,带回来一瓶酱香型酒。于是,我们在那个阴沉沉的下午弄来点小菜,其实就是凉拌黄瓜、盐水花生,还有用酱油和陈醋泡的萝卜缨子啥的。我们喝着那发出辛辣滋味的酒,喝到醉醺醺的。
我说:“我喜欢爱琴海的饮日诗人,就是埃利蒂斯。这家伙的诗感性、野性、孟浪,你听那首《畅饮太阳》,跟摇滚乐似的。当然博尔赫斯也了不得。‘我贫困和富足中的日夜,与上帝和所有人的日夜相等。’我太爱这句话了,他老人家1986年就走了,真庆幸有一段时间能跟这位大师共同存活在地球上。史蒂文斯,一个超级隐士,超级喜欢色彩和音乐,那诗里满是野兽派绘画的风格。他崇拜自然,欣赏南方的海和北方的雪……”
我嘀嘀咕咕的,近乎痴迷、陶醉地瞎聊。她眼神里冒着兴奋的光波,好像其中也有诗的成分。她说:“你还不知道吧,最近我迷上了绘画,偷偷地画,趁你出去遛弯时,我才拿起铅笔和本。就在那本上、在我休息的空当,画出那些人物、那些线条和生命……”
晚来,外面起风了,伴着雨,淅淅沥沥地敲打窗门。
妻子从她的收藏夹里取出一摞摞肖像画,我有些惊呆,更多了些激动。翻阅画面上的人物、神情、体态、仪表,他们的精、气、神沾满了岁月的光泽,浸透了人生的风骨、肌理。就在一瞬间,这些大师巨匠变成你身边的亲人或是朋友,音容笑貌,栩栩如生。
她画出了聂鲁达沉吟时的手势,那托着腮帮的造型,似在从容遐思,默默等候灵感的不期而至;威·休·奥登的“虎面”,皱纹堆叠着远近沟壑,屏息静气,凝神体察;头戴学士帽的纳博科夫挤眉弄眼,一副顽皮,好像洛丽塔的精灵就埋藏在他的脑盖四周;爱默生深邃的眼神、高高的鼻梁和坚毅的嘴角,本身就如同雕刻着爱与美的生命气质的塑像;瓦尔特·惠特曼蓬勃的胡须仿佛洋溢着原始野性的莽原上的草茎,浓眉豹眼里蹿动着猎猎雄风;年轻的洛尔迦,无边的忧愁袭上眼角,安达鲁西亚的风光岁月临摹出精神仪态;老去的歌德看透了世间繁华,环视宇宙的倦目里盛装着燃烧过的生命灰烬……
我们欣赏着这些动人的肖像画,闲聊这些画中人物的作品、生平和轶事。慢慢地,睡意袭来,窗外的雨滴更加淅淅沥沥。
直到后半夜,传来急迫的敲门声,两个人都惊醒了。我一看座钟,才凌晨两点左右。打开门,只见慌里慌张的楼下住户气喘吁吁地说,他们家被水淹了。赶紧去阳台察看,方才发觉,由于没有做封闭,杂物堵住了下水口,雨水淤积起来,连外屋地都满是,渗透到楼板,顺着溜到了底层住户的家。
我们各自披着一层塑料布,就端着盆往外泄水,忙碌得通身汗水和雨水混杂在一起。
那夜的雨慢慢减缓了,像熟睡的儿童的呼吸,也像诗的呼吸。
倦怠的两个人再也无法入睡。索性坐在灯光里,继续浏览人物肖像画。看永生的地中海阳光下打盹儿的加缪,远处是青春,爱情和死亡;凝视戴草帽的叶芝、抽烟的萨特、撇着嘴角的拉金……
聊到天亮,雨水终于停下了脚步。新鲜的太阳宛如红里透金的鸡蛋黄,挂在天上。是周日,我们吃完早点,又去了皂角园。
秋意裹挟着一层舒爽,露水挂满了枝头。皂角树的果实已悄然长成,往下垂落着成熟的身姿。
有几个小孩在荡秋千,忽高忽低,忽上忽下,有个顽皮的小家伙故意摔倒在地上,让他的同伴扶他起来,还嘿嘿地笑。
吹萨克斯的中年汉子从前也来过,那会儿音调发涩,还不够圆润饱满,如今好像上了道。
我们在园子里越走越远,不一会儿,她和我玩起了捉迷藏。
她躲进丛林中,在巨大的假山石背后。
我找了半天,愣是没有发现。
后来有一位年近花甲的阿姨碰到我,笑眯眯的,用目光示意她在哪里。
或许,当初她和自己的同伴儿也玩过类似的游戏。可是忽然自己就老了。
归途中,我们又说起诗。说起在诗歌中停留的时光,甚至说到了死——今生和来世的界限,两个人遐想着,猜测着。
我们又诵读起史蒂文斯的《星期日早晨》,尤其是读到“人生从何处来,又归向何方”时,那别样的问询好像获得了新的意义,似乎有了答案。
答案就在风里,在早晨起落沉浮的光线里,似有若无,抑或在叶子和枝条的空寂中飘飘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