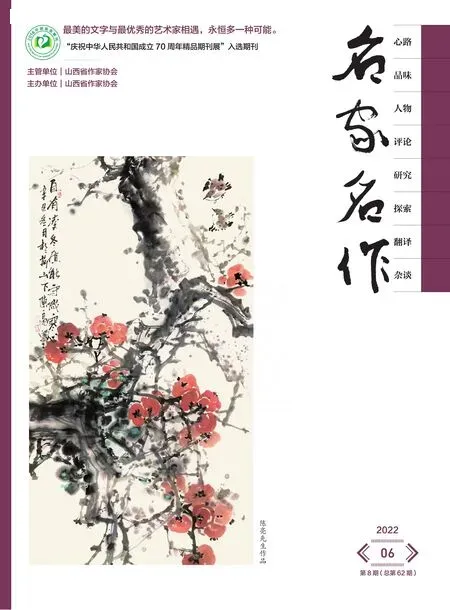荀子和墨子的天道观刍议
2022-08-06徐如平
折 娜 徐如平
荀子与墨子都是先秦诸子思想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天道观与其他思想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二人的天道思想都有一定的先进性,对后世天道思想有一定的启发性,对当今生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墨子的天道观
墨子关于天的主张,最明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天志,一个是非命。首先,从《墨子·天志》中可以看出,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是可以知道善恶的天。“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无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之天欲义而恶不义也。”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天有自己的意志,有其想要的东西,也有其厌恶的东西。由此可知,墨子的天是意志天。又从“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可知天的意志集中体现了墨子的兼爱思想,顺从天意的人就是古代先圣帝王尧、舜、禹、汤,他们“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得到了赏赐。而不顺天的意志就是古代暴王桀、纣、幽、厉,他们“上垢天,中垢鬼,下贼人”,得到了惩罚。墨子把天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给天塑造了极端威严的形象。但从实质上来说,墨子只是将天作为一种工具,一种体现自己思想的工具。“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这句话体现了这种实质。墨子思想中不只是天的形象,鬼的形象也有同样的作用。
其次,墨家也主张非命,“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墨子·非命》)由此可知,墨子是完全否定“命”的概念的。 他认为所谓“命”实质上是“暴人之道,圣王之患,天下人之后害”,如果一切都听从于命,相信贫富、治乱、寿夭都是由“命”来决定的,那就必然会导致人们放弃自己的努力,“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使得社会生活陷入混乱停滞之中。以“非命”作为基础,墨子同时也主张“尚力”。墨子认为人自身具有“力”,完全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来改造自然,治理社会。禹、汤、文、武时之所以国泰民安,原因不在于“命”,而在于禹、汤、文、武能够努力劳作,奋发有为,改造自然,治理社会。为什么许多国家的现实状况与君主的理想相差甚远,“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间者众”,根本原因就是信“命”的人太多了,根本不相信通过人自身的努力可以富国强兵,生活富裕。
从表面来看,“天志”和“非命”是两个相反的概念,也有的人认为,墨子提出的非命观与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相对立,墨子一方面在肯定天命,一方面又否定天命,但深入研究后可以发现它们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对于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的说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原来墨子不信命定之说,正因为他深信天志,正因为他深信鬼神能赏善而罚暴。……所以他说能顺天之志,能中鬼之利,便可得福;不能如此,便可得祸。祸福全靠个人自己的行为,全是各人的自由意志招来的,并不由命定。若祸福都由命定,那便不做好事也可得福;不作恶事,也可得祸了。”薛柏成在《墨子讲读》中说道:“从墨家‘强力’的观点出发,‘非命’并不是否定天和鬼神,而是与其‘天志’‘明鬼’观念相结合,主观上借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在客观上利用鬼神的宗教权威来曲折的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两种说法都有合理性,我认为墨子的学说作为一个十分完整的系统,不会出现这么前后矛盾的说法,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墨子对“非命”的阐述,不是与“天志”“明鬼”对立,而是对其的补充和发展。墨子认为“天志”是积极向上的、正义的,而“天命”则是消极的,被固定的,没有发展的生活方式,因此不能顺着命定的命运生活,而是积极寻求由自己决定的生活。从墨家所代表的下层小生产者的阶级立场来看,他们在社会中并不是规则、法律的制定者,而是执行者和顺从者,必然会受到上一阶层的剥削与压制。因此他们一方面将天作为可以为自己主持公道的主宰者,认为天一定会惩罚剥削自己的上层阶级,另一方面又相信一切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而获得,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安慰或者说是寄托。这也是为什么墨子会提出如此相悖的两种思想的一种解释。
二、荀子的天道观
首先,荀子的自然天。在荀子之前,人类对天的认知十分有限,普遍将天与“神”联系起来,孔子虽然对天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但没有脱离天决定人的限制。荀子强烈地批判了庄子的哲学,认为庄子将天道看得太重,庄子思想中才会有很多的安命主义和守旧主义,同时又不认可儒家墨家提出的赏善罚恶的“有意志的天”,因此荀子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朴素唯物主义天道思想。但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自然天是占据主导作用的。他的《天论》中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火召),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可见,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界中的所有日月星辰、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以及气,都可以被当作是天。因为在生产力落后的时期,人类无法对自然界的运转做出科学的解释,因此才将万物运转神化,认为这些都是受到“天帝”的控制,荀子改变了这种认知,提出自然天,但又没有完全否定天的作用,使得对天的认知走向理性化。与老子提出的“道”的概念很像。
荀子将天看作是无意识的天,又将天人分开,要想富国富民就必须注重人自身的作用,上段中说道想要“天不能贫,天不能病,天不能祸”,就要强本节用,养备动时,循道不忒,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子在《天论》中说道:“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荀子不主张人类过于依赖天的赐予,主张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服天,利用天。荀子的天道思想也延续到他的人性论之中。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依这几条界说看来,性只是天生成的,伪只是人力做的(‘伪’字本训‘人为’)。后来的儒者读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把‘伪’字看做真伪的伪……大家都以为凡是‘天然的’,都比‘人为的’好。后来渐渐的把一切‘天然的’都看作‘真的’,一切‘人为的’都看作‘假的’。……独有荀子极力反对这种崇拜天然的学说,以为‘人为的’比‘天然的’更好。所以他的人性论,说性是恶的,一切善都是人为的结果。这样推崇‘人为’过于‘天然’。”
其次,便是天人相分。与天道相对应的是人道,因此天人关系是荀子天道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天的变化与人无关,天也不会对人有情感和赏罚。“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荀子译注》)社会的安定与混乱不是上天造成的,而是君主们的政策与行为造成的,天地万物不会因为禹的贤明或桀的暴虐而改变,但人民的生活却会受到影响。因此国家的兴衰、社会的治乱、人类的祸福不应从天地、日月、星辰找原因,应从人类自身寻找根源。至于人类应该如何做,荀子也给出了答案:“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这句话的意思是用合理的措施来对待天就吉利,用不合理的措施来对待天就不吉利。加强农业,节省用度,那么天就不会让人贫穷;按时耕种,天就不会使人痛苦;顺应自然规律,不出差错,天不会使人受到灾祸,所以说旱涝不会让人饥饿,冷暖不能使人生病,奇异的现象也不能带来灾害。人类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自己劳动,自给自足,自己满足自己需求,合理对待自然,这样人就会衣食充足。
要肯定人的作用,但又不是完全弱化天的作用,荀子对天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制天命而用之”这一主张之中。但又不是完全“制”,也表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论述。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提出:“人本身及其环境又是自然存在物有其‘天’(自然)的方面,从而如何处理好这个方面,即人如何遵循客观自然规律,使‘天地官而万物役’也就是‘知天’这恰恰又是荀子非常重视的。”廖名春也认为,荀子天道观中还有一些“天人合一”说的残留。楼宇烈则认为,“制天命而用之”是指人具有这种“能参”天地生养万物过程中的主动性、能动性,既知其所为,又知其所不为,达到人天和谐的状态。这些学者都认为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和人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统一的,可以看出荀子的天人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十分理性的程度。
三、荀子、墨子天道观的联系和区别
这样的“非命”“尚力”思想与荀子的“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思想是有很大的相似性的。墨学作为春秋时期的显学,墨子的活动时期是明显早于荀子的,从上文荀子的天人关系思想可以看出吸收了墨家的“非命”“尚力”思想。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也说道:“一方面,事在人为,命运不是由‘天’定(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吸收了墨家的许多思想,包括‘重力’‘非命’‘强本’在内)。”同时在对天的论述方面,荀子和墨子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对于天的地位的提高和推崇不用多说。对于荀子来说,“天是不能够主宰人事的,所以不必去深究天的奥秘,只需要弄明白人的规律就够了。另一方面人本身及其环境又是自然存在,物有其自然的力量,从而如何处理好这个方面?……这里强调三个‘不失其时’,其实也就是要根据客观世界的规律来种植耕作,逐渐天人之分,也必须‘顺天’。‘顺天’在这里倒是更为具体和更为现实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所以说荀子和墨子对于天,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顺服的意思,是他们对于“天”的认知的共同点。
但是他们二人对天的认知有很大的差别,从哲学上来看,他们对于天是否有意志,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荀子认为的天是自然天,只是物质所构成的天地万物,是唯物的天。 孙伟在《从“知天命”到“制天命”——荀子天命观思想新探》中这样说道:“‘天’是产生万物的自然,没有道德属性,而人也没有来自 ‘天’的道德使命。‘天’没有神圣性。”由此也可知“天”只是物质意义上的天,没有道德,也没有神力。而墨子的天则是有意志的,可以作为人类模仿的标准,也会对人类的行为进行规范,赏善罚恶,客观唯心的天。从上文“天志”“非命”是否对立也可以看出墨家的天包含着小生产者们“赏善罚恶”的期待,必然是有意志的人格天。
四、荀子、墨子天道观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他们的思想对我们解决某些问题也有借鉴意义。比如,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由于人类过量排放二氧化碳,燃烧石油、煤炭,导致了严重的污染。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全球臭氧层被破坏。在这个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更加凸显出来。这个时候荀子的天人观念便为当今的危机提供了解决的思路。在解决当前人与自然矛盾的问题上,我们也应该拿出当时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勇气和毅力来解决我们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