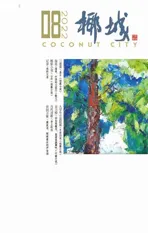山恋(短篇小说)
2022-08-05◎杨锋
◎杨 锋
弟弟做了个梦,甜美的梦。他笑了。
可是,梦中断了,弟弟恼了,狠狠地踢了一下被子。
岩崖顶上的飞泉,沉闷、单调地滴着。冬天刚过去,天地仍然密封在一口深深的地窖里。一切都是死一般的冰凉僵硬,一切都还在沉寂中鼾鼾的昏睡。
然而荒山醒了,是兄弟俩沉重的山锄,狠狠地砸醒的。
过完年,热闹的村庄变得沸沸扬扬。每天都有三三两两的小车从村口开出,在村外的道上疾驶,消失在远方山凹处。也有一伙伙的男男女女,拖着拉杆箱朝临时汽车停靠站走去。这时候,弟弟周老二总会坐在自己的家门口,眯着眼射一会太阳,目送远去的小车和渐渐消失了的男男女女,心里就会默默地说,又走了一批。他就会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该动身了?可是看看哥哥周老大,一点动身的意思都没有,他不知道哥哥怎么想的,问哥哥,哥哥从不正面回答,有时笑笑,有时说,着什么急。弟弟是有些急,年过完了,也热闹过了,大家都陆陆续续各奔东西南北,他觉得再待在家里,实在有些彷徨、寂寞,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不如出去的好。
这些年,兄弟俩在外打工,虽然辛苦,但快乐,也挣了一些钱。哥哥说,给你说一门亲事吧。弟弟也不反对,也该是成家的时候了。可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上,弟弟心里有些烦,对哥哥说,趁早出去吧。可是哥哥偏偏不急。上元节过了,该走的都走了,没走的也该是最后一批。哥哥却突然说,我们上山吧。弟弟没有明白,茫然地看着哥哥。哥哥肯定地说,对面那片山多肥实,却荒了。
弟弟不解地看着哥哥。
我们把它开垦出来。
可是,弟弟仍然没有明白。哥哥把劈山的机器买回来了,他才明白了。但他仍然是一脸茫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开垦荒山?
哥哥诚实厚道,性格内向不善于言辞。他的想法,弟弟常常难以明白,他的行为,弟弟经常跟不上趟。
哥哥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家乡的群山绿油油的,漫山遍野的花,漫山遍野的山果。弟弟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哥哥说,记得我们小时候,山是我们的庇护所、游乐场。粮食不够吃的时候,我们在山里拾山果,用火烧烤。真香啊。可是现在……哥哥望着山,惆怅。他常常会出神地望着远山,会自言自语地,那郁郁葱葱的山林,陪伴着他的整个少年时代,是他少年时代的渴望、梦和歌。现在,一说到现在,他会忧伤地摇头,那山真荒凉啊。多少年,他就梦想着能把那片荒山开垦。于是,他毫不犹豫向村里承包了那片荒山。
父母去世早,兄弟俩相依为命,哥哥是弟弟的依靠,是弟弟的灯塔、方向。哥哥也像慈父母,处处精心呵护着弟弟。哥哥本来想安排弟弟出门,但他不放心,弟弟从来就是哥哥的跟屁虫,弟弟也不习惯独自出门。哥哥说,上山吧,于是,像五年前第一次出门打工一样,毫不犹豫跟着哥哥上山了。
夜,真静,死一般的静。松明子烧到了尽头,忽闪忽闪了几下,灭了。只有那火红的碳火,像一只狰狞的鬼眼,闪闪的亮着,盯着。岩崖洞里失去了唯一的光明,顿时黑乎乎的,没有月光,没有星光,天底下抹了一层厚厚的灰,夜风不时地踢着简陋的寨门,啪啪的响。寨门外的芒草丛里,窸窸窣窣的,似有无数的妖魔鬼怪在蠢蠢欲动。弟弟想,这地方一定会出鬼怪。他再也睡不着了,他睁着双眼,盯着黑黢黢的岩洞顶。他不怕鬼,但真怕这空寂、单调、无聊的夜。真怕这清苦、荒无人烟的单调的生活。他突然后悔了,真不该跟哥哥上山。他想着刚才的梦,自己非常有钱,西装革履,大沓的人民币,甩手几千几万。盖起了洋楼,整套的现代化家具。还开着高级小轿车,——嘻,还相中了个漂亮的老婆。
然而是梦,一个中断了的梦。他有些恨自己,真窝囊,连梦都做不完整。
哥哥在沉沉的睡,他侧过身,听着哥哥均匀粗重的呼吸,和微微的鼾声,闻着哥哥那强烈的男子汉的气息,他感觉到了,哥哥壮实的身体里,藴藏着无穷的力量。他能把整座的荒山开发,他能把整座荒山绿化。然而他,觉得不能,他坚定地认为,一定不能。黑暗中,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会儿,他又想起了刚才的梦。他仿佛见过那梦。什么时候?在哪里?
一辆小轿车哧啦一声停在他身旁,扬起了一股灰尘,他吓了一跳,他心里正想骂,车窗拉下,伸出一个细小的脑袋。嗨咿,二同学。最近可好?
是“尖猴”?不错,是他。
那天,哥哥让他进城采购一些物质,却意外遇上了。他们从小就是“死对头”。拼学习成绩,他从来就是属一数二,“尖猴”是倒数。在体力上也想和他较劲。他们常常在校外的沙滩上争高低。“尖猴”天生体弱,不是他的对手,但他天生有一股犟劲,屡败屡战。让他佩服,更让他不耐烦,甚至厌烦。中学毕业后,他们分开了,听说他随他父亲做生意去了。小时候虽然淘气,现在并无什么介蒂。
尖猴,你想吓死我啊。
还认识啊?
你就是成灰,我两指头一搓,也能搓出你的模样来。
最近好吗?
他本想说,好,在你面前,我什么时候孬过。看看眼前的现实,他难以启口。他不由把头转向别处。
别灰心,凭你的聪明才智,一定会大有作为。走,多年不见,到寒舍咱哥俩好好聊聊。再喝两口。“尖猴”硬把他拽拉上了车。
他涨红着脸,心里隐隐的痛。本不想去,却已经坐在了车里柔软舒适的座椅上。小车在一栋小洋楼前停住。是褚红的西式小洋楼。他张着嘴。这是你家?
请进。
这怎么是他家?他的记忆里,是一栋又矮又破,几乎要倾倒的小屋。他曾经嘲笑过,像个牛棚。他突然觉得,小洋楼太刺眼了,太嘲笑人了。那窗,那门,像是一只只嘲笑人的嘴巴眼睛。他真想扭头就走。
这楼连买带装修共花了五百多万。
五百多万?他吓得差点从沙发上滑落下来。
他感到不平、愤懑。他“尖猴”并没有比自己多长什么,也没有比自己更聪明,凭什么他如今富得流油,过的跟王子似的生活?而自己在这荒漠的山上,挖山种树?于是,他不停地思索,日夜寻找答案。于是他做了那个梦,那个甜美的梦。
天亮了,哥哥推醒了弟弟。吃饭了。
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乱石垒起来的锅台上,放了一碗干菜。弟弟瞥了一眼,味蕾迅速随着污物从肠道里排泄了。他想,要有一碗鱼,或者肉什么的多好。然而没有。洞口飘来阵阵的野草味,与洞里的潮腐味暧昧地卿卿我我,弥漫在整个洞中,令人晕厥和作呕。弟弟突然想起那天“尖猴”的家宴,是那么的丰盛,看看这山洞里的人,过的是什么生活?原始啊,可悲啊。他胡乱扒了几口,郁郁地搁下了饭碗。
不舒服?
没有。
哥哥从瓦罐里掏出一个咸鸭蛋,将就一餐,你嫂子今天会送菜来。弟弟再也没有胃口,他闷闷不乐地坐着。望着还是朦朦胧胧的天空。哥哥突然说,我昨晚上做了个梦——又是梦。弟弟蓦然转过头,望了哥哥一眼。哥哥继续说,我梦见我们种的树长大了,密密麻麻的结满了果,黄澄澄、油亮亮,那香气——弟弟忍不住笑了,他再也不想听哥哥说梦,他走到门口站着。天,还是朦朦胧胧,他又折回洞中,倒在露水打得潮漉漉的床上。哥哥继续说梦,年底再把我们的房子升高二层,万一你说上媳妇了可以做新房。
可是,钱呢?
这几年咱哥俩打工积了十五万,拿五万投资山场,五万盖房,五万加上你嫂子养家禽畜积攒,够你娶媳妇。三年后,这里就不再是荒山了,绿油油的一片,累累硕果。我们的日子好着呢。
弟弟想,这就是哥哥的梦?哥哥上山的梦?
弟弟觉得,哥哥的梦就像烧过的灰一样,太枯燥无味了,太可怜了,五百万呢,小洋楼呢?他闷声不响走到洞口,捆扎一把树苗,撩在锄头把上,顺着山道走去。天还早,那山,那草,那田畴,那山间小路,和小路尽头的村庄房子,一切都还在朦朦胧胧中。山顶上的雾,还在不断地往下压,它似乎是在向这片世界宣战。只有小溪潺潺的流水声,在这寂静的清晨,不管不顾的响得格外清脆。但他觉得格外的刺耳,格外的沉,像锤子,一下一下不停地捶他沉重的脑袋。他寂寞地走着。他又在想夜晚的梦,也想着这清晨。城里人在干嘛?“尖猴”在干嘛?早跑步还是公园里锻炼?还是在做发财的美梦?也许在准备早餐,豆浆、蛋糕?还是牛奶面包?这才是现代人的生活。可是我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他突然有些愤然,他们能,为什么我就住定要在这荒山野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在这寂寞、荒凉中流逝美好的青春?是命吗?他想,也许是,那年,高中最后一年,同学老师都认为他是名牌大学的预备生。可是,哥哥大病一场,接着嫂嫂又生病,注册时候,家里一贫如洗,嫂嫂把借来买药的钱给他。他大哭了一场,发誓永远不进校门了。这难道不是命?
雾,没羞没躁的越滚越厚,天空一片灰暗,红彤彤的太阳在晦暗中痛苦地挣扎,变成一枚随意抛在空中的钱币。一片烧过的山,一片黑乎乎的地,哥哥奋力地、有节奏地挥舞山锄,头顶闪着道道的弧光。哥哥满头大汗,他把冬衣一层层剥去,剩下最后一件单衣,雾在他身上肆意狂欢,被他的山锄撕裂得支离破碎。重重的山锄声地动山摇,把它震得魂飞魄散变成点点的水珠四处逃窜。哥哥仍然是满头大汗,他把上衣脱光,用衣服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把衣服捆扎在腰上。他回头看了看身后,留下了一片新土,留下了一行行整齐的绿苗。树苗浸着他的汗水带着他的心和爱,也带上了他的希望和期待。他满意的笑了。
弟弟举着山锄,他觉得很沉很沉,那捆树苗散乱在他的脚下。他的心也像锄头,沉沉的。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扔下锄头,仰面躺下。烧过的草茬小灌木茬,刺着他的脊背,生生的麻木的痛。雾越来越浓,缠缠绵绵滚滚搓搓终于变成厚厚的云。又演变成颗颗粒粒的雨,噼噼啪啪打在弟弟的脸上,凉嗖嗖。他没有躲,也没有遮挡,任凭雨鼓点般敲打。
你怎么啦?哥哥关切地问。
哥哥,我想回去?弟弟说,我要和“尖猴”一起做生意。
哥哥愕然,注视着弟弟,好一会儿,他似乎明白,一阵阵的忧伤爬满全身。他梦噫般地说,这土多肥实,如今荒芜,真可惜。
它就是一片荒山,寂寞、荒凉。
扯。哥哥不同意,他注视着那片种满了树苗的山坡,眼里放出一片绿绿的光茫。你真想去做生意?他转头问弟弟。
看“尖猴”要什么有什么,看我们,还在过原始野人般生活。
哥哥叹了口气,去吧,存折在你嫂嫂哪里,留下尾数,其余拿去做本金。
弟弟走了,哥哥第一次感到了孤独。仿佛一片孤舟在海风狂澜中漂流。他忧忧地望着弟弟远去。他想不明白,弟弟怎么就这么突然走了呢?他望着这空阔的原野,望着迷迷茫茫的天地间的一切都是朦朦胧胧,似乎也觉得自己的一片都是迷迷茫茫、懵懵懂懂的了。这一片大地,原来有密密麻麻的原始树木,树上长了山果果。父亲是护林员,整天在森林里转,经常采回来一袋袋的山果果,把它们磨成了粉,与大米粉搅拌,熬成一锅香喷喷的糊糊,父亲说,饿了吧,吃吧。他接过父亲递给的糊糊,诱人的香气,让他味觉也稀里糊涂的空了。他狼吞虎咽,一碗接一碗。父亲笑嘻嘻看着他,眼睛好像在问他,饱了么?他摸摸圆鼓鼓肚皮,傻傻的笑。父亲说,这是山里面的山果果做的,好吃吗?他砸吧着嘴,感觉到苦椎子的杂味,他皱了皱眉头,就是有点苦。他一口一口喂弟弟,饥饿的弟弟,一口一口吞咽,他想问弟弟,苦吗?他没有启口,他怕弟弟饥饿。从此他常常随父亲进山,拾许许多多的山果果、蘑菇、山鸡野兔。填补时常咕咕的饥肠,还让他品出了人生的五味杂陈。山上那些的树,茵茵绿绿,庇护了许许多多的生灵,也庇护了山外许许多多的人家。后来,他常常带弟弟在山里寻找童年喜爱、童年的乐趣,童年的梦。那一年,突然漫山的大火,把山林烧毁了,又把那漫山的树木砍伐了,一车车的运往山外,消失得无踪无影。接着是漫山遍野的人,漫山遍野的红旗,一个冬天过后,满山都是浑黄的新土,父亲悲伤地说,再也没有了山果果、山货了。他不解父亲为什么那么伤心。父亲死了,他承担了家里的重担,他突然明白了,但他明白得太晚了,也无济于事,眼前的一切,已经是光秃秃一片。但他记住了父亲临终前的期望:不知什么时候还能长满树木?你要想办法,努力努力。那时他笑了父亲,也许他在想,那又怎么样呢?父亲继续说:在那里给我找块墓地吧。他没有按照父亲的遗愿,他并不明白父亲的心愿;他也不可能做到,漫山遍野的人,漫山遍野不长胡须的玉米和不长穗小麦高粱。没有给父亲留下墓地的空位。他给父亲在村后半山挖个墓穴,没有隆重的仪式,平平常常落葬,算是完成父亲的一生。多年以后的现在,他终于明白了父亲。
哥哥转身往对面父亲墓地望着,深深地歉疚地望着。但他还是长长的舒了口气,冥冥之中,仍然没有让父亲太失望,那个墓穴高高在上,可以远远地直视着他挥舞山锄。可以瞭望四方。看着四方的山岗绿遍,父亲仍然是个护林员,随时都可以眺望呵护群山万木。
哥哥想着,父亲死的时候,他才哇哇细语,不谙世事,又怎能理解父亲,理解这片山?
哥哥快步登上山头,望着山下,一行行幼稚树苗在风雨中晃晃悠悠,他往远处眺望,仍然一片荒芜的山岗,他把目光慢慢地往回收,几千亩的荒山秃岭,他突然嚎叫,我能把这里变成绿树茵茵,周老大记住,一九九五年,你三十岁,二零一五年,当你五十岁的时候,这里一定是绿树茵茵,茶果飘香,
哥哥似乎没有了任何的遗憾,他一如既往每天挖山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