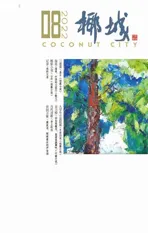海南,中国的大客厅(散文)
2022-08-05李美皆
◎李美皆
因为是乘飞机从天空直抵海南岛坚实的地面,并非舟车劳顿跨海而来。所以,没有登岛的感觉。岛只是我的一种理性认识,感性中的海南是热带,是抬脚可及的海,岛屿的感觉倒不显著。
我的“印象海南”,首先便是丰腴的大叶植物和草木葳蕤的无缝“地衣”,其间身量高挑风致绰约的椰子树脱颖而出——其实是不是椰子树外地人并不确知,棕榈树椰子树总是区分一时下次又忘记,最后索性放弃辨认,椰子树成为一个合并同类项的“能指”符号;其次便是四面皆海,似乎从任何立足的地方出发,几步便可抵达海。总之,我的海南印象是椰风与海风一体的,模糊又顽固。
中国真正的热带省份唯有海南,国人若要在国内寻迹热带,便只有往海南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南是海南人的海南,也是中国人的海南。尤其到了冬天,这个大岛就是所有来此避寒之人的暖气片。我在11月份的三亚遇见一位来自东北的无腿行者,三轮车就是他的家,骑到哪儿家就在哪儿,像蜗牛一样。他说,我就我自己,无牵无挂,还不往暖和的地方去嘛?起码海南就算露宿街头也冻不着人。这是大实话。我有点羡慕这种摆脱了家的羁绊的轻松豁达,温暖的地方就是家,人的天然的向光性使他选择了海南,海南为他提供了一个天大地大的庇护所。若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生在中国,也该往海南去的吧?那就不至于在大年夜冻死了。至于一个流浪汉的吃饭问题,在当今中国那是不成问题的,比如,我们当场就扫了他的收钱二维码。
三亚海边的绿化道上,一群群花团锦簇的男人女人在椰风中翩翩起舞,他们周身都在散发着一种气息:享受人生。他们在冬日的椰风中愈发舞出了生活的高致,人生就是辛劳有时,享乐有时,沉重有时,轻扬有时,此时此刻,他们是快乐的。其中还有高品质的民间乐团,非常享受自己烹制的音乐盛宴,歌者在现场伴奏中庄重地演唱,体验小小的高光时刻,坐在轮椅上的观者陶醉地伴着手势张口和声,虽听不清声音,那份享受却是一望便知的。说宾主尽欢都不确切,这里似乎无所谓宾与主,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多半是在冬天离开寒冷的家乡,候鸟一样移居海南,松散筋骨,舒展腰身。他们不一定很有钱,但是,正如智者所言,大自然中最珍贵的往往是免费的,比如阳光和干净的空气。这一切,在海南一一实现。海南张开怀抱,把自身变成了大家的家,此时,海南就是中国的大客厅。
我们从海滩走来,拎着鞋子,幸福着别人的幸福。光着的双脚似鼓掌,一路快乐地拍打着大地,在街角砍几只椰子,捧着边走边吸,走回酒店意犹未尽,与好客的主人再聊一会儿她的黎族家乡的风俗人情,以及那些下南洋的亲人们。
海南现在是与度假连在一起的,是当代中国人的冬日乐园、海洋乐园,这在古代的海南人是无法想象的。曾经,海南是著名的流放之地、蛮夷之地,苏东坡就曾流放于儋州中和镇,他有诗云:海南万里真吾乡。好在,苏东坡是能够在沼泽中看到鲜花的人,他以近乎娱乐人生的旷达精神,发现了流放海南的几许快慰:至少,这里荔枝好吃,这里百姓不错,这里还有条叫“乌嘴”的好狗。但并非人人都是苏东坡,这里确乎曾是苦地,一般人难有苦中作乐的精神。孔见新出的《海南岛传》,就写到了旧日海南人的胸中块垒。“过高的治理成本和愈戡愈乱的局面,让许多人认为海南岛的统治得不偿失。这片蛮荒之地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汉朝甚至曾经中止对海南岛的统治。这种弃儿之感,就是海南人的胸中块垒,这是外乡人所体会不到的。正如自己置身雨中时便觉得全世界都在下雨,生来置身陆地,就本能地感觉全世界都是陆地,根本无法带入岛民的岛屿之感和身世之感。我在海南所见到的孔见,永远是一件原白麻布的对襟盘扣短袖衫,青色裤子黑布鞋,十分接地气的样子,看起来很“海南”,然而,他的祖上其实是宋代从中原迁徙而来。流民的精神基因似乎融进了他的血液,他的书写,带有为海南所张目所扬眉吐气的沉郁与快意。孔见写道,“现在,这里已经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一个坚实的原点,既是出发之地,也是抵达之地,一个可以顶天立地地站立的地方。……此时此刻,这座岛屿显得那么完整,具足生命存在的全部要素。它不欠不余,静美绝伦,是引人入胜的目的地,阳光最为眷顾的所在,所有道路都通往的地方。”是的,今天的海南,已然换了乾坤,流放之地变成了度假天堂。曾经,来此是一种惩罚和流离,现在,则全然变成了享受。来此度假的中国人只会由衷感谢:中国的版图上有这么一座热情的大岛和一片丰饶的海洋。
海南女人最久远的美名,当是“定安娘子”。“娶妻当娶定安娘”,是海南民间更古早的传说,他们把定安娘子当作“镇家之宝”,她们美丽善良,温柔贤惠,心灵手巧,很会持家。海南作家王姹写到的“女人肩挑背扛的,往往是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在我的意会中就是“定安娘子”的形象注解。
“文昌女人”也是美名在外,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据说在以前和现在,海南男人也常以娶到一位文昌姑娘为荣。文昌姑娘的温柔隐忍与坚韧美丽,有人习惯用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宋氏三姐妹”来代表,虽然她们并非在文昌出生与长大。女人下田干活,男人坐在椰子树下喝“老爸茶”,是许多海南以外的人对海南的男人女人的“刻板印象”,其中当然隐含着不平,唯独海南人自己,竟毫无如此不平之气。有人解释,海南太热,男人阳气旺,与这种热是相克的。有人解释,传统的海南人就是男人出海女人做田的,就这样沿习下来了。没有人为你解释下一步的疑问:可是,现代化的捕捞不是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男人去做海了吗?为什么还要习惯女人做田?
出海出洋,曾经是海南男人的志业,他们下南洋,去异乡,赚到钱寄回家乡,除了供养一家老小,就是实现盖大房子的家族宏愿,那些著名的大宅老屋就是这样留下来的。他们也许叶落归根,也许就在异邦开枝散叶,但他们的老宅,就是精神中永恒的家的所在。有些家族中多数人去了海外,对乡土的眷念却依然如初,海南人解释说,他们认为是家乡亲人和先祖的保佑使他们在海外发达的,所以始终对故乡心存感恩。现在,同宗同族的很多在国内的已经发展得比外面的好了,而且,越来越多的异乡人来到了他们的家乡,财富和人的流向都发生了逆转。这就是令无论在家还是在外的海南人都欣慰的新海南。
在儋州,意外地领略到海南的森林田园,它们就在窗外,推窗可及。听得见林中鸡鸭鹅的声音,但只闻其声不见其面。两个姑娘从窗下走过,口中说着:看看跟我期望的是不是一样?嗯,是的,看看跟我期望的是不是一样。客房的装点很像古典的新房,跟女伴开玩笑说,只是缺个新郎。以为住在林密人稀处,还带了电脑,结果是一次都没打开,此地风物,领略不及,怎么可能舍得宅在屋里呢?
随便一节枯老的根桩,不小心落进几粒种子,都能长出羞涩嫩绿的小苗,不经意间成为小家碧玉般的盆景,非煞费苦心的盆景可比,有人说,那是灵芝上的小菜。光透过棕色木栅格投进,落在暖黄的墙上,给人寺院一般的安宁,但又有家常的温暖。那种黄,我管它叫寺院黄。一束干了的野花不失时机地挂在木栅上,使木栅显出了墙的质感,很好地分割了空间。这样的木栅,与其说是隔断,不如说是营造了光影互动的空间感。墙上也是影子的栅格,与实在的栅格相呼应,光影舒朗,生动可人。田园风格的红花布绿木面的客厅家具,宁帖相宜,朴素可亲,看着就想放松地坐下去,仿若回到老家。
民宿的大姐爬上杨桃树杈,摇落一地杨桃,绿黄橘的色泽,代表不同的成熟度。虫子咬过的,一定是格外甜,因为虫子不傻。在自然界,要相信它们的判断力,它们才是自然的主人。一会儿装盘端上桌来,杨桃被横切出星星的形状,切片美到让人一看就想吃,却又不忍下口。所谓美的盛宴,必是照顾到视觉的,就是这样的轻食,恰到好处地满足了感官的多元审美。在二楼连廊上拿着长杆钩下木瓜的热情帅气的小伙儿,却不是民宿的伙计,而是长期的住客。大姐伸出捞鱼的网兜,在一簇累累果实的下方承接木瓜的坠落。果实过于饱和,那些被“计划生育”掉的,落到地上,发出咚的一声。与杨桃簌簌而落相对应的,是木瓜的孤独回响。这就是最真实最富有生命力的田园。
古盐田的前面,装置着时间的定语:两千年。疤痕般的一块块椭圆的晒盐台,似高低相连或散落的枯荷叶盘,使大海都染上了沧桑,沉淀着民生的苦沉况味。置身此间,仿佛轻盈是一种没心没肺甚至罪过,虽然它们于审美上确是别有一番风致的。尤其天阴风大时,古盐田似乎是中世纪的颜色,又似《简爱》和《呼啸山庄》里的沼泽,总之叠加着许多欧洲文艺经典的印象。自从看了安哲罗普洛斯的《雾中风景》,那片雾就写进了心里,时时被触动现身,那是他的“沉默三部曲”之一。而此刻古老的海和盐田就是沉默的,除了撕裂的风,穿过中世纪以及勃朗特姐妹的沼泽,从历史深处横贯东西地吹过来。
老盐之老,原来并非修辞而已,是真的老。几十年的老盐无论做热敷还是食用,都是很贵的。又想起了一出机场时,热汗涔涔口渴难耐的我从陈先生手里接过那杯冰镇老盐柠檬水,嘬一大口,瞬间爽遍全身。老盐百香果,老盐金桔柠檬,都是海南饮品中的经典,怪不得我在北京无师自通地用百香果加盐汽水会感觉那么美味呢,原来是暗合了经典。这次去海南,才知道芒果加酱油是真的,并非无厘头。不过要强调一下,是青芒果。海南人说起青芒果加酱油,是吸溜着口水说的。海南人吃水果喜欢加盐,因为盐去酸去涩提味。海南人几乎吃啥水果都有糖盐两种口味供选择。海南人还热爱姜,红糖加姜也是经典口味,再加椰丝椰蓉等,就是常见的点心馅料。而海南的椰蓉包也是咸甜两种的。海南人对于姜简直有一种近乎宗教的热忱,我这口味博爱却唯独不吃姜的人,居然接受了海南的各式姜味点心,因为他们为姜选择了最佳的伴侣:红糖。古法红糖成功地降服了老姜的辣味,也降服了我对于姜有生以来的排斥。红糖和老姜,是醇厚的味道搭档,和谐共生,甜蜜默契。海南的姜汁椰子粉与咖啡配在一起,也是很独特的“海南”风味,而且充饥。
椰子,也是海南食物中的一大“教派”,堪称“椰子教”。外地人只知道喝椰子汁,实在窄化了椰子,海南人是把它当食物的,与椰蓉椰丝椰片相关的点心自不必说了,椰子鸡也是一道美味,鲜甜悦人,百喝不厌,吃鸡倒在其次了。
直接吃椰子的果实,在我这是第一次。那是做种子的老椰子,外表是木头色的,可以从外到里,一层层吃下去。外面长着竹笋状的芽,叫椰胎,口感如嫩笋;内有口感绵软的完整一球果肉,叫椰宝;椰壳内壁有胶质的椰果冻,刮一撮,滑滑地吸入口中,活性比人工果冻强得多;椰果冻下面是一层椰油,可以食用也可以美容,直接用作唇蜜是极好的。老椰子通常是拿来做种子的,不舍得吃。一颗老椰子放在土里,都不需要埋,它就自觉地生根发芽了,多么谦虚的生命。很多海南的植物,都有温良恭俭让的品性,不要人费神的。我脑子突然短路了,很傻很天真地问,原来一个椰子只能种出一棵椰子树呀,那么,一颗种子换一个椰子,还有什么意义呢?主人奇怪地说,一棵椰子树上不会只长一个椰子呀。我恍然大悟。连这也需要恍然大悟的人,真的需要捂脸的表情包了。不过,如果只长一个椰子,那就会格外甜的,而果实越多越不甜,果以稀为贵。海南的椰子有青椰、红椰、金椰三种,以青椰为最大众化。嫩椰水多,但不甜,水越多的越不甜。一天当中,太阳越充足时摘下来的椰子越甜。这就是我听热心的酒店活动总监讲解的“椰子”的故事。
享用椰子是一大快事,手刃椰子是更大的快事。当你用刚刚握着鲜花的手拿起长杆绑着的镰刀,把椰子从高高的树上钩下来,沉甸甸拎起,好似拎着一个大元宝,带着丰收的喜悦步入店堂,自己拿大砍刀威武地把椰蒂砍掉,露出椰肉,插进吸管,滋溜一口,特别有成就感和快感,大大超越喝椰子水的愉悦。若是自己借助攀爬工具直接爬上椰树砍下椰子,更是一种特别的过瘾了。全方位的体验,才是椰子最无私奉献于人的赏心乐事。
鹧鸪茶与栳叶,都是在别处不见而在海南很普及的,随便到哪里都有鹧鸪茶伺候,栳叶则是百搭的“配料”,可以炖鸡,可以配着贝壳粉一起嚼鲜槟榔。在民宿门口遇见厨师拿着刚刚从树上摘下的树叶走过时,问之,答曰,栳叶。然后,你去转一圈回来,栳叶炖鸡已经出锅了。在这里,你吃到的都是你看到的,你明了每一样食物的来历。鹧鸪茶下肚打前锋,压轴的儋州松涛鱼头就该出场了,那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鱼头,鲜甜肥美滑口,吃了这口就想着下一口,真的是好吃得停不下来。据说是海南五大名菜之一,又经过了民宿自家师傅的工艺改良,剁椒的酸甜辣度的调配恰好对我胃口,变动一分怕都没有如此完美了。
说起栳叶,我还要描述一下此行最不可描述的海南神物——槟榔。儿子上初中时有一次想体验一次嚼槟榔,我以为跟嚼口香糖差不多,根本没当回事,可是看他如临大敌的样子,我便从他吃进嘴里开始观察他的表情。先是肃穆等待口腔反应,可是迟迟不见反应,我问他怎么样?他不说话,眉毛和嘴角有微微的颤动,好像被麻翻了一般,看不出是痛苦还是震动。我再次问他,到底怎么样嘛?他吐了出来,说,没法形容,嘴巴里面好像爆炸了。我说,像吃跳跳糖?他说,也不是。我颇为不服地说,有那么不可描述吗?我试试。他郑重地说,我劝你别试。这次在海南见到鲜槟榔,我又想起了儿子那次的不可描述,跃跃欲试说,我要尝尝。可是,海南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尝。这愈发激起我的尝试欲,我说,不就是一颗槟榔嘛,有什么大不了!他们说,鲜槟郎对于没吃过的人劲儿太大了,会醉的。有位朋友说他就醉过,我问醉槟榔是什么感觉,他说,不可描述。又一个“不可描述”。我在街边看到挑担卖鲜槟榔的大妈,自己嚼得满嘴血红,看起来甚是惊心动魄。朋友劝我不要买,大妈劝我买,两方博弈,我在禁忌与诱惑之间,想象着那是怎样的不可描述。有年轻女人从店里走出来,拿起一颗鲜槟榔,用栳叶包了塞进嘴里,似乎示范给我看。鲜槟榔地道的吃法,就是加栳叶和贝壳粉一起嚼。我终于被两张流着血红汁水的嘴吓住,按捺着自己的蠢蠢欲动扬言道,我早晚要尝一尝。越禁忌越诱惑,那几天,我的槟榔情结成了朋友们的一个梗儿,一遇槟榔摊儿,他们就说,你的槟榔又来了。然而,直至离开,我终究没有一试。也许有些滋味就是不必亲尝的吧?如同人生。
驱车于海南,行道树都是风景。海口到儋州,一路紫色三角梅;儋州到三亚,一路不知名的小白花。而在去亚龙湾的路上,两边的树抄起手来了,形成一个拱顶,像极了南京中山陵风景区的道路风景,只是树种不同,一个是榕树,一个是法桐。
亚龙湾森林公园下着雨,热带雨林十分应景地有了雨淋的生动。林边亦即海边了,楼上人多风大,然而仍然贪恋高处的风,往上走,往上走,那是日常不能抵达的境界。喜欢那个著名的电影取景地,往下看其实是没什么景观带的,然而,深入天空的平台,给人直通蓝天的清旷高华之感,似乎人生的某种可能。我想起了北京某水镇的云端咖啡馆,也是相同的风致带来相同的爱悦。
在中寥村,看黎族人在水边亭中歌唱,绿水青山,载歌载舞,美哉,生活!自然这是一个表演,但又有什么关系呢?艺术本就来源于生活。水中几只身为道具兼群众演员的大白鹅比人还抢镜,表演完了,一行人赶上鹅回家,鹅乖乖入栏,人该干嘛干嘛。有乡路带领,人在绿中行,与大城市的人流车河的裹挟貌合而神离。有一句话说,旅游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到别人呆腻的地方去。主旨是:反正都是一个呆腻。这话仿佛是说旅游的不值,但其实是毫无道理似是而非的划等号。不同就在于,在这里,你有审美的心情,你有新鲜的愉悦。别人是不是呆腻,与你何干?没有一种他乡,是无人涉足过的,但他乡意味着他者的角色感,审美必要的间离,如此已经足矣。
我们在等待竹竿舞上演的间隙,在村路边的摊档上买几只椰子和百香果,悠闲地坐在藤椅上,看黎族妈妈熟练地把果子开好,你只管吃喝就是了。黄花梨文昌鸡都是名品,在海南的村庄,经常可以看到大群的鸡在黄花梨棕榈树下悠闲地觅食度日,对于千里迢迢来看它们的人完全无视和无感,不由你不感叹:海南的鸡真幸福。
我所住的万泉河边的这家民宿具有无敌江景露台,老船木长桌紧抵城墙一样的青砖露台墙,类似无边泳池。喜欢老船木日晒雨淋的劲道,相比之下,精致人工气息的家具就像温室里的花朵,少了点质感。坐在老船木的长凳上,观山望水,看万泉河上的夕阳,整个露台和身后的木器都镀上了金,身被金光的人,有微醺的温暖感。清新的早上,就着老船木长桌吃一碗鲜肉菜的米粉,一碟小鱼干佐餐,把煮鸡蛋和咖啡杯直接放在船木桌上,不用碟,另有一种接地的素朴。发一条朋友圈:早,万泉河边的露台早餐。“早”后面的微笑,是心满意足不折不扣的。这是诗意栖居可以短暂实现的证明。
日月湾畔,遇到了最符合我对于海边浪漫想象的一家民宿。心里不由得又涌起一个念头:度蜜月就要到这样的地方来。曾经,在鼓浪屿邂逅一家一见就想度蜜月的小旅馆,闺蜜说,将来度蜜月就要来这里。结果,她的蜜月迄今尚未来临。我却在桂林的阳朔西街,又遇上了那家小旅馆及其店猫,仿佛遇见了久违的亲戚。当然,猫已逝,在那里的猫只是一个传说,然而,依旧有前世今生的故事感,一家小旅馆瞬时变得丰满立体起来。
喜爱一家店,或许就是从喜爱店长开始,天时地利人和,这家店一点也不缺。唯一的缺憾,或许就是这里也有蚊子。在海南,我在醉饮美景时,蚊子也在醉饮我。离开海南数日,我在朋友圈里看到海南美丽的海边酒店,还很记仇地留言:我在这里被蚊子狠狠地叮过。当然,我在海南任何地方都会被蚊子叮,招蚊子又爱穿裙子,没办法。是的,没办法,浅薄如我,穿裙子、戴一戴平时戴不着的首饰丝巾帽子,以及拍照,无疑是我出去玩的动力之一。店长拿来草药膏,并且叫我不要动手,蹲下去帮我抹在腿上的样子,实在让我感动到抱愧。在另一家海边酒店,我一人独享一个偌大的鱼疗池,恶狠狠地补偿了蚊子对我的“残害”。
抱着帆板出店过街,就是日月湾最好的白沙碧海。这里不独海水和沙滩优秀,还有深沉的礁石,打破了审美的单调。两块相对矗立的礁石,被称为海门。不是矫情不是穿凿,只有出海数日,视野中只有无边海平面的人,才会体会到那两块礁石的意义,它们给人一个回家的指归点,一个望眼欲穿终有时的盼头。
浪漫的冲动与实景的违和,容易使人犯尴尬病。但在这里,碧海蓝天白浪沙滩,使浪漫毫不勉强,更无矫情之嫌。如果浪漫可以上演,就该是这里吧?同行的姐姐是个实在人,一屁股坐进了海里,好像到人家做客,盘腿上炕,一屁股坐到了热炕头上。都和衣坐进了海里,接下来也就豁然放开了。浪起来,与海浪无关。
水流沙退,人在漂移,晕眩,恍惚。感觉海水在无限地退下去,人就倒了,过程却不自知,面对的只是倒下的事实。这就是晕水吗?恍惚间还留心到,水退时,蟹的小窝在汩汩冒泡。
就这样,在海南,细细体验着,让美好的精华渗透进每一寸肌肤,内外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