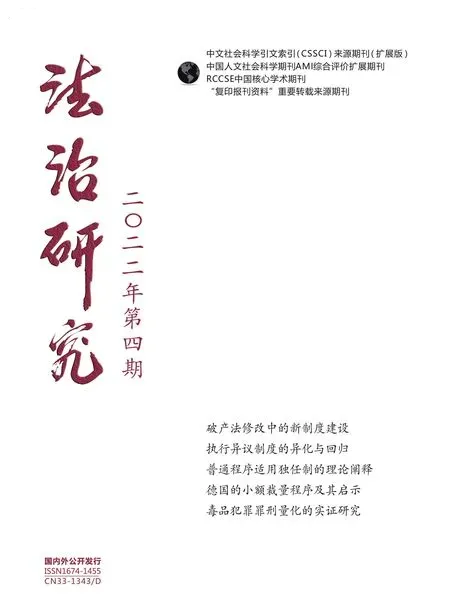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的理论阐释*
2022-08-02杨秀清
杨秀清 谢 凡
“案多人少”话题由来已久。2019 年12 月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授权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20 个城市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和部分专门人民法院开展试点。在两年改革试点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司法解决纠纷的效率、加强民事审判工作实效,回应社会对法院公正、高效审判的现实需求,今年1 月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下称《民诉法修正》)围绕独任制的扩大适用、完善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等方面进行了修改。“无论是以满足便民司法的社会需求为目标,还是以法院案多人少、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为动因,通过司法改革或民事诉讼法修改实现诉讼促进和司法资源优化配置,都是毋须讳言的命题。然而,司法的产品是正义,而不是案件本身。当进入司法的社会纠纷达到法院能够承受的阈值时,如果继续加量运行,司法的正义就会受到威胁,司法消弭社会冲突的功能就会事与愿违。”①傅郁林:《“司法提速”需要科学化和系统化》,载《上海法治报》2021 年11 月27 日。自《民诉法修正》公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后,社会各界对以最高人民法院的繁简分流改革为基础,为了提高诉讼效率、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矛盾为目标,以简化程序为主要内容的修改思路产生较大分歧。其中,独任制的扩大适用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诉讼促进成为半个世纪以来各国司法改革主旋律的世界背景之下,回应我国语境下“案多人少”的现实需要修改民事诉讼法,如何在符合民事诉讼基本规律和原理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与科学简化诉讼程序以便提高诉讼效率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中国语境下的“案多人少”
“案多人少”形成的“人案比”压力和积案问题并非中国的独有问题,而是全球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各国司法面临的规律性共有问题。由于诉讼制度是在一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程序法律制度,因此,只有深入剖析中国语境下“案多人少”的形成原因,才能在符合民事诉讼基本规律和原理的前提下,以保障司法公正和当事人基本程序权利为基础,探寻通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与简化程序实现提高诉讼效率目标的中国应然路径。
(一)“案多”的法院外部环境因素
1.“案多”的社会因素
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民商事纠纷呈现出“案多”的表象与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伴生问题密不可分。首先,经济总量高速增长必然引起民商事纠纷数量与类型的增多。改革开放40 年,中国总体经济高速增长。“1978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 亿元,之后连续跨越,1986 年上升到1 万亿元,1991 年上升到2 万亿元,1995 年上升到5 万亿元,2000 年突破10 万亿元大关,2006 年超过20 万亿元,2008 年突破30 万亿元,2012 年突破50 万亿元,2017 年首次站上80 万亿元的历史新台阶,达到827122 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 年3679 亿元增长到827122 亿元,总体翻了225 倍。”②《数说改革开放40 年变化,生产总值增长225 倍》,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640223381&ver=3513&signature=0LPyRcCNs0bj8FyWuCrKmLoDe42PbwCm1So*BtRG4n41AYIRJJdXrlBgNJSu-uW2nt4Ep*0GCwuW8W-t1hx7MfaaogJ2LdQWstRkpPP3*RltI0q7Nca FGVUtmOvKEOLU&new=1,2021 年12 月23 日访问。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伴生民事纠纷数量的剧增。笔者通过Alpha 智能检索系统,以最为常见且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联的“合同纠纷”为关键词、以“基层人民法院”为法院层级、以“一审案件”为审级,截至2022 年2 月8 日检索日,2001 年至2020 年的案件数量如下图所示。因2001 年至2010 年之间每年案件数量均为25 万件以下,而2011 年至2020 年之间每年最大案件量接近800 万件,因此,分别采用5 万件和100 万件作为比例尺用图示1 与图示2 表示。

图示1

图示2
从图示1 和图示2 可知,2001 年至2020 年以五年为一个时间周期,增长倍数分别为2005 年是2001年的21.15 倍、2010 年是2005 年的18.92 倍、2015 年是2010 年的14.18 倍、2020 年是2015 年的2.58 倍,20 年共增长了14631.84 倍,其中从2012 年至2019 年每年增长量都超过100 万件。其次,社会突发事件引起行业性纠纷案件数量的增长。例如近两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旅游、餐饮与美容保健等服务业的停业,导致实际经营者经营困难引发的消费、房屋租赁等纠纷增多。又如经济发展中的新兴P2P 模式的运作核心在于资金池的管理,大多数P2P 公司并不具备应有的管理能力,资金流动性出现问题最终崩盘,而大规模有效风险控制机制的缺乏导致集中暴雷事件引发投资者纠纷急剧增加。
2.“案多”的政策变化因素
“案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离不开一国法院所处的外部环境对其职能以及解决纠纷类型和数量的影响,其中政策因素不容忽视。首先,国家政策变化引发某种类型案件数量的短期剧增。例如当下引起国人广为关注的国家对国民义务教育培训的整顿问题。近些年来,素质教育的开展和教育投资的火爆催生了各类教育培训机构。随着国民义务教育的市场化发展,教育机构的数量及培训规模日益剧增,严重冲击了国家的教育布局和人才储备布局。一旦资本将义务教育这一资源垄断割据,必然加速阶层固化,导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关闭寒门学子的升学之道。为此,国家强力出台了对市场化国民义务教育机构的整顿政策。在新冠疫情和国家政策变化的双重作用下,由于行业性问题的政策配套纠纷解决方式的缺失导致特定类型纠纷短期剧增。通过Alpha 法律智能检索系统,以“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为关键词,以“基层人民法院”为法院层级,截至2022 年2 月8 日检索日,全国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为2018 年7855件、2019 年14057 件、2020 年25355 件、2021 年30651 件,每年增长一万件左右。其次,司法政策变化引发类型化纠纷激增或降低。例如2015 年9 月1 日《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利息的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引起小贷公司及民间借贷纠纷大幅增加。通过Alpha 法律智能检索系统,以“民间借贷纠纷”为关键词、以“民事”为案件类型、以“基层人民法院”为法院层级、以“一审”为审级,截至2022 年2 月8 日检索日,全国基层人民法院从2014 年到2020 年审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014 年3606432 件,2015 年4891396 件,2016 年6184371 件,2017 年9204095件,2018 年10518242 件,2019 年12080789 件,2020 年11752754 件。从2014 年 的3606432 件 到2017 年的9204095 件,增长1.55%;再到2019 年顶峰的12080789 件,比借贷利息调整前的2014 年增长2.35%;2020 年8 月最高人民法院调整民间借贷利息后,2020 年为11752754 件,相较于2019 年的顶峰案件量下降了2.72%。由此可以看出,司法政策调整对类型化纠纷数量变化影响较大。
(二)“人少”的法院内在因素
1.“人少”的相对因素:法院附加职能的增加
近些年来,法院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作用日益强化,通过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机制,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局,法院承担的附加社会治理职能范围逐渐拓宽,参与和谐社区与家庭构建、基层普法宣传、接待涉诉信访、诉调对接、政府征地拆迁、招商引资、扶贫等各种社会活动。如佛山市高明区有77 个行政村,农村总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征地、土地承包等纠纷日益增多,涉农案件类型也越来越复杂。高明区人民法院深入开展诉源治理,探索和创新“枫桥经验”,充分发挥类案法律适用统一导向作用,有效降低类型化案件发案率,为高明的乡村振兴、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③《高明法院:积极发挥司法职能,服务基层社会治理》,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638683457&ver=3477&signatur e=4h1mOVGw-Fc48lB2TRJqGBmkMEHKqLiE321plbg28DVMKq-Vf0I9Kr8v7pIosZwn7RSPQ-pIMa2u2QBy9sD8qpNqVJxbr4OoPFJJI3nZvczTQ*9m 6ybgeekUm4frQwHg&new=1,2021 年12 月5 日访问。山西阳泉市孟县人民法院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加强与各政府单位、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将法院的调解工作与政法委、司法局的网格化相融合,初步实现了民间矛盾纠纷初始阶段有序疏导和及时化解,大力提升司法服务水平,打通基层社会治理神经末梢,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④《孟县法院全方面提升司法服务水平,构建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638683457&ver=3477&signature=Imj9JtunmujK*6VzNlIMIR3Y1J9jZjwe9gp4K0fa8YGBSx7mZBFJESa6H3wPq7BV0h1rXb9UgxjK32SNrQ1f*TbMxEq-csj2nhLTvEvi0Z 8TtDRbBYYX1JcQ*mZplXG0&new=1,2021 年12 月5 日访问。在此背景下,法院承担的附加社会治理和司法公共社会服务职能的增加削弱了法院基本审判职能的发挥,消耗着法院本身极为有限的司法资源,一定程度上导致法院审判人员数量的相对减少。
2.“人少”的绝对因素:员额制法官的减少与动力不足
受制于法院队伍建设的各种历史原因,截止法官员额制改革之前,全国法院存在不少名不副实的法官。有的身处行政管理岗位长期不办案,有的因专业能力不足不能独立办案。员额制司法改革的目标是推动法官的职业化、专业化和精英化,但由此也伴生了民商事案件数量持续大幅上升与法官员额制的紧张关系。据统计,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 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总数为60 余万件,同期法院法官(包括民商事法官的全部法官)人数约为6 万余人,人均10 件。员额制改革前全国法院法官大约21 万人,相比1978 年增长约3.5 倍;而2016 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19994651 件⑤《中国法律年鉴》(2016 年),中国法律年鉴社出版2017 年版,第1159 页。,人均约95.21 件,相比1978 年增长约9.52 倍。2017 年法官员额制改革全面完成,全国法院共遴选产生12 万余名员额法官,相比较员额制前法官人数减少42.9%;而全国法院2017 年受理各类案件22601567 件⑥《中国法律年鉴》(2017 年),中国法律年鉴社出版2018 年版,第1176 页。,人均188.35 件,相比1978 年增长约18.8 倍。以某省T 区法院为例,对照员额制改革前后的法官人均办案数量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6 年、2017 年两年的结案数量和结案率变化不大,但2017 年法官员额制在该法院的运行导致办案法官人数大幅减少,带来的结果是人均结案量的陡然增加,人均结案量从144.90 件上升至296.56 件,增加了一倍。⑦林思圻:《法官员额制改革的隐忧与思考》,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644281910&ver=3607&signature=-v-L5Xjn HVUfrE7jms5s6AiLmeNrT4oXLPbt5xMzS6hOvcWN7ntyOm1v-D13qrMCIKYxrm9v70Lek8Km0o1-hVi5tFRbJWeSln59VdSIh3S2rtDrj5IB9UbUZLonty D7&new=1,2022 年2 月8 日访问。此外,我国通过法官员额制改革确立法官职业化、专业化与精英化目标的同时并未建立与其相配套的一项重要制度,即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反之却实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由于预期待遇难以提高、终身追责加大了职业风险、审判自主权难以落实、案件负担大大加重等原因,法官入额积极性并不高。某市法院2016 年组织第二批法官遴选时,全市符合报名条件的人数为1722 名,结果只有827 人报名,仅占总人数的48%。⑧《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前世、今生和未来……》,https://mp.weixin.qq.com/s?src=3×tamp=1644281910&ver=1&signature=pp0o5LRsax h6d6RMNi9NUZot7lWrwKxzu*6ry6rVCw8BSvpFzaQhyHUllffiIl7m0PWdC835kgGpQgRJhgSBQWjct1X4q2H4G5l*MvTFvNlCmBK38kuaB2jAihdn*OS h*OssHu6SzgcBXsYJymJgSDGqdhdphoufHluF,2022 年2 月8 日访问。可见,在案件数量增幅远大于法官人数增幅的情况下,法官员额制改革以及配套制度的缺乏使得法官人数减少且入额动力不足,由此引起人案比压力加剧在所难免。
二、基层人民法院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的司法困境
为了解决司法资源有限与当事人诉诸法院解决纠纷需求不断增加之间的紧张关系,此次《民诉法修正》采取了将审判组织与审判程序“松绑”的思路,第40 条第2 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该规定一改我国长期实行的独任制适用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实行合议制的做法,将独任制扩大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的普通程序。然而,此种以回应司法实践需要为导向的民诉法修正思路是否符合民事诉讼基本原理并能否解决“案多人少”的现实问题,值得反思。
(一)适用的前提条件:背离民事诉讼基本原理
根据《民诉法修正》第40 条第2 款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适用独任制的前提条件是案件“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这就意味着,一个民事案件被法院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的逻辑进路是:第一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36 条的规定,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第二步,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再根据“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前提条件适用独任制。换言之,根据案件是否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区分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成为这一逻辑进路的起点。虽然《民诉法解释》第256 条对简单民事案件的标准作出解释,且在第257 条采用列举方式明确规定了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但现有法律规范关于简单案件标准的规定仍采取抽象概括式的表达方式,缺乏明确的识别标准。司法实践中,基层人民法院立案庭往往依据案由、案件类型、争议标的额以及起诉状载明的内容等对案件繁简分流进行初次判断,难以准确预测案件的繁简程度,导致适用简易程序的简案不简在所难免。即使经过初次判断确定适用普通程序的非简单民事案件,是否符合“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这一适用独任制审理的标准也离不开对案件基本事实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根据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辩论主义,其基本含义之一是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者消灭的必要事实(这被称为主要事实),只有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才能作为判决的基础(换言之,法院不能将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作为判决的基础)。也就是说,即便是法院通过证据能够认定的事实,但如果该事实未经当事人主张,那么法院就不能基于该事实来作出判决。由此衍生出了主张责任的概念,即在辩论主义下,只要是未被当事人主张的主要事实就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基础,反过来说,为了使主要事实能够作为判决的基础,当事人就必须对其进行主张。⑨参见[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329-331 页。我国《民诉法修正》第12 条规定的辩论原则是否反映了大陆法系辩论主义的核心,即当事人辩论对法院裁判权的制约,学界尚存不同观点。然而,庭审中心主义是现代各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潮流和共同目标,这就要求作为法院裁判基础的事实必须由当事人提出,法官对案件争议事实的心证形成必须受制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辩论。由此,根据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法院对一个民事案件欲作出事实认定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判断,应当遵循基本程序要求,否则可能构成突袭裁判。
审判组织分为合议制与独任制两种形式,一个民事案件应采取何种审判组织形式,理应由法院在受理案件后根据案件适用的程序以及具体情况予以确定,而案件事实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则应由审判组织对案件经过审理后才能予以认定和判断。因此,《民诉法修正》第40 条第2 款将“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作为基层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的前提条件,该标准不仅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且未经审理即作出对案件基本事实和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相悖。
(二)适用的现实需要:审限的变相突破
此次《民诉法修正》的重点内容之一为将独任制扩大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的普通程序。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说明》中谈到:“对于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解除独任制与简易程序的严格绑定,推动独任制形式与审理程序灵活精准匹配,适应基层人民法院案件类型多元的工作实际。实践中,部分案件的核心和关键事实清楚,仅部分事实细节或者关联事实需进一步查实,查明需要经过当事人补充举证质证、评估、鉴定、审计、调查取证等程序环节,耗时较长,这类案件总体上仍为简单案件,并无组成合议庭审理的必要,适宜由独任法官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从中可以看出,独任法官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现实需要,是因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所需当事人补充举证质证、评估、鉴定等程序环节耗时较长,简易程序的审限无法满足审理需要。笔者通过与部分基层人民法院法官的交流得知,在“案多人少”的背景下,员额法官有时面临一种难以克服的尴尬困境,即因为承办案件数量过多导致能够确定排期开庭时已经超过简易程序的法定审限。在此情形下,法官倾向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而非简易程序,因为普通程序的审限更长,而其他审理程序并无区别。因此,真正制约我国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并非案件事实本身是否简单,而是审限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迟延裁判治理成为不同法域国家所面临的共有问题。由于建国后我们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以法院为中心发现案件客观真实的诉讼观念。根植于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占主导地位的司法现状,我国1991 年《民事诉讼法》确立了审限制度,为我们熟知的域外民事诉讼法几乎没有类似审限制度的相关规定。审限制度的确立和贯彻体现出我国立法者和人民法院解决民事诉讼裁判迟延问题的态度和决心,并且其对遏制迟延裁判发挥了积极效果。⑩参见任重:《民事迟延裁判治理转型》,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 年第4 期。作为提高诉讼效率的一项举措,我国司法实践中借助审限制度形成了一套包括结案率、简易程序适用率、简易程序案件平均审理期限、简易程序转换率等在内的审判管理与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此次《民诉法修正》所确立的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制度事实上变相突破了简易程序的审限制度,使得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在适用灵活便捷的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同时适用普通程序相对更长的审限,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审限制度给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带来的办案压力。然而,回归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范畴,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视角审视我国民事诉讼的审限制度,不难发现审限制度将作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重要内容之一的审判法律关系中的一方主体当事人排除在外。一方面审限制度主要是一种法院内部的管理和考核制度;另一方面,《民事诉讼法》并未对受法院违反审限制度迟延裁判影响的当事人设置相应的救济机制。因此,背离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从审判管理与考核评价机制角度治理迟延裁判问题的立法思路难免有失偏颇。
三、大陆法系国家独任制适用的规律
(一)大陆法系国家独任制的适用
1877 年德国《民事诉讼法》诞生以来,曾几次以“促进诉讼”“简化诉讼”为目标进行改革。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组织形式为独任制与合议制。最早的独任法官制度在以集中辩论促进诉讼为目的的1924 年的修订中得到确立,但被限定为权力有限的“准备型独任法官”,其权力仅限于将案件尽可能地充分准备以便由合议庭进行最后的审理。当时的单独法官制度旨在减轻合议体(或部)的负担,并尽可能准备辩论确保合议体面前的口头辩论能够尽可能一次完结。⑪参见段文波、高中浩:《德国独任法官制度改革与启示》,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6 年第1 期。1974 年《减轻州法院负担和简化法庭记录法》规定州法院在一审程序中可以引入独立审判的独任法官,突破了传统的民事案件合议制原则。1993 年《司法减负法》扩大了独任法官审理的范围。此后,一方面法官专业水平和道德修养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随着民事诉讼案件数量逐年增长,司法资源不足带来的审判压力使得更多案件由独任法官审理成为必要。2001 年的《民事诉讼改革法》进一步改革了独任法官制度,将合议庭与独任法官的功能进行划分,并将独任法官分为“固有型独任法官”和“强制型独任法官”⑫《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4 条规定了固有型独任法官,第384 条之一规定了强制性独任法官。,改革后原则上诉讼由独任法官审理,在法定的特殊情况下方由合议庭进行裁判。⑬该部分对德国独任法官制度的确立和演变的描述,参见丁启明译:《德国民事诉讼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4 页。由此可见,德国独任制扩大适用的改革主要是针对位于四级法院体系中第二层级的州法院,而非最基层的初级法院。
德国法院体系中的普通法院自上而下由联邦最高法院、州高等法院、州法院和初级法院等四级法院构成,其中联邦最高法院和州高等法院为上诉审法院,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州法院或者初级法院审理,其界限由德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事物管辖确定。德国州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取决于争议额的管辖。根据德国《法院组织法》第71 条第1 款规定,所有没有分配给初级法院的纠纷都由州法院管辖。根据2001年《民事诉讼改革法》修订后的新规定,自2002 年1 月1 日开始,所有超过5000 欧元的金钱或者金钱价值请求权纠纷一律由州法院管辖。另一类是不取决于争议额的管辖。即一些案件不论争议额大小,在事物上均由州法院专属管辖。主要是由于官员或法官违反职务而产生的对国家或者其他公法团体的请求权,从《反不正当竞争法》《股份法》《专利法》《建筑法》等大量联邦法律中产生的请求权等。⑭[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年版,第197-198 页。尽管德国2001年《民事诉讼改革法》第348 条规定了“固有型独任法官”,但也明确列举了不能适用独任制,应由合议庭管辖的情形,包括因银行和金融业务、治疗处理、商事案件、保险合同、版权和出版权、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产生的纠纷等。可见,德国改革扩大后的独任制审判组织主要审理的是传统民事案件,凡是涉及到商事以及金融、保险、现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案件仍然采取合议制。此外,独任法官审理的案件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有特殊困难、案件具有原则性意义、双方当事人一致申请时,也应提交合议庭审理,是否接管由合议庭决定。
日本裁判所自上而下由最高裁判所、高等裁判所、地方裁判所、家庭裁判所⑮日本家庭裁判所是与地方裁判所同级的专门审判家事案件、未成年案件和人事(婚姻)案件的裁判所。和简易裁判所等四级所组成。最高裁判所和高等裁判所为上诉审裁判所,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地方裁判所和简易裁判所审理,地方裁判所同时也可以作为简易裁判所审理案件的控诉审裁判所。在日本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中,事物管辖主要解决的是第一审裁判权如何在简易裁判所与地方裁判所予以分配的问题。日本《裁判所法》第33 条第1 项第1 号规定诉讼标的物的价额即诉额在140 万日元以下的请求由简易裁判所管辖;《裁判所法》第24条第1 号规定上述请求以外的请求由地方裁判所管辖。⑯[日]伊藤真:《民事诉讼法》(第四版补订版),曹云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47 页。依据组成裁判所的裁判官数量的不同,可以将裁判所分为合议制与独任制。地方裁判所根据日本行政区划设置于各都道府县厅所在地。根据日本《裁判官法》第26 条第2 项的规定,在地方裁判所中,原则上采独任制。采用合议体审判的事件是由其他法律加以规定的。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场合,以及需要以合议制对裁判的内容进行决定的场合,则由3 名或者5 名裁判官组成合议制裁判所。⑰参见[日]伊藤真:《民事诉讼法》(第四版补订版),曹云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25-26 页。简易裁判所作为最基层的裁判所,其数量全国最多。简易裁判所通常由法官单独进行审判,而且为了使它既简易又迅速地处理诉额小的轻微案件,根据诉额决定其事物管辖。⑱[日]兼之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 年版,第19 页。
(二)大陆法系国家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的基本原理
1.德日两国第一审程序的繁简分流设计以法院层级为基础
通过上述对德日两国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的立法检视可知,在同为法院四级设置的德国与日本,均通过事物管辖制度解决民事审级制度中第一审民事案件裁判权在法院体系中作为初审法院的下面两级法院之间的分配问题。换言之,德日两国法院体系中四级法院有明确的职能定位,下面两级法院的职能均侧重于审判第一审民事案件,只是第二层级法院兼审最基层法院的上诉案件。德国初级法院与日本简易裁判所作为最基层法院均通过法定争议金额确定其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范围,⑲德国初级法院管辖不超过5000 欧元的金钱或者金钱价值请求权纠纷,相当于人民币3.5 万元左右;日本简易裁判所管辖诉讼标的物的价额即诉额在140 万日元以下的请求,相当于人民币7.7 万元左右。且明显低于我国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标的金额。⑳2021 年10 月1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规定:当事人住所地均在或者均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 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 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我国目前未将争议标的金额作为基层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的标准,因此,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简单民事案件均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此外,就第一审程序的具体内容而言,德国与日本民事诉讼法均对作为最基层法院的一审程序作出了特别规定,体现了两国民事诉讼法对不同层级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不同价值追求。最基层法院管辖争议案件的标的额较小,涉及当事人的民事权益较小,更侧重于为当事人提供一种简便、快速地接近司法正义的程序。而作为高一层级的德国州法院和日本地方裁判所则管辖超出法定标的金额的案件,更侧重于通过规则与环节完整规范的程序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由此可见,德日两国的最基层法院仅管辖争议标的额小的案件,其第一审民事案件事实上主要由德国州法院和日本地方裁判所管辖,特别是德国对于大量涉及联邦法律的案件不论争议标的额大小均由州法院管辖。除了小额诉讼以外,其第一审程序的繁简分流设计是以法院的层级为基础在法院体系中下面两级法院之间进行。因此,德国初级法院和日本简易裁判所适用的第一审程序可以称为简易程序,其第一审普通程序均适用于德国州法院和日本地方裁判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不存在同一层级法院内部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划分问题,体现了不同层级法院审判权以及当事人诉讼权利行使的程序保障不同。换言之,德日两国以第二层级法院第一审普通程序为基础,考虑到初级法院和简易裁判所作为最基层法院审理案件所涉争议标的额较小的特点,立法对其程序作出简化的特别规定,这样使当事人在不同程序中的权利和审判者在不同层级法院的权力相对清晰。
2.德日两国普通程序独任制适用与法院层级无关
基于以法院层级为基础的第一审程序的繁简分流设计,德日两国通常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法院并非法院体系中的最基层法院,而是第二层级的法院,且德国州法院还管辖基于大量联邦法律产生的请求权纠纷案件,不论其诉讼标的额如何,这就导致德国州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范围广于日本的地方法院。在德日四级三审终审的审级制度结构中,不仅四级法院的审级职能定位清晰,即下面两级法院为第一审法院,上面两级法院为专门的上诉审法院;而且各审级法院的职能定位也相对明确,即第一审法院的职能系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上诉审中第二审法院的职能侧重于通过纠正第一审裁判错误实现个案正义和当事人私权救济,第三审法院以法律审为其基本职能。在这种“金字塔式”审级制度中,德日两国第二层级的法院虽然兼具审理当事人不服最基层法院一审裁判提起上诉的案件,但其主要职能是根据事物管辖制度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除法律另有特别规定以外,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以独任制为原则。因此,从德日两国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的情况来看,其蕴含着作为国家公共司法资源的审判组织形式与个案民事纠纷解决所体现的职能相匹配的理念,与法院的层级无关。特别是德国,为了促进诉讼将扩大州法院独任制适用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即使如此,2001 年《民事诉讼改革法》仍然将可能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法律适用较为复杂的涉及商事、银行、金融、保险、现代信息技术等纠纷案件排除在独任制适用范围之外,以通过合议制集体民主决策保障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正确性。因为这些类型民事纠纷的解决不仅涉及到个案当事人私权利益的维护,可能还涉及国家发展所需的经济秩序以及法律的统一适用问题。
四、我国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之完善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在我国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以及确定上下级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与权限制度均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时,域外样本之经验借鉴不能脱离本国实际。我国自建国之初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形成了四级法院设置的法院体系,以此为基础1982 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开始即在法院体系中形成四级法院均可依法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中级以上的法院依法受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的四级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虽然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受理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涉外和国内民事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其管辖的特殊案件,但司法实践中主要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确定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争议标的额,且呈现出争议标的额不断提升的趋势。以《授权决定》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并于2021 年10 月1 日起开始施行的《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第1 条明确规定“健全工作衔接机制、完善内设机构设置、优化审判力量配置,在实现审判重心进一步下沉的同时,推动将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法院审理,逐步实现基层人民法院重在准确查明事实、实质化解纠纷;中级人民法院重在二审有效终审、精准定分止争;高级人民法院重在再审依法纠错、统一裁判尺度;最高人民法院监督指导全国审判工作、确保法律正确统一适用”。同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明确规定:当事人住所地均在或者均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 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 亿元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至此,我国形成了不同于德日两国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主要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制度设计,且自《民事诉讼法(试行)》开始,我国就形成了基层人民法院内部以是否为简单民事案件为标准而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的程序设计,且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除简单案件外,也必须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21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修订版,第284 页。该程序制度设置的目的在于根据民事案件的不同情况为当事人提供繁简不同的程序,实现第一审案件审理程序繁简分流的制度设计目的。普通程序通过更为完整规范的程序设计为当事人提供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程序保障,而简易程序则侧重于使当事人能够快捷灵活地接近司法正义。正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将基层人民法院的一审程序区分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且基于目前第一审民事案件主要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司法现状,才产生了此次《民诉法修正》将独任制扩大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普通程序的需要。但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疑问:第一,既然基层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繁简程度决定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还是简易程序,这就意味着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为非简单案件,对此类案件适用独任制能否保障争议案件事实的查明。第二,除法律规定的特殊类型案件,划分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范围的标准系争议标的金额,此次《民诉法修正》并非将独任制扩大适用于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而仅仅限定于基层人民法院,其正当性难免令人生疑。由此可见,虽然此次《民诉法修正》确立了审判组织形式与基层人民法院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松绑的基本思路,但具体规则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确立第一审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审理的原则
关于审判组织形式与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法院层级以及所适用审判程序之间的关系,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并未作出严格限制,仅在第35 条第2 款规定,“简单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虽然该试行法第124 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但基于当时“涉外案件”均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级别管辖规定,《民事诉讼法(试行)》并未严格排除中级人民法院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的可能。1991 年《民事诉讼法》第40 条第2 款将《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5 条第2 款修改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且将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涉外案件的范围修改为“重大涉外案件”。至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了审判组织形式与第一审审判程序之间的捆绑关系,即简易程序适用独任制,而普通程序适用合议制。之所以如此,与我国上世纪90 年代初制定《民事诉讼法》时,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的数量较少、多数法官未经过专门法学教育培养和国家未实行统一法官职业资格考试的现状相关。
此次《民诉法修正》基于审判组织形式与第一审审判程序松绑的基本思路,确立了基层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的制度。虽然这种修正思路作为应对近几年司法改革背景下第一审民事案件进一步下沉至基层人民法院的立法策略,对于缓解基层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审判压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在我国主要以争议标的金额作为划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之间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范围的级别管辖制度框架下,将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仅限定于基层人民法院的立法思路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有待商榷。
民事审级制度是一国为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司法救济以及法律统一适用而设置的基本诉讼制度,审判组织形式与审判程序的设置应以民事审级制度中不同审级法院的职能定位为基础。在民事审级制度中,一审法院的职能定位系解决民事纠纷,只是基于民事纠纷的性质以及个案所涉当事人利益的差异由不同层级的法院采取形式各异的审判组织,并适用不同的程序进行审判。不同审判组织形式与审判程序蕴含着不同的诉讼价值。就审判组织形式而言,合议制的制度价值在于通过合议庭的集体民主决策保障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正确性,独任制则具有灵活、高效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优势。而一审审判程序之所以划分为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其价值在于保障当事人在不同程序中的诉讼权利和审判者在不同层级中审判权的正当行使。其中普通程序的制度价值在于为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获得司法救济提供完整规范的程序保障,而简易程序则具有灵活、便捷、高效解决民事纠纷的特点。因此,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所采取的审判组织形式不应当因法院层级差异而有所不同。换言之,回归民事审级制度中一审法院以解决民事纠纷为其职能定位这一基本诉讼原理,应当确立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以独任制审理为原则,以合议制审理为例外的基本制度,而不是《民诉法修正》所确立的基层人民法院有条件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的制度。此外,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虽然民事案件数量的爆发式逐年增长与员额制改革所带来的法官人数减少之间所形成的“人案比”压力剧增,但我国法学教育的快速发展与近20 年来实行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极大提升了法官的专业化素养,为保障法院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奠定了专业人才基础。
(二)明确第一审普通程序合议制审理的例外情形
明确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的原则之后,必然涉及哪些例外情形应适用合议制审理的问题。此次《民诉法修正》第40 条第2 款将基本事实是否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明确作为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亦或合议制审理的判断标准,与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心证来源于法庭直接审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理相悖。重新审视第一审普通程序合议制审理的功能,明确其适用的情形,应以实现合议制这一审判组织形式在以集体民主决策机制保障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正确性的价值为基础。
民事诉讼是国家对社会公众提供的一种带有公共福利性质的司法服务。在现代社会,无论审判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人们都不能无视实现正义的成本问题。为实现司法服务所承担的通过解决纠纷实现正义的职能,国家需要支出公共成本,配备相应的司法资源,而且这种司法资源不可能随着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救济需求的增多而无限制无条件的增加。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民商事关系的复杂化,现代民事审判制度除了给诉讼的当事人带来直接的诉讼利益外,还承担着越来越复杂的多重社会功能,如对同类纠纷的当事人以及潜在的当事人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司法过程的能动性而导致法的形成与发展、实现社会正义与维护法律秩序等。22参见杨秀清:《司法过程能动性的理性思考》,载《河北法学》2010 年第1 期。合议制是以3 名以上的单数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集体审理与评议的制度,相较于独任制审判组织形式,合议制审判组织所占用的司法资源更多。因此,在确定普通程序合议制审理案件的具体范围时,不应以案件事实本身是否复杂为标准,而应当侧重于考量司法解决个案民事纠纷是否同时承担促进法的形成与发展、维护法律秩序等公共职能因素。因为保障案件事实的查明是审判程序的具体设置应考量的问题,即审判程序的具体规则与环节的设置应当与案件事实的繁简程度相适应。事实复杂的案件配之以具体规则与环节完整细致的普通程序;反之,则应以灵活简便的简易程序保障民事纠纷的快速解决。德日两国普通程序合议制审理的例外规定给我们以同样的启示。德国《民事诉讼改革法》第348 条明确规定,因银行和金融业务、商事案件、保险合同、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产生的纠纷等由合议制审理,即蕴含着司法在解决此类纠纷时发挥维护法律秩序等公共职能的重要作用。同理,日本地方裁判所采用合议体审判的事件由其他法律加以规定的立法思路,也反映了普通程序合议制审判的侧重点不在于解决个案民事纠纷,而是保障相关立法特殊价值的实现。
综上,基于司法解决民事纠纷是否承担社会公共职能这一标准,适用普通程序合议制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兼具统一法律适用、促进法的形成与发展、维护法律秩序等社会公共职能。可以包括以下几类案件:第一,涉及法律规范解释分歧的案件。制定法的基本要素是抽象法律概念所形成的法律规范,其在适用于个案审判的过程中可能会涉及法律规范的解释问题。对于可能涉及法律规范解释分歧的案件的裁判,不仅涉及当事人个案民事纠纷的解决,还涉及法律解释规则的统一问题,应当由合议庭审理,以保障法律适用的正确。第二,涉及可能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要旨不一致的新型法律问题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对法律统一适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社会与科技的迅猛发展,社会问题的日趋复杂,都对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新的要求。制定法与生俱来的稳定性难免呈现滞后性的特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只能由个案审判来完成。23参见杨秀清、谢凡:《再审制度与审级制度衔接研究》,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286 页。一旦案件所涉及的新型法律问题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旨不一致,该案的裁判就不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个案纠纷的解决问题,应由合议庭集体审理,以保障法律适用的正确。第三,涉及续造法律规则的新型法律问题的案件。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时代的产物。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言:“一种法律在初成立时,都有其环境上的需要,并且,使其合理的,亦是这种环境。但事实上,往往产生这法律的环境已发生变化,而这法律却仍然有效。”24[英]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7 年版,第351 页。因此,如果一个民事纠纷可能涉及法律漏洞需要填补时,应发挥合议庭集体民主决策的智慧,以促进法的形成与发展。第四,涉及类案裁判规则的案件。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事纠纷涉及的商事关系呈现出类型化或者一方主体呈现出群体化的趋势,此类案件的裁判不仅涉及个案当事人之间纠纷的解决,还涉及类案裁判规则的统一问题。为了在实现个案公正裁判的同时维护法律秩序,应由合议庭集体审判。
《民诉法修正》的实施意味着法院繁简分流试点作为一项司法改革制度落下帷幕,独任制扩大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普通程序的确立宣示着审判组织形式与审判程序的松绑。然而,此次《民诉法修正》所规定的基层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的前提条件是否具有正当性,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命题,即如何在民事诉讼基本原理框架内,使得价值功能存在差异的审判组织形式与审判程序制度合理衔接,有待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