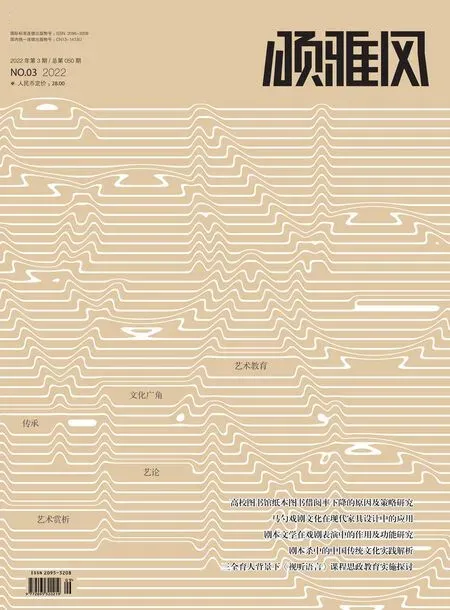中国视域下的西方音乐史研究
2022-07-21郑棋文
◎郑棋文
对于高校来讲西方音乐史研究对专业人才培育意义深远,可有效强化音乐专业人才文化修养,为音乐行业发展提供优质人才保障;在中国视域下研究西方音乐史可以为东西方音乐文化交融碰撞提供条件,营造音乐文化融通发展的良好氛围,为中国音乐史健康发展给予启发,使音乐史得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基于此,为使中国音乐史得以良性发展探析西方音乐史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不同阶段
(一)研究初期(1949—1966)
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利于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发展的政策方针先后施行,为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摸索着发展给予支持,同时致力于消除国家建设阻力,这注定1949—1966年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是曲折的。1949—1956年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目标,与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维系良好的外交关系,优化国际环境,这为国内文艺空气净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奠定了研究西方音乐史的政治基础。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音乐史研究阻力较大,虽然在1962年总结了经验教训,但依然陷入了阶级斗争绝对化与扩大化的“困局”,文艺界展开“整风运动”,西方音乐史学习与研究步调放缓。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领域政策奠定了西方音乐学术研究基调,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予以分析:一是成立音乐团体及专业音乐院校,如1949年筹建中央音乐学院、1951年成立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1956年成立中央乐团等,这为西方音乐史本土化研究奠定基础;二是音乐杂志出版,为研究西方音乐史搭建平台,如1950年创刊的《人民音乐》等,虽然受环境所限,西方音乐相关内容较少,但为音乐文化交融碰撞给予支持;三是派遣学生出国深造,到东欧、苏联学习音乐表演专业技艺,吴祖强、李德伦等留学生成绩优异,成为立足中国视域研究西方音乐的重要人物。1957年,包括“德彪西风波”在内的事件阻滞西方音乐史在中国研究与发展。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音乐史研究速度较慢,但对肖邦、李斯特、巴赫、贝多芬等重要作曲家的研究始终未曾停止,如《民间音乐在巴托克创作中的运用》(许勇三)、《莫扎特的歌剧》(钱仁康)等,部分文献资料见解独到、弥足珍贵,同时《俄罗斯音乐史》《西洋音乐史》《音乐发展史论纲》等西方音乐史译著为早期基于中国视域研究西方音乐文化提供了条件。纵观总体,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音乐史研究处于蓄力阶段,这说明西方音乐史在中国处于发展起步阶段,虽然成效甚微但仍充满希望。
(二)研究复苏期(1976—1989)
这一时期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步入蓬勃发展阶段,文化氛围健康,政治环境宽松,对西方音乐史的态度明显改观,虽然学术研究领域较为活跃,但整体仍保持严谨的状态,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依旧为西方音乐史基于中国视域的研究与学科建设夯实了基础。复苏期西方音乐史研究特点有以下几个:一是音乐期刊恢复出版,《人民音乐》及其他艺术类刊物为研究西方音乐史提供了平台,对西方音乐史在我国研究与发展给予支持;二是专业院校恢复授课,天津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院校陆续招生,培育优质人才,推动音乐教育事业发展,在音乐教育工作步入正途的基础上促进西方音乐史研究,各院校承办学术交流会及研讨会,如1986年由天津音乐学院主办的美国音乐研讨会等,从中国视域出发研究西方音乐史;三是研究会议顺利召开,如1984年在北京召开西方音乐研讨会、1986年天津音乐学院召开美国音乐研讨会等,针对音乐教育、音乐表演、流行音乐等课题展开交流活动,与西方音乐史相关的译文、论文数量持续增多,同时为音乐院校、音乐期刊联动互助搭建桥梁,打造和谐、活跃、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助力西方音乐史在我国不断寻求研究方面的突破,学术研究专家开始健全西方音乐史研究体系,钱仁康、李英华等研究人员付诸努力,在中国视域下推动西方音乐史发展,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为西方音乐通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西方先锋音乐、西方流行音乐、西方现代音乐、美国黑人音乐、爵士乐等逐步成为研究领域的主体,使中国视域下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得以百花齐放。
(三)研究繁荣期(1989年—至今)
在市场经济确立主导地位的背景下进一步改善音乐研究宏观环境,音乐家立足音乐领域从中国视角出发研究探索,西方音乐史研究迎来春天,加之外交环境良好,国内外文化交互顺畅,促进社会建设及国民意识觉醒,其间提出科教兴国等决策,这些政策均为文化、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发展提供优质条件,西方音乐相关学术研讨会举办频次增加且质量不断提高,助力西方音乐史研究活动持续发展。以首次美国音乐研讨会年会为例,在会上围绕作曲家、音乐教育、大众音乐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讲话,针对美国音乐作品及学科范畴相关问题予以讨论,继而使西方音乐史得以在我国稳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西方音乐史相关研究成果取得质的飞跃。繁荣期西方音乐史研究特点有以下几个:一是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1989年),囊括亚非拉音乐、欧美音乐两个条目;二是20世纪80年代与西方音乐史研究相关的“方法论”为20世纪90年代更多研究方法的推出与应用提供条件,西方音乐史学术研究著作风格更为多样;三是研究内容细分,研究人员专注于某个领域深耕细作,如谭冰若以国外通俗音乐研究为主、蔡良玉以研究美国音乐为主等,另有学者对国别史、音乐断代史、专题史等方面的研究较为专业。
二、中国视域下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展望
基于中国视域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成就有以下几个:一是各个时期对西方音乐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最终打破“重中间、轻两头”研究局限的束缚,确保各个时期的研究占比较为均衡。古代音乐、古典音乐、浪漫音乐、现代音乐均在研究之列;二是对西方音乐作品及作曲家的评价追求公正客观;三是研究内容日益复杂,资料更为充实,东西方音乐文化交融碰撞利于打破西方音乐史研究瓶颈;四是专题史、国别史研究进步较大,以《美国音乐史》《苏联音乐史》等国别领域研究著作为代表,学术含量不断增加,从专题史角度来讲,研究内容包括流行音乐、器乐、声乐、摇滚乐等类别,这成为推动西方音乐史研究活动齐头并进的重要条件。
虽然中国视域下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成果明显,但不足之处客观存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影响力有待提升,包括西方音乐断代史在内的研究领域有待深耕,研究提升空间依旧较大;二是虽然国别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国别史研究过于集中的问题突出,未能将主要精力分散到容易被忽视的国家与地区,如芬兰、格林兰、挪威等,还需更加关注不同国家及地区的音乐历史,使国别史研究更为系统全面;三是研究成果推广效率需要提高,确保研究成果能转变成我国音乐行业进步的动力。
中国视域下西方音乐史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且研究程度持续深入,未来在弥补研究缺陷的前提下要在研究方法的变革与创新层面上下功夫,例如运用高新技术整理并存储西方音乐史相关文献资料,创建电子图书室,为研究人员选用素材提供便利条件,同时整合资料并有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对基于中国视域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趋势、现状、阻力等方面加以分析,这为制定具有前置性的研究方案提供条件,保障研究方向准确,研究方法更为高效,通过合理的设计规划提升研究水平,在研究中可少走弯路,助力研究成果提高推广价值。未来在研究西方音乐史的过程中需要解决西方音乐社会史、音乐文化史、音乐风格史等方面的研究与中国音乐史脱节的问题,充分利用西方音乐相关史料进行研究,在中国视域下分析西方音乐史,为中西音乐文化结合奠定基础,用中国眼界研究西方音乐问题,这可为西方音乐史料来源渠道拓宽指明方向,使西方音乐史研究具有中国特色,协调西方音乐传播程度、传播范围与中国视域下西方音乐史研究理论创新的关系,继而用发展眼光看待西方音乐史,还需融入心理史学、比较史学、口述史学等研究内容,赋予西方音乐史跨学科属性,将人类学、社会学、美学等文献研究成果引入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继而增强西方音乐史研究与发展的生命力。无论处于哪个时期,人才均是西方音乐史在中国研究与发展的“主力军”,这就需要加大基于中国视域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推广力度,引领专业领域的学者、学生、教研人员参与其中,携手完善新理论、新方法、新体系,使研究活动可在社会各界共同展开,在新时代提升西方音乐史研究水平。
三、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音乐史在中国视域下的研究与发展并不顺利,无论是坎坷还是在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均为新时代西方音乐史深入研究给予支持,引领社会各界共建利于学术研讨的良好环境,在此基础上细分研究领域,鼓励研究人员扎根专业领域深耕细作,在累积研究经验的同时探索中国特色理论、方法、体系发展出路,未来数字技术、优质人才、内容扩充将成为西方音乐史研究动能,弥补研究缺陷,提升研究水平,继而助推我国音乐历史文化研究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