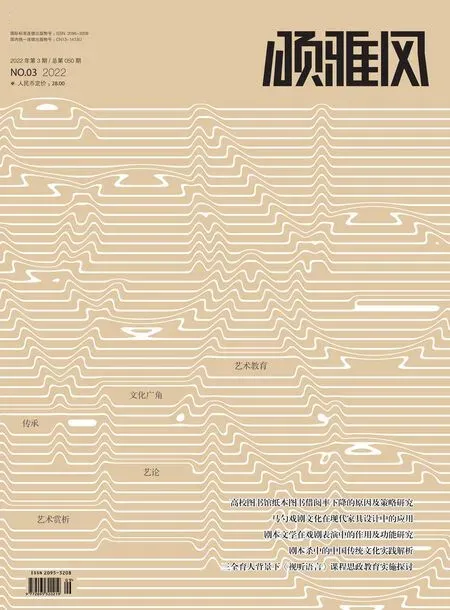挖小根蒜
2022-07-21王春梅
◎王春梅
作者单位:沈阳市法库县农业农村局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无意阅读高鼎的《村居》诗作,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关于美好的春天里的种种事情来,比如挖小根蒜。
小根蒜,是百合科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鳞茎近球形,外包白色膜质鳞皮,果为蒴果。别名菜籽、荞子,在我们东北,鲜的小根蒜叫大脑崩,成熟后称菜籽。
小的时候,每年春天我们都要迫不及待地去田地里挖大脑崩,因为冬天没有什么吃食可以寻觅,单调、枯燥的冬天很是漫长。
东北的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放学后,刮了一天的大风也像劳碌了一天的人们似的,有些倦了——脚步终于轻了下来。事前约好的几个小伙伴拎着小筐、镐头,嘴里嚼着饼子,带着家里的大黑狗,奔着人烟以外的国道西或者揽青地,有说有笑地出发了。
大地苍茫而苍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挖大脑崩,眼里、心间都是一个概念。
与前一年的荒草一样,大脑崩原有的芽苗枯黄、虚弱地贴在地上,不仔细瞧根本看不出来。我们像一小群嗅着地面行走的小羊,彼此保持距离弯着腰、低头一路寻找。重新发苗的大脑崩,有的翠绿、倔强地打个卷端坐着,有的还红着鼻子蒙头大睡呢。无论何种姿态,一经确认,便扒去上面隐蔽的枯叶,毫不犹豫地用力刨下。有时,它们的果实隐藏颇深,像与我们暗暗地较劲似的,必须多刨上几镐,那个带着长长须根、无限留恋大地眠床的大脑崩方能出得来。挖掘过后,旁边留下一堆儿新土、像眼小井儿似的坑穴。
每成功挖到一颗大脑崩,都让我们异常欣喜。
大脑崩你不敢来,你来我打死你。听说越是说大脑崩不敢来,它越是异常勇敢地出现在你面前。于是便故意念着咒语一般地排遣寂寞。
大脑崩不挑土质,很多地方都有它的身影。但是作为乡下长大的孩子,潜意识里自然知道哪些地方是要避开的,比如谷地抑或草甸子上,那里的大脑崩多有一层难解的黑皮包裹,打理起来异常费事,所以每次出去,或南或北、心里都有严格的界定。
风停了,大地像泛起了浅浅的黑色的雾,升起又落下。我们知道该回家了。集合到一起的小伙伴们虽然嘴上没有发声,眼睛却像为自尊的口令驱使着,你看看我的筐,我瞧瞧你的筐,心里暗暗做着比较。尽管大家都很努力,但天不作美——我们来早了,最多的也就挖上两大把。
用清水泡上一会,摘去黄叶,洗几遍,白白净净、青枝绿叶的大脑崩上桌了,它极其鲜明的色度激动着桌上所有人的视线,也像一种招引,让扒进嘴里的每一口饭食都变得顺滑、有味。如果抹上酱汁,再来一口脆生生、辣丝丝的大脑崩,嗯,够爽!
像星星之火,一冬天毫无生气的餐桌终于现出了希望。
清明时,在东北有吃酸菜、大脑崩馅盒子的传统习俗,只见母亲将烫好的玉米面擀薄,用带有蓝边的小饭碗扣成一个一个圆形的面片,上面放上用猪油和好的香喷喷的混合馅料,两个一合,少顷,飘着特殊的袅袅香味,热乎乎、油汪汪的大脑崩馅盒子上桌了。争先恐后、一张张吃了一冬天咸菜大酱、牙关发紧的嘴像松绑了似的,特别舒坦。
如同家有小女初长成,渐渐地,大脑崩长大了,变成菜籽了。捡拾菜籽最好的时段是在种地时。彼时,天更暖了,风象轻纱似的拂动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和大地里。
走,捡菜籽去!准备过后去找有求必应的大娘家的三姐,小筐、镐头一拿,纵横阡陌中奔一处有犁杖耕作、被称作大块地的偏远地块走过去了。
老爷在呢!远远地看到那个模糊的人影,一路猜测中,三姐发声了。三姐嘴里的老爷是我们家族里的爷爷,在生产队当车把式。
老爷!捡菜籽呀?我们微笑着算是回应,怯怯中跟在老爷的马犁杖后面。我们看了,那不是在种地,应该在翻地,因为就老爷一个人在。打过招呼的老爷仍在自己的热情里忙碌着,不赶我们也不理我们。
喔!吁!他与那听话的马儿说着难懂的话,也不时在空中舞动着鞭子,发出一声声脆响。前面的马儿点着头、带着粗重地呼吸,集体向前。地上一些这样那样、包括像翠生生的苦麻子,还盛开着黄色、白色的小花,瞬间都在重重的马蹄下沦落成尘,碾作成泥了。犁杖后面,对着翻向两边、黝黑、松软的泥土,我们默默地观察。
少顷,透着新鲜泥土的气息,藏在地层深处、白花花的菜籽被翻上来了,像珍珠,也像蚂蚁蛋,那么洁白、光亮,水灵灵的。好多的菜籽啊!瞪大眼睛、激动中的我们急躁了,沿着垄沟各把一边,赶紧扑过去、一把一把,来不及仔细清理泥土就都一起装进了小筐里。因为那是一处与另一个村落接壤的地块,很快,比我们的脚步快上许多的犁杖就要在老爷的吆喝声中返回来了,就要在一垄挨着一垄的翻耕中抑或重重的马蹄下重新埋没了。为了最快速度捡拾更多的菜籽,几乎什么都顾不上了——我想,当时果断丢掉碍事的镐头的我们一定是很狼狈的,因为碎发一绺一绺地随着我们大幅度的动作垂荡在眼前,鞋子里面凉丝丝的灌满了泥土,一双小手污没着,更不知道时间几何。
风停了,琥珀色的晚霞渐渐从天边退去,周围的树木、沟渠、沟渠对岸、太平沟那个养鸡的人家,都像一下子掉进了神秘的静寂里。远处,牛羊哞哞叫着指认着家门,我们知道时间不早了。再看看手里的小筐,已经多半筐了。
三姐,咱们回家吧。走吧。抬头看看我:哎呀,你捡的好多!多吗?差不多。说着瞧瞧三姐的筐里,满意也满足地向村里走去。
一时吃不完的菜籽可以先行晾晒,晒干后随用随取,也不用洗,用手搓一搓,呼地一吹便干净了。
咸只一样,辣有百种。菜籽的辣就像被咬住了似的,叮在一处不动弹。不像辣椒,谁惹跟谁急。它不是,辣是辣,但不长久,像个容易改口的孩子,只要咬上两口饼子,自然就消解了。
后来我长大了,远离了玉米、高粱,去到一个玉米看不见我的地方生活了。
我的婆婆是个念旧又特别勤劳的人。如果说她身上有一百种优点,那么勤劳仍然位居榜首。
菜籽下来时,勤劳的婆婆每年都要为我们晒上一些。晒好的菜籽藕荷色,饱满、晶莹,大珠小珠落玉盘——装在一个敞口的陶器里。
让人预想不到的是若干年后、一向隐忍的土地终于面露难色、无力承载万物了,它虚弱着。太多的大脑崩没有跟了来,不仅大脑崩,像蒲公英等等都敬而远之了。
野菜越来越少了。
奉土地为神灵、对于地里所有植物,都像八辈子老姑舅亲似的的婆婆将难得一见、尚未长大的大脑崩,随着洗菜的水有意倒进菜园里。年复一年,像一场疗伤,不知不觉间已经“百花齐放春满园”了。坐在屋里,没事看向窗外,看向绿乎乎、在风里轻轻摆着的大脑崩的芽苗,心里像长了草似的,为一顿“好饭”热望起来。
托婆婆的福,吃大脑崩再不用去广漠的大地里费心了,在家就能轻松解决。
那种精心灌注的便利与美好,仿佛又回到了小的时候。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一站一站,总是不断地有人上车或下车。若干年后,婆婆走了,婆婆的菜园自然也没有了,以往的美好都成了一去不复返的记忆,在岁月里风干着。
小根蒜有行气、通阳、导滞的功效。百度数据让越来越少的小根蒜增加着身价,不似当年“慌不择路”的我们,纯粹地只是为了充饥。
如今,一到春天,市场上仍有卖大脑崩的,一小堆儿一小堆儿被小心呵护着。我知道那都是来自遥远山野里的美味,价格自然不菲。物以稀为贵在这便有所体现了。
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带上我的儿孙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午后,拿上小筐一同去草长莺飞、广袤的田野里挖大脑崩, 像怀念那些与自己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一样的特殊感受分享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幸福,有福也要惜福。
挖小根蒜,这是一代人的记忆。尽管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毕竟给过我快乐,滋养过我枯燥的生命,所以,一提起来,连人带物——眼前飘扬的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总是倍感亲切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