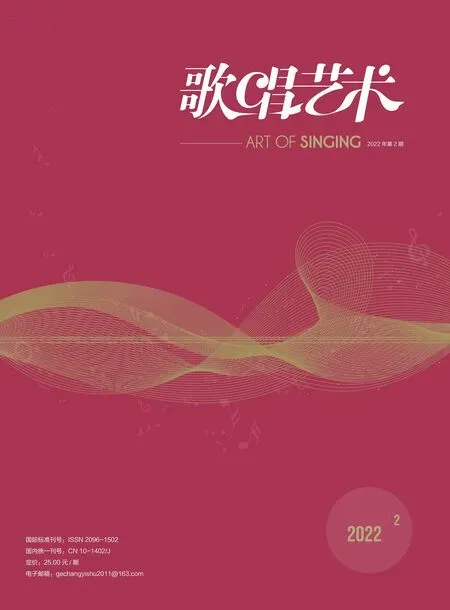关于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与生活》的一些演唱提示与指导(二)
2022-07-15刘子彧
刘子彧
在上篇《关于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与生活〉的一些演唱提示与指导(一)》中,有幸和大家分享了舒曼及其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与生活》的相关常识,接下来,继续聊聊“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的内容吧。
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的
(一)走近舒曼
作曲家舒曼常因其早年遭受双极性精神错乱的折磨而被一些人不友好地称为“疯子”或“神经病”。他的情绪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走,一会儿是神经质般的欢愉,一会儿是自杀性的抑郁。这样的精神世界时刻影响着他的音乐创作和音乐评论,但同时也赋予了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魅力。细细想来,舒曼是一个矛盾体:他自我冲突与矛盾的内心世界,在他的音乐作品中投射出一系列对比——冷与热、快与慢、动与静、和谐与对抗、理性与感性、快乐与悲伤、梦幻与现实、逃避与面对等。正如在《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第十六章“浪漫主义”中“门德尔松·舒曼·肖邦”一节部分所说:“古典主义者的个性是坚定的,一致的;浪漫主义者则有二重个性。舒曼曾信服地把二重个性拟人化为弗洛伦斯坦和尤瑟比乌斯。这是舒曼幻想中所产生的人物,把浪漫主义艺术家的心灵分歧用文学的形式予以具体化了。浪漫主义的自我是永远在形成中的,因为那无穷止的斗争本身就是它的心灵。”19世纪德国早期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认为:“一个人要发展个性就必须把几个人的个性吸收到自身中去,然后把它们消化。”倘若我们从诺瓦利斯的浪漫主义艺术美学思想出发,就会发现舒曼的生活与创作,就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将不同性格进行消化与调和的过程。
舒曼可能早就感知到自己的双重性格,甚至能和自己内心的两个“我”对话。因此在撰写音乐评论时,他给自己起了很多名字,幻想出无数个不同身份、不同思想、不同性格的自己。这些各式各样的“舒曼”中最有名的便是弗洛伦斯坦(Florestan)和尤瑟比乌斯(Eusebius),这两个名字分别代表了他性格中主动和被动的两面。弗洛伦斯坦代表热爱生活、激情昂扬的一面,尤瑟比乌斯则代表悲观颓废、消极逃避的另一面。(为了方便写作与阅读,下文用字母“F”代表弗洛伦斯坦,用“E”代表尤瑟比乌斯。)
(二)走进《妇女的爱情与生活》
对《妇女的爱情与生活》的音乐分析,我认为应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整体再到局部。基于上文提及的弗洛伦斯坦和尤瑟比乌斯,在演唱该套曲之前,不得不考虑宏观把握整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舒曼式思维。
1.《妇女的爱情与生活》情绪安排

表1 音乐情绪与个性特质对应关系表
由表2可以看出,套曲《妇女的爱情与生活》八首作品中有四首情绪热烈,四首含蓄内敛。代入字母“F”和“E”来理解,四首可以用“F”表示,四首可以用“E”表示,依次是“E——F——E——F——F——E——F——E”。这样的安排与上文所说的“不断斗争”“不同性格之间的消化与调和”不谋而合。前四首的音乐风格“E——F——E——F”和后四首的音乐风格“F——E——F——E”都展现出带有循环交替特征的结构。同时,前四首与后四首形成了一种镜像结构。

表2 八首作品音乐情绪分类的对应关系表

这里所指的“结构”与传统意义上的曲式结构意义不同,所以我把它们叫作“情绪型结构”。“F”和“E”的交替出现,体现了舒曼矛盾的内心世界,印证了其创作中冲突的与消化调和。前后镜像的设计象征着舒曼通过这部作品投射出自己的真实生活。写到这里,笔者好像突然明白舒曼当时为何去掉了原诗九篇中的一篇。因为倘若由九个部分构成这部套曲,不论是多出了一个“F”,还是一个“E”,都无法达到平衡,情绪型结构就不能形成典型性和对称性。
2.《妇女的爱情与生活》力度安排
舒曼非常重视音色的变化和钢琴伴奏等特定的音响。他善于用细腻的手段来挖掘人的内在情感,以及音乐更深层的含义,因此他的艺术歌曲具有非常强的抒情性和诗意。套曲中每一首歌曲的力度选择,以及旋律声部与钢琴伴奏声部力度的安排都需要被关注。下表可以帮助每一位演唱者更直观地感受套曲中每一首歌曲的力度设定。
(1)“弱”同样是一种力量
从下面表3中不难看出,这部套曲整体力度的安排并不是亢奋、激昂的。这就是几乎所有关于这部套曲的研究文章都予以“优美、抒情、诗意”结论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也告诉每一位歌者一个简单却又容易被忽略的道理:情感的宣泄不一定需要咆哮、歇斯底里地哭喊。喜悦也好、悲痛也罢,表现它们的存在与力度强弱没有绝对的关联。开心不只是开怀大笑,悲伤也不局限于放声大哭。于我个人感受而言,默默地从眼角滑落的滴滴眼泪远比号啕大哭显得楚楚可怜,白居易也告诉我们“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道理。所以歌唱啊,不靠音量刷存在感!“弱”同样蕴含着一股力量,同样能表现内在情感。在歌唱艺术中,轻不一定是弱,有时候轻声会凝聚着很强的力量,这种内力的深厚和凝重,常常比倾诉、宣泄更为感人,更能够撕心裂肺;而声音响不一定是强,强并不完全是力,更重要的是质。

表3 八首作品力度对照表
(2)唱出强弱不简单
很多歌者认为有强有弱的演唱才能体现出力度的对比,才有可能被冠以“有乐感”的美名。暂且不说乐感是否就是单纯强弱的问题。单从强弱处理出发就会带来一些思考:如何量化所谓的强弱?哪里要强,哪里要弱?
从强到弱,会经历很多层次。如表3所示,其力度从最强的到最弱的分出了六个层次。严格来说,想要唱出强弱对比,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演唱能力,即能唱出的最强和最弱音量,随后按照不同音量划分出对应的力度层次。然而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因为强和弱是具有相对性的。
第一,强弱自身相对性。强与弱只有同时存在并相互参照,才能体现出对比。差距越大,对比也就越强烈。就好比一场声乐比赛,不同的演唱者在同样的音乐厅演唱相同的作品时,听众很容易听辨出谁是“大号”嗓音,谁是“小号”嗓音。同理,演唱一首作品如果从头到尾只用同一种音量,或是音量变化微乎其微,会让人听起来平淡无趣(作曲家要求的“平淡”除外)。
第二,强弱在不同环境下的相对性。同样的力度,在不同的环境下会给听者不同的感受。比方说一个餐厅正播放着“恭喜发财”的背景音乐,此时你可能听不见邻座的说话声。如果突然背景音乐停止了,周围安静了,你可能会觉得邻座的说话声很吵。演唱者不得不考虑到这种感知变化,必须学会在不同的场合及时调整自己的演唱音量。至于如何去调整,那就得去问问你的声乐老师了。
第三,强弱没有随意性。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音乐艺术是感性的,所谓的“乐感”就是人对音乐产生的主观感觉。因此强和弱的表现也体现了个人的主观色彩。我不否认每个人对强弱的感知会有所不同,这是一种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但这不代表随意。在一首歌曲中,强弱的安排首先应遵循作曲家的意愿,也就是标有强弱记号的位置必须按照要求做到。当旋律中没有标记明确的强弱记号时,应当结合前后音乐情境、旋律走向、节奏安排等力度记号以外的音乐元素合理设置,而不是随意的处理为:今天强、明天弱,后天不强也不弱。令人遗憾的是,在实际的课堂教学和课下练习中,许多演唱者恰恰认为没有标记强弱记号的部分是自己自由发挥的大好时机,当所谓的“歌唱状态”好时,往往唱得十分卖力,而状态不好时,可能就轻轻带过(此时此刻相信有很多人会意地笑了)。不论演唱、演奏,没有那么多随意的“我觉得”,所有的“觉得”都应基于客观存在的乐谱和不可歪曲的作曲家创作本意。
(3)放下主角光环
许多独唱演员都具备一种独霸舞台的气场,那是一种视觉需要。但,声乐表演艺术同样是听觉艺术,因此声音才是应该重点关注的。从表3可以清楚地看到钢琴伴奏声部并不是躲在旋律声部身后的配角,它与旋律声部构成有机整体,共同承担着表现音乐的责任。
我甚至大胆地认为,舒曼在创作《妇女的爱情与生活》时已经把演唱和演奏的两部分也纳入矛盾对抗的体系中,这体现了其精神世界在音乐创作上的渗透。作为演唱者,钢琴伴奏的存在更像是自己的另一半,相辅相成,相互依赖又彼此成就。(如何学会听懂钢琴伴奏的内容,之后将会以每首歌曲为例详细分析。)
3.《妇女的爱情与生活》调式调性布局

续表
通过表4的归纳,估计大家要感叹舒曼有多喜欢“折腾”了。一首短短71小节的《他比任何人都高贵》和只有52小节的《姐妹们帮我梳妆》,都安排了多次调性转换。频繁的转调、离调,再一次证明舒曼纠结不安、矛盾对抗的内心世界。但尽管动荡不安,却还坚守着一些传统。比如表现幸福生活的时候运用大调,悲伤痛苦的时候运用小调。整部套曲以降B大调开始,不论过程多么复杂,尾声仍回到降B大调,回到原点,像极了人生。

表4 调式调性布局
4.《妇女的爱情与生活》曲式结构布局
对于演唱者来说,曲式结构是与音准、节奏关系最遥远的音乐元素。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曲式结构对演唱的影响往往体现在情绪上。结合右上表5来看,一部曲式的歌曲情感表达是直接的、简单直白的。回旋曲式的歌曲可以表达出反复、慌乱、不知所措的心境。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因为有了再现部,起到了强化情感的作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有点啰唆,那就说两遍。变奏曲式的歌曲因为变奏手法的灵活运用,彰显了歌曲的灵动性,塑造出活泼的人物个性。

表5 曲式结构布局
不知不觉中,已经带着大家从情绪、力度、调式调性、曲式结构四个方面宏观了解了整部套曲,把握了整部套曲的整体创作思路。只有这样,才能在接下来每首歌曲的细化分析中,找到舒曼的逻辑。这样的分享是否比上来就直奔具体作品的文字描述更加有趣呢?(未完待续)
注 释
①“情绪型结构”,源于现代小说的一种结构形式,即以人物情绪为主要线索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