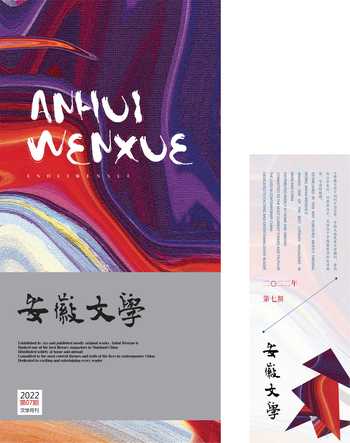请给我一个读小说的理由
2022-07-14张晓霞
张晓霞
人渴了要喝,冷了要穿,孤独了要出走,读一篇几千字的小说,当然也是有需求的——向小说寻求某种精神的满足。在这个人人都在“奔跑”的时代,坐下来读一篇小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简直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饱食一顿纯肉馅饺子还困难,“信息像雪崩一样传来,吸引了我们散漫、肤浅的注意力,我们像被烟熏出巢穴的蜜蜂,嗡嗡地从一种噪声飞向另一种噪声,从一个标题飞向另一个标题”(乔治·斯坦纳语)。那么,作为一种传播载体,曾经负有为读者提供娱乐、常识、信息、情感乃至意义等功能的小说,被海量的新闻、信息、“海陆空”相协的音、影、视像所替代,小说和新闻之间出现叠合,小说的许多功能正在被新闻和资讯抢掠,在这个多元的、信息疯狂繁殖且无信息死角的自媒体时代,闪烁于屏幕中的信息如雾霾一样飞扬,所有人都成了“滑屏”的观众,所以,在人们的阅读耐心像太阳下的冰淇淋一样易融化的今天,作为一个读者,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可以让他屏蔽这一切,静静地捧起小说?
《入伏》是一篇诚实的小说,作者没有一点炫技的意思,表达得“一本正经的老实”,稍显啰唆的叙述,以及一板一眼、实实诚诚的行文腔调,无悬、无疑、没惊喜,一切皆在意料之中,看不到这个小说与众不同的野心和光芒,无论情节还是见识,没有提供超越人们已有经验的发现和思考,虽顺顺溜溜却少了心理的曲折和超拔的飞逸。从小说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句号,抬头想,这样一篇几千字的小说用不足五分钟的短视频会演绎得淋漓尽致。《感动中国》中不乏这样情深义重的故事,《今日说法》每天在播着故事的前半段,电台有类似题材更入心的专访,图文并茂的微信平台也一再看过。小说复制现实,呈现表层的生活流程,比起媒体人用共情掌控、情感煽动的类似故事,稍显寡然。又读再读,一些隐现于意识里的判断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历历可数的答案。
其一,有故事但故事缺乏吸引力。
小说描写了底层的贫民家庭,在忽然降临的灾难面前的无力和用生命坚守的道义。朱加明、朱加海兄弟俩的父亲在等红绿灯时被匆忙中赶往工地的老祁撞飞,面对父亲的住院费,兄弟俩即使倾尽可怜的家财也束手无策,总算在提前预支工资后让父亲顺利出院,朱加海本以为更悲惨的老祁在工地出事后索要医药费无望,可老祁老伴最后用老祁摔死拿到的赔偿金偿还了医药费。命运的偶然之手伸过来的时候,对于打工者来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一个事故导出另一个事故。两个家庭,一种艰难,生存的难,一个偶然性的旋涡,对打工家庭构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威压和剥夺,最后坚守信义的老祁只能制造另一场事故,以命抵债,压得不能活的债。应该说这是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故事,故事的缘起和触点来自社会新闻,小说具有“元新闻叙事”的意涵,像加长版的新闻事件,始终绕着事件时序打转儿,从进医院、等电梯、病房、兄弟对话、要钱、吵架、老祁死、出院、收钱,这的确是一种真真切切的现实,作者没有在一串零散驳杂的真实中过滤出自己的小说界面,他变成了耕地的农夫,从这头犁到那头,直接照搬生活。开头就缺少一种牵引读者往下走的吸引力,骑电动车、停车、看手机、关手机、进医院,目之所及的医院日常,这些情节和信息并不新鲜,没有超越我们的认知智慧,有“空转”之嫌,其后的一系列兄弟争吵、要钱、夫妻对话,无一不是作者滑行其寡淡的叙述风格,为了讲故事而硬讲故事,小说始终没有迈进虚构的“假”世界中去,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方式体现命运的偶然性下底层的真实处境。事故止步,故事出发,只按“意旨命令”推进故事,中规中矩,有序不乱,没有一点冒犯读者的智商,没有在生活的褶皱间呈现其该有的腥气、挣扎与破碎。我们拿出“稀缺”的专注力去阅读小说,渴望在新闻结束之时、生活停顿之处,在媒介够不着的地方,小说能是文字的感觉承担,又是心灵的思辨负载,能让小小的事情变得“兴趣盎然”。收起《入伏》,故事随着阅读的结束而结束,既没有向小说外延伸的冲动,也没有不自觉产生的想象与感动。
其二,有人物但人物没有生命力。
读完《入伏》,我仰头闭目,想理一理,有哪个人还“活着”,但很遗憾,朱祁两家六人,都面目模糊,没有一个活生生地“立”在我的大脑。作者像新闻一样只顾专注叙述事件,却没有倾力刻画人物,人物被作者控制得太紧,只顺着事态呈现。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脾性,他们是群像中的一个,使读者看不见、听不到、更触摸不着他们的苦与痛,因神散形乱无个性而变得没有生命力。
其三,有细节但细节缺乏想象力。
作者事无巨细地铺排式地描述每一个场景,不厌其烦地描写人物所经之处的动作,将日常所见当细节在小说中大肆铺陈,一次次分散了注意力,与本质毫无关系的描述,拉淡了阅读兴趣外,使小说的血肉枯干失色。第一次去老祁家索要医药费和老祁老伴送钱来,看到这两个细节,我不由得在心里“笑”了起来。这些情节新闻桥段里“上演”过了,你倒是来点儿新的呀,细节引诱我们去想象,作为剥视生活、剥视人性的细节想象力,需要独创的、有张力的情节或信息。尤其朱加海在小区外为老祁烧纸那一段,最后趋光的情节可以有,但末了朱加海的解释多余,这样滴水不漏的设置,“狗尾续貂”般折损了小说飞起来的翅膀,使小说成为现实的索引又加了重重的一笔。许多的时候,小说的价值,不在于作者所说出来的部分,而恰恰隐藏在作者想说而未说的地方。老祁“偏偏”在没有防护网的工地“意外”掉下,私以为是本小说的亮点。
细节的粗糙,就是情感的粗糙,是观察和体验的粗糙,导致语言也无法传达深刻的思想。欣赏小说,即体察故事、人物、思想的细密褶皱。因为《入伏》在这三个方面突破的欠缺,小说就少了以自己的方式带来的独特阅读享受。《入伏》是个粗毛坯素材,缺少精加工,深加工。还是这个故事,若深入的心理开掘,化腐朽为神奇,会成为一个令人回味和富有启示意义的立体故事。
在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文学要想抗拒寂寞的命运、分享新闻的荣耀,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被热闹的新闻和喧嚣的资讯层层包围,图片、音视频,甚至AR、VR,花哨的极端现实挤压着传统小说的表达空间,让我们沉浸于戏剧性的感叹和廉价的感动中,小说若只有复述生活的能力,始终没有摆脱让人烦腻的新闻式现实,缺乏想象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可能性,心灵探索的力度弱,除了庸常化的经验描摹,对这个世界的表达,少了崭新的发现,不能提供对抗生存压力的勇气和力量,时间终究会让这种不必要的存在落满灰尘。小说须“向内转”,转向孤独而痛苦、細腻而复杂的个体内心,从小角度深深切入,复活个体的日常感悟力,这样小说才不会枯萎,走向它不可替代的未来。
责任编辑 黄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