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整体文学中的《格萨尔》
2022-07-12徐新建
徐 新 建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2017年10月,由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与西北民族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多民族《格萨尔》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

图1 中国多民族《格萨尔》学术研讨会会议图片
会议期间,杨洪恩教授接受媒体采访,强调格萨尔的“故乡”在中国,但在过去它的研究中心实际在国外;如今,随着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抢救性保护和多学科研讨,“格萨尔的‘研究中心’已经真正回到了中国。”[1]
笔者赞同这种跨文化的国际视野及立足本土的自省和自信,并在与会发言中做了回应阐述。本文即在会议发言稿基础上修订而成。感谢西北民族大学的盛情邀请及与会专家杨洪恩、诺布旺丹等的宝贵意见。
一、由“世界体系”派生的国别文学
流传于藏、蒙、土族、裕固族等多民族传统的格萨尔说唱,近代后被逐渐列入中国文学整体之中并逐渐占有重要位置。这一转变具有多层面的深远意义,值得深入评说。较长时期以来,在将“格萨尔”列入中国与世界文学整体的学术讨论中,学者们较多强调了其作为神话和史诗的文类贡献,然而结合20世纪后中外文学的交融并置来看,其意义并不仅限于此。
以国别为单位的“中国文学”,实质是近代东西方文化冲撞的结果,是由众多民族国家搭建起来的“世界体系”派生物。这样的冲撞、派生,极大挤压了汉语表述的“天下”格局,改变了东亚地区历朝历代以“夷夏之辨”为基点、从行政治理到文化认同的封贡传统[2]。面对如此剧烈的变局,近代中国的精英们,尤其是汉语界的革新人士起而行之,重新搭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法则的世界新秩序,并按照现代性分类体系及标准,构建出满足彼时之需的“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一如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发表《新中国未来记》所昭示的那样,具有数千年传承的汉语书写至此挤入了国别林立的文学之路,期盼着借助“维新变法”之推动,以语词构建的国家意象,别古迎今,再造国民①。然而仅以“小说界革命”掀动的一系列改良而论,由国别文学引出的问题繁多,涉及甚广。例如,若以国为界,何为“中国文学”?它的构成是什么?边界何在?汉语精英的书面表述能否代表中国文学整体?近代以来,这些追问不断涌现,牵引着中国文学的深层走向,也搅动着一代代文学参与者的多重心绪。

图2 任乃强的《藏三国》与蒙文本的《格斯尔》/网络图片
以此为背景再来谈论多民族传承的“格萨尔”,便有了更为开阔的历史参照。作为民众生活的口头诵唱,“格萨尔”长期存在于甘、青、川和西藏等地的藏族社区,后又随文化传播逐渐流布到蒙古、裕固等族群之中。在这样的时期里,“格萨尔”属于自在文化,拥有自身的分类归属及文体特征,并对应着世代相沿的信仰功能,既不需要被认定为“文学”,亦无所谓是否被纳入更大的认知体系。直到清康熙年间蒙文刻本的《格斯尔王汗传》在京城面世[3],这一自在式的民间流传才较为正式地进入王朝系统,逐渐进入官方视野。不过彼时与之对应的还是“五族共和”的帝国体系,格萨尔这样的民间诵唱,充其数也只能列在为科举制度所尊崇的文类之末,放置于王朝正统的知识话语底层,不可与被定为主流价值的经史子集相提并论。
二、多民族中国的跨族别比较
民国之后,新文化推动新思想与新观念,加之现代国家引出的边政学之需,于是有了任乃强在四川康区对“藏三国”的意外发掘。任乃强的贡献在于不但把“藏三国”的他称恢复为藏人流传的“格萨故事”,而且通过以实证为基础的考察,加上对其“诗史”特征的强调,把在藏区长期传诵的这一口头文本,引入汉语学界的现代视野,并将其与《封神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等相对照,开启了“格萨尔”在多民族中国的跨族别比较[4]。
接下来,使“格萨尔”进一步融进中国文学整体之中的代表人物是老舍。具有满族身份的老舍在新中国建立后被推举为中国作协领导,并在20世纪50年代代表官方机构发表关于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工作报告。老舍报告将“格萨尔”列入其中,将其作为少数民族的史诗杰作加以肯定,强调与蒙古族《江格尔》及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等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都是“构成祖国的文化历史的宝贵财产”[5]。
以如今眼光来看,老舍报告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一方面从多民族角度扩展了“中国文学”的边界与内涵,另一方面也通过“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使“格萨尔”等各民族文学获得了新的共同体属性,亦即多民族国家平等多元的族别成员身份。这样的推进即便在任乃强等所处的民国年代也是不可想象的,那个时期的官府学界甚至还有很多人拒不承认边疆各民族的存在,要么宣称“中华民族是一个”,要么主张以华裔人群“同源同种”理论取代中国的多民族国情和历史。所以新中国的老舍报告是一个标志,失去这标志就不会有“格萨尔”与整体中国文学相交融的今天。
自老舍报告之后,伴随着少数民族民间与口头文学收集调研工作的开展,“格萨尔”与中国整体文学的关系进入了从歌辞到传唱及至仪式与传承人的全方位拓展,用文学人类学话说,也就是开始了从文本到本文的视野转型。该转型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高潮,中经“文革”十年断裂,又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重启,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当今。在此阶段中做出贡献者不少,若从多民族关联及民间与作家打通角度概括的话,可以贾芝为象征。
1979年,成立不久的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牵头,组建了国家级的“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由贾芝出任组长。新时期贾芝领导的格萨尔工作体现为两个突出方面,一是进一步明确其作为长篇“史诗”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另外则是继续推动对格萨尔诵唱传承的活态研究,鼓励参与者“到民间去”,面向田野,在文学的生活现场,考察多民族的“格萨尔”传承。
作为全国性格萨尔工作的领导者,贾芝本人也撰写论述,不但将“格萨尔”誉为“中国史诗”,而且将其带入国际文坛,回应西方学界断言“中国无史诗”的长期挑战,以少数民族的杰作案例,彰显“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价值和地位。在题为《中国史诗〈格萨尔〉发掘名世的回顾》的文章里,立足于文学实践的族别视角,贾芝首先把格萨尔界定为一部藏族民间艺人的口头传唱,并且是被藏族人民奉为社会生活的指路明灯,然后再将其放置到多民族国家的整体中,主张如若整理面世的话应当先出版藏文本,然后才译成汉文,“向全国各民族、各地区推广流传”[6]。
三、列入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的“格萨尔”
晚清民初的新文学运动以来,经过王国维、陈独秀、胡适和鲁迅那批学界前辈开拓及老舍、贾芝、马学良、降边嘉措等不同民族作家、组织者的接续,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历经数代演变,其所蕴含的多民族特性终于在刘再复、周扬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合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词条一类的权威表述中得到确认。此后的“中国文学”被阐释为“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7],含义扩展,更具包容。
在这过程中,“格萨尔”的出现无疑起了奠基性作用。我的体会是,对于日益成为整体的“中国文学”而言,通过被称为“仲肯”等各类艺人在多民族群体至今传承的活态诵唱与传播,《格萨尔》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了其所赢得的“史诗”美誉,而至少还体现在另外两个方面,那就是:扩大“中国”所指,“带活”文学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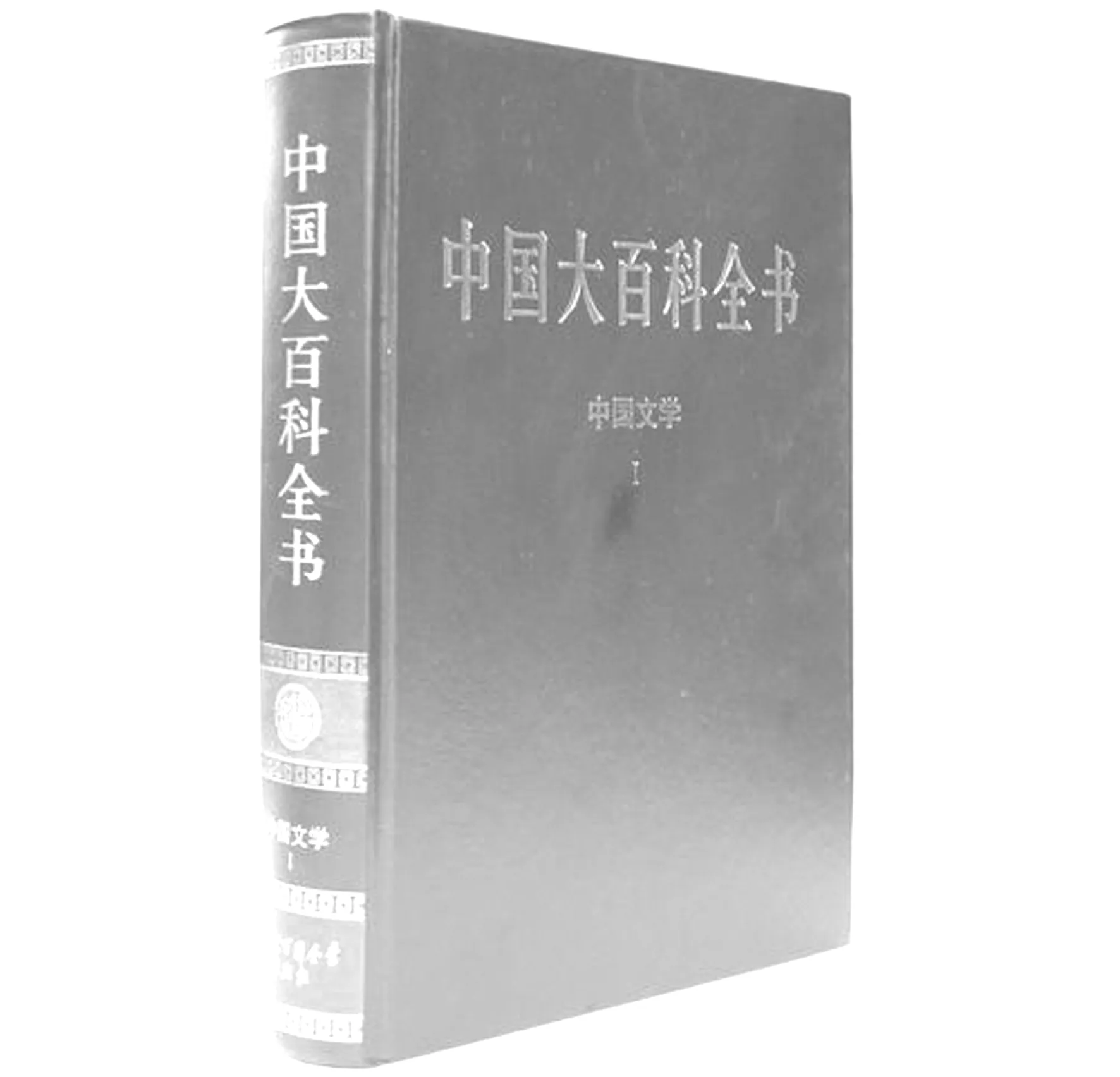
图3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网络图片
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反过来,在“文学中国”的审美信仰层面,一如贾芝指出过的那样,《格萨尔》具有的“指路灯”价值还有待认知和评论[6]。为此,笔者曾做过如下的相关回应:
当把“史诗”还原到实践之中、把各民族“文学”从现代性审美定义中解放出来之后,需要确认的是:在多民族文化的世代相承中,无论“格萨尔”“玛纳斯”还是“亚鲁王”,都不仅只是文字文本或历史记忆,而更是在生活实践中使族群凝聚的超验信仰,是连接神俗的多元人生[8]。

图4 阿来重述的《格萨尔王》
从人类由古至今以想象实现超越看,中国文学整体中的格萨尔乃至与之关联的江格尔、玛拉斯、亚鲁王,均意味着以生活为载体的精神实践与信仰升华。
2015年,作家阿来的《格萨尔王》推出英文版向世界各地发行。该著以民间传诵的格萨尔为基础,参与了重述神话的全球计划。计划由不列颠的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宗旨强调:
神话是人类历史上一条久远的线索,希腊、罗马、印度、中国这些古老文明,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神话,阅读、审看和研究神话,就是阅读、审看和研究人类的文明史[9]。
“重述神话”的丛书计划跨越国界,要求来自各国的加盟作家根据自己的想象,融合个性风格“对神话加以重构,赋予其神话新的含义”[10]。对此,中国藏族作家阿来进行了神话与地域文化及族群信仰关联的阐述,强调格萨尔的流传与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他说:
青藏高原那样广阔,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大面积存在,也就说这个史诗流传的土壤、产生的土壤还没有巨大的变化,在那个环境当中,老百姓消遣的方式,或者他们对山川大地、对历史的理解跟信仰决定了它还能够流传[11]。
四、结语:古今连通的传诵、重述和展演
2020年8月,笔者参与的四川大学课题组到青海考察,在青海民族大学同行带领下,前往西宁市力盟商业街调研,访问了以传承格萨尔文化闻名的民族文化餐厅——“岭·格萨尔藏文化主题风情宫”。风情宫以藏地风格装饰,入口处挂满了《格萨尔王传》人物的木雕面具和全国格学界的名家照片,室内还布置了“格萨尔王”的专题展室,其中包括唐卡绘制的英雄格萨尔和彩绘的三十名将。
在此之前的2019年1月,青海省藏族研究会在此举办藏历年庆祝活动,期间进行了盛大的《格萨尔》歌舞表演。岭·格萨尔演艺厅里人头攒动,呼声雀跃,在台上台下的炙热交流中呈现了古今相通、人神关联的氛围,令人分不清是现实的生活场景还是文学的远古想象。

图6 西宁藏式餐厅里的格萨尔歌舞表演②
可见,在古今连通的传诵及重述、展演中,《格萨尔》的传承不仅超越族别、跨越国界而且贯穿了多种多样的文学类型,由此表明其“世代相承”的意义包含了如今所说的“非遗”却不能等同于“非遗”③,因为,遗产指向过去,传承则面向未来。
【注释】
① 《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模仿域外政治小说创作的长篇作品。其中突出了“万国并列”的世界景象:“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已经将太平条约画押……”可参见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资料截图自优酷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AyMTM1NjkzNg==.html.
③ “非遗”即汉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在词源上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的术语“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转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