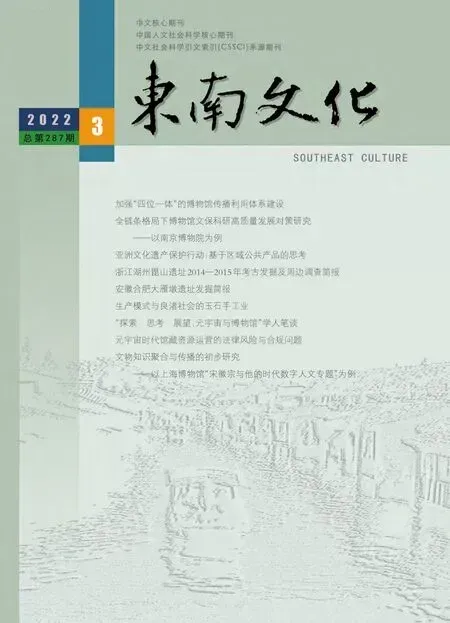山海之间:两周时期“江南—岭南”的文化交流线路及其变迁
2022-07-06吴桐
吴 桐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两周时期,“江南—岭南”之间的文化交流以江南因素的南传为主,以直口豆及敛口豆、曲壁豆、碗(杯盅)类及“米”字纹陶器为代表,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主要线路大致呈现出“东南沿海—内陆赣江流域—东南沿海”的循环往复的态势。这一变动不仅是江南地区文化交流主体空间位移的客观要求,更是越、吴分别面向海洋与面向陆地的文化与社会特性深刻影响的产物,而这种差异在导致东南沿海内部文化联系密切程度起伏、反复的同时,更导致了越、吴于两周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图景及其融入“中华一体”进程的先后与方式之别。
我国东部沿海存在一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其内部又以长江为界,在具体文化因素的形制、形态、流行程度、传播方式及其被纳入“中华一体”进程的先后与方式等诸多层面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1]。较之长江以北,长江以南的材料相对分散,研究成果虽然显著但仍有待深入。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西周、秦汉两次统一之间,即两周时期这一地区内部文化交流的主要线路——“江南—岭南”的交流线路与其历时性变化进行考察,在补充这一文化传播带的具体细节的同时,也可以将其置于更大的时空背景以窥地区文化与社会之特性。
一般来说,江南包括苏南、皖南、浙江、闽北及赣东北在内[2],岭南则泛指五岭以南,但考虑到两周时期后者内部具体文化因素分布的空间差异及其与外界联系的远近,本文所论“岭南”应特指包括粤中、粤北、粤西及桂东北在内的地区,与江南之间隔以湖南、江西及粤东闽南[3]。两周时期,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以江南因素的南传为主,具体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春秋早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分别以直口豆及敛口豆、曲壁豆、碗(杯盅)类及“米”字纹陶器为代表。因此本文尝试以这几类器物的传播为主要切入点,对各阶段“江南—岭南”的文化交流线路、变迁及其成因进行考察。
一、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
这一阶段,江南因素的南传以直口豆与敛口豆为代表,自西周中期始,此类器已为岭南原始瓷之大宗,在硬陶中也有相当大的比重,只是具体形制、纹饰及演变规律与江南所见有所差异,显然是本地改造的产物。湖南、江西及粤东闽南发现的同类器则与江南所见多无二致,其中湖南、江西发现甚少,分别仅于湖南澧县宝宁桥下层[4]、江西进贤寨子峡[5]见有一例,与岭南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空白地带,而粤东闽南则发现较多,自北向南于福建惠安蚁山、音楼山、丰泽鹏溪山、南安尾山仔[6]、云霄墓林山[7],广东揭东面头岭[8]等地皆有分布,勾勒出一条相对完整的交通路径。岭南地区此类器物最早且最常见于粤中而少见或未见于粤北及粤西、桂东北的现象也进一步表明,这一阶段此类器确应主要经粤东闽南或者说东南沿海南传而至(图一)。

图一//第一阶段江南直口豆与敛口豆的南传
文化的交流并非单向。这一阶段江南地区所见玉器以玦为主,且常见数玦同出一墓,最甚者如浙江西山大墩顶所出22件玉器皆为玦[9],类似的现象多见于粤中环珠江口一带[10],有研究者称之为“列玦”[11]。考虑到江南地区自良渚中期以来玉玦发现较少[12],且这一阶段环珠江口分布有大量玉石玦作坊[13],因此当以后者向北影响更为合理。除此之外,岭南地区在这一阶段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凸纽形玦[14]与有领璧环[15],此类器于江南也有零星发现,分别仅见于西山大墩顶[16]与浙江黄岩小人尖M1[17],同样应是由前者影响的产物(图二)。

图二// 第一阶段江南—岭南文化交流的其他内容
不难发现,这些来自岭南的文化因素高度集中于浙南闽北,即杨楠所分“黄山—天台山以南地区”[18]。从直口豆与敛口豆在江南地区的发现情况来看,其最早形态“上腹极浅,下腹较深,圈足较高”首见且多见于浙南闽北,其在浙南闽北所占的数量比例明显高于江南其他地区[19],其生产窑址目前也仅发现于浙南闽北,即福建武夷山竹林坑[20],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此类器可以被视为“浙南闽北传统”。从这一点来看,浙南闽北事实上构成了这一阶段江南地区与岭南文化交流的主体。虽然玉玦、凸纽形玦、有领璧环等岭南因素少见或未见于粤东闽南,但从原始瓷尊、提梁盉、夹砂陶甗形器等同形器在浙南闽北与粤东闽南的共见来看,这些岭南因素的北上应仍以东南沿海为主要途径。
二、春秋早中期
西周—春秋之际,直口豆与敛口豆在岭南陶瓷器中所占的比例明显降低,曲壁豆开始出现,并于春秋早期一跃成为岭南最常见的陶瓷器,至春秋中期仍保持这种优势地位。其形制、纹饰及演变规律同样经本地改造,江西及粤东闽南发现的同类器则仍与江南所见多无二致,但其具体的发现数量与空间分布情况却与前一阶段完全相反。粤东闽南仅于福建惠安蚁山[21]、长汀赢坪[22]发现3例,且部分年代可能早至前一阶段;相比之下江西的发现则明显丰富,自北向南于九江神墩[23]、德安陈家墩[24]、清江营盘里[25]、筑卫城[26]等地皆有发现,年代也更接近春秋时期;至于湖南则未见有与江南同形者。由此推测,这一阶段“江南—岭南”的文化交流线路可能已由东南沿海转移至江西赣江流域(图三)。

图三// 第二阶段江南曲壁豆、碗(杯盅)类的南传
如果说从曲壁豆的空间分布来看,这一线路的转移尚属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这一阶段原始瓷碗(杯盅)类在粤北的出现则可进一步确证这一转移事实的发生。春秋时期,碗(杯盅)类取代豆类成为江南原始瓷之大宗,但这一阶段其于岭南仅见有3件,且集中分布于粤北,即广东和平杨村坳(简报图八︰14)[27]与曲江石峡 T40②A︰11[28]、T41②AH76︰1[29]。遍查湖南、江西及粤东闽南同时期的材料可知,三地中仅有江西樟树樊城堆出土1件此类器,即78T4②︰26[30],与上海金山戚家墩(简报图八︰14)[31]形制基本相同,尺寸也较接近,且形制略早于粤北所见,恰可构成“江南—赣江—岭南”时间上从早到晚、空间上从北到南的传播现象(图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鄱阳湖与粤北之间交流线路的存在,以及这一阶段“江南—岭南”文化交流线路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的转移。
这一阶段岭南文化因素向北影响明显,于湖南、江西多有发现。仅以两地所见岭南因素的空间分布而论,其传播路径似乎是由粤北入潇湘流域,沿湘江北上,在攸县附近经九岭山与罗霄山之间的廊道进入江西境内,再由袁河入赣江,直至鄱阳湖一带(图四)。但事实上,这两地所见岭南因素的表现形式判然有别。除湖南耒阳灶市[32]、资兴旧市[33]发现有几件原始瓷曲壁豆、盘外,湖南所见岭南因素皆以夔纹为主[34]。相比之下,江西所见岭南因素则以器物为大宗,如江西清江筑卫城T4②︰1[35]与广东博罗横岭山 M264︰4[36]形似;江西安义铜锣山(简报图三︰7)[37]口部虽残但所余部分与横岭山M325︰3[38]颇为接近;筑卫城T24①A︰3[39]、江西万载井窝里(简报图三︰2)[40]及天子街(简报图三︰7)[41]分别与横岭山T0304①︰42[42]、M131︰1[43]、M133︰3[44]总体形态相近,仅鋬的方向略有差异;江西新余拾年山 T9②︰4[45]与广东深圳西丽水库 NXX︰16[46]基本相同,仅沿部略凹;江西萍乡田中古城78PXS采︰1[47]与广东封开牛围山(简报图二︰1)[48]、江西德安陈家墩 J6︰2[49]与深圳大梅沙 T204②︰4[50]皆大致接近;江西宜丰秋形垴 06YQ I采︰1[51]与横岭山 M093︰9(+)[52]几乎完全相同,至于夔纹目前则暂未发现(图四)。从这种表现形式的差异来看,湖南与江西之间应当并不存在以岭南因素为主要内容的直接的文化联系。因此这一由湘江转赣江的道路也并非是岭南因素向北辐射的主要路径。岭南与江西之间应当存在更加直接的文化联系,其路径很可能是由粤北经梅关入江西,顺赣江北上。萍乡、新余、宜丰等地所见应是由赣江支流袁河、锦江而非湘江传播而至的结果。虽然赣南目前尚未发现岭南因素北上的直接证据,但从前一阶段两地共见有垂折腹釜、簋[53]等现象来看,这一路径应有相当大的概率存在。

图四//第二阶段岭南因素的向北扩散
相较于前一阶段以玉玦、凸纽形玦、有领璧环为代表的岭南因素在浙南闽北的流行,这一阶段典型岭南因素已罕见于江南。事实上,除曲壁豆外,两地共见而形近者不过寥寥,主要包括敛口圜底钵如广东和平杨村坳(简报图八︰7)[54]与江苏武进大茅山M9︰14[55],盘如博罗梅花墩T3③︰25[56]与大茅山 M9︰15[57],敞口凹壁盆如博罗横岭山M211TB︰1[58]与江苏金坛三星墩D3M1︰6[59],侈口罐如横岭山 M085︰13[60]与江苏溧阳门口田D1M1︰24[61],垂腹罐如香港东湾︰102[62]与金坛鳖墩M2︰17[63],折棱器盖如博罗银岗 H7︰31[64]与金坛晒土场D1M3︰9[65]等。不难发现,这些器物于江南集中在宁镇及环太湖西侧(图五)。从曲壁豆最早出现并主要流行于太湖杭州湾、宁镇等现象来看,此类器可与直口豆、敛口豆相对,被认为是“太湖杭州湾—宁镇传统”。虽然这一阶段豆类器逐渐为碗(杯盅)类器取代不复为江南原始瓷之大宗,但其于宁镇及环太湖西侧仍多有发现,如金坛牯牛墩M1所出66件随葬品中,曲壁豆共有41 件[66],且其延续时间较长,在苏州俞墩 M3[67]、武进腰沿山 M2[68]、江阴曹家墩 D3M1[69]等春秋早中期墓中仍偶见此类器随葬。如果说前一阶段曲壁豆主要还是“太湖杭州湾—宁镇传统”的话,那么在这一阶段,此类器更宜被视作“宁镇—环太湖西侧传统”。因此总体来看,宁镇及环太湖西侧事实上已经取代了浙南闽北,成为这一阶段江南与岭南文化交流的新的主体。

图五//第二阶段江南—岭南文化交流的其他内容
三、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
春秋晚期,曲壁豆于岭南迅速消失,碗(杯盅)类代之兴起,随之南传的“米”字纹陶器也直接导致了岭南“米”字纹陶类型的出现及其对夔纹陶类型的取代,后者虽仍有所保留但所见相当零星,且多受“米”字纹陶器的影响,由圜底为主变为以平底为主,如广东惠来饭钵山(简报图1)[70]、封开利羊墩H1︰3[71]等皆是如此。与前两个阶段不同,这一阶段江南因素在岭南的表现形式呈现出直接输入而非本地改造的态势,后者所见碗(杯盅)类与最常见的“米”字纹陶,即坛、瓮、敞口鼓腹罐、直口圆鼓腹罐与江南所见无论形制、纹饰还是演变规律皆高度相似,表明这一时期“江南—岭南”的文化交流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
这些器类于江西、粤东闽南皆有较多发现,且以后者所见数量、种类更为丰富,所涉年代更长,出土地点也更加密集,即便是第一阶段直口豆、敛口豆所见亦不可与之同日而语。至于前者则仍主要见于赣江下游[72],以碗(杯盅)类为主,“米”字纹陶器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图六)。从这些器类的发现数量、种类、年代、空间分布以及江西、粤东闽南两周时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态势来看,这一阶段江南因素的南传应有较大可能再次以东南沿海为主要路径。但与前一阶段的情况相似,赣南发现的空白并不等于事实的空白,赣江线路仍有存在的可能,因此有必要考察包括岭南在内的各地区江南因素的具体发现情况,以明确这一阶段“江南—岭南”文化交流的主要线路。

图六// 第三阶段江南碗(杯盅)类、米字纹陶器的南传
这一阶段来自江南影响的主要内容,即原始瓷敞口直腹碗(杯盅)类、敞口斜弧腹碗(杯盅)类与硬陶坛、瓮、敞口鼓腹罐、直口圆鼓腹罐等器类,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在江西、粤东闽南与岭南陆续出现。考察这一时期各器类在各小区的式别[73]与数量分布可知,粤东闽南,特别是粤东在这些器类的出现与传播过程中始终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部分器类如硬陶坛、直口圆鼓腹罐等最早仅见于这一小区,部分器类如原始瓷敞口直腹碗(杯盅)类、硬陶瓮等的最早式别虽同样见于其他小区,但仍以粤东发现数量最多。相比之下,江西几乎尽为原始瓷碗(杯盅)类,其具体式别不早于粤东闽南,具体数量也不超过粤东闽南(表一),且多出于一墓。即便认为这一阶段江南因素仍部分经赣江南传,但总体来看,这些江南因素也确应主要经由粤东闽南渐次传播而最终流行于岭南。

表一// 第三阶段岭南、粤东闽南、江西各小区江南因素器类的式别与数量(单位:件)
至于前一阶段作为江南因素南传重要孔道的粤北在这一阶段同样丧失了在文化交流中的优势地位,仅于战国早期发现1件硬陶敞口鼓腹罐X式。虽同为这一广大地区所见此类器物的最早式别,但数量远不及粤东,更可能是经后者传播而至。而且从原始瓷敞口直腹碗(杯盅)类的发现情况来看,虽然这一阶段粤东所见最早式别VIII式早在春秋中期便已见于粤北,但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间隔,且这一式别在春秋晚期的江南仍然有所发现,因此仍有较大可能是由江南直接传播而至。至于IX式、X式的出现则更进一步证明江南与粤东闽南之间存在相当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表二)。这也再次证明这一阶段“江南—岭南”文化交流的线路已重新由内陆为主让渡为以沿海为主。

表二// 粤北、粤东第二、第三阶段原始瓷敞口直壁碗(杯盅)类的分布情况(单位:件)
在线路转移的同时,文化交流的主体也再次发生变化。这一阶段江南因素虽于春秋晚期便已直接出现在岭南,但数量、种类皆较少,其大量出现与流行要到战国早期才得以实现。而在战国早期的江南地区,灭吴之后的越国一家独大,太湖杭州湾自然也成为江南文化与社会之核心。相比之下宁镇与浙南闽北的发现则相当零星,很难与这一阶段江南对岭南强烈影响的文化交流态势相匹配,由此可知这一阶段江南与岭南文化交流的主体已再度转移,至太湖杭州湾。
四、讨论:面向海洋与面向陆地
通过上述梳理,可将两周时期“江南—岭南”文化交流各阶段的江南主体、主要线路、表现形式以及两地间联系的密切程度情况归纳如下(表三)。

表三// 两周时期各阶段“江南—岭南”文化交流的主体、线路及密切程度
如果说江南因素在岭南表现形式的变化可能主要与春秋晚期以来越国的迅速政治化有关,从而呈现出一种由“岭南改造”到“江南输入”的单向变动的话,那么这一文化交流的主要线路与密切程度的变化则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的态势,其主要线路由沿海西移至内陆又复归于沿海,其密切程度也经历了先密切后疏离然后再度密切的历程,尽管不同阶段这种密切联系的表现不尽相同。
这一变化态势的出现显然与“江南—岭南”文化交流的江南主体的变动有关。一方面,在“江南—岭南”文化交流以江南因素南传为主的情况下,江南主体的空间位移不仅会导致文化交流内容的变动,同时也会因交流起点的改变导致传播线路的转移。而这一线路先西移后东移的变化趋向显然可与江南主体由浙南闽北西移至宁镇—环太湖西侧再东移至太湖杭州湾的位移方向相印证,当是后者直接影响、作用的产物。
另一方面,这种变化背后还蕴藏着相当深刻的文化与社会内涵。第一阶段时,浙南闽北的文化面貌虽与太湖杭州湾不尽相同,但仍以共性为主,且与宁镇吴文化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虽不宜将之等同于春战时期的越国,但认为其属于广义的越文化范畴应当无疑[74]。第二阶段时,宁镇吴文化开始不断东扩,春秋初期环太湖西侧大部已属吴地,前引诸墓从墓葬形制、随葬品面貌来看也尽为吴墓,因此这一阶段文化交流的江南主体应为吴国或吴文化。至于第三阶段,特别是战国早期以来,太湖杭州湾已明确为越国之地。从这一点来看,江南主体的空间位移事实上正是吴、越之间文化与社会力量对比的空间表现,也正是这种“越—吴—越”的主体反复导致了“江南—岭南”文化交流线路“沿海—内陆—沿海”与密切程度“密切—疏离—密切”的循环往复态势的出现。
尽管这一问题颇为复杂,但仍可从上述讨论中得出这样两组对应关系:(1)越文化为文化交流主体时,交流线路以沿海为主,江南与岭南两地之间联系密切;(2)吴文化为文化交流主体时,交流线路以内陆为主,两地联系相对疏离。由此观之,越文化应具有明显的海洋性特征,不仅在于其主导下的文化交流线路倾向于沿海,更在于这一沿海的线路串联起了东南沿海内部密切的文化交流,并构成了后者的重要内容。至于百越都城分布的海洋性特征[75]则可为这一越文化特性存在的又一明证。相比之下,吴文化则具有明显的陆地性特征,其主导下的文化交流更依赖于内陆交通,相应的东南沿海内部的文化联系也较疏离,而第二阶段大量中原文化及楚文化因素在吴地的出现则进一步表明,吴文化更重视与内陆文明而非东南沿海的文化与社会沟通。事实上自西周以来,吴文化与外界文化交流的重心便是如此。较之越文化,吴文化与内陆文明的联系时间更早,持续时间更长,联系也更加密切。从这一点来看,越文化或者说东南沿海“自交阯至会稽”的广义越文化与吴文化可以说是分别面向海洋与面向陆地的两个世界。或许也正是这种文化与社会特性的差异导致了二者于两次统一之间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图景[76]及其融入“中华一体”进程的先后与方式之别。
五、结语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基本明晰了两周时期“江南—岭南”文化交流各阶段的主要线路,其大致呈现出“东南沿海—内陆赣江流域—东南沿海”的循环往复的态势,而这一变动的出现不仅是江南地区文化交流主体空间位移的客观要求,更是越、吴分别面向海洋与面向陆地的文化与社会特性所深刻影响的产物,并直接导致了东南沿海内部文化联系密切程度的起伏与反复。
这种海洋性特征只是作为边疆的东南沿海有别于吴、楚、中原的一个侧面,其具体的文化与社会内涵复杂而独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形成恰是中原与边疆长期互动的结果,对于边疆本身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在这一长期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不同内涵,也有助于在不同地区的对比中更好地理解作为这一文明核心的中原地区文化与社会传统的形成过程及其特质。更重要的是,边疆的存在为理解中国国家与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视野与更加宏大的历史背景。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或许只有伴随着边疆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才能最终明了究竟何以中国。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周广明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