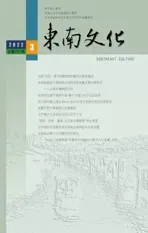安徽金寨斑竹园出土青铜器年代及相关问题
2022-07-06朱华东
朱华东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9)
内容提要:金寨斑竹园组铜器由爵、斝、尊各1件组成,年代可定在西周早期。其中斝、尊有殷墟晚期风格,爵则为西周式样,其埋藏性质属于山地模式,是大别山区迄今出土的唯一青铜器组群,也是江淮地区西周铜器编年的重要一环。该组铜器所代表的人群或许是受外部势力侵扰而逃避于此的某支族群。
金寨斑竹园组青铜器出土于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斑竹园镇太平山村汪下湾遗址(现属吴家店镇),1984年当地村民在此处取土时发现,共计3件,爵、斝、尊各1件,现收藏于金寨县文物管理所。过往对此组器物的著录并不完备,对其年代认识也未达成一致[1]。由于重要信息的缺失和资料的碎片化,学界对此组铜器的忽视也成为了必然。鉴于此,本文将完整介绍该组铜器信息,另拟就其具体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作初步分析。
一、器物介绍
父戊爵,金寨0023,通高22.5、流至尾长19.3、柱高4.8、腹部最大径6.6、腹深8.2、足高11、鋬内最大径3.2厘米。前流后尾,整器向尾侧倾斜明显。流尾上翘明显,流槽宽阔且较深。椭方形菌形柱较高,位于流折交接处偏后方。腹部瘦长,呈卵形,圜底,下接三扁足。三足外撇,截面扁阔,呈刀形(图一︰1)。腹部一侧设半环形鋬,并与一足对应,鋬首呈牛首状,鋬内对应腹壁铸阴文二字“父戊”(图二︰2)。爵腹装饰花纹,共分3组,并以凸弦纹为界栏,上下端各饰一周连珠纹,中部为主纹饰,其内纹饰以大小不一的雷纹填充,并围绕两处对应的乳丁状目纹分布,以象征兽面纹(图二︰1)。流下方的腹壁纹饰磨损明显,表明该器为实用器,且被长期使用过。整器无明显铸痕,器底和三足可见细长的丝状磨痕,可能为铸后磋磨所留痕迹(封二︰1—3)。

图一//斑竹园出土青铜器
父乙斝,金寨0026,残高15.5、腹部最大径13.9、颈径10.5、鋬内最大径6.8、弧裆高5.7、裆径8.5厘米。口沿出土时缺失,后经简单修复。器型属于连裆鬲形斝,其口沿微外侈,并向下斜收,颈部较短,袋足式腹部圆鼓且较深,下接圆柱状短足(图一︰2)。整器较光素,仅在鋬下的口沿处装饰两道凸弦纹。鋬较宽大,首部装饰牛头状兽面,鋬对应腹壁有阴文“父乙”二字(图二︰3)。三角形底范痕清晰,并延伸至三足内侧。外底中央可见补痕一处,方形,灰绿色锈(封二︰4)。
兽面纹尊,金寨0025,通高26.8、口径21.1、底径14.5、腹部最大径11.6、腹深8.1厘米。圈足和口沿出土时残损,后经简单修复。方唇、侈口,口沿直径为整器最宽处。长颈微束,圆鼓腹,下接较高的圈足,底部折沿较高(图一︰3)。纹饰以腹部为中心布局,腹部上下各饰两周细凸弦纹,腹部纹饰为独立的兽面纹造型,共两组,嘴角内卷,呈微浮雕状,空白处则以细雷纹填充。在其身侧各饰一只鸟纹,花朵状冠,鸟首向外,并以兽面纹为中心呈轴对称状分布(图二︰4)。颈部上端可见数处方形金属芯撑。范线被打磨干净,大致可知分范处位于两组鸟纹之间。底范与圈足范结合处的纰缝被保留(封二︰5)。

图二//斑竹园铜器拓片及摹绘
这3件铜器中,尊、爵铜质相近,色泽偏墨绿,纹饰精致而清晰,器表被打磨得极为精细,光泽感较强,也无明显铜锈。而斝的制作相对粗糙,铜质与前者有一定区别,纹饰含糊不清,器表较粗糙。
二、年代及文化属性
3件铜器的器形和纹饰可为进一步探索其年代提供依据。父戊爵的流槽宽大,上扬角度较大,其卵形腹和刀片状足等特征最早出现在商末的爵上,这些特征在西周时期更常见。菌状柱的位置已明显从流折交接处向口沿处偏移,也属于西周铜爵常见特点。此爵造型可与陕西宝鸡竹园沟M4出土的禾子父癸爵[2]相比。朱凤瀚将此类卵形爵定在西周早期(原文DeⅢ式)[3]。腹部所饰兽面纹以雷纹构图,仅有一对兽目,其图像可与西周早期的父乙方罍颈部纹饰对比[4]。而以连珠纹作界栏的设计,在商末周初也时常出现,如宝鸡石鼓山M4[5]出土的兽面纹尊的上腹部。在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偏晚的M111[6]出土铜器装饰上,此类简化体兽目纹出现的比例也不低。
父乙斝的特征也较鲜明,根据岳洪彬的研究[7],这种鬲形斝出现在殷墟三期晚段,至四期时开始流行,成为此期可见斝的唯一类型,并沿用至西周早期,但总体数量较前段明显减少。甘肃灵台白草坡M1[8]出土的斝可与之比对,该器素面,颈部两周弦纹,鋬内腹壁有铭文,这些特征均与斑竹园斝类似。白草坡M1属于西周成康时期。
兽面纹尊属于觚形尊式样,或被称之为“筒形尊”。此型尊最早见于殷墟三期早段,第四期常见,至西周早期则更为普遍,并使用至西周中期前段[9]。王世民等将其分为两型[10],斑竹园尊属于其中的圆体无扉棱尊(Ⅱ型),与其相似的有宝鸡竹园沟西周康昭时期M8[11]出土的鸟纹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早期史尊[12]在造型和纹饰上均与斑竹园尊可比对。就所饰兽面纹而言,斑竹园尊兽面纹与陈公柔[13]所分的Ⅰ3式独立兽面纹大致相似,最早出现在殷墟二期,在西周早期仍流行。该器的鸟纹则属于陈公柔所分的小鸟纹(Ⅰ9式)[14],鸟身竖立,对称分布在兽面纹两侧。斑竹园尊所饰鸟纹为短尾鸟,花朵状冠直立,而非常见的呈飘举状花冠的长尾鸟纹。与此相似的纹样,参考陈公柔的分类,属于西周成康时期。
从3件铜器的造型、纹饰看,爵为西周早期新见式样,斝和尊的造型则沿用殷墟晚期式样,变化不大。爵、尊纹饰总体与殷墟晚期相似,但又有所变异,属于西周早期风格。从氧化色泽和做工层面看,爵、尊色泽相近,均呈墨绿色,做工精致,与斝反差较强烈。推测前二器铜器合金成份及铜料有共同来源,且是在相隔不长的时间内利用同一批铜料铸造成形的。斝可能为仿制品,由于该器底部存在修补疤痕,属于日用器的可能较大,其外表泛黑的氧化层可能与埋藏环境有关。由于爵、斝上均可见明显的使用或修补痕迹,尤其是爵纹饰的磨损痕,说明该器物使用过较长时间。由上分析,可将这批器物的制作年代定为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由于几件铜器实际使用时间较长,其埋藏时间也有可能会晚至西周中期。
三、相关问题
斑竹园组铜器相对年代的判定为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打开了空间。首先是相关地域内商至西周的青铜器分期问题。就目前材料和认知而言,江淮乃至淮河以北沿岸地区该段时期铜器发展的时代序列并不完备,仍有一定缺环。现有出土材料中,商代早中期青铜器有一定数量,且分布相对集中,主要存在于江淮中西部地区,沿淮以北也有个别地点。至殷墟三期后,相关材料的分布范围更加广泛,除淮河沿岸的寿县及环巢湖一带的肥西、舒城等地外,皖西南地区的宿松、望江、岳西等地也有零星出土。目前江淮地区西周铜器的断代尚不完善,主要原因是能明确判断为西周早期的铜器较少,绝大多数属于西周晚期。如与中原地区及周边区域相比,关于沿淮及江淮地区青铜器的年代认识仍有不少疑问。该区域的青铜器在商晚期突然增多,至西周早中期又急剧萎缩,至西周晚期方才有较广分布。众所周知,作为礼制的青铜器,代表的是一种具有引领效力的先进文化,其传播的力度、广度以及他者的接受度已非其他材质器物可比拟。江淮地区与中原毗邻,交通便捷,文化往来频繁,该区域的青铜文明出现较大跨度断层的可能性相对较低,而在西周早期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转折时段,相应时段青铜器数量如此之少,着实让人难以理解。
究其缘由,相关器物出土偏少或许是一方面,但断代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也不容忽视。上述分析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商、西周铜器分期的断层,其中普遍缺少西周早期铜器的衔接。诚然,商末周初铜器的准确断代并非易事,西周早期各地沿用乃至仿制商式铜器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给断代造成了较多困扰。这一时期安徽境内的青铜器也有类似问题,一些时代归类模棱两可的铜器基本被主观地拖进了商代的编年范畴,人为地造成了江淮地区商末铜器数量的堆积,以及西周铜器分期头轻脚重的局面。事实上,安徽淮河北岸和江淮地区一批众所周知的商代铜器,如仔细辨识,属于西周早期的其实并不在少数。
先看沿淮北岸。该区域殷墟晚期的青铜器材料集中出土于淮河干流沿岸的安徽颍上县境内,有郑家湾、王岗、赵集等地点[15],另有几件拣选器可能也出自上述区域,这批铜器过去一直被视作殷商时期器物。但笔者检视过沿淮各地收集的相应时期的铜器,发现有相当比例的器物已具有明显的宗周风格。仅就颍上出土器而言,郑家湾出土的1组铜器较典型,所见铜卣提梁两侧的兽头已为羊首状,羊首或兔首装饰是西周早期的卣的特征,而殷商时常以龙首装饰或仅以环钮衔接提梁。该组铜器中也存在尊卣配对形式,被视为西周时期常见的组合形态[16]。赵集王拐村也有一批“商器”出土,其中的车舆饰(原报告定为“车軎”)特征最鲜明,与张家坡西周墓地[17]出土的“栏饰”一致。上述颍上铜器年代至少可断在西周成康时期。而沿淮地区零星出土或拣选的晚商铜器中,能明辨为西周时期的可以举出更多的例证。
再看沿江北岸一线。安徽太湖、潜山、东至、枞阳等皖西南地区也存在较多西周早期铜器。如潜山彰法山遗址[18],该地出土的兽面纹尊在器型和纹饰上皆与斑竹园尊相同,同出的弦纹爵[19],也属典型的西周早期式样,色泽也与斑竹园爵相仿。长江流域出现的悬铃铜器和甬钟似可作为标准的西周铜器元素或器类。在铜器底部悬挂小铃铛的现象始见于殷商时期,但数量少,出土器类有限(以豆、觚等为主),基本位于陕晋高原地区。西周早期,悬铃铜器数量激增,出土地多位于宗周及其周边,器类也以带有高方座(圈足)的簋、罍等高大型器为主[20]。枞阳汤家墩遗址出土过1件悬铃方彝[21],李学勤先生曾指出该器年代属于西周初期[22]。甬钟始见于西周早期,江淮中西部地区西周甬钟出土数量较丰富,其年代可见明显的由沿江向北渐晚的现象[23]。太湖界岭出土的1件甬钟[24],属于细乳钉阳纹界格钟,为甬钟早期形制,属西周早期偏晚,是这批甬钟之中最早的1件,而江淮地区中西部甬钟则属于西周中晚期风格。
最后看江淮中西部区域。该区域出土过少量殷墟晚期铜器,以爵、觚、戈等器为主,分布在巢湖以西的肥西、舒城、庐江等县,但器类单一且组群关系较零散,也缺少明显可辨的西周早期器类。零散出土的,具有西周早期式样的有2件:其一为巢湖峏山出土的龙首钮盖盉[25],长颈椭圆腹三足;其二为庐江金牛出土的1件刀形足爵[26],造型与斑竹园爵相似,腹部饰分解式兽面纹,无铭文。
由上可见至少在西周早期,周文化已进入江淮地区,其输入路径客观上存在南北两条。北线利用淮河向南传播,目前仅有颍上一个点存在,如果结合淮河上游的河南信阳浉河港[27]以及大别山以西的湖北随州叶家山等地出土的西周早期铜器来看,宗周势力或许首先抵达随枣走廊一带,向东则利用淮河上游的支流进入大别山东侧的淮河干流。南线则通过随枣走廊抵达长江中游,并顺江东下,至太湖、潜山、东至、枞阳等沿江一线,继而转折北上,并向江淮中、西部传播。这种现象通过若干青铜器类可以管窥,如太湖界岭钟与随州叶家山M111出土乳钉纹钟一致,汤家墩方彝底座内的悬铃现象在叶家山墓地高频出现[28]。从典型周器的分布来看,南线的传播路径似乎更明显。笔者也认为上述三个区域尤其是安徽沿淮和沿江两个区域内所见商末风格的青铜器,与宗周势力经略江淮有关,有相当比例铜器的埋藏年代极有可能已经进入了西周早期。
其次是斑竹园铜器存在于山地的原因。该出土地点被命名为“汪下湾遗址”(图三),位于金寨县西南,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该地处在一条东西分布的狭长山谷地带之中,是整个大别山较为特殊的地带。历史上此地便设有关隘——长岭关,以管理商贸交通。斑竹园铜器的主人缘何生存于此地,也耐人寻味。人类学的相关理论认为[29],生活在山前平原的“低地”族群与“山地”族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山前平原地区的部分居民为获取相对的自由和安全,逃至山区生活,并重构社会形态,以适应山区的流动性生活。山区地貌所形成的“地形阻力”(friction of terrain)和“距离阻力”(friction of distance)也为新的生存空间提供了安全的庇护。大别山东麓以下“低地”面积广泛,当地称之为“田畈”。如果没有外界的驱动力,很难想象至迟在西周早期会有一支族群放弃山下“低地”的优越生活,转而选择“山地”的生活。至于这支族群的归属,目前仅靠现有的3件青铜器,还不足以提供确证。

图三//斑竹园铜器出土地点示意图
笔者认为一种可能为淮河以南的淮夷。淮夷族群的典型陶器有敛口钵、曲柄盉、折肩鬲等,主要分布于江淮地区中西部[30]。大别山区域内调查发现的商周遗存数量尽管相当有限,不过东距汪下湾遗址直线距离不过20余千米的金寨双河镇,曾出土过1件曲柄陶盉[31],属于典型的淮夷式风格。该盉上部的钵口内敛,锥形足,可与霍邱堰台1期陶盉[32]相比,相当于西周早期后段至西周中期前段。而江淮地区现有的曲柄陶盉出土资料也存在一条自沿淮向南逐渐传播的轨迹[33]。同时文献资料也有不少关于西周时期淮夷的生存受到西周势力挤压的史实,如西周早中期时,沿淮平原地区的土著与姬周的关系并不稳固,“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史记·鲁周公世家》)。不过属于南迁的殷遗民的可能也不能轻易排除,西周初年微子启受封于宋,随之同行的殷遗民不在少数,其活动范围已至淮河流域。而顺着淮河的主要支流,如颍河、涡河等则很容易顺河抵达淮河干流,并可沿史河、淠河等南岸支流到达大别山东侧山麓。
综上所述,斑竹园组铜器年代属于西周早期,无论在器形、年代上还是地域分布上均是安徽江淮地区难得一见的实物资料。器形上,鬲式斝为安徽唯一出土器,该组铜器在年代上进一步丰富了江淮地区西周青铜器编年,并可与淮河和长江干流沿岸所见西周早期铜器串联起来;地域分布上看,该遗址是淮河以南地域少见的山地埋藏模式。该组铜器所对应的族群可能是受到外部政治压力,从淮河南岸的平原地区辗转迁徙至此的一支群体。
(附记:本文资料的收集得到宫希成先生和金寨县文物管理所何辉先生的帮助,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