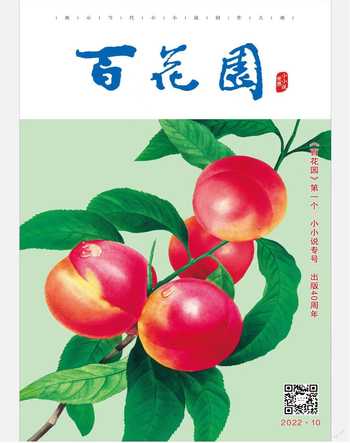大写家
2022-07-05赵长春
赵长春

钱瑞峰好写。
墙上写,地上写,沙上写,树叶子上写。锄把儿上写“钱氏瑞峰之锄”。所用的毛笔,也在笔管上刻着“钱氏瑞峰之笔”。后来,学了普通话的小孩子们拿着他的笔一个劲儿地念诵,大人们笑,他就改成“钱氏瑞峰之用”。
钱瑞峰好写,在于他写得好,至少,是袁店河上下字能拿得出手的为数不多的人。大字,不好写,在墙上,如簸箕,钱瑞峰能驾驭。站在梯子上,钱瑞峰挥着大扫帚,在洋铁桶里一蘸,稍一顿,趁着墨汁不滴,唰唰唰——“人有多大胆”,飞龙走蛇,气势磅礴。墨汁很简单,浓石灰,和了袁店河中有黏性的白泥,写上去,不滞不淋;再挪一下梯子,再一蘸,再一顿,一声吼:“地有多大产!”后面的感叹号,像个粗墩墩的树桩,尾部收了一下,又放大,圆点儿实实在在。
那些年头,钱瑞峰有干不完的活儿。上山挖梯田,红旗招展。钱瑞峰不用下大力,指挥着人在他划定的框框里填石头——罗汉山上少有的白青石,白中泛青,青中泛白,与框框外的黄土、青草、树木相比,很显眼。框框很大,人们起初看不出来个啥。一天,两天……半月后,那字就显出来了——“农业学大寨!”每个字有二层楼高,就在面向公路的山坡上,是一景。多年以后,封山育林,用这几个字的石料,竟盖了一溜儿的护林房。钱瑞峰很心疼:“唉,你们不懂啊,这是文物啊!实体文物,不能拆的。”人们不信,等信了,晚了。
钱瑞峰写字,没有人教,就是自学,自己琢磨。《人民画报》《人民日报》就在生产队的广播室里,他总是去看,琢磨上面的书法作品,按照报刊上的样子划拉。有一回,他划拉“毛主席萬岁”那几个字,划呀划呀,硬是将画报上伟人的脸磨出了一个小洞。好在妇联主任发现了,将画报一收,让他赶紧走了,就将画报放在桌子一角。第二天,队长发现了,要追查,谁都说不知道。
妇联主任对钱瑞峰好,因此,钱瑞峰可以到生产队的广播室里看报。一些旧报刊上的书法作品,钱瑞峰就剪贴起来,放在《毛泽东选集》里,厚厚的。晚上睡觉时,还要比画,拿指头在腰腹上的被子上画。日子长了,也画出来个洞洞。晒被子时,人笑。他问:“笑啥?”人们说:“你的劲儿真大……”
大家就都笑起来,钱瑞峰一脸茫然。妇联主任心里叹了口气。
钱瑞峰喜欢上山。罗汉山、丰山上各有一个庙:汉山寺、丰山寺。因为“破四旧”,寺里早已没有了香火,一片荒草,卧着被砸倒的各色石碑,碑上有真、草、隶、篆的字。他就看,蹲着,趴着,弯腰,侧身,不觉得累。不能耽误生产,他就趁晌午头儿,趁大清早,拿了馍,提一瓦罐水上山。渴了,饿了,就地解决。他带着纸、笔,慢慢地描,慢慢地画。有天,队长带着俩民兵突然到了他身后,长枪指着他。他招招手:“队长,你看这个‘寿字,多好!”
队长不耐烦:“老子以为你在找宝呢!你老祖爷没有给你留下藏宝图?”
钱瑞峰就不再吭声,把那几张纸卷好,放进“为人民服务”的黄挎包里,顺着他踩出来的小道,下山,一路心想:老祖爷呀,我知道你建寺所留下的宝了,就是这些碑刻——历朝历代的字呀!
钱瑞峰的祖上做过数省巡抚,后来回到袁店河,在罗汉山和丰山上建寺,把在各地搜罗的石碑运来,镶嵌在庙基、寺墙上,立在寺院里,各形成了一处很好的碑廊……
有些日子,村里不需要钱瑞峰的字了,他就守在邮局,免费代写书信——毛笔小楷,竖行,很古雅。过了些日子,人家不让他写了,说:“竖行,看着太累,写得又太古。”钱瑞峰长叹一声。
钱瑞峰还好写各种文章,小说、诗歌、散文、评论,都写,小楷字看起来很舒服。他只管写,写好了,就存起来,标上年月日、天气、地点,很清楚。只是很少发表。天天写,月月写,年年写,每年总是一大包,就放在自己屋里的床下、梁头。有一天,妇联主任来他家,要给他收拾一下屋子。他赶紧拦住了:“你别动!我的东西我知道在哪里……”
迟疑了一下,人家走了,汪着泪。然后,钱瑞峰铺纸,润笔,闭目,流泪,摇头,写下一个字:爱。又写一个:爱;再写一个:爱;再写一个:爱;再写一个:爱……写了大半夜!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