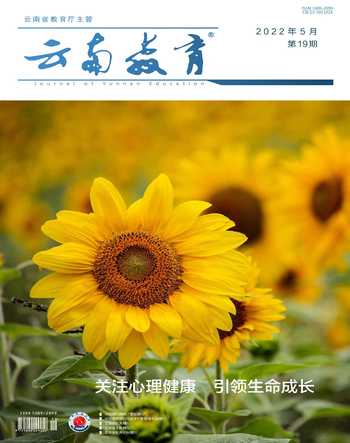文脉流长厚乡梓
2022-07-05北雁
北雁

我母亲出生在一个叫大果的白族村子,多年后她被嫁到大果村往南大约一公里的小果村,再之后就生了我。然而我的童年时光,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因为我始终觉得母亲的故乡大果,不仅面积更大、人口更多,历史人文也更为悠远,在古迹斑斑的村落深处,也许还深藏着远比我们小果村更为丰厚的秘密。
那时我的外公尚还健在,被母亲带一个口信,就在村口的牌坊下等我。“牌坊下”是个地名,事实上我从未见过这里有什么牌坊,但大人却告诉我说大果村口的确有过一座石牌坊,在建筑工艺尚不发达的年代,的确有着一种气宇轩昂的气度。说起上面的刻绘和文字,就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绝!
长大以后我外出求学,终于见过许多更高更大的牌坊,同时也深深地知道,牌坊是中华特色建筑文化之一,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也是祠堂的附属建筑物,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兼有祭祖的功能。
大果和小果所在的老茈碧坝子,依山傍水,风光秀丽,前有洱海之源茈碧湖如同明珠闪耀,后有罗坪山气势逶迤,同时又因其丰富的物产,自古就被世人颂以“沃野平畴”“稻壤花村”的美誉。加之民风淳厚、文脉绵长,实在算得上滇西高原上一块地灵人杰、鸾翔凤集的风水宝地。
事实上大果村就是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村里的确也有一座家族祠堂,然而在当时,它却被改造为村里的小学,作为整个行政村的中心完小,记得每到学年末,我们都会被老师带到这里进行期末考试,旧意斑驳的格子门窗、粗壮的梁柱、六角形地砖,如同时间的烙印,一直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外公叫杨鹏振,是一个有着30多年教龄的乡村教师,所以他有足够的耐心为我讲述那些流传在乡间的故事。关于大果村的故事,当然就是从那座早已不见踪影的石牌坊和祠堂说起的。我方始知道,后来被改为大果小学的马家祠堂中,曾走出名振三迤的马氏“一门三将”,曾在抗日战争中数挫日寇,抗击外侮,令敌胆寒。更重要的是,其中还走出了一位被季羡林先生颂之为“云南学界领袖群伦”的马曜先生。
关于先生的介绍,搜狗百科里是这样说的:“马曜(1911年10月11日-2006年2月6日),云南洱源县人,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现代教育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诗人。一生著作颇丰,代表作主要有《云南古代史》《白族简史》《白族异源同流说》《孔子评论》等。2006年2月6日逝世,享年94岁。”
作为早期的共产党员,并为云南和平解放作出较大贡献的马曜先生,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后孜孜不倦地投入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历史与民族学研究,可谓功勋卓著、誉满全国。文脉流长厚乡梓,在家乡人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种昭示和启迪,不断影响着后学子弟。
我外公说,马曜先生温文尔雅,为人亲和,而他和我们家也颇有渊源。早年家贫,外公就曾在马家门下的店铺做过学徒,后来又曾在马家祠堂做过短暂的零工。但马曜先生见他天资聪颖,又谦虚谨慎,为人正直,便一直鼓励他读书,后来我外公从洱源县初级中学就走上教师岗位,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吸收成为共和国第一代人民教师,36年勤勤恳恳执教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学校,这与马曜先生对他的鼓励、帮助和培养分不开干系。很多年后,马曜先生回乡,还曾为我外公写过一幅字。马曜先生的书法,颇具金石之气,正如同他一辈子的刚直性格,被我外公当作座右铭,一辈子珍藏在身边。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大果村文脉不迭,人才辈出,至今已培养出近百名大学生。其中,备受马曜先生称道的,差不多就是我的大舅杨荣昌了。那时,我大舅刚初中毕业,就因为“文化大革命”导致学业荒弃,作为知识青年回乡接受再教育,之后便在大果小學代课。然而他却凭借自己的聪颖明慧和务实笃学,考上大理师范民代班转为公办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云南民族学院,成了全县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2011年退休。
外公告诉我,大舅上大学时,正是马曜先生担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他从而可以近距离接受一代学林大儒的点拨和诲导。而马曜先生对他这位小乡党也极是看重,多年后,我大舅杨荣昌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成为一位成果喜人的演讲家、评论家、教育家和作家,先后被北京大学等17所国内著名大学和人民日报新闻培训中心等多家机构聘请为客座教授,毕生公开演讲5 000余场,被列入“云南高校四大铁嘴”和“云南四大演讲家”,并且是“四大铁嘴”中唯一的云南本籍人和少数民族学者;由他参与合著、编写、主编或专著的著作共出版29种,并用15个笔名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论报》以及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论坛》等国内100多家报刊发表各类文章600多篇,逾200万字……确切地说,他一生成果的取得,与马曜先生一直的关怀和培养,也分不开关系。
而我外公和大舅,一直都对马曜先生备为尊重。1996年,云南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马曜先生从事创作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书,其中收录了一篇由我大舅撰写的文章《学林巨松——白族学者马曜素描》,他认为马曜先生是诗人,“少作已追二李”,而一本《茈湖精舍诗初集》格律谨严、对仗工整、意境高远,博得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罗庸、钱基博、王灿、刘文典、阎毅任、徐嘉瑞、季羡林等大家的极高评价;他认为马曜先生是历史学家,对先秦史和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卓有建树;他认为马曜先生是民族学家,从1951年起,便经常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并适时予以理论总结,其成果有的见之于著作,有的被云南省委采纳而成为拟定具体政策的直接理论依据;他认为马曜先生是学术活动家,众多学术成果,令人瞻仰;他认为马曜先生是教育家,系列教育理论和教育成果,令人叹服。同时在他研究的成果里,有一篇《干老枝丰屹学林——马曜和他的民族学研究管窥》,从马曜先生对云南民族史的系统研究、对民族学理论的真知灼见、民族政策中的睿目独见三个方面,浅述马曜先生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后来这两篇文章,又都被收入他的综合文集《茈湖文心》第2卷中,字字句句,表达了他对恩师的一片敬重之情。
2006年2月6日,马曜先生去世后,亲属遵其遗嘱,将其骨灰葬回老家大果村马氏坟山。彼时,我舅杨荣昌亦在病中,但惊闻噩耗,却依旧拖着病体随同马家亲属一起回乡,并亲自来到马家坟山痛哭一场后,将恩师骨灰安葬。出于马曜先生对他才学的赏识和认可,先生的墓志铭,也是我舅写的,在结尾处,他用一首诗这样赞道:“道德文章第一流,寿高人伟垂千秋。祖茔留迹神长在,松青柏翠云悠悠。”
在马曜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我收到了马曜先生世侄马荣邦先生赠送的由他参与编辑的《学冠琼林》纪念文集一书,这时我的外公和我的大舅也都先后去世,一时感慨不已,写下这些纪念文字,一同缅怀这位令家乡父老为之骄傲的学界大师,同时也表达自己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