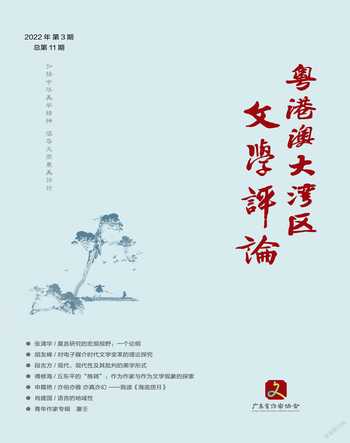多维视角下的现代城市问题
2022-06-30冯祉艾
冯祉艾
摘要:南翔短篇小说集《伯爵猫》,通过调节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来推动创作,加大了社会认知深度,透出一种学者或文人气质,内中的非文化优越感和非训诫说教方式,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普适情怀和人文关切。小说多以生活小事触发文学机杼,并能见微知著,揭示现代城市和人文情感的多个向度。就《伯爵猫》的文学表达来看,内在的很多因子,都隐约浮现出学者的态度、见识和关注重心,缘其在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方面,更推重价值判断,守住批判的立场,让人的世界,也有万灵万物加入,凸显了知识分子的善良与清趣。整体气质,除温暖柔和、深沉宽厚外,也有学者的刚直坦率与绝不敷衍。
关键词:生态;多维;城市;学者;困境
一、万物共生的观照与反思
南翔小说对动物有着特别的关注,乃至于不少短篇直接以动物命名,如《珊瑚裸尾鼠》《乌鸦》《果蝠》等。以此三篇为例,虽然它们都以具体的动物贯穿整篇,但在表达的侧重点上却颇有不同,最终都指向关于万物共生的生态反思。“世间万物”是一个宏大的命題,而“共生”则是相对带着科学和哲学意味的考量,关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乎自然命运与人类命运的羁绊与牵扯,其间包含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和积极思考的学者精神。
短篇小说《珊瑚裸尾鼠》在家庭关系的外壳之下,触及了对濒危和灭绝物种的关注与惋惜。事实上,其家庭情感的关系在触及这一观念时,已经不是简单的父子、母子、夫妻之类的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上升到自然生态与人类便利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肖医生和方设计师具有大多数环保主义者的普适共情能力,也不乏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主义在曹老师这类为人之妻的眼中,是可理解、可适当接受,但无法完全共情的。这与感性能力和济世情怀无关,家务事会将人浸泡在生活世俗的柴米油盐中,这些琐碎又无法被量化价值的繁杂之事,如同生存必需的束缚把人禁锢在所谓世俗的反复轮回里。故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巨大的现实挤压,理想主义的宣言多数只是无力的捶打,甚至是鼓吹,毕竟在琐事之中,“人类便利”相比“万物共生”,更能快速将人从烦琐的生存苦海中予以短暂解脱。
因而,也便造就了肖医生和曹老师婚姻问题的本质矛盾,亦是老生常谈的、类似“科技是把双刃剑”的两方阵营的交锋。双方的博弈最终落点于反思,在完善的解决方法尚未出现之前,所有对理想、理念、理论的追求都稍显无力。作者在《珊瑚裸尾鼠》的篇章中显然还是倾向“万物共生”这一和谐美好愿望的,在铺陈矛盾的基础上,给予“人类便利”以普世的理解,又赋予“万物共生”以深刻的意义。在末尾完成相对而言稍显无奈却也算和谐的注脚,以肖曹之子的梦魇作结,为珊瑚裸尾鼠举行的葬礼、“复活”的灭绝物种……不论是梦中所思,还是实际所为,皆是向着“万物共生”目标前进的助推力道,细弱而具有魔幻主义色彩,朴直却显出对人类现实处境的深刻反观与思考。其对自然生态损耗的深长惋叹,其犹如夜暗时分星星之火的这类小说叙事,取态积极,底色斑驳。这样的文学创作,足证其自身血脉就天然带着浓重的理想主义成分,它观照伦常、城市乃至万物今昔,不避山林川泽,但也实录桨声灯影。洞察幽微,作家会从具象着手绘出隐于层阁之内的文化图式,人和物以当下的面目出现,又对标历史,通过不同的形象塑造,还原人事的变化逻辑,复现一种正在被逐渐消解破坏、弃置遗忘的时空景观,像“一片灰白色的突兀的礁石”以及“海潮不断涌动的灰白之上”的“点点深绿”,像“与天际一色,浩瀚而庄严”的“湛蓝的大海”,像“雪白一团的仓鼠”,像“体形庞大且不寻常……有着古怪的、隆起的鼻子和棕红色的毛发”的“珊瑚裸尾鼠”。南翔目光所及,是“万物共生”的现世观照,也是更为宽阔的未来观照。作为生态小说,南翔的这个作品,可以确认其“创造性”系于濒危物种,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其对“人”的麻木不仁、鲜有行动或者恣意妄为所作反思。小说家可能并未特别举出病例,令警号长鸣,而是将“珊瑚裸尾鼠”(其实也就是明天的“万物”包括“人”)绝灭的事实沉痛摆在所有受众面前,这无疑是阒寂无声时突然爆发的尖利哨音。不外加任何装饰的这类哨音,也许正是最高等级的示警:它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那些消亡的“它们”的今天,就是“人”的明天。这种观照和反思,是更宽的双重或多维视角,是知识分子的,是现代的,也是文学的,当然同样是聚焦于历史的(一切成为过往的,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已绝灭的或正绝灭的,当然也在其中);而肖医生和方头“在礁石缝隙里”“戳”下的那块“白底之上镌刻着一行黑字”的石碑,石碑上格外刺眼的那行“黑字”:“珊瑚裸尾鼠发现与终焉之地(1845-2019)”,无疑是一种凭吊,但这样的凭吊,又何尝不是在凝眸现实!小说所具有的挽悼不舍意味和警示唤醒性质,恰恰集合了作家的反思批判和守护寄望:至深的痛切和仁厚。所有这些,既是多维视角,也是透彻悟解,是由哲学抽象、文学具象、历史成像与未来想象等攒积、聚变、爆燃而生成的有机体,是南翔筑垒于艺术理想之上的高壁缅然,也是让人经历“心灵转折”的“小于一”。
这种“小于一”,其能指与所指,紧贴亨利·列斐伏尔所勾勒的、和社会构成等相关的场域(有时候甚至会显示为空间形态):既取决于历史、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干预度,同时,它又和市井坊巷彼此形成符号性象征,各自对应文化、经济或社会情境,既呈整体性,又含独立性,为一个时代提供特殊的文本范式和话语系统。我们可以稍微逸出当前的设定,将目光从《珊瑚裸尾鼠》投射至整部《伯爵猫》,去追踪别的映像轮廓或图形细部,尤其是作为篇章基点的标志物。如此考察下来,我们几乎可以随处看到南翔作品中的这类“小于一”:“檀香插”“曹铁匠的小尖刀”“车前草”“玄凤”,甚至“苦櫧豆腐”和“伯爵猫”,其形其态,其旨其义,尽管各有其社会学、生物学或环境发生学特征,但它们作为逻辑自洽的小说行为体或意涵载体,语汇容有不同,但其传达的物质性或精神性脉动,本质上却根系相连。即如“鼠”字猥碎,却仍迸发出星火虽微、足以亮眼的光芒。
在短篇小说《乌鸦》中,乌鸦的存在则伴随着人的成长。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人的命运浮沉往往不由自主。乌鸦的出现是一个契机,在那个如同橡皮泥可以随时捏扁搓圆的年代,乌鸦在少年眼里象征着理性的智慧和自适的意志、自主的意识。在这个短篇中,乌鸦的形象显然超出了原型意义。我们不妨看看其具有人类文化学特征的小说构型:以体现“乌鸦反哺”的《慈乌夜啼》契合中国传统美德之孝道文化,又以日本乌鸦在马路上借车辆破核桃的细节实例,展现了人与动物共生的可能性;借写乌鸦之灵奇,道中心之期许,乌鸦来去、啄食等等意象,不完全是世间情景的精确再现,而是包孕了作家的观照与反思,南翔是在用文字构筑一条双向通道:他是在用高墙深禁,反衬绿篱、通途、远山和轻云,是在用拘囚做参照系,找出人的复归坐标。这样的观照、反思,已经比仅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要深刻得多。作家在这里,是要探寻文学的、心灵的至洁境域,觅得一条更开放、更包容、更温煦、更光明的去路,鼓舞自适之精神,宣言解放之新思。文中少年在智慧与仁德的修持中步步高升,从对乌鸦的态度推及对人类未来的展望,最后收束于小说的重峦高处:天罗地网的束缚于乌鸦及人都不美。万物首先得有灵魂无忧无虑、不受捆缚的飞翔,然后才有可以尽情尽兴的视觉展示,如此方能形成世界的多样性、多元化。《乌鸦》的人鸟对视与交流,实际上就是一种隐喻,万物都需要发生、成长、活动的空间,尘世的一切,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生命形态,都不能短其翅翎、绝其门径。举凡自然或人文结体,我们都必须善待。一句话,百鸟不能少和鸣,湍流不能少澹淡,只有守住“人”的底线,不断提升、不忘初衷、不断突破,才能脱离狭隘的偏安一隅,获得与天地并生的心灵辽阔和自由。82DEA8A6-0626-4ABC-B4C7-B38D0A864950
与《乌鸦》一样,短篇小说《果蝠》也有一个具特殊意义的时代背景——新冠疫情。自疫情发生以来,抗疫文学迅速成为此类书写的一个新的方向,《果蝠》采取的是科学启蒙小说的形式,不苛求纪实性与时效性,避开了抗疫文学的常用套路,选择并立足于一种富有浪漫气息的现实进向。在人物塑造方面,男女主人公分别作为生命科学和中文系的大学教师,在知识分子的层面凸显了“自然共生”的视角,理科和文科思维的交合,既有理性的解释,又有文艺的阐述,而果农则是从自然的角度传达出一种淳朴天然的归隐态度,三方结合,在疫情这一“灾难文学”的叙事中,融合了科学的理性观照和艺术的感性铺陈,在一众抗疫文学中脱颖而出,展现了独特的个性与风采。
疫情之下对蝙蝠这一物种的排斥,导致共同认知的分化、转移乃至倾侧,偏激情绪也因之涌浪高涨。但这种行为其实于事无补甚至有害,这是由于其忽视了疫情产生主要在人而非物种本身。人类的打扰才让宿主变成病毒传播链条,祸患确是源于病毒,然而,人的口腹之欲、享乐之举和任意所为,才是真正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那只黑手。人类必须清楚的一点是:自己的家园是地球,但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家园。人类科学的发展呈现善恶两面性,自然的进化固然也是好坏并存,在对自然的适应过程中,不同的物种都在选择和进化,人类成为地球最具智慧的生物,蝙蝠的身体也在上天入地中百毒不侵,病毒会存在,是自然本身的附带属性。至于其存在于何处,则是物种不同的进化选择的结果。仅就新冠病毒传播而言,“病毒”更像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假使人类行差踏错,只想着一味以继续破坏自然平衡的方式去回应自然所施以的惩罚,那就必定会得不偿失。
《果蝠》是跟心理意象、生命拷问有关的一类小说。疫情环境下,“果蝠”的授粉技能和物种身份之间的矛盾,提早浮出水面,并引发了“该不该”将其扑杀的讨论。而在这背后,实际上是更迫切的人与自然如何相容的问题。作品逐步揭示生态平衡与人类生活所具有的隐秘且内在的联系,传递出对于生命、生存、科学的关乎人文价值核心与族群审美品格的思考。这当然还是一种学者式的观照与自省。这种严肃中,间杂焦虑,对现代知识分子使命与担当的峻急呼唤,同样值得身处疫情中的每个人去正视。一如沈从文所言,作家就“应该像‘大司务那样,善于认识生活,明白极多”,南翔推出心理意象、进行生命拷问,其创作立场、情感建构,尤其是他在这个短篇中的价值呈现,显然与沈从文所说的精神指征是高度相关的。《果蝠》以更为文学的方式契合了生态发展和科学发展的时代精神,让读者对前沿性、现代性的思想导引,更加具体可感。
二、学者视角与民间维度
南翔书写所表现出的学者视角,不仅有对自然生态平衡的关注,还有对民间文化传承的凝视。其作品中所无法遮没的民间维度,又特别彰显了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系念。以《曹铁匠的小尖刀》为例,深圳来的学者教授孙老师带着两个学生做非虚构采集——“非非遗”写作,本身就带着学者独有的普适取值,而关注非非遗的民俗工艺,对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更广泛、全面的调查与研究,则是在致力于非遗文化保护。这当然是学者视角,也是民间维度。在对曹铁匠的采访中,作家不仅发现了其“干一行,爱一行”的工匠精神,还察见了普通人身上的某些文人特质。以真诚、爱意来塑造民间人物、展示民间景象,這样的小说,如果没有很深的民间认知、民间意识,是无法进入,更不可能去专题勾描的。我们可以据此做出一个判断:南翔的学者视角,和他作品中的民间维度,显然有着很深关联。《曹铁匠的小尖刀》中的“非非遗”笔墨,即为学者视角,叠加“非学者”的民间表达,故而它既相关知识精英的文化体认,又避免了过于精英化的疏离倾向。作品所展列的田野调查的元素,流露出的平凡淳朴的民间气质,恰好融合了学者视角与民间维度,这是南翔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从小说所涉的调查采访段落中可以看出,对于曹铁匠的传统民间技艺,曹铁匠本人,企业家吴天放,学者教授孙老师及他的两位学生,视角都有所不同。这种差异,由不同立场、不同身份、不同经历所造就。尽管视角不同,却不妨碍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点,即其寓意均形成了共轴——都成了庞大的时代背景的映射,一代人的聚散离合、骨血意气成为碑刻,镂镌于社会变迁的巨幅版面之上。《曹铁匠的小尖刀》的故事,当然不是惊心动魄的形制,它的高妙之处,在于不露声色,是把惯常职业,寂寞相守的场所,过气的手艺,多数人不以为意的泛黄记忆,用细节揉搓成的线绳串起、圈住,再行展开;是把人内心的嵯峨山势、翻滚波澜,通过凉热并现的抚触、晕染、打磨,有序推出。南翔的这种写法,非有学者视角与民间观照,非有丰富的文学实践,难以为之。准此,曹铁匠的形象,是特殊社会环境之下做散点观察的很好目标,更是作家追本溯源式的民间挖掘样本,是一种艺术铸炼,具有认识论价值,而且其意义是隐伏于故事深处的。曹铁匠的角色,无疑是南翔小说的一个文学贡献。在改革的年代,人们面临多种多样的选择,有人闷声做老本行,有人下海经商,有人潜心于研究终成学术中坚……在小说的语境中,不同选择引出不同境遇,两者并无好坏之分,各安生理,氛围积极。但时代并非只有春风风人,也有寒雨雨身:儿子的夭亡是曹铁匠淳朴平凡的一生中深埋于心底的一抹悲凉。这个小说不是专力于讲生死,作家写曹铁匠儿子的夭亡,或许只是要告诉读者,曹铁匠即使遭逢如此人生变故,心志也未能被夺,道途也未能被阻。那么,曹铁匠的“冥顽不化”得到了什么样的回馈呢?答案可能是,他一直在追寻父亲的足迹,以图固守父亲“全能铁匠”的尊严。小说人物对话的音频收放和行动交集的画幅翻卷,许多都带着怀旧性质。这里所讲的怀旧,不是复古,不是自失,而是前移,是文学的自适。从小说流转的苍翠里头,我们约略可以推测出作家的真实想定:社会身份的改易,从来都属于那些敢于在没有路的地方,辟出新路的人;生死是不可测的,富贵也不由人,但命运向好,却必须不懈爬坡,倾尽力气。在澎湃的时代浪潮中,什么样的人能伫立于浪头眺望,什么样的人会被掩埋在退潮后的沙土中,其实都是峥嵘平陆自有来处。或许不存在天生的悲剧性格,但在时势的推动下,不同性格必然会导致悲剧和遗憾的出现。曹铁匠如此,吴天放如此,别的人,也一样如此。回到曹铁匠的故事当中,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的变动不居,也非常真确地通过小说人物生活的升降沉浮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社会生活的走向,被作家捕捉住,最终都形于笔端。成为文学事件、文学现实、文学珠玉。比如曹铁匠那种民间工艺,因缺少研究和宣传,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技艺如此,人生亦然,人生无法完美,而人生总要向前,经南翔写成小说,也便由与世界的一般关联,实现了文学关联,由单一阐释获得了多维阐释,也获得了远胜于本体的价值体认。82DEA8A6-0626-4ABC-B4C7-B38D0A864950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南翔小说的学者视角,不是化外的独立产物,也不是冰河的早期孑遗,它是植根于人文沃壤当中的骆驼刺、白坚木,顽强不移地锁定于多维观照、多维书写乃至民间维度。
曹铁匠们出现在南翔笔下,成为“非非遗”的叙事对象,不可能是其近于巧合地自动走到作家视野中,一定是南翔经过凝望、甄别、选择、塑形的结果。这还是属于学者视角与民间维度的范畴。曹铁匠的故事如此,《回乡》中,广福的故事也如此,《疑心》中,大姨的故事还是如此——综观整部《伯爵猫》集子的各个篇什,其人物故事,莫不如此。
三、现代城市的情感困境
南翔是由内地调入深圳高校的人文知识分子,是学者作家。他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之际,直接到了这座辨识度极高的创新之城的文化教育现场,目睹作为改革开放突破口的深圳的雉羽鲜艳,亲见城市的日新月异、飞速发展(这种情形,成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许多感受是与众不同的。他的《伯爵猫·自序》,即以“大江茫茫去不还”为题,虽非言深圳的具体景象,却道出了他对所身处的世界(当然也包括他对所身处的城市)的立面认知。在时代的快速变迁中,大量的、丰富的信息涌入这座城市,也同时涌入人的大脑之中,因新旧观念的冲击而产生的大大小小的矛盾,让南翔对于现代城市的情感困境,有了更多的关注,也有更多的思考。
如果说现代城市的情感困境分很多种,那么夫妻关系是南翔小说中最为常见的。
所谓夫妻关系,短篇小说《檀香插》对此有过诠释,即是两个没有血缘的人结合,生产出与两人相关的一种血缘关系,这两个人也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清晰又朦胧、坚韧又脆弱的关系。
清晰又朦胧,坚韧又脆弱,两种反义词汇的交融可见关系性质之复杂。凭着一腔深爱维系这段关系,彼此心理相容的接受度又影响到此一关系的正负取值,宽则悦,窄则忧,宽窄的内在反映是感情的绷紧或松弛。太绷紧了,激情过剩而显得轻浅且无余力,但太松弛了,不免趋于平淡,让人感叹那逐渐消散的热情如白开水般食之无味,虽为生活必需,却少色彩。
夫妻关系的婚姻情感在南翔小说中总是承载着一份更深的蕴含。小说《车前草》,也写了夫妻关系,不过,小说中的人物,由于与生俱来的性格差异和观念的不同,令夫妻在沟通交流时难以互相理解,更为残酷的是,因为与生俱来,所以很难通过后天的习得与顿悟开窍,这是婚姻的内伤,是其隐于背后的悲哀,也是人与人关系中恍如高崖般的隔断,中藏许多无奈。
当然,《车前草》中的夫妻关系并非该文描写的主要部分,但其中婚姻的裂缝不在于绝不可弥合,不在于大起大落,不在于无法原谅,所有矛盾冲突,都源于毫厘微末,都是些小细节、小习惯上堆砌积累的瑕疵,细微之处的拦阻,其结果往往是引致逐渐坠入更为巨大的深渊。从“我在这世界里只看到你”的双宿双栖,到惟愿独自立于天之涯地之角的劳燕分飞,不起眼的位移叹息最后成了守与弃的决断沉吟。一个天长地久的神话,很可能没有结局,只待在时间最终流逝处,怅然相望,心事难道,呜呃霜晨:前方到底是生命的尽头,还是爱的尽头?这种小说处理,印证了该文表达的主题:人世间一些大小事情的决定与转圜,常常起于细微,放置在南翔短篇小说风格的整体语境中,则是见微知著。再打开《伯爵猫》的其他作品,《痛点》《选边》《凡·高和他哥》等等,相当部分都可以看到小说家的这种星斗微茫笔墨。这种烟草云林处的群山寂寥,正是出于作家的文学自觉。
再说夫妇情爱,还是短篇《珊瑚裸尾鼠》。这个小说对婚姻关系的描写篇幅更大,动荡更甚。值得一提的是,在該文中,妻子曹老师提出了“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舍弃一段不恰当的关系是一方的独立、解放与觉醒,但快速脱离之后的归宿竟也是茫然。而这种茫然是一种现实的困难,也是婚姻关系加速断裂之后形成的又一层挤压。
除去婚姻关系,家国情怀和故土情结也是在时代紧张中遗留的情感问题,南翔的短篇小说《回乡》以“回乡”为主题,既有台湾民胞回乡寻根,也有早年因遭遇不公终至离家的母亲对家乡的复杂情绪。其中无不涉及时代因素:国内动荡之后两岸的长期分离,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统驭下女儿所承受的亲情的隔阂,都是特殊时段所发悲声,也是情感的挽歌。
回乡是一个观察点。作家在这里又一次展现了学者视角和民间意识,当然,更吃重的是他更切近、更冷静地楔入放大了情感困局。这不仅是维系亲情的机会,也是能看清人情纠缠、人性弱点的节点。血缘维系的亲情遭长年离散,加上多种因素(同样函括政治)的掺杂其间,“回乡”成为更加复杂的情感表达。不同的人生际遇,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家庭位置,造就了不同的生活理念、态度、习惯、表征,家庭关系也因此变得游离。其中也有让人觉得动容的地方,像广福为父亲(“我”的大舅)用樟木板做“四脚枷凳”,像大舅妈利索地替大舅从一只银亮的小药盒里取出一粒药来,让大舅就着温水服下,像大舅于1984年、1985年先后三次托人将三笔港币从香港带回汨罗老家等等,这样的细节,是不会褪色的。而最令人动情之处,在于世俗对亲情的崩坏捆绑,依然抵不住血脉流淌的紧密维系。这样的血脉联系,似乎有种天生的黏合力跟感召力,即使小舅对大舅有各种各样功利性的索求,那种贴近和卑怯,那种指望与怨恨,都是贫瘠求生的结果。而且,即令兄弟在一些地方,互有不满,但在小舅与大舅的相处中,依然能看出在物质需要的表面之下,仍有一种精神需要和依赖,不论小舅行为举止中如何凸显势利的嘴脸,但终归还是在亲兄弟的联系上游走。在“海外关系”如悬于头顶之利剑的年代,所有的担惊受怕和自私索取,似乎都能诠释为一种人情之间的亏欠和弥补的交互,一种亲情上的难以割舍和温和的忍让。
小舅对大舅如此,母亲对小舅亦然,在对一方的弥补中,又免不了对另一方的亏欠,母亲对小舅行为的默认,让“我”对小舅一直啧有烦言,而大舅对表哥的弥补,却是以他另一个家的破裂为代价。在特殊的时代,造就了特殊的家庭关系;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孩子,在长期的贫困苦难之后,忽然获得以亲情温暖换取的大量物质补偿,并反而因为沉迷于物质执念而损耗了自身生命。总之,这类弥补与亏欠的难以平抑,也让抱着过头向往的小说角色,亲手制造了自身家庭支离破碎的悲剧;至于努力想要弥补的一方,也付出了远远超过当初预期的代价,情感上的渴求与心理上的间距,到末了,其矛盾也还无法消除。因长久缺席和带着牺牲性质的补偿,对付出者和被补偿者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
而究其根本,亲情关系转变为补偿关系是一个特殊时代所造成的,在荒唐的语境之下,人物的命运、情感、关系都蒙上了悲剧性的色彩。血缘的维系还在,可是家乡的味道却变了。短篇小说《回乡》以患病开篇,回乡为线,以望乡之诗作结:波澜一般漫涌过来的水流,涌动再涌动,坚定、无声而带着席卷一切的力量,渐渐掩盖了一切,带走了一切……
四、结语
南翔的短篇小说集《伯爵猫》契合时代记忆,引发精神共鸣,以学者的视角去观照当下,以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手抚摸现代情感,以理性的眼光凝视自然的凋敝与文化的式微,既有建构,又有解构,以知识分子的方式替文学发声,不管是温和还是尖锐,其小说,始终都集中于多维视角、人文观照,不离现代反思,不离民间立场。82DEA8A6-0626-4ABC-B4C7-B38D0A86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