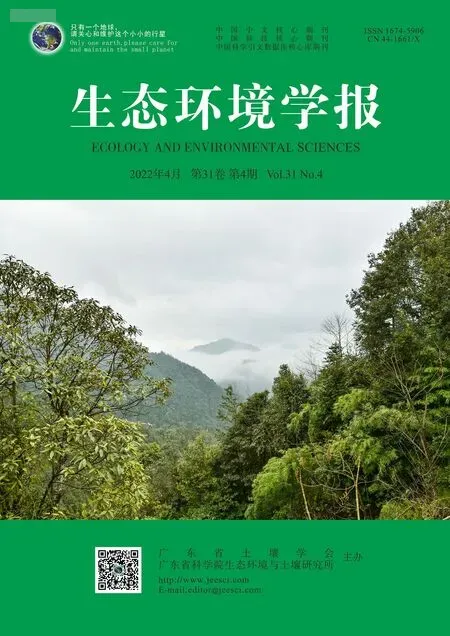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格局及重要生态廊道识别
2022-06-25韦家怡李铖吴志峰张莉吉冬青程炯
韦家怡 ,李铖*,吴志峰 ,张莉,吉冬青,程炯
1.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华南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广东省农业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650;3.自然资源部大湾区地理环境监测重点实验室,广东 深圳 518060;4.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458;5.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随着快速城市化的推进,大量自然景观被城市基础设施取代,引发了诸多环境问题,如生态系统受损、生物多样性下降、城市热岛效应等(Cao et al.,2021)。如何协调城市建设空间与生态空间的矛盾,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成为当下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生态安全格局,是针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在排除干扰的基础上,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完整性,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有效控制和持续改善的区域性空间格局(马克明等,2004)。生态安全格局作为国土空间三大战略格局之一,是缓解城市化发展与生态保护间矛盾的重要途经,对合理配置资源和保障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目前,生态安全格局识别方面已初步形成“生态源地-生态阻力面-生态廊道”的主流研究范式(Peng et al.,2019)。生态源地是促进生态过程的关键斑块(Peng et al.,2018a),可通过直接识别法和综合评价指标法识别。直接识别法,即直接选取关键生态要素或筛选地类识别源地,例如以自然保护区或大片生态用地作为源地(丁宇等,2019;马世发等,2021)。但是,这种方法忽略斑块自身生态环境质量,具有一定局限性。综合评价指标法,注重生态系统功能并将其量化,应用更加广泛(Peng et al.,2019)。例如,基于生态系统功能进行源地识别(毛诚瑞等,2020),或将生态系统功能与形态空间格局分析(Li et al.,2020)、人类生态需求(Jiang et al.,2021)、土地退化风险(Peng et al.,2018b)和生态敏感性评价(彭建等,2017a)等指标体系结合进行源地识别。通过综合评价指标法进行源地识别时,当前也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关注生态系统自身功能属性(吴茂全等,2019)。例如,基于生境质量、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系统功能(张剑波,2016;周汝波等,2020)识别源地。另一种,除了关注生态系统本身,还综合考虑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间的关系。因为生态源地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在进行源地识别时需要将其纳入考虑。例如,Jiang et al.(2021)耦合生态系统功能和人类生态需求,进行源地识别。生态敏感性能够反映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欧阳志云等,2000),需要与生态系统功能评价相结合进行源地的识别。陈德权等(2019)和王浩等(2021)选用植被覆盖度、高程、坡度、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壤侵蚀指标进行生态敏感性评价,完成广东省源地识别。王秀明等(2022)结合水土流失和石漠化敏感性,完成粤港澳地区源地识别。现有研究在高度城市化区域进行源地识别时,未考虑环境污染敏感性因子。
生态廊道是物质和能量在源地间流动的关键载体(Kang et al.,2021),是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廊道如“经络”、“骨架”般连接源地,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维系生态过程等功能。廊道保护与建设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受生态保护成本等因素制约,规划过程中不能对所有廊道采取相同措施。各廊道的位置和质量不同,其中重要生态廊道起着关键作用(Xiao et al.,2020)。因此,在识别生态安全格局基础上,应当进一步识别重要生态廊道。廊道识别方法包括经验判断法(官卫华等,2007)、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简称MCR模型)(Jiang et al.,2021)和电路理论(Huang et al.,2020)。其中,MCR模型因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可扩展性被广泛应用(Jiang et al.,2019)。但是,MCR模型识别廊道后,未能分析廊道属性特征,无法进一步表征廊道重要性。重力模型可有效表征廊道重要性(孔繁花等,2008)。但是,传统重力模型识别重要廊道时,未考虑生态斑块的自身功能和连通性(Xiao et al.,2020)。景观连通性对于廊道十分重要(Foltête,2019)。重力模型和连通性指数相结合是评价廊道重要性的有效方法(Xiao et al.,2020;古璠等,2017),但尚未得到广泛应用。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其历经多年高强度开发,面临水质下降(王金华等,2020)和大气污染(张宝春等,2011)等环境污染问题。在该地区开展生态安全格局识别,有助于促进粤、港、澳三地环境协同治理进程。虽然前人(如Jiang et al.,2021;周汝波等,2020)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安全格局识别,但是在评价体系中未纳入环境污染敏感性因子,对环境污染约束的考虑不足。识别重要生态廊道时,传统重力模型忽略了生态斑块的自身功能和连通性。鉴于此,本研究在前人基础上作出改进:(1)引入环境污染敏感性因子,辅助识别生态源地,并以自然保护区和港澳郊野公园重叠率验证结果;(2)基于修正重力模型,结合连通性指数,进一步识别重要生态廊道,以期为推进环境协调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粤港澳大湾区(21.33°—24.23°N,111.21°—115.25°E)位于中国华南地区珠江流域中下游,由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组成(图1)。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河网密布,北部区域多分布山地,植被种类丰富。南部沿海区域广泛分布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海岸带生态系统复杂,是动植物生物多样性集中的区域,拥有多处以保护阔叶林和野生动物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将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湾区作为发展战略定位之一。人口高度集聚、工业化发展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使得该地区面临水体、大气等环境污染问题。具体表现为: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放超出海域自净能力,珠江口海水水质常年处于劣四类(王金华等,2020);电力、陶瓷、钢铁和有色金属冶炼行业众多,相比国际湾区,PM2.5和 O3浓度较高(湛社霞,2018)。

图1 研究区位置图Figure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包括土地利用、道路、植被覆盖、土壤、高程、年均降雨、潜在蒸散发、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港澳郊野公园兴趣面(Area of Interest,AOI)、港澳工厂类别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PM2.5年均浓度、水环境与大气环境重点排污企业、夜间灯光以及部分现行国家标准相关信息等,数据来源及分辨率见表1。

表1 数据来源Table 1 Data source
2 研究方法
2.1 生态源地识别
2.1.1 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
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的代表性模型包括InVEST模型、ARIES模型和SolVES模型,其中InVEST模型的开发程度、操作性和科学合理性较成熟,被广泛应用(李敏,2016,王耕等,2021)。因此,本研究选取InVEST模型进行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参考《广东省主体功能区划》、《广东省生态红线划定指南》及前人研究(陈德权等,2019;王浩等,2021),结合研究区自然禀赋,选取生境质量(朱杰等,2020)、碳储量(Sun et al.,2017;Hu et al.,2020)、土壤保持(潘美慧等,2010;张海波,2014)和水源涵养(Bai et al.,2019)4种指标进行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
2.1.2 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价
生态系统敏感性指生态系统遭受外界干扰时,引发环境问题的难易程度。当前研究仍处发展阶段,指标体系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吴献文等,2021)。评价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指标法,多数研究进行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价时,较少考虑生态环境问题(康秀亮等,2007)。因此,本研究综合区域实际环境问题,选取生境、水、土壤和大气四方面(表2),利用综合指标法进行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价:(1)区域内经济活动频繁,生态用地流失严重,以土地利用类型、植被覆盖表征生境敏感性;(2)以距水体距离和距水环境重点排污企业距离,表征水环境敏感性;(3)基于土壤侵蚀量,表征土壤环境敏感性;(4)以 PM2.5年均浓度值和距大气环境重点排污企业距离,参考环境空气敏感区功能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6)分类标准,进行大气环境敏感性分级。国家标准行业卫生防护距离范围为50—4400 m(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3),因此选择4400 m为间距划分大气环境敏感性。

表2 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sensitivity
2.1.3 生态源地识别及其验证
针对单项评价结果,采用析取法(熊善高等,2018)得到综合评价结果。参考《全国生态功能区划 (修编版)》,将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结果划分为一般重要、中等重要、较重要和极重要4级,将生态敏感评价结果划分为低敏感、中度敏感、高度敏感和极敏感4级。以极重要和极敏感区域进行源地初筛,剔除面积小、分布零散的斑块,完成源地识别(周汝波等,2020;康洁铭等,2020)。将识别结果与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叠加,以面积重叠率验证结果合理性(Xiao et al.,2020)。因港澳不设自然保护区,故将港澳郊野公园纳入验证过程。
2.2 生态廊道识别
2.2.1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模型)
MCR模型源于累积耗费距离理论,认为物种在源地间迁徙需耗费成本。相比其他模型,该模型能较好地模拟景观对空间运动过程的阻碍作用,揭示景观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彭建等,2017b)。本研究使用MCR模型识别廊道,包括两个步骤:(1)构建生态阻力面,反映物种迁徙的难易程度。若仅通过景观类型赋值,会忽略景观内部的空间异质性。本研究考虑地形和人类活动阻力指标,利用夜间灯光和地表曲率修正景观阻力面(Zhang et al.,2017)。(2)识别生态廊道。廊道是源地间生物迁徙、联系的最佳路径,是生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流动的通道。以源地中心点为生态节点,综合源地间距离和生态阻力,提取最小阻力路径,即廊道(Dong et al.,2020)。
2.2.2 廊道识别及其宽度设置
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逐点生成最小阻力路径后,产生大量冗余路径。去除重叠和经过2个以上生态节点的路径,并用 ID字段对生态廊道进行编号。《珠三角地区水鸟生态廊道建设规划 (2020—2025年)》提出,未来规划廊道平均宽度为1000—1500 m。在此范围内以100 m为步长,分析廊道地类占比情况。
2.2.3 重要生态廊道识别
重力模型能表征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特征和不同要素的相互作用,模拟生态流在源地间流动所产生的关联,定量表征廊道重要性(吴健生等,2020)。但是,传统重力模型忽略了斑块间生态重要性、敏感性和连通性。景观连通性指数通常包括整体连通性(IIC)、可能连通性(PC)和斑块重要性指数(dPC),其中dPC指数能较好地评价源地间的连通性水平(杨志广等,2018)。因此,本研究以生态重要性和敏感性修正重力模型,结合dPC连通性指数实现廊道分级。为降低数据量纲差异影响,在数据处理前需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Xiao et al.,2020)。针对重力模型和连通性评价结果,基于等间距法进行廊道分级,并使用四象限法对结果予以展示(Xiao et al.,2020)。
3 结果
3.1 生态功能重要性和敏感性评价
生态功能重要性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极重要区32552.6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58.7%,以林地为主(90.5%),沿着江门西南部、佛山西部、肇庆西北部、广州东北部、惠州东部、深圳和香港沿海部分地区环绕分布,分布特征呈现四周高中部低(图2)。单项重要性评价结果显示,生境质量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林地广布的山地丘陵区(图 2a)。单位碳储量范围在119—360 t·hm−2间,肇庆、惠州、江门和广州承载了研究区内近 81.9%的碳储量(图 2b)。土壤保持高值区主要位于江门南部、广州惠州交界处、惠州东南部、深圳大鹏湾和香港郊野公园等地区(图2c)。水源涵养最大值为 1969.8 mm·hm−2,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由西北部、东部向中部山地丘陵递增(图2d)。

图2 生境质量(a)、碳储量(b)、土壤保持(c)、水源涵养(d)和生态重要性分级(e)Figure 2 Habitat quality (a), carbon storage (b), soil conservation (c), water conservation (d) and ecological importance classification (e)
生态系统敏感性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极敏感区33845.5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61.0%,主要分布区域为外围的林地(78.2%)、水域(8.8%)和耕地(7.9%)(图3),中部水体区域、佛山南部、中山北部和珠海东部是主要高值区。单项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生境质量敏感性呈四周高中间低分布特征(图 3a),水环境敏感高值区主要位于中部地区,分布于河流交汇处和入海口,如西江、綏江和北江交汇处、顺德水道、珠江水系等(图3b)。土壤侵蚀以低敏感为主,中度敏感区(453.7 km2)和高度敏感区(235.9 km2)较少(图 3c)。区域大气环境敏感程度整体不高,呈西高东低特征。因考虑了重点排污许可企业的空间分布,大气环境敏感区域分布于肇庆东南部、江门北部和中部、以及沿海的部分风景名胜区和香港郊野公园等(图3d)。

图3 生境(a)、水环境(b)、土壤环境(c)、大气环境(d)和生态敏感性分级(e)Figure 3 Habitat (a), water (b), soil (c), atmosphere(d) and ecological sensitivity classification (e)
3.2 生态安全格局识别
生态源地、生态节点和生态廊道共同构成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格局(图 4a)。本研究共识别出28块生态源地(图4a)。生态源地面积为20370.8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6.7%,以林地为主。将生态源地与31个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8个港澳郊野公园叠置分析(图 4b、c),发现自然保护区、郊野公园有67.0%落入源地。重叠率较低处位于肇庆西江鱼类保护区、惠州白盆珠保护区部分区域和港澳郊野公园。这些地区接近海岸带,多位于岛屿上或面积较小。区域生态阻力值为0—317(图4a),广州(17.7%)、佛山(14.0%)和东莞(13.8%)生态阻力值占比较高,而澳门(111.4)、东莞(86.7)和深圳(85.4)的生态阻力均值较高。廊道识别结果显示,廊道总长2300.4 km,主要于研究区外围,呈环状分布(图5a)。廊道1000—1500 m缓冲区内,林地比例为82.7%—85.5%;随宽度递增,林地占比下降,而耕地、水体和建设用地比例上升(图5b)。

图4 生态安全格局(a)、生态源地验证(b)和验证案例(c)Figure 4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a), validation of ecological source (b) and sample of validation (c)

图5 生态廊道编号(a)和不同宽度廊道地类占比(b)Figure 5 Number of ecological corridors (a) and proportion of land use type in different corridors widths (b)
3.3 重要生态廊道识别
采用等分法对廊道进行重要性分级(图 6a)。结果显示,研究区共有 25条高重要廊道,长度为1552.3 km,占总廊道长度的67.5%,呈西多东少分布,主要位于肇庆、江门西南部、广州东北部、惠州内部及广州惠州连接处,主要为林地、耕地和水域。基于连通性指数,采用等分法将廊道进行分级(图 6b)。结果显示,高连通性廊道有 8条,总长847.3 km(占比36.8%),低连通性廊道有28条,总长1453.2 km(占比63.2%)。区域内廊道连通性普遍较低,高连通性廊道主要位于北部地区的肇庆市、佛山市北部、广州市和惠州市,少数位于江门市内部。

图6 生态廊道重要性(a)、连通性(b)、重要性-连通性四象限图(c)和重要性分级结果(d)Figure 6 Importance (a), connectivity (b), importance-connectivity four-quadrant diagram (c) and priority classification of ecological corridors classification (d)
综合考虑重要性和连通性,采用四象限法,将廊道划分为四个级别(图6c、d)。其中,高重要-高连通廊道3条,长度371.0 km,长度占比16.1%,分布于肇庆市内部,江门市内部及广州市和惠州市之间。高重要-低连通廊道22条,长度为1181.3 km,长度占比51.4%,呈西多东少规律,贯穿于江门市内部、江门市与佛山市之间、佛山市西部及其与肇庆市连接处,少数分布于东部的广州市和惠州市之间,以及惠州内部。低重要-高连通廊道5条,长度为476.3 km,长度占比20.7%,位于肇庆市西南部及广州、佛山连接处。低重要-低连通廊道6条,长度为271.8 km,长度占比11.8%,位于研究区南部沿海地区珠海市和中山市连接处、以及深圳市与惠州市、香港的延伸处,少数位于肇庆市南部,生态阻力值较高。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生态源地主要由林地组成,呈环状分布,多位于研究区北部林地广布的肇庆和惠州,少量散布于江门、珠海和中山;中部平原地区除了少数林地,几乎无生态源地,与前人研究结果类似(Jiang et al.,2021;周汝波等,2020)。Hu et al.(2019)和 Jiang et al.(2021)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的热点区域主要位于北部高森林覆盖区以及高密度河网区和海岸带,而中部一些城市(即澳门、东莞、佛山和广州),由于城市化水平高,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风险较高,不存在或者仅存在较少生态源地。此外,本文以自然保护区、港澳郊野公园与源地面积的重叠率进行验证,显示重叠率达67%,表明生态源地多位于生态保护边界范围内,是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与前人结果一致(Peng et al.,2018b;李怡等,2021)。
生态功能重要性和敏感性评价结果,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具体来说,生态功能重要性高值区主要位于研究区外围山地,低值区位于中部平原。生境质量、碳储量高值区主要分布于植被覆盖较高的林地;土壤保持高值区主要位于江门南部、广州惠州交界处,惠州东南部,深圳大鹏湾和香港郊野公园等区域;水源涵养高值区由东北-西南方向,向东西两侧递减,低值区位于中部平原地区。前人针对综合生态功能(Zhao et al.,2018;Zhou et al.,2019)和单一生态功能(生境质量,Jiao et al.,2021;碳储量,吴隽宇等,2020;土壤保持,林媚珍等,2021;水源涵养,王世豪等,2020)的研究,也发现类似规律。王浩等(2021)、甘琳等(2018)和吴献文等(2021)基于自然生态因子、城市扩张因子和生态服务因子进行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价,发现研究区高敏感区多位于外围林地和山区,因此这些区域的生态系统易受干扰。单因子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略有不同:相比外围林地和山区,研究区中西部水环境和大气环境生态敏感性更高,主要源于该区域河网密布和大气污染水平较高,是进行生态修复和保护的重点区域(Cheung et al.,2003;湛社霞,2018)。但是,受限于数据可获得性,本研究采用距离因子来间接表征水体和大气污染敏感性,有一定局限性,未来可尝试基于直接的大气或水体污染数据来识别环境污染敏感区。
本研究识别的廊道位于源地之间,其分布特征主要受区域自然禀赋的影响。考虑到传统重力模型在识别重要生态廊道时的缺陷(Xiao et al.,2020),本研究使用生态系统重要性和敏感性评价结果修正重力模型,并结合连通性指数,识别重要生态廊道。修正重力模型和连通性指数的研究结果相互补充:前者显示西部区域廊道重要性较高,而后者显示北部区域廊道连通性较高。研究区高重要廊道呈西多东少特征,这是由于西部肇庆和江门分布的源地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保存较好,景观破碎程度较低(虞文娟等,2020),源地间相互作用力大。高连通廊道北多南少,这是由于北部廊道起着维系西北部和东北部源地物种迁徙、能量交换的作用;南部廊道受珠江入海口阻隔,连通性程度不高(吴健生等,2020)。依据重要性和连通性,廊道被划分为不同类型,应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和管理措施(Williams et al.,2005)。高重要-高连通廊道贯穿于研究区的西北、西南和东北,位于重要源地之间和生态保护区内,累积阻力值较小,生态服务供给能力较高,对于物种丰富度、迁徙和珍惜濒危动物保护起重要作用(Li et al.,2020;吴健生等,2020;牛沛航等,2021)。此类廊道应严格管控,禁止破坏,加强保护。高重要-低连通廊道位于相邻源地间,距离较短,累积阻力较小,对于物种迁徙很重要,但是连通性差,可通过增设绿带、拓宽廊道宽度,增加景观连通度的方法加强保护(史娜娜等,2021)。低重要-高连通廊道距离长,累积阻力值较大。此类廊道虽然生境适宜性低,但是高连通性对维持生态系统安全、稳定性和整体性具有重要意义(吴茂全等,2019),应以维护为主,加强生态修复为辅(张玥等,2020)。低重要-低连通廊道面临较大生态阻力,对整体连通性贡献较低。此类廊道主要位于研究区的生态恢复区(Li et al.,2020),应重点关注生态脆弱区,有针对性地进行生态恢复,避免受人类活动过多干扰,以保障生态过程有效流通(何建华等,2020)。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和生态阻力面赋值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设定阈值问题,这也是当前研究的共性问题(Xiao et al.,2020)。
5 结论
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是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科学识别至关重要。本研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识别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源地,利用修正重力模型和连通性指数识别重要生态廊道,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结果显示:
(1)生态功能重要性和生态系统敏感性高值区主要位于研究区外围山地,低值区位于中部平原地区。单因子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略有不同:研究区中西部水和大气环境敏感性较高,易出现污染问题,是进行生态修复和保护的重点区域。
(2)研究区生态源地总面积为20371 km2,主要位于研究区北部林地广布的山地丘陵区,与自然保护区边界高度重合,而中部平原地区几乎无生态源地。
(3)研究区共有潜在生态廊道36条,总长2300 km,呈东西两侧环绕式分布。其中,高重要-高连通、高重要-低连通、低重要-高连通和低重要-低连通廊道分别为3条、22条、5条和6条。高重要廊道大多位于研究区西部,而高连通廊道多位于北部。依据廊道重要性和连通性特征,应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