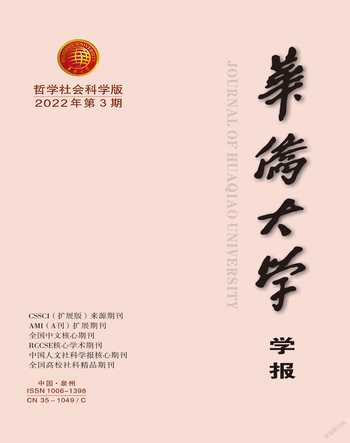白先勇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融合
2022-06-23程彩霞郑绍楠
程彩霞 郑绍楠
摘 要: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具有将中国传统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相融合的特点。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来看,白先勇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前见”与佛教思想紧密相关,他将西方现代主义人—神对立的张力结构置换为今—昔比照的无常变化。以佛教的“四法印”来观照,白先勇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人生虚无和痛苦的体验是通过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来完成的。在文学的终极关怀层面上,白先勇没有走上佛教“寂静涅槃”的出世解脱之路,而是代之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悲剧的尊严”的抗争精神,并且他将大乘佛教的悲悯情怀与“悲剧的尊严”相融合,呈现出解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的境界。
关键词:白先勇;佛教思想;现代主义精神;《台北人》;视域融合
作者简介:程彩霞,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台湾文学(E-mail:cxcheng0728@qq.com;江苏 南京 210023)。郑绍楠,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学、文艺理论(福建 泉州 3620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台湾乡土小说流变研究(1965-2015)”(18BZW149)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2)03-0130-13
白先勇是当代世界华文文坛备受瞩目的一位作家。他于1960年代前后登上台湾文坛,受到当时风行于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去美国留学后更深入地研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然而白先勇从小就浸润在民间小说、古典诗词等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他的作品同时还包蕴着明显的传统色彩,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特点。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体现在方方面面,既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又有小说技巧方面的(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84—85页。)。对此,学术界已经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课题可以盖棺定论,没有再深入挖掘的空间。事实上在这一大课题之下有一个子问题——白先勇如何将中国传统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相融合?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白先勇曾坦言“自己基本的宗教感情是佛教的”(蔡克健:《同性恋,我想那是天生的!——PLAYBOY杂志香港专访白先勇》,白先勇:《树犹如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3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教思想对他具有特别深刻的影响,并且他在创作中将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相融合,使其作品呈现出一种艺术的张力和独特的魅力。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停留在大轮廓、粗线条的描述上,远远达不到深入探究的程度。据[KG(3x]于此,笔者将以白先勇的代表作《台北人》为文本分析的重心,选取中国传统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相融合这一视角,来具体考察白先勇的作品所体现的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特点。
学界许多研究都关注到佛教对白先勇思想和作品的影响,如王晋民认为白先勇作品的“人生如梦一切皆空”的思想实是佛家的“色空”观念的表现,“人生是痛苦不幸”的思想与佛家的“四谛”“十二缘生”等思想相契合,白先勇作品中显示的宿命论来源于佛家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说(王晋民:《论白先勇的小说》,《多元化的文学思潮:王晋民选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第146—147页。)。方忠从“空”的历史观、人世无常、因果报应与宿命的角度论述白先勇与佛教文化的关系(方忠:《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70—78页。)。这些研究最大的问题是往往颇具随意性地拈出几个佛教关键词,如色空观、“四谛”(特别是苦谛)、无常、因果、轮回等,将其机械地套用到对白先勇作品的分析中,而未能将佛教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白先勇的创作。其实只有在佛教整体思想的烛照之下才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在融合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过程中,白先勇对佛教思想的吸收是具有选择性的,即有些佛教观点他是深信不疑的,有些则被他有意识地遗漏掉了。这种选择性的吸收也是本论题需要特别关注的。
研究者也发觉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在白先勇作品中的融合,但遗憾的是往往一笔带过。既往的几篇硕博论文关注到白先勇的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关联。朱立立认为白先勇小说中形成了一种“存在主义的时间焦虑与民间佛教的人生无常感悟互相融摄”(朱立立:《论台湾现代派小说的精神世界——战后台湾知识分子的认同建构与自我追寻》,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第64页。)的时间哲学,还使“隐含叙述者身上存在主义式的勇敢面对破碎现实的勇气”与“中国民间信仰中命运的绝對性主宰下的人物形象”这两种对立的力量在小说中达到一种非常本土化的综合(朱立立:《论台湾现代派小说的精神世界——战后台湾知识分子的认同建构与自我追寻》,第71页。)。丛坤赤认为白先勇“把存在主义者对人类存在的形而上思考,拉回到中国传统佛教对芸芸众生的世俗关怀上来”(丛坤赤:《把心灵的痛楚变成文字——论白先勇的悲剧意识》,山东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第18页。),强调佛教对白先勇笔下人物的存在主义式痛苦的舒缓作用。而谢非则强调白先勇小说的存在主义意味更浓,具有与命运抗争的“悲剧的尊严”,“不像佛道文化在看待命运时骨子里的悲凉和空虚”(谢非:《现代主义中国化的艺术探索——论白先勇短篇小说的叙事技巧及其存在主义内涵》,上海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第82页。)。这些研究较为深入,但对白先勇佛教思想和西方现代主义精神融合的机制是怎样的,还是缺乏有意识的、系统性的论述。笔者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一 探讨白先勇佛教思想与现代主义精神的融合机制,需要引入现代解释学
西方现代解释学认为,一个人对另一种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是一种充满“偏见”的行为,而不可能像传统解释学所理解的那样——排除解释者的各种“前见”,从而把解释者中立化,尽可能去符合作者灌注在文本中的原意。这意味着任何人在理解接受另外一种事物时,都不可能像一张白纸一样绝对的客观中立。相反,他的存在结构决定着他有自己的历史境遇和个人情境,而这些都构成了解释活动不可能加以排除的“前见”。就白先勇而言,他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精神进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他本人的“前见”不仅不曾缺位,而且应当是隐秘且无时不在地发生作用。因此,他对西方现代主义精神(以存在主义为核心)的理解必然充满解释学意义上的“偏见”。以往的研究者,对接受者和接受对象处于不同的文化视域之中,多少都有所注意,但是,他们往往在没有自觉的方法论指导下就展开问题的研究。这导致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对于被接受的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性质缺乏深入的论述;第二,对白先勇理解和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前见”之内容和内在精神旨趣没有深入理解和比较精准的定位;第三,以上两个问题,则导致了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对于二者融合的内在逻辑和对话机制都不甚明朗。有鉴于此,本文将引入现代解释学作为方法论依据以克服上述三个问题。2E10EF0C-E9F6-457D-B424-4CFE6C49C838
(一)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性质
首先来看白先勇的接受对象——西方现代主义精神。西方人的虚无感和难以言明的痛苦是伴随着理性形而上学的崩塌以及传统宗教信仰的式微,即尼采所谓的“上帝死了”而到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说过,“上帝死了”对人类来说绝不是一句廉价的口号,它将使人付出昂贵的代价。萨特所言对于有着悠久宗教信仰传统的西方人来说,绝对是真实的。 “上帝死了”之后,西方的哲人和作家是这样描述自己的人生处境的,叔本华认为整个人生像一个钟摆一样永远往复于无聊与痛苦之间;诗人波德莱尔感叹灵魂像没有桅杆的破船,在丑恶天涯的海上飘荡颠簸;荒诞派剧作家尤内斯库说:“在这样一个现在看起来是幻觉和虚假的世界里,存在的事实使我们惊讶,那里,一切人类的行为都表明荒谬,一切历史都表现绝对无用,一切现实和一切语言都似乎失去彼此之间的联系,解体了,崩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
《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68—169页。)漂泊感、幻灭感、末日感、无常感、罪孽感、无聊感弥漫纸面。刘东在分析现代主义哲学鼻祖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情绪时指出:“叔本华那种‘人之大孽,在其有生的哀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反映出了西方心灵因找不到(过去一直有着的)支点而发出的痉挛和颤抖;人对上帝的抛弃,在这里就被体验为上帝对人的抛弃。而在另一方面,出于对上帝的爱情的惯性,上帝对他们的抛弃就加大了西方人原罪的感觉。”(刘东:《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2—153页。)其实,这种感受又何止于叔本华,对于西方作家而言,虽然上帝已死,上帝从作家的文本中退场隐遁,但是在上帝退场之后那个巨大的价值空白被填满之前(事实上一直没有完成),“出于对上帝的爱情的惯性”,上帝将如游荡的幽灵一般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在场”。如果我们细读西方现代派的作品,不难发现,虽然上帝隐遁,西方人对虚无和痛苦的体验背后莫不存在人—神对立的张力结构和紧张关系。脱离开这个张力结构,则无法深入地理解现代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二)白先勇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前见”
对于处身中国文化圈的白先勇而言,他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过程中有自己的“前见”。考察白先勇“前见”的内容及内在精神旨趣,对于我们理解白先勇何以在西方各种思想潮流中选择现代主义,以及如何与自己本有的视域相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1.白先勇“前见”的内容——历史境遇与个人情境
西方现代主义中“上帝死了”的命题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即陌生而又熟悉的命题。之所以说陌生,原因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西方人的基督信仰,就连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体验都是极为有限的。就白先勇个人而言,他在香港短暂的求学时光中有一段基督教经验,但他最终没有接受这种信仰(蔡克健:《同性恋,我想那是天生的!——PLAYBOY杂志香港专访白先勇》,第343页。)。因此他的这种宗教体验是比较肤浅的。之所以说熟悉,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也遭遇了类似“上帝死了”的命运。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说,尼采的“上帝之死”的哲学命题,其意义并不只限于基督教世界,而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命题。就中国而言,虽然中国人不信仰基督,但是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冲突之际也遭遇了“上帝死了”的命运。这里的“上帝”是指从先秦以来所形成的一套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佛道为辅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古老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这套延续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受到剧烈撼动,开始走向分崩离析。遭遇价值的虚无感、生存的荒诞感和无根基性,以及在这种虚无和无根基性中感到彷徨、焦虑、孤独、挣扎和痛苦,则是中国人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白先勇对东西方所面临的相似的“文化危机”深有认同:“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經历的战争及革命的破坏,比起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传统社会及传统价值更遭到了空前的毁灭……我们的文化危机跟西方人的可谓旗鼓相当。”(白先勇:《〈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写在〈现代文学〉重刊之前》,《树犹如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5页。)这种相似的历史境遇,使白先勇在了解西方时更容易把现代主义思想引为自己异域的知音。
不仅在历史境遇上,白先勇作为个体生命的具体处身情境,对他趋向现代主义也有某种影响。他童年时期生肺病,与家人隔离了四年多,这在他的心灵上留下很深的阴影,使他早早体会到人生的孤独和痛苦。白先勇童年、少年时期是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等战乱环境中度过的,后又经历了国民党败退台湾,父亲白崇禧到台湾后在政治上失势,家族急剧衰败,这些经历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家国巨变的幻灭感。白先勇天生有同性恋倾向,这给他带来一种身份认同的困惑。母亲马佩璋的病亡更使他直面生死,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可以说,童年生肺病的孤寂、家国巨变的幻灭感、特殊的情感倾向、母亲病亡的生死体验构成了白先勇个人独特的对于人生虚无和痛苦的体认。
作为多灾多难的中国现代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作为一个具有饱满人生经历且精神生活坎坷多舛的将门之子,以及作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文学天才,白先勇对于一种异域精神的接受自然不会满足于“如是我闻”“萧规曹随”的层面。换句话说,他的精神旨趣和文学感性的建构不可能建立在西方现代主义对自己历史境遇和个人情境的掩盖和遮蔽的基础之上。那些思想旨趣和写作技巧都全盘西化的中国作家,其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对西方文学和哲学思想的接受是建立在一种遮蔽自己历史境遇和个人情境,从而缺乏“视域融合”(伽达默尔语)的拿来主义基础之上,即他或多或少地将自己的“先在结构”排除出去(实质上也不可能完全排除),而这个“前见”是中西对话中作为对话主体的主体性的保障,也是中西融合的前提。2E10EF0C-E9F6-457D-B424-4CFE6C49C838
2.白先勇“前见”的内在精神旨趣
在对白先勇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前见”进行一番概述之后,现在可以比较清晰看出,白先勇是在一種怎样具体的历史境遇和个人情境中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精神而不是其他。但是这里还存在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白先勇本人的“前见”在他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过程中产生了何种作用?最后达成了何种效果?这里边存在的困难在于白先勇本人对于传统式微的历史境遇和命运多舛的个人情境是如何理解的(比如有人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对待,对此看到的是“凤凰涅槃”的新生)。如果我们不了解白先勇本人是如何理解他的历史境遇和个人情境的,其实就还没真正了解白先勇“前见”的内在精神旨趣,那么也就无法探明这种结构如何影响他对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接受。所幸的是不论是从白先勇创作的文本之外还是文本之内,都可以看出他“前见”的内在精神旨趣与佛教思想紧密相关。
小说文本之外,白先勇多次表露自己对佛教是很有亲近感的,甚至坦言他的基本宗教感情是佛教的,“对佛教那些特别感到惊心动魄”(刘俊:《文学创作:个人·家庭·历史·传统——访白先勇》,白先勇:《树犹如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2页。)。在他的小说文本中,很多研究者也都注意到他的叙事中弥漫着佛教的思想底蕴,欧阳子指出:“细读《台北人》,我感触到这种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页。)遗憾的是,在此论题上,学者们对白先勇佛教的思想底蕴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就以“一切皆空”“悲凉空虚”等概述了结。对于这种佛教的思想底蕴如何具体“结合”到西方现代主义精神中去的理路和机制也缺乏深入的探析。
以“一切皆空”“悲凉空虚”等来概括佛教教义以及白先勇小说中的佛教思想底蕴,固然没什么大问题。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佛教思想具有哪些内涵层次?白先勇对这些佛教思想是全盘接纳?还是有选择性的接受?为什么?
阐述佛教教义的典籍有三藏十二部,法门据说有四万八千之多。佛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分出大小乘,且又因修行方法和对教义理解的不同而宗派林立。因此,在介绍佛教思想时,根据角度和需要的不同,其内容可繁可简,可深可浅。为了比较全面地把握佛教思想的内涵又不过于漫无边际,本文采取佛教“四法印”来探讨佛教思想的内涵。所谓“四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寂静涅槃”(印顺法师:《佛法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5页。)。此“四法印”乃佛陀在世之时亲制,其目的就是为了突显佛法与外道法不共之精髓,以方便辨别法之真伪。凡符合此“四法印”者,虽非佛说也是佛法,反之,与此“四法印”不符合者,即便是佛亲口所说,也非究竟义。
佛教又称“空门”,是故人们常以“一切皆空”来涵括佛教教义,佛教之“四法印”就是对此“空”的不同层面的具体展开。对佛学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佛家之“空”,不是指一无所有的“断灭空”,或物理学意义上的虚空。“空”的涵义的直接解释就是无自性,“一切皆空”指的是一切法由于从众缘生灭,没有常住性、独存性、实有性。从“四法印”来说,“空”的第一层意义就是“诸行无常”。“诸行无常”指的是,举凡世间一切有情无情物念念不住地流转变易,经历着生老病死或生住异灭,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具有超越时间的永恒性,以是义故,有生必有死,有壮必有老,有盛必有衰。所谓“诸法无我”,则指的是无主宰义,具体到有情众生上,就是对自身和周围的一切不能做主,不能自由支配,而不得自在。所谓“有漏皆苦”,则是觉者对于有情世间的价值判断。一切有情众生莫不依蕴、界、处诸法而立,而诸法无常无我,然众生因无明起颠倒见,不明无常无我之真谛,住相生心,而生常我执,起惑造业,生无量苦。佛教无常无我法印可以直接推出或者说包含着“苦法印”,此法印与前两法印的意思相承接。最后一法印“寂静涅槃”,则在前三法印的基础上指出离苦得乐,获得究竟解脱的可能和道路。龙树菩萨说:“有为法无常,念念生灭故,皆属因缘,无有自在,无有自在故无我;无常,无我,无相,故心不着,无相不着故,即是寂灭涅槃。”(《大智度论》卷二十二)此“四法印”之间的关系,大有任一法印含摄其他三法印之义,从而成为一个圆融的整体。凡论及佛教教义是否如法问题则不可须臾离开“四法印”。我们借助佛教的“四法印”,将佛教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呈现出来,将有助于我们清楚地看到白先勇对佛教思想的态度——他认可佛教无常无我的理念,对于苦的理解也基本来自佛教,但是他并没学曹雪芹接受佛教“寂静涅槃”的解脱思想。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留待后文论述。
了解了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性质和白先勇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前见”这两个问题后,就可以着手解决第三个问题,即白先勇的佛教思想是如何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融合并在文本中呈现的?
二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于人生虚无和痛苦的体验,在白先勇这里是以佛教式完成的
(一)白先勇对现代主义文学中“现代虚无”之体验
尼采提出“上帝死了”这一开创现代性的文化哲学命题,其内涵是指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和基督教信仰给人预先提供的关于人存在的终极价值和意义失去其统摄性和有效性。正如英国诗人叶芝所说的“一切都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人之生存处在一种“被抛”的茫然无依的状态中,人生在世充满着“烦”(Sorge),人生的常态是孤寂、苦闷、绝望。不仅如此,随着“上帝之死”,必有一死之人失去救赎以及永生的希望,于是,人之生存不论是贫富贵贱还是顺逆苦乐都显示出一种深深的幻灭虚无之感。尽管如此,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虽然上帝隐遁,但是在现代主义精神里,人—神之间的张力结构依然存在着,成为现代派作家运思写作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背景。刘小枫也指出:“西方审美主义是在神性精神传统的背景上分裂出来的,尽管离开了超越的神恩,仍然与超然的上帝有一种紧张关系。”(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页。)2E10EF0C-E9F6-457D-B424-4CFE6C49C838
回到白先勇小说的文本,我们可以很容易感受到他的小说同样也弥漫着和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类似的虚无感和幻灭感。不少论者在此发现了白先勇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同构”之处,比如二者都感受到傳统价值毁灭形成的价值真空给人带来的失重感和茫然无依感;二者都看到“上帝”死后的现实世界呈现出丑陋、荒芜、衰败的一面。但是这种“同构”的外观往往使人们对白先勇接受和融合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内在机制的探讨停留于表面。
在《台北人》里,我们看不到西方现代作家写作时所依托的人—神之间的张力结构和紧张关系。这不难理解,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影响并且对此传统有着深切爱恋的中国作家(欧阳子认为白先勇“是一个十分尊重中国传统和痴恋中国文化的人”(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第308页。)),神恩救赎的宗教体验对白先勇来说,虽不陌生,但也绝对谈不上融入他的精神结构,用现代解释学的话来说,他的接受者视域根本不存在这一维度。那么问题来了,西方人对虚无的体验根源于人—神之间的紧张关系,白先勇对虚无的体验源自何处呢?细读《台北人》可以发现,小说虽没有西方那个二元论景观和张力结构,但还是可以发现一个勉强有些类似的张力结构,这个张力结构不是存在于人—神、罪孽—救赎、此岸—彼岸之间,而是主要存在于今—昔之无常变化的对比之中。在这今—昔比照的叙事张力结构之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虽然白先勇和西方现代派的文学都在传达一种虚无和幻灭之感,但是白先勇对于这种虚无和幻灭感的体验与西方作家的体验是不太一样的。白先勇对虚无和幻灭感的体验,不是放置在一个隐蔽的人—神对立的架构里,而是内置于历史时间之流的无常变化中。而且在这种过去—现在的无常变化中,他看到的不是历史进步的上升画面,而是不断衰亡堕落的悲观图景。
我们且看白先勇是如何在小说《冬夜》中呈现这种虚无和幻灭之感的。小说的故事虽然发生在短短的数小时里,情节也基本依靠人物的对话来推动,但是小说内在的今—昔比照架构却很清晰。小说的两位主角——余钦磊和吴柱国,曾是中国现代五四爱国运动的健将和领袖。通过小说人物的回忆和对话,可知他们曾经怀揣真挚的爱国理想,以昂扬的斗志和永不妥协的精神,发动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然而20年后的现在,头顶光秃、一身老病的余钦磊虽然还在大学(之前在北大教书)教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但是充满浪漫主义的理想已然无可奈何地让位给残酷的现实。他续弦的妻子世故且现实,完全无法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翻译拜伦诗歌的工作竟至七八年“没译一个字”,因为即使译出来也没有多少人看。抚今追昔,难掩无尽的失落和空虚,但是生活还得继续,他满心想的是如何设法出国教书多赚钱,来还清巨额的债务。他昔日的同志吴柱国表面上在学术界功成名就,可是精神情况和余钦磊差不多。时光流逝,世事无常,吴柱国的理想火矩早已熄灭,他虽能在现实中风光地活着,但背叛理想的愧疚和空虚却深植心底。他把自己20年来在美国大学讲授唐代制度文化看成是空虚无用的吹嘘,并且认为自己以两年一本的速度所写的书,其内容“都是空话”,仅仅是为了应付美国的聘任制度。他说:“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会写的了。”(白先勇:《冬夜》,《台北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5页。)在今——昔的比照中,在无常的作用下,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暮气沉沉,光辉灿烂的理想最后只剩下冰冷功利的现实,激情澎湃的浪漫精神退化为对生计的种种操劳……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难抵无常无我的法则——因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四法印”之第一、二法印),一切人事物都要经历生老病死和生住异灭,是故有生必有死,有壮必有老,有盛必有衰,没有任何人或力量可以阻止这种事实的发生。
这种历史的无常作用在白先勇的其他篇章里还可以看到:贵族之家的零落破败(《思旧赋》)、丰功伟绩的逐渐湮灭(《国葬》《梁父吟》《岁除》)、荣华富贵的转眼成空(《游园惊梦》)、充满灵性的爱情退化为欲的深渊(《花桥荣记》《一把青》)、灿烂的文化逐渐失色(《国葬》《秋思》)……面对美好事物无可奈何地逝去,小说弥漫着不胜今昔之怆然感、失落感、幻灭感、虚无感。这里所传达的对人生的体验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佛教式的体验。所谓“中国佛教式的体验”在本文中指的是,中国古人将佛教的“无常无我观”融入历史的变迁中,从而形成一种具有佛家韵味的历史感。在中国古典文学里,这种因世事无常无我而引起的历史感喟比比皆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桃花扇》)、“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红楼梦》)……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的白先勇对这些古典作品以及作品背后充满无常意味的历史感不仅非常熟悉,而且他还把这种具有“历史感”的文学境界当成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和自己文学创作的追求目标(余秋雨:《世纪性的文化乡愁——〈台北人〉出版二十年重新评价》,白先勇:《台北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9—260页。)。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白先勇虽然认同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内核——虚无主义,但是对这种精神内核的体认却是地地道道中国式的,更具体地说是佛教式的。正因为如此,虽然白先勇和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都体验到了时代之“虚无”,但是因为白先勇具有佛教意味的“前见”的作用,他的体验是以佛教式达成的。
(二)白先勇对现代主义文学中“现代痛苦”之体验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想见白先勇对于“虚无”之时代处境所带来的痛苦体验也与西方的不尽相同。西方人在描述上帝死后所体验到的痛苦时常常用的词汇是“畏”“被抛”“烦”“孤独”“绝望”。这些词的内涵必须放置在人—神的张力结构中去分析才能看得明白。在白先勇的《台北人》里,我们能很清楚地感受到白先勇对所谓时代之痛的体验是迥然有别于西方的。固然,我们也可以用“畏”“被抛”“烦”“孤独”“绝望”这些词去描述白先勇在小说中所流露出的痛苦体验,但是,还是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原因在于这些词汇是一些高度语境化的词,它们的准确内涵只有放在西方人—神对立的话语语境中才能得以澄清。一旦去除这个语境,而套用到白先勇小说的文本语境中,则必然产生削足适履之感。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白先勇对于痛苦的体验是典型的佛教式体验。《金刚经》里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第三十二品)《华严经》里亦说:“如实知一切有为法,虚伪诳诈,假住须臾,诳惑凡人。”(《华严经》卷二十五)《台北人》中“过去”所承载的功绩、富贵、爱情、理想、青春、生命……这些人们所珍视的东西,哪一样能够永恒不变?哪一样能够抵挡无常的脚步和时间的风化?不过在佛教看来,无常无我本是宇宙人生的实相,并不会直接导致痛苦。如果人们能够勘破无明,了达无常、无我之实相,并对一切的生命形式和生命体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第十品),那么人生则能够跳出三界而随缘任运逍遥自在。之所以“有漏皆苦”(“四法印”之三),其苦因正在于对无常无我的有为法(有漏)的无常性、无我性不能清醒认知,从而生起种种妄执。2E10EF0C-E9F6-457D-B424-4CFE6C49C838
《台北人》里的主角都是一些不能放下对“过去”的执着的人。这些人有将军、有知识分子、有小学教员、有社交名媛、有上流社会的贵妇人、有老迈的女仆、有帮佣工人、有军队的兵士、有小摊贩的老板……虽然他们处身不同的社会阶层,贫富悬殊,行业不同,不过导致他们烦恼和痛苦的原因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那就是他们都有一段难忘的“过去”,并且对这段“过去”死死地执着不放。白先勇很擅于写人性深处那种隐秘而又深切的痛苦,但这种痛苦却没有基督教文化中罪与罚的色彩,这种痛苦更多地是一种佛教式的无常苦、无我苦、执着苦。对于这些苦,《台北人》的14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有非常精彩的呈现,当然最为出彩的还是《游园惊梦》这一篇。在《游园惊梦》中,叙述者时不时地钻入参加宴席的钱夫人的意识流里,在阅读的同情理解中,读者可以分明地感受到身处热闹欢宴中的钱夫人,其内在感受简直是一场精神的凌迟。之所以受罪,原因在于出身卑微的钱夫人有过一段辉煌的“过去”,并对这段“过去”不能忘记也不能放下。出身南京秦淮河得月台的卖唱小姑娘蓝田玉,为赫赫有名的钱鹏志将军迎娶为填房夫人,成了将军夫人。被钱鹏志当女儿宠爱的蓝田玉在南京度过了一段众星捧月、风光无限的富贵生活。这段生活是她最光彩的记忆,也可以说是她所有痛苦的源头。国民党败退来台之后,蓝田玉虽然还是人们口中的“钱夫人”,但是她的境遇今非昔比。随着丈夫死去,她富贵的社会地位不再,青春年华不再,只一个人独自居住在台湾南部。在参加台北窦公馆的热闹华贵的宴会中,在酒精的作用下,在钱夫人恍惚的意识中,仿佛过去的一切都重现出来——富丽堂皇的客厅、春风得意众星捧月的女主人、衣裙明艳体面高贵的客人……回过神来,才发现那个被众星捧月的女主人不是自己,而是她在南京唱戏的一个姐妹(桂枝香——窦夫人)。对钱夫人而言,曾经有多么辉煌灿烂,现在就有多么凄凉落寞。
过去的已经过去,如梦幻一般,可是白先勇小说的主角们往往喜欢沉浸在梦里,且“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欢愉过后,梦醒时分,那种落寞就显得格外凄凉。这些执着而痛苦的人有《岁除》里的赖鸣升、《冬夜》里的知识分子吴柱国和余钦磊、《秋思》里的华夫人、《花桥荣记》里的小学教员卢先生、《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的帮佣王雄、《永远的尹雪艳》里尹公馆里的座上宾们、《思旧赋》里的顺恩嫂、《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的“教主”、《国葬》里的秦义方……他们有的孤独、有的绝望、有的失落、有的茫然无依、有的干脆沉入虚幻的梦境中自欺欺人。尽管他们痛苦的内涵不同,痛苦的程度深浅不一,但是他们对“过去”的执着和不肯放下却是一致的,这是他们为种种痛苦所纠缠不休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白先勇体验虚无主义的时代之痛,是以佛家的无常苦、无我苦、我执苦而达成的,因而迥然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对痛苦的体验。不过,如果仔细深入地辨析,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两种异质性的体验中发现某种“同构”的地方。不论是白先勇还是西方现代派,他们对痛苦的体验,都是出于一种“执着”,执着于那个已经逝去的美好理想或者传统。在西方,刘东把这种“执着”称之为“对上帝的爱情的惯性”(刘东:《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第152页。)。而在白先勇这里,不论是作家本人还是他小说里的主人公都不同程度地“执着”于“过去”。因为在小说的文本里,“过去”绝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它拥有太多正面的意义和光明的内涵。欧阳子说白先勇小说里的“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第5页。)。“过去”这个词在白先勇这里和西方人的“上帝”有几分接近。也许正是出于这种体验的异质同构性(即格式塔心理学所谓的Heterogeneous Isomorphism),白先勇才能把西方现当代主义文学中的那种痛苦用非常东方的方式传达出来,并且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的境界。
三 白先勇小说的终极关怀层面,体现了佛教的悲悯情怀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悲剧的尊严”的视域融合
(一)以“悲剧的尊严”的抗争精神来取代“寂静涅槃”的出世解脱
如上文所论述,白先勇以佛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的“前见”,去体验西方现代主义精神中的虚无和痛苦。如果按此佛教教义的逻辑推演下去,虚无且痛苦的人类的最后出路必然是勘破无明,放下我执、法执(自然也包括对“过去”的执着),走向“寂静涅槃”(“四法印”之四)的解脱之境——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就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 按照这一逻辑,那些能够斩断“过去”,活在当下并接纳现实的人才是小说中理想的人物,比如《岁除》中的骊珠和俞欣、《冬夜》中的邵子奇、《梁父吟》中的王家骥……。不过白先勇显然没有采取这种佛教解脱论的立场。最明显的根据就是白先勇对于那些没有“过去”或斩断“过去”的人,不仅没有持赞赏的态度,而且还“有那么一点儿责备的味道”(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第13页。)。对于那些执着于“过去”,不能或不肯面对现实的人反而给予最多的悲悯与同情。可以这么说,如果白先勇采取这种解脱论的立场的话,那么,他小说的思想水准还停留在两百多年前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水平。
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为人们呈现出一个虚无的、充满痛苦且没有意义的世界。然而如果白先勇不接受佛教的“寂静涅槃”的解脱论观点,他将如何安顿文本中那些苦难的芸芸众生呢(或者说他将如何安顿他自己,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以往也有学者有所論及。余秋雨认为白先勇“在一种令人无奈的兴亡感和令人沮丧的无常感中获得精神自救”所凭靠的是他的“文化乡愁”,在此乡愁中有“逝去已久的传统文化价值”,“有民族的青春、历史的骄傲、人种的尊严”(余秋雨:《世纪性的文化乡愁——〈台北人〉出版二十年重新评价》,第261页。)。这种观点似乎是受到欧阳子“救赎论”的启发。欧阳子认为:“在《台北人》世界中,对过去爱情或‘灵的记忆,代表一种对‘堕落,对‘肉性现实之赎救。”(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第20页。)此外,欧阳子还指出白先勇小说创作“褒昔非今”的态度,还直接受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影响。这里所论述的都很有道理而且也是事实。但是如果把这一问题放在“白先勇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融合”这一论域里,其所论则不够深入全面。2E10EF0C-E9F6-457D-B424-4CFE6C49C838
本文认为白先勇之所以没有从对世事无常、人生幻灭的体认中,最后走上曹雪芹的老路——佛教的寂灭解脱论,原因在于他的思想里还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具体而言,白先勇在对小说人物的终极关怀层面上,更认同西方现代主义对于人的价值的强调以及抗争精神的突出,强调一种“悲剧的尊严”。受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影响,他对红尘中的“人”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赞扬那些与命运抗争以维护自己尊严的人。关于这一点,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哲学基础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他影响很大,白先勇在台大读书时就接触到存在主义哲学并服膺于这种哲学精神:“‘存在主义一些文学作品中对既有建制现行道德全盘否定的叛逆精神,以及作品中渗出来丝丝缕缕的虚无情绪却正对了我们的胃口。”(白先勇:《不信青春唤不回——写在〈现文因缘〉出版之前》,《树犹如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9页。)在台湾当时肃杀的政治氛围里,人性是受到极大压抑的,而存在主义的“叛逆精神”和“虚无情绪”就是对现有道德的反抗,对被压抑的人性的解放,因此对青年白先勇格外具有吸引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表征就是对人性的充分挖掘,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哲学基础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人”极端重视,并将它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企图在荒诞中树立人的价值,确立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对“人”的高度重视与白先勇的创作思想非常契合。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写作时,白先勇说:“我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化成文字。”(白先勇:《我的创作经验》,《树犹如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7页。)白先勇写作是为了表现人性,他创作的思想底蕴就是对人的生存形态的关注和思考(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第1—37页。)。
更进一步而言,白先勇认同存在主义对“人”的重视,主要是认同存在主义强调人虽然必定要失败,人生虽然是虚无的,但是人依然要努力地与命运抗争,在这种抗争的过程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维护人性的尊严,白先勇将其称为“悲剧的尊严”:“存在主义是探讨现代人失去宗教信仰传统价值后,如何勇敢面对赤裸孤独的自我,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中,对自己所做的抉择,应负的责任。存在主义文学中的人物,往往亦有其悲剧的尊严。”(白先勇:《秉烛夜游——简介马森的长篇小说<夜游>》,《白先勇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所谓“悲剧的尊严”就体现在明知人生的荒谬和痛苦却仍然与命运不屈抗争的过程中,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一种直面痛苦人生的决绝姿态。
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这篇充满隐喻与象征的小说里,白先勇写了一个叫王雄的退伍老兵的故事。王雄的故乡在湖南乡下,他18岁那年被国军截去打日本,此一离乡二十几年,再也没能回去。王雄随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退伍之后就在“我”舅妈家作帮佣。人高马大、木讷且沉默的王雄对于无常之命运貌似最能随遇而安,所求无多,可是在他内心深处却无时不眷恋着他老娘给他定了亲的小妹仔。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人高马大的他愿意任凭一个任性顽皮、名叫丽儿的小女娃任意驱使。他把玉娃娃般的丽儿当作他在大陆定了亲的那个白白胖胖的小妹仔。可是随着丽儿长大,“俨然是一副中学生的派头了”,“王雄好像猛吃了一惊似的,呆望着丽儿,半晌都说不出话来”(白先勇:《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台北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3页。)。丽儿已经不是他心目中的小妹仔了,王雄精神的寄托破灭了。当精神的寄托破灭之后,王雄对嘲弄他的喜妹展开报复,报复她那成熟丰满的肉体。他痛恨成熟,正是因为丽儿长大了,她才讨厌王雄,疏远王雄,她才越来越不像他心目中的小妹仔,从而使他的情感无处寄托,使他的精神陷于崩溃。因此他想到了海峡对岸的大陆,想到了家乡的赶尸习俗,他要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故乡,去找他日日思念的小妹仔。最后他以自己的死亡来向这无常的命运抗争,以死来维护自己的尊严。王雄是一个死死抓住“过去”不放的人,他的生命完全沉浸在“过去”,将对小妹仔的思念寄托在丽儿身上,希望破灭后便以死来抗争。对于王雄的结局,白先勇有着佛教的悲悯,王雄仿佛是归思泣血的杜鹃。对于王雄的抗争,作者更是礼赞,他将王雄比作怒放的杜鹃花,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正象征着王雄的滴滴血泪,是他因对故乡和小妹仔极度思念而流的血泪,如此地壮丽,如此地动人心魄。类似写对无常命运的徒劳抗争,并以此体现“悲剧的尊严”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的金兆丽,《花桥荣记》里的卢先生,《岁除》里的赖鸣升,《国葬》里的李浩然将军……在无常且神秘不可测的命运面前,他们都是一些凡夫俗子,都是一些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人。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从他们的位置和立场对命运发起抗争,尽管看起来必然走向失败而徒劳无功。白先勇坦言:“我写的常是人的困境,因为人有限制,所以人生有很多无常感。在这种无常的变动中,人怎样保持自己的一份尊严?”(白先勇:《我的创作经验》,第143页。)白先勇没有让他笔下的人物走向佛家“寂静涅槃”的出世解脱之路,而是执着地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与命运进行顽强的抗争,并独自承担着抗争失败的痛苦,在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过程中体现出一种“悲剧的尊严”。
(二)大乘佛教的悲悯情怀与“悲剧的尊严”的融合无间
不过我们在白先勇对“悲剧的尊严”的礼赞的文学叙述过程中,又可以分明地感受到他对笔下的芸芸众生持一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悲悯情怀。当然,这种终极关怀是随着白先勇写《台北人》的过程慢慢地呈现出来的。在《台北人》的第一篇《永远的尹雪艳》里,这种悲悯的味道最淡。閱读此篇时,我们可以感受到白先勇仿佛站在他自己小说人物——“死神”的化身尹雪艳的立场,超然冷漠且无情地俯视着那些卑微又可怜的人。但是随着白先勇对各色各样“台北人”的描写之深入,他在《永远的尹雪艳》里那种超然物外漠视群生的视角,悄然消失不见了。在白先勇的“文化乡愁”的作用下,他对于那些拥有“过去”而脱离现实的人给予最多的同情和悲悯,而对于那些没有“过去”或刻意斩断“过去”、能和功利化的现世合拍的人似乎有些不满和嘲讽。然而即便存着厚此薄彼的态度,我们依然可以在白先勇的叙事语调中感受到一种虽然隐隐约约,但是不绝如缕且逐渐增强的终极关怀——有情皆苦、众生皆可原谅的悲悯情怀。这种情怀或者说情感向度随着《台北人》写作的展开,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到了《台北人》的最后一篇《国葬》,则得到集中的呈现。其中的原因正如欧阳子所分析的:2E10EF0C-E9F6-457D-B424-4CFE6C49C838
白先勇开始写作《台北人》的时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艳,打算冷冷地,完全客观地,高高在上而不赋予丝毫感情地,写几个讽刺社会的小说。可是才写完第一篇,他就已经心软;接着一篇篇下来,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随同小说人物,在心理上亲历了他们个人的生命悲剧,终于彻悟人生是茫无边际的苦海。如此,写至最后一篇《国葬》时,作者仿佛已看破红尘,超升解脱而变得大慈大悲。正如老和尚刘行奇,在两半句话和几滴眼泪里,替芸芸众生担当着无限的忧苦(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第333—334页。)。
《国葬》这篇小说依然写死亡,依然写人物(李浩然将军)对命运的徒然抗争,依然通过抗争的失败突显人物的“悲剧的尊严”。但是,小说对芸芸众生,包括那些没有“过去”的人的嘲讽和不满态度则荡然无存。小说中高僧的出场,极具象征意义。这位高僧原是李浩然将军的一员大将,参加过北伐、抗日、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他因兵败滞留大陆成了俘虏,后又展转香港来到台湾出家为僧。他的坎坷心路和所经历的苦难,仿佛是白先勇笔下芸芸众生以及他自己本人所有心路和苦难的凝缩和代表。《台北人》的开篇献辞如是写道:“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小说的末篇,让一位亲历这个“忧患重重的时代”的高僧出场拜祭李将军的亡灵,首尾呼应,托寄遥深。白先勇让高僧刘行奇在小说的最末处出场,放在整个文本的语境中,读者不难体会,白先勇正欲借此人物形象以大乘佛教之大慈悲心为小说中那些痛苦的亡灵(李浩然、王孟养、王雄、卢先生、娟娟、五宝……)唱一首“安魂曲”,也向那些活着的、苦难重重的芸芸众生,无分别地示以悲悯之心。
西方现代主义在面對一个虚无且荒诞的世界时,强调个人的主体性意志以及个体性抗争精神,并且在这种抗争中重新确立“上帝死了”之后人的价值和尊严。有时候为了突显这种主体性意志和个体性抗争精神,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不免会遇到“他人是我的地狱”的极端处境。就这一精神旨趣来说,强调众生皆有佛性、同体大悲的佛教似乎与之并无相通之处,更谈不上融合。不过,如果仔细探究,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大乘佛教和西方现代哲学某种内在相通的地方。大乘佛教要求菩萨在进入真如境界之后,要不忍众生苦而不独趣涅槃,并发愿重返那个充满无常、虚无的苦难世界,广行六度万行去救度沉溺苦海的芸芸众生。可是芸芸众生无穷无尽,何时能够全部度脱呢?面对这个问题,大乘佛教呈现出其独特的具有抗争性的“悲剧的尊严”。这种“悲剧的尊严”体现在大乘行者“众生无尽誓愿度”“众生无尽,我愿无穷”的弘誓里,体现在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里,这也是佛教悲悯精神的内核。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比较清楚佛教的悲悯情怀和西方现代主义精神中的“悲剧的尊严”,这两种精神旨趣迥异的思想何以在白先勇的小说中能够融合无间地走到一起。白先勇作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优秀当代小说家,在他小说的终极关怀层面典范性地呈现出解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他通过描写人的不屈服于命运、礼赞人的抗争精神进而突显人的“悲剧的尊严”,通过描写众生的苦难来呈现悲天悯人的佛家情怀。写“悲剧的尊严”让白先勇的佛教思想超出中国古典文学(以《红楼梦》《桃花扇》为代表)的寂灭解脱论倾向。而他的大乘佛教的悲天悯人情怀,又使他在强调“悲剧的尊严”的时候,避免陷入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中的“个体的主体性”的困境中,从而使两者互不冲突地交织在一起。这种终极关怀其实就是“视域融合”的产物,它不仅让白先勇在思想水准上超越了两百多年前的《红楼梦》,也超出了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
结 语
袁可嘉认为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文学成就“与其反传统的程度往往成反比”,“艾略特、叶芝、伍尔夫、奥尼尔、普鲁斯特、卡夫卡等则在力求创新的同时从传统中汲取有益养分,加以发展改造,最终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确有成就的实力派。”(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2页。)由此可见,传统并不像有些作家认为的是对自己创作的一种束缚和限制。就白先勇而言,他的文学创作之所以取得很高的成就,就在于他自觉地继承中西两个“传统”。更重要的是通过他带有“前见”的“理解”,让这两个“传统”互相敞开对话,从而形成某种超越两个传统原有“视域”的“视域融合”。本文对白先勇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融合的研究,既是对白先勇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这一问题做一个深入的探讨,也是试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就文学如何继承传统来发展自己这一课题做一个个案研究。
On the Integration of Pai Hsien-yungs Buddhist Thought
and Western Modernist Spirit
CHENG Cai-xia, ZHENG Shao-nan
Abstract: Pai Hsien-yungs literary cre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mbining Chinese traditional Buddhist thought with Western modernist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hermeneutics, Pai Hsien-yungs “foresight” of accepting the spirit of Western modern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Buddhist thought. He replaced the structure of man and God in Western modernism with the impermanence of the present-past comparis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isms “Four Dharma Seals”, Pai Hsien-yungs experience of nothingness and suffering in Western modernism literature is completed through Buddhisms “impermanence of all actions”, “selflessness of all dharmas” and “all omissions are bitter”. In terms of the ultimate concern of literature, Pai Hsien-yung did not embark on the path of Buddhist “silent nirvana”, but replaced it with the fighting spirit of “tragic dignity” in Western modernist literature, and he integrated the compassion of Mahayana Buddhism with “tragic dignity”, showing the realm of “fusion of Horizons” in hermeneutics.
Keywords: Pai Hsien-yung; Buddhist thought; modernist spirit; Taipei People; fusion of horizons
【责任编辑:陈 雷】
收稿日期:2021-10-122E10EF0C-E9F6-457D-B424-4CFE6C49C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