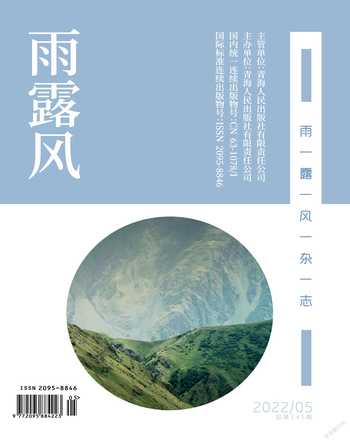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中国
2022-06-19蔡文孟


摘要:《石榴树上结樱桃》是李洱继《花腔》之后的另一部长篇巨作。不同于李洱之前的作品,该小说并没有把视野的焦点聚集在知识分子身上,而是把目光投到了正在发生变革的中国农村。《石榴树上结樱桃》作为一部在近些年来被翻译到国外,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小说,其对人性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揭示。在李洱塑造的乡村权力场中,人们在面对着权力的诱惑时,道德与良知都在备受考验。小说中刻画的人物,看起来似乎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很遥远,但是仔细想想又仿佛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周围。本文将通过分析小说中丰富的文本内涵与作者高超的叙事艺术来对《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小说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并借以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有更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乡村社会;李洱;狂欢化
在20世纪90年代活跃在文坛的新生代作家中,李洱拥有着一种独特的探索精神和更深层面的反思性力量。在消费主义盛行、商业化浪潮裹挟着文学创作的背景下,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先锋与实验的写作姿态,坚守着文学阵地。他在对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以及对人性的挖掘上表现出了卓越的探索,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个人写作风格。从《花腔》到《石榴树上结樱桃》,虽然题材发生了改变,从知识分子与历史革命的关系转变为乡土中国,但是李洱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却没有改变。他曾将自己的写作比喻成“站在地狱的屋顶上凝望花朵”,这种写作姿态包含了对人们生活困境的焦虑。透过《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文本,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一直所保持的写作姿态。在小说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独特观察以及知识分子立场的批判精神。
一、《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叙事手法
作为一个少产的作家,李洱在接受采访时曾坦言:“我一天写七八个小时,但最后能留下一千字就谢天谢地了。为了表达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我要比较深入地了解它们,知道我写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1]李洱的写作习惯,使他有别于其他作家,他似乎更追求文字的练达。《石榴树上结樱桃》作为李洱首部描写中国乡土的长篇小说,他敏锐地感觉到正在发生冲突与变异的乡村现实,并通过极具个人化的叙事手法展示出来。本部分将从狂欢化的叙事技巧与隐喻的叙事策略来分析该文本叙事手法的独特性与高超性。
(一)狂欢化的叙事技巧
狂欢化理论是巴赫金理论学说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否认其在文学创作领域掀起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李洱也将其运用在了《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写作当中。
1.狂欢化理论的来源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灵感,来自欧洲中世纪的狂欢节。狂欢节是一种全民的狂欢,不分地位与才能的高低,人人都可以参与。在狂欢节上有一个加冕与脱冕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国王可能会遭到全民的辱骂与殴打。从中可以看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包含着他的某些政治意识形态倾向,他想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生活的不满。因为巴赫金生活的时代正是斯大林掌政时期,由于政治意见的不同,使得他一直被边缘化,并且处处遭受打压。
狂欢化理论想要表现出的是一种对全民的关注,是一种通过相互接触获得的集体性感受。[2]在巴赫金眼中,以往的文学作品常常被作者自己的独白思想所占据。作者统筹着作品的一切,包括人物的支配,这样呈现出来的人物缺失了主体性。而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应该是多声部的,至少应该是双声道的,作家与主人公的意识也应该相互分离。艺术家可以掌控任何表述,但是在塑造主人公的时候,作者只是一个外力。小说的叙述语言是作家的,主人公的想法却是个人化的,是可以和作家抗衡的。甚至,在作品当中开口讲话的每个人都能和作者平起平坐。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让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段有了新的认识。
2.狂欢理论的运用
李洱在文本中展示出了他高超的写作技巧和娴熟的语言运用能力,把文本的表现力发挥到了堪称完美的程度。面对着官庄村日常生活时空的碎片化,他提前设置了一个核心话语事件,将人们引领到一个共同的时空中,也就是人们一起狂欢的“广场”上,开展彼此的交往活动。在这个“广场”上,人们除了讨论核心事件外,也能谈论其他的事件,无论这些事件是高尚还是卑鄙。而李洱所设置的核心话语事件就是竞选村委会主任,事件的主要线索就是以孟小红为中心的竞选团体联络以孔繁花为中心的竞选团体之外的人们,并利用姚雪娥违反计划生育的事情成功地扳倒了孔繁花。在小说中,“狂欢广场”的变体是村里大大小小的不同场所。它们有的是县里的会议室,有的是某个领导的办公室,甚至有的是某个村民的家里,这些地方都是聚集村民“狂欢”的空间。在这其中开展的会议,有私密的也有公开的,人们讨论的内容有村里发展的大事,也有柴米油盐的小事。
与乡村日常生活狂欢化的时空呈现相呼应,李洱在小说中的语言运用也具有狂欢化。在语言学的意义上,狂欢化理论反常的思维方式让来自民间的俚语、方言、习惯用语等都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巴赫金认为这些发生在民间的俗语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反而在这其中有着顽强的解放性。这是一条崭新的语言道路。语言是具有对话效果的,不仅涵盖了社会的变迁与历史的喧嚣,还与人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在《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就杂糅了方言、职业术语、不同年龄的语言等社会性杂语,这些语言产生的效果就像是一场狂欢的盛宴。
在这场语言的狂欢中,有中国的诗词歌赋,也有外来的西式英语。放羊倌李皓躺在丘陵上吟唱着诸葛亮的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3]草台明星二毛在与孔繁花的聊天中也会借用毛泽东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的诗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除了诗词,在官庄村人们还会学习《英语会话300句》中的西方英语词汇,如:welcome,fans,等等。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既有融入当下意识形态话语的普通话,也有粗俗的方言俗语。所以,我们会看到一幅荒诞的人文景象,官庄村的人们经常操着脏话聊时事政治。“先进生产力”“资源共享”“取长补短”“优化组合”等词汇可能会与“我靠”“滚蛋”“弄拧了”等词汇共同出现在官庄村村民的口中。除此之外,小说中狂欢化的叙事语言还糅合了各种形式与体裁的语言,这其中有歇后语、顺口溜,也有民间俗语与颠倒话。在这一场场语言的狂欢中,反衬出了现代化进程下中国乡村的杂乱与热闹。C262316D-DAA1-47DE-88C8-D1129A69B2C3
(二)隐喻的叙事策略
隐喻被视为修辞学领域中的一种修辞类型,也是让文本更加丰富的叙事策略。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格,是对两个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构建,把作为本体的一个事物表述为作为喻体的另外一个事物。本体和喻体从形式上通过比喻词连接起来,从内容上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似性让这种关联可以被理解。[4]通过阅读李洱的作品,我们能够轻易地发现他善于运用隐喻的叙事策略来暗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
以《石榴树上结樱桃》为例,只是从书名来看就会令人疑惑不解:为什么在一棵石榴树上能够结出樱桃?按照我们的常理来看,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文本的内容,就会发现作者暗藏其中的深意。“石榴”与“樱桃”都曾有着多子多福的含义,人们常用来比喻具有出色繁衍能力的女性,而李洱就是借用这两种植物来隐喻小说中的两位女性主人公——孔繁花与孟小红。在“村干部选举”这一中心话语事件上,孟小红苦心经营,从一直以来的配角,到最后摇身一变成为了主角,成功取代了孔繁花,接管了官庄村,使得“石榴树上结樱桃”这一伪命题得以成立。
除此之外,石榴来自西域,可以视为与中国一起成长的传统事物。而樱桃产自东洋,是一种外来物种。把樱桃嫁接在石榴树上,也隐喻了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融入了西方制度的乡土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乡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西方的制度,被官庄村照搬照抄。例如,村干部选举像西方的总统选举一般,孔繁花在选举之前让张殿军帮她写演讲稿,还请了二毛搭建草台为她的竞选造势。而官庄人的思想也有所影响,他们甚至把孔繁花与张殿军比喻成伊丽莎白女王与菲利普亲王。
小說中每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场面,都能让人看到封闭、落后的中国乡村在现代化道路上与西方的摩擦与碰撞。而这一切,让我们懂得了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现代化的发展切忌操之过急。这也是李洱利用“隐喻”这一叙事策略的用意,让读者去思考文本之外更深层次的含义。
二、《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文本意图
乡土题材,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书写题材。李洱在采访中说过:“我们写了近一百年的乡土中国,用传奇的方法写苦难,其实是把乡土中国符号化了。相对来说,写‘苦难是容易的,而具体写乡村生活的‘困难是困难的。当下这个正在急剧变化,正在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却没有人写。”[5]对于乡土中国的叙述,李洱想要呈现的是它在急剧变化与复杂的现实当中痛苦翻身的样子。所以在《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小说里,李洱用一种近乎原生态的笔触,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乡土的真实面貌与其中的农民群像呈现了出来。这一部分内容将主要从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困境与个人意识在世俗中的消亡来解读《石榴树上结樱桃》背后的文本意图。
(一)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困境
《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故事背景主要发生在官庄村,而官庄村就是现实中国的缩影。与以往的乡土书写不同,李洱没有书写单一的人性善恶与面对文明坍塌的惋惜。小说中出现的官庄村没有鲜明的地理性与文化性,它就是千百个被现代文明冲击着的村落中的一个。《石榴树上结樱桃》直击的是新世纪的中国乡村生活,关注的是乡村中的新变革与变革后的新乡村。[6]
在小说中,围绕着乡村选举,村民的生活被描述得细致入微。但是小说的重点并不突出官庄村的民主政治,而意在揭露人们在毫无波澜的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下对权力的躁动。在这场“保权”与“夺权”的较量中,其实体现出了传统官本位思想在现代化的异变。孔繁花面对着一直充当自己助手的孟小红,虽然欣赏与佩服,但是并不想把村支书的职位拱手相让,而是把孟小红预定为自己的接班人,等自己干不动了再“传位”给她。我们从“预定”和“传位”这两个词语中能够看出,旧思想在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民主政治在官庄村中只是一个形式罢了。再者,是官庄村在经济上的现代化。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工厂的入驻,带来的是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如造纸厂的污水肆意排放等。李洱冷静客观地描写了乡村现代化经济模式窘迫的发展状况。最后是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撞击下,作为孔孟之乡的官庄村,丝毫不见儒学中仁爱与礼教等精粹,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一个个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的官庄村村民。
官庄的现代文化发展路程是艰难的。官庄村呈现出来的现代化,只不过是旧的事物套上了新的外壳,其本质上却还未发生改变。这是官庄村所面临的现代化困境,也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困境。
(二)个人意识在世俗中的消亡
在官庄村悄无声息的权力斗争中,那些在思想上稍有进步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已经被异化,甚至是消亡了。[7]李洱在《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出场的时候有着鲜明的个人意识。在这其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李尚义和裴贞夫妇。裴贞是以一个知识女性的形象出场的,孔繁花在远处就能闻到她身上独特的香水味道。裴贞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喜欢穿花格裙,在天气冷的时候喜欢穿高领毛衣。她甚至还萌生了把自己孩子送出国外赚外汇的先进想法。李尚义在小说的一开始也是以一个谦谦君子的形象示人,他每天出门都会西装革履,会与他人文明地问好。在课堂上他是言传身教的好老师,在村子里他是“计划生育”的榜样。
但是随着故事接近尾声,李尚义与裴贞的形象都发生了改变。我们发现,李尚义把自己家里的旧椅子拿到学校,然后把纸厂办公室的好椅子拿回家里。因为祥生承诺让他当校长,所以他背地里帮祥生拉选票。他的“好老师”形象也发生了变化,在乡教办的旁听课上,他假模假式地表扬学生,但私下里又破口大骂学生,完全没有了为人师表的模样。裴贞也表现出了她泼辣与记仇的一面。因为她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孔繁花让她把胎儿打掉,她因此一直记恨着孔繁花。并且她还监视着官庄村全村妇女的肚子,一发现谁家超生,她就给孔繁花打小报告,因此她也成了“姚雪娥事件”的导火索。
李洱巧妙地把乡村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裂变,放入了官庄村日常世俗生活的进程中,塑造了一系列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交融中前后对比强烈的个体形象,更加立体形象地展示了乡村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生百态,旨在点醒知识分子身上的个人意识与人文情怀。
三、结语
回顾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这短短几十年里发生的变化,可谓是沧海桑田。传统的乡土书写与思考模式,已经不能够准确地描述纷繁复杂的社会现状,这需要作家对当下的乡土中国,能够有新的观察视角与描写的切入点。作为一位优秀的新生代作家,李洱在商业化浪潮的裹挟中挣脱而出。他用独特的叙事手法与深刻的思考力量,向我们充分展示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乡村现状。《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出现,不仅为乡土中国的书写扩宽了一个新的思路,也给读者带来了一种人生哲学上的反思。
作者简介:蔡文孟(1998—),女,黎族,海南陵水人,硕士研究生在读,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张英,李邑兰.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我[N].南方周末,2008-11-06(D21).
〔2〕王春辉.巴赫金"狂欢化诗学"浅析[J].齐鲁学刊,2004(05):159-160.
〔3〕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4〕徐德明.《石榴树上结樱桃》:叙述和隐喻之间的对位与张力[J].当代作家评论,2005(03):52-58.
〔5〕吴虹飞.李洱 作家嘴里开花腔[J].南方人物周刊,2009(12):76-79.
〔6〕梁鸿.“灵光”消逝后的乡村叙事——从《石榴树上结樱桃》看当代乡土文学的美学裂变[J].当代作家评论,2008(05):115-122.
〔7〕邱永旭.论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对乡村生存状态的批判性书写[J].当代文坛,2021(03):73-77.C262316D-DAA1-47DE-88C8-D1129A69B2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