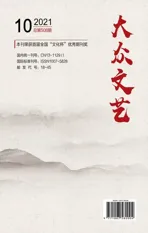《堂吉诃德》时空体分析
2022-06-11赵梓贺
赵梓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00)
《堂吉诃德》中对时空体的运用有多种模式的变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时空形式。《堂吉诃德》的时间是一种超日常时间与日常时间的交织。这个超日常时间首先是一种由机遇主导的时间,小说中的一切故事以及主人公的行为充满着“突然性”与巧合。这种偶然性的机遇是主人公主动追求的结果,使得在其冒险经历中得以穿插他人的故事。与之相对立的是桑乔的完全不同的日常时间,其考虑的是普通人离不开的低下的日常生活。《堂吉诃德》中的空间由两种空间模式构成——道路时空体和广场时空体。道路时空体中的经典情节“相逢——离别”在小说中有广泛的应用,这使得主人公冒险历程中的一切偶然性因素在情节中具有了合理性。每一次的相逢就是一次奇遇的开始,而相逢之后便往往自然地进入广场时空,广场中的各种不同阶级的人物聚集在一起发表议论、进行谈话。道路时空体与广场时空体的交替出现构成了小说的空间变换。《堂吉诃德》中桑乔的小丑形象使小说形成了另一种独特的时空,桑乔在冒险故事中处于“自己世界里的大道”,以小丑的眼观来审视堂吉诃德的冒险行为,以讽刺模拟的方式对荒唐的陈规陋习予以揭示。
一、超日常时间与日常时间的交织
《堂吉诃德》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时间:超日常时间与日常时间,这两种时间在小说中交替出现。堂吉诃德作为追求成为游侠骑士的探险者,在其身上是完全看不到日常生活的迹象的,冒险才是其生活的全部。他的冒险过程是一个以机遇为主导,不断追求机遇,充满“突然性”的时间。而与其对立的桑乔,则是以日常时间为主导,在桑乔身上,我们才能看到在堂吉诃德身上完全不见的日常生活。桑乔与堂吉诃德相反,是追求日常生活稳定的时间。两种时间随着堂吉诃德与桑乔共同的游历,在小说中交替出现。
堂吉诃德经历的冒险,是超日常生活的非常的事变,在这个超日常的时间中,琐碎、低下的日常生活是消失不见的。堂吉诃德仿佛处于独立的世界中,不与任何人发生关系。他的家乡,我们只知道在曼查,具体地方却模糊不清“曼查有个地方,地名就不用提了”;他的家庭及一切的背景信息对读者来说都是未知的——除了一个女管家,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外甥女——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堂吉诃德的全部了。而他的这仅有的两个家人,与他仿佛没有任何的情感联系。桑乔在外出冒险中尚且会不时思念起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妻子写信,想象自己当上总督后妻子和女儿的生活。堂吉诃德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家人,女管家和外甥女与堂吉诃德只是机械地靠人物设定绑定在一起,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联系。“主人公同日常生活无关,也不由日常生活所决定。”通过堂吉诃德的模糊的背景以及亲人的隔绝,堂吉诃德便得以从日常时间中抽离出来,转而进入骑士生活中冒险的超日常时间。
在堂吉诃德的超日常时间中,是由机遇与“突然性”的因素组织起来的。整个的骑士冒险经历是由偶然的同时性和偶然的异时性所支配的:人物偶然地出现在一个地点,又偶然地从该地点消失。偶然与突然成为堂吉诃德生活的日常,成为司空见惯的事。这种偶然性对于堂吉诃德来说,是最如意的境地,其只能在这个充满奇特偶然性的世界里生活,并在奇特的偶然性中保持自己的统一性。
堂吉诃德的经历可以看作日常——超日常——日常的公式。其在自己村庄中可以看作是日常的,但在小说中仅占非常微小的一部分,而小说的主体是其超日常的骑士冒险。由日常——超日常是其人生经历的一次重大转折,而这样的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其发生是毫无缘由地突然。“想到这些,他心中陶然,而且从中体验到了一种奇特的快感,于是他立即将愿望付诸行动。”主人公的骑士游侠生活就在这一瞬间的念头中决定并迅速施行。而在其游侠生活中,机遇仍然在不断发生作用。堂吉诃德一行人恰好在刚刚即将睡觉时遇见了进来旅店的费尔南多与卢辛达,由此才有了多罗特亚与费尔南多、卡德尼奥与卢辛达的相逢;失散多年的兄弟恰好就在这一天同时相遇在同一间客栈,由此又引出了克拉拉与堂路易斯的爱情故事。堂吉诃德的一路上的所有奇遇,都是要靠这种偶然的同时性才能联结,偶然的一次次发生,在日常时间中是不可能的,但在超日常时间中则可以任意地安排时间使其变成常轨,也就不再令读者感到奇特了。而堂吉诃德人生经历的另一次重要转折,超日常——日常,同样充满偶然性。大学士参孙假扮的白月骑士与堂吉诃德决斗,以堂吉诃德的退隐为赌约。这一切来的毫无征兆,事前没有任何情节上的铺垫,“一天清晨,堂吉诃德全身披挂地在海滩上散步……一个同样全副武装的骑士向他走来,骑士的盾牌上还画着一个亮晶晶的月亮。”白月骑士就这样仿佛凭空似的出现在堂吉诃德面前,提出了决斗的要求,而堂吉诃德也同样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整个决斗的过程十分简短:“白月骑士的马跑得比较快,所以,它跑了三分之二的距离才与堂吉诃德相遇……凭借巨大的惯性,把堂吉诃德连人带马装倒在地上,而且撞得不轻”。堂吉诃德只有在这样的偶然性中才能保持自身的存在,一旦回归日常,便是处于病态之中,其一旦想要与这种偶然生活决裂,也就是其破灭之时(塞万提斯也无法想象堂吉诃德如何在日常中生活)。由偶然性开始,又由偶然结束,这便是堂吉诃德的超日常时间。
与堂吉诃德的超日常时间相对的,是桑乔的日常时间。桑乔与堂吉诃德不同,他有着清晰的定位:农夫,其日常生活是清晰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堂吉诃德每天在游历中想的是种种历险经历,而桑乔只考虑最实际的、日常的问题,包括晚上在哪里吃饭,如何过夜,战斗中会不会受伤等等。桑乔虽然与堂吉诃德一起经历冒险,但其始终处于日常时间之中,从未进入到堂吉诃德的超日常时间中去。虽然桑乔在过程中也有同堂吉诃德一样沉溺于游侠骑士小说,但驱动他的是堂吉诃德给他的许诺:答应给他一座小岛做总督。这个现实生活的诱惑才是支撑桑乔冒险的动力,而不是超日常的奇遇。他在冒险中从事的,是与家里别无二致的日常工作,替堂吉诃德备马,照顾堂吉诃德起居等等。桑乔是属于日常时间的,当堂吉诃德被迫结束冒险回到家里后,其脱离了超日常时间便一病不起直至死亡,无法在日常时间中存在;而桑乔则可以继续在家乡的日常时间中继续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堂吉诃德》中表现出的桑乔的日常时间。
堂吉诃德与桑乔一同进行冒险,超日常时间与日常时间便在小说中交替出现。往往在堂吉诃德进行了超日常的安排与幻想之后,随之而至的是桑乔的日常时间。堂吉诃德不可一世地向敌人冲去,桑乔便在之后提醒其注意格斗带来的危险;堂吉诃德把客店当作城堡,把老板娘当作公主,桑乔便在之后考虑如何在客店中饱餐一顿;堂吉诃德主动寻求机遇,而桑乔便惦念着家里的妻子和女儿的安危。
《堂吉诃德》中的时间,便是处于超日常时间与日常时间交织中的时间,当读者刚刚沉迷于堂吉诃德的冒险故事时,桑乔便马上把读者拉回到日常时间中去。这种交替出现的时间与空间的变换一起,形成了对堂吉诃德的游侠梦的披露与讽刺模拟。
二、空间的变换:从道路到室内广场
《堂吉诃德》中的空间显示出从道路到室内广场的变化。道路是小说中主要的空间形式,其典型模式是相逢——离别,这种结构与时间的偶然性的结合使得堂吉诃德可以不断遇见新的机遇,其历险过程得到了空间上的无限延展。道路时空体随后引出广场时空体,这虽然不是在真正的广场而是室内,却具有一切广场时空体的特征。室内广场使得不同阶级的人得以超越空间的界限聚集在一起,使得小说具有了狂欢化的特征。
道路时空体是《堂吉诃德》中主要空间形式,在这一空间中占据主要情节的是“相逢——离别”模式。“不论怎样的相逢,时间规定是离不开空间规定的”相逢的情节是,双方在同一时间里处于同一地方,道路为这一相逢提供了无限可能。每一次的相逢都是一个新的冒险情节的开端,将叙述从堂吉诃德和桑乔身上暂时挪开,聚焦于全新的主人公故事。而离别意味着叙事焦点重新聚集在堂吉诃德身上,其将踏上新的道路,遇见新的故事。通过这一模式,堂吉诃德的冒险故事的时空可以无限延展,其中不断穿插新的甚至可以是与堂吉诃德毫无关系的故事,道路是无限的,小说篇幅也就是无限的。而作者可以随意地把握道路的长短,进而把握小说的篇幅:堂吉诃德可以在出游一年后遇到白月骑士而小说结束,也可以在出行一个月后,完全取决于作者对于道路的安排。
我们可以随意举出几个例子看出道路“相逢——离别”情节的作用。堂吉诃德和桑乔在莫雷纳山遇见了绝望的卡德尼奥,便引出了卡德尼奥长篇讲述自己的故事。这完全是一个独立于主线的全新的故事情节,叙事焦点在卡德尼奥身上而不是堂吉诃德。卡德尼奥故事结束后是堂吉诃德在山中的修行,焦点又回到堂吉诃德身上。堂吉诃德接着在路上遇到多罗特亚,引出多罗特亚的故事;与多罗特亚分离后有在路上遇见了费尔南多等人。堂吉诃德中的偶然的机遇,在道路时空体上具有了无限可能。
与道路时空体相随的是室内广场,在室内广场中不同阶级的人物突破时空的限制,置身于同一空间之中。不同阶级的人物聚集在一起,才使得道路时空体中插入的故事得以连贯起来,故事具有了完整性。最为明显的例子是那个堂吉诃德多次路过的旅店和公爵夫人的城堡。在堂吉诃德多次经过的客店中,不同故事的主人公在这里汇聚到了一起,有理发师、有公主、有战犯、有律师、有圣骑士团、也有被释放的罪犯,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却得以在客店中走到一起。人物的近距离接触使他们各自交代自己的经历,于是卢辛达和卡德尼奥的故事得以完整连贯起来。而广场中人物的相聚不是瞬时性的,是一种类似于道路时空体中的相遇,人物一个一个地出现,在客店这个广场中相遇。战犯讲完了自己和公主的经历,律师才能随后进入客店,战犯与律师在广场中出现,失散多年的兄弟才得以相认,战犯的故事至此才得以完整。这种人物在广场中的相遇,同时也具有狂欢化的性质,堂吉诃德、桑乔、理发师、圣骑士团等等一切人在客店中失去了身份的象征,以平等的零距离的方式进入到狂欢中去。“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人们相聚和交集的地方……都会增添广场狂欢的意味。”桑乔才得以对理发师进行嘲讽,堂吉诃德对执法者进行争执,以至于最后所有人混战在一起,整个客店变成了小型的狂欢化广场。
道路时空体与广场时空体是《堂吉诃德》中主要的空间形式,几乎所有的情节都以这两个空间的变换结合在一起。道路时空体使堂吉诃德的偶然性机遇得以出现,小说的空间形式得到无限延展。广场使得道路中的不同人亲密接触,各个故事得以完整,同时人们失去了身份的象征,不同阶级在广场中狂欢。这两种时空体与小说中交织出现的超日常时间与日常时间结合,形成《堂吉诃德》的讽刺模拟风格。
三、小丑:讽刺模拟风格
超日常时间和日常时间与道路和广场时空体的结合,得以使小说形成讽刺模拟的风格。这种讽刺模拟风格形成的关键是《堂吉诃德》中的小丑形象的观察。小丑角色使得人物失去了私人领域,整个人变成一种公共的人物形象,实现了人物的外在化。同时通过这种外在化,小丑实现了对人物的无情的揭露,形成了讽刺模拟的风格。
小丑是《堂吉诃德》风格形成的关键,这小丑的角色不是堂吉诃德,而是他的仆人桑乔。小丑形象有其独特的优势:其形象上的微不足道使得人几乎不会在其面前有防备。由此其获得一种观察他人的独特视角:独立的他人视角,可以对任何人进行无遮拦的窥视。这使得人物具有了外在化的特征。在广场时空中,人物的外在化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每一个出现在广场中的人都是公共的人。广场是各类人聚集的地方,也是小丑桑乔的天堂,他可以在广场时空体中对广场上的任何人进行无障碍的观察,任何进入广场的人,都是毫无私人生活可言的公共人物——即使有,也会在桑乔的揭示中展现在公众面前。而在道路时空体中,也是由于桑乔的存在,构成了一种“移动广场”,对堂吉诃德的随时的揭露,包括其如何在客店中把老板的女儿当作公主,想象与其恋爱,与杜尔西内亚的“爱情”故事等等。这是纯粹私人生活的领域,读者与作者都是难以窥探的,但小丑桑乔则不同,其角色的微不足道(当然不是作用上的微小)使得人并不会在其面前有任何戒备心,能够全面的无所顾忌的展示自己的全部。堂吉诃德最私密的经历就是因为桑乔才能出现在小说中,由此变成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实现人物的外在化。
小丑桑丘在对人物的私人生活进行窥视的同时,也在对人物进行着无情的披露与讽刺。小丑在这个世界上作外人,不同任何人的生活发生联系,任何人的生活方式都不能令其满意,他们可以看出任何人的反面和虚伪。《堂吉诃德》作为一部充满幽默色彩的小说,其笑声大多数并非来自堂吉诃德的疯狂行为,而是桑乔对堂吉诃德的无情揭露。堂吉诃德一本正经地与敌人大战,是一种严肃的行为,而桑乔随后就对其进行讽刺:所谓的骑士敌人只不过是一个牛群。这是作者选取的独特视角,如果没有桑乔,堂吉诃德的荒唐行为会将所有读者蒙在鼓里,而通过小丑桑乔的转述,我们才能发现堂吉诃德自以为勇敢的行为是多么的幼稚和可笑。正如海涅所说,《堂吉诃德》“把高超的事物和平常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互相烘染衬托”。
《堂吉诃德》的时间和空间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时间上是超日常时间和日常时间的交织出现,在超日常时间中机遇占主导地位;而桑乔则是完全对立的日常时间,考虑与骑士完全不同的日常生活。空间上,道路时空体使得小说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具有无限的延展性;广场时空体则使人物故事得以完整,并为狂欢化创造了基础。所有的这一切要靠小说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小丑桑乔来进行窥视和无情的揭露,《堂吉诃德》由此有了讽刺模拟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