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祖坟
2022-06-09双公平
双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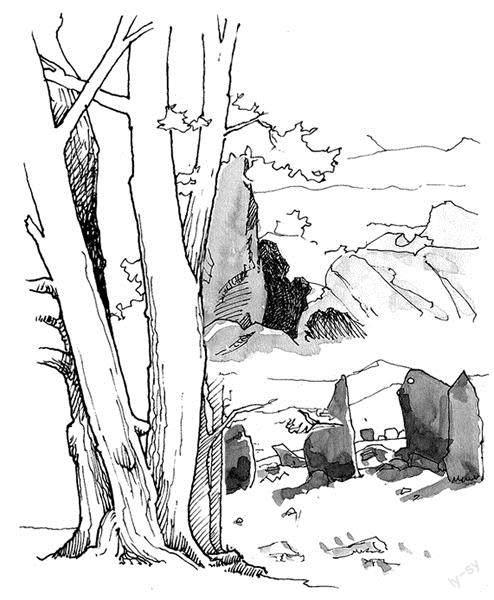
老寿山终于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其实,那个叫李家拐角的地方,那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早已经没有家了。但老寿山每次回去,仍说是回家。“我要回家一趟。”过完年,老寿山对儿子说。儿子正在手机上戳戳画画,头也不抬:“您去年回去待了几个月还没待够啊,今年又要回去?”
老寿山说:“我不是回去玩,我是回去盖房子。”
“盖房子?”儿子这下把头抬起来了,一脸的惊,“我们在武汉不是住得好好的吗,怎么突然想起来回乡下盖房子?”
是突然想起吗?笑话。自从把接送孙子上学的任务完成后,闲下来的时间就多了起来,老寿山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老寿山最怕闲着,闲下来的日子像无底洞,让他摸不到边际,找不到目标。你说看电视吧,自己喜欢看的,年轻人不喜欢,他们爱看的自己又没兴趣,你还能总是和他们抢频道?只有看手机。手机字太小,主要是刺眼,看一会儿就头昏脑涨眼发花。儿子叫他没事学人家打打牌,可儿子不知道,他坐上牌桌就犯困,连牌都出不顺溜。儿子还给他买了几百元一根的钓鱼竿,他耐着性子去钓过两次,鱼没钓着几条,却感觉比挑一天大粪还累。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老家得有房子,没有房子,百年之后就不能入祖坟,自己已经是虚七十的人了,老寿山可不想死后成为孤魂野鬼。唉,儿子还没到那个岁数,这些话说给他听了,他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再说了,儿子儿媳空闲的时候心思都在手机上,根本就没有说话的兴致,老寿山就不想多说什么,说了也白说,搞不好还会引起儿媳妇的误会。老寿山只好笑笑,说:“人老了,叶落归根。”
这个理由显然不充分,儿媳妇也不赞成,说花那么多钱去乡下盖一幢没人住的房子,有这个必要吗?老寿山说:“怎么没人住呢?我去住啊。”看儿媳妇欲言又止,老寿山又说:“我有钱,不花你们的。”
老寿山当然有钱。送走老伴的第二年,老寿山就带着没考上大学的儿子女儿,还有给老伴治病拉下的一屁股债,离开了李家拐角。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不说红火的生意,单是现在住的这套三居室,都由原来的四十多万,涨到三百多万了。
但老寿山就是要回老家盖房子。
老寿山刚把行李放好,旁边座位上来一花白头发老头。老寿山看花白头发口罩上面的眼睛有些熟悉,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花白头发也发觉老寿山在看他,伸手把口罩往下一拉,几乎同时,老寿山也把口罩拉下了,两人相视大笑。
原来花白头发和老寿山同住一个小区,有一天老寿山去超市,碰见花白头发躺在路上,行人见了都绕过去。老寿山本也打算绕过去,看见花白头发扭曲的脸,心里老大的不落忍,就停下来把他送去医院,因此熟悉了,其实互相连名和姓都不知道。
老寿山问:“你这是?”
花白头发说:“我回家呀,把老房子拆了盖新的。你呢?”
老寿山拍拍花白头发的肩膀,朗声大笑:“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花白头发说他多年就有回家盖房子的想法了,在城里待着什么都好,就是闲下来没事的时候不好过。儿子儿媳忙得经常不在家,就是在家也没有多少话讲,连隔壁左右的人都不认识一个,这样的日子,闷都把人要闷死。特别是去年,防疫时小区封了,关在巴掌大的屋里出不能出进不能进,那几个月真是比死还难受。“本来解封后我就要回家盖房子,结果儿子不答应,一直拖到前天才好不容易松了口,我怕他一时三刻变卦,连招呼都不打就溜了。”
花白头发一脸的得意。
老寿山和花白头发的体会是一样的。只是去年封城时,他刚好回老家看望岳母,被滞留在乡下。虽然乡下也封村封路了,但农村天广地阔,开门就是熟悉的人,聊的也是熟悉的事,除了有村干部时不时骑着绑了喇叭的摩托车,喇叭里喊着不要聚集、自觉隔离之类的话语制造点紧张气氛,其实和平时差不了多少。那些日子,老寿山每天都和武汉的儿子微信视频,知道城市隔离的惨状,庆幸自己回到了乡下。虽然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舒心,但却比关在武汉那个鸡笼似的房子里强之万倍。
吸取去年的教训,老寿山这回没有去住岳母家。他在镇上的“如家客栈”开了一间房。稍事休息,想想镇上虽然离家不远,但盖房子耗时长,来来回回的次数频繁,便去花一千多元买了辆电动车。车行对面刚好是一家卖绢花的,看看天色还早,老寿山就去挑选了一些不知道名字的绢花,红的绿的白的紫的都有,扎成大大的一束,又买了些香纸鞭炮,去给老伴“吊清”。
有多少年没有给老伴吊清了?老寿山自从离开李家拐角后,除了亲戚朋友请客,或偶尔在春节前看一看岳母才回家一趟,顺便去老伴的坟头上烧一炷香,但那都不是吊清的时候。去年滞留在家,又因疫情政府号召不吊清,街里连绢花都买不到。本地乡俗,过了正月十五,再到清明节,这段时间是吊清的时节。头年给老伴吊清的时候还是用彩纸扎的“清明吊”,花花绿绿地插在坟头上,微风下晃呀晃,像极了古时候的“宫灯”。二十多年了,清明吊早已被满坟五颜六色的绢花替代,老寿山却再没有给老伴吊过清,想想都觉亏欠得慌。
电动车直驱老伴的坟地。李家拐角的祖坟地原来在塆前。老寿山记得,那是好大一块坟地啊,里头安息着他的爷爷奶奶,还有早早丢下他的父亲母亲。那是在他二十来岁的时候吧,却被公社组织一班人给平了,说是不能让死人与活人争耕地。后来,李家拐角人便把坟地迁到了塆后的一块贫瘠地上。
老寿山来到塆后,在离坟地不远的一个土堆前停下。这是一个将近两人高的大土堆,上面长满了茅草和一些不知名的灌木,人们叫它“始祖坟”。据说不知多少年前,李家的始祖领着儿子女儿,从江西逃难到此地,贫病交加,倒毙在路旁,当时始祖的儿女便把始祖裹張草席,就地草草地葬了,并落下脚来,开枝散叶,繁衍了这片人家。因为住在柳河的拐弯处,人称“李家拐角”,并传下规矩:死者为大,不管是哪里人,若殁于此地,李家拐角的任何人,不得拒绝入土,让死者变成孤魂野鬼。但是有一个条件:不得享用棺木,只准草席裹尸。
老寿山从记事起就听人们讲这个故事,也不知真假,只是人们每到坟地祭拜,都要先到始祖坟前上一炷香。当然,平坟那年也有干部下令平掉始祖坟,但没人敢动,据说有一个愣头青不信邪,在坟上挖了两锹土,当天夜里就发高烧说胡话,以后就没人敢再动这个心思。
老寿山也不例外,点燃一炷香,插在始祖坟脚下参差不齐的香签中,躬身拜了几拜,喃喃自语:“老祖宗保佑啊,我的新屋顺顺当当……”
与始祖坟不同的是,塆后的坟地里都只是半人高的坟包,虽然刚过完年,离清明节还远着呢,就已经花团锦簇了,小北风吹过,沙沙沙沙,列队欢迎着老寿山。老伴的坟很好找,就在第二排的中间,左边有一块空地,杂草丛生,那是留给他百年之后的长眠地,可是他在这里却没有房子了,没有房子就没了家,就不是李家拐角的人了,百年之后就不能在这里安眠。老寿山去年来上过坟,坟上倒也干净,只是坟前的青石墓碑,早已不堪二十几年的风雨剥蚀,早先的黑底红字,几乎成了一块白板,只依稀看得见中间的“桂兰”两个大字。
老寿山抚摩着老伴的名字,说:“桂兰,我回来了,回来盖房了。我知道你在那边很寂寞,等把房子盖好,我就可以回归故土,和你团聚了。桂兰,那时候我们就一起讲讲话,讲些什么呢?就讲你为了这个家累死累活,终于把自己累倒了……啊,你不喜欢听?那就讲你不嫌我穷,瞒着你家大人偷偷和我好,我们总是手拉着手舍不得放开……”
吊清的鞭炮响过,老寿山把电动车骑到内弟门前,从车上提下两箱酸奶。岳母九十多岁的人了,身体还行,就牙口不好,说喜欢喝老寿山买的酸奶。内弟媳妇见了,先是愣怔了一下,然后就笑眯眯地跑过来,口里说着“姐夫你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伸出双手欲接老寿山手里的两个箱子。老寿山知道这内弟媳妇素来是个口甜心苦的人,特别是当年为卖房子的事,内弟媳妇的心里可能永远记恨着他。唉,都怪当年的情况太特殊,不然的话,老寿山说什么也不会为一千元钱得罪内弟和内弟媳妇。后来老寿山也问过自己:你这样做妥当吗?那年儿子看上了武汉的一套房子,老寿山手里的钱不够,找亲戚朋友借遍了还差一万元,无奈之下才回家卖老屋。连房子带宅基估价一万二,虽只打算卖一万,可内弟只肯出九千,结果老寿山咬紧牙关硬没答应。老寿山觉得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拼死拼活,还不都是为了儿女?这样一想,顿觉释怀。
老寿山见内弟媳妇伸出双手来接两个箱子,便把身子一侧,只递给她一箱,另外一箱仍旧提着,一直提到楼房后面岳母住着的小屋里。这是老寿山去年住过两个多月的小屋,他熟悉小屋的每一个角落。小屋里黑黢黢的,老寿山睁大眼睛看了半天才看到,岳母歪在角落的椅子上假寐。老寿山放下箱子,和岳母说了几句话后,这才和内弟媳妇告辞。
内弟媳妇有些诧异:“这天都晚了,你还要去哪儿呢?”
老寿山说:“去旅馆呀,我在镇上的旅馆里开了一间房。”
内弟媳妇说:“都到家里了还住旅馆?这就是姐夫你的不对了,家里又不是没地方住呢。”
老寿山淡淡地一笑。把老屋卖掉后,老寿山偶尔回家需要过夜,的确是住在内弟家,反正只借住一宿,也不管内弟媳妇有什么想法。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去年年前腊月二十八回家看望岳母,老寿山本打算在二十九赶回武汉过年的,武汉却封城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据说很厉害,村干部们都上门登记了,口罩捂得只剩下眼睛,说武汉回来的人是重点,嘱咐老寿山自觉隔离,不要乱跑乱串门,若身体不适要随时报告。一向自恃身体堪比年轻人的老寿山,眨眼之间就似乎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病毒,稍不小心就会钻到谁的身体里边去。
内弟媳妇看向老寿山的眼神都变了,像个神经病似的不住唠叨:“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一大家子人哪!”
老寿山听得心里既烦躁又无奈,说:“这样吧,你去找张彩条布,我到外面搭个棚住。”
岳母不同意:“大冷天的還不冻坏了?你要不嫌我,就去我屋里住吧,我不怕。”
于是老寿山吃住就搬到岳母的小屋里,一直住了七八十天。
大年三十的晚上,村里、塆子里也封了。老寿山正在小屋里同岳母说话,忽听内弟媳妇在门外叫喊起来:“这一封也不知要封到什么时候?光吃饭不干活,上十张嘴呢,金山银山都要被吃空了!”老寿山一时怔住了,内弟媳妇的话就像一个大嘴巴子掴在脸上,脸不疼心却疼。
刚开始,老寿山自觉地待在小屋里不出门,好在有手机做伴,也觉不出什么。当他和儿子微信聊天,得知他们住的这个小区虽无一例病人,但仍要隔离,度日如年之后,实在坐不住了。这天是大年初二,天晴得格外的好,没有了走亲戚拜年的人,塆子里似乎冷清了许多,但各家各户出门在外的人大都回家了,在各自的门口晒太阳,戳手机,你一句我一句地互相传递着信息,聊着互相感兴趣的话题,倒显得比往日更热闹。老寿山从小屋上前来,和看得见的人远远地大声招呼着:“新年好!”“新年快乐!”内弟媳妇见了,忙叫过两个孙子:“快,给姑爷爷拜年。”
两个孩子异口同声:“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这俩臭小子!”内弟媳妇有些不好意思,老寿山摆摆手,哈哈一笑,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两千元钱,说:“回来得仓促,姑爷爷也没带多少,给你们一人一千元压岁钱,也不知这钱上有没有病毒。”
内弟媳妇赶忙接过,笑道:“姑爷爷您说到哪里去了?都是内亲,谁嫌过谁呀!”
望着内弟媳妇满面春风,老寿山心里一扫雾霾。早知金钱能够找回尊严,又何必等到今天?
不过这些都过去了。老寿山说:“这回是盖房子,时间长,住旅馆方便,就不麻烦你们了。”
翌日,老寿山就去找村主任申请宅基地,谁知村主任却说以他的条件不能批。村主任是同学的儿子,老寿山又去找同学,同学再找村主任,仍然没有用。村主任说:“您这明显不符合政策,就算是我同意了,镇里也不会批。”
老寿山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没用,只好去想别的办法。正犹豫着是回旅馆呢,还是去找内弟商议,忽听前面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还有洋鼓洋号,吹着一支不知道名字的曲子。老寿山还以为是结婚的,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支送葬的队伍,孝衣孝帽,花圈孝带,白浩浩地拉了将近半里路远。“这才成个阵势”,老寿山在路边停车观看,心里忍不住赞叹。听看热闹的人讲,这人是服了“助壮素”去世的,他是挑了个好时候。真是“死都要挑个好时候”啊,要是放在去年这个时候,死了也就死了,疫情严重,不准操办,不准请客,简单得跟死了条狗没两样。老寿山清楚地记得,前年,腊月里,老陈哥的儿子去美国出差,女儿便把他从上海接到家中过年,去年正月的一天,夜里突发心梗,还没等到120到来,老陈哥就走了。疫情期间,儿子远在美国不能回来安葬,只好委托妹妹。妹妹把父亲火化后送回老家,老家却因老陈哥户口已迁出,拒绝他入土。无奈之下妹妹又把父亲的骨灰运回李家拐角,放在屋后的自留地头,日晒夜露,风吹雨打。父亲的骨灰一天不入土,女儿的心中就一天不安宁,终于兄妹俩协商好,把父亲埋葬在李家拐角。
安葬的那天老寿山去了,按祖传的规矩,没有草席,就用一块白布代替,把骨灰从骨灰盒里倒在上面包裹了。女儿看着父亲入土连个骨灰盒都不能带去,哭得天昏地暗,晕倒在地。老陈哥是个好人,走的前一天和老寿山说了好半天话。老陈哥说自己很想回家,死后能埋在自家祖坟地里,也不至于做了孤魂野鬼。谁知话音未落,却死在异乡埋在异乡,临了连个骨灰盒都没装一个。老寿山不禁一陣唏嘘,热泪盈眶。
老寿山来到内弟家,内弟果然提供他一个信息:听说塆里的铁柱要卖房子。
不管是真是假,老寿山先去找铁柱。铁柱在北京做生意,已经把房子买了,家里又没老人,就想把老屋卖掉。老屋是个破瓦房,铁柱几乎十多年没回来住过了,并不值钱,值钱的是房子底下的宅基地,铁柱说最少得三万。老寿山说自己只是想盖间小屋养养老,花三万买个宅基地不划算,只肯出两万。但铁柱死不松口,老寿山就给儿子打了一个电话。年纪大了,但凡大事都得知会儿子一声。儿子接了电话,说:“买吧买吧,您说行就行。”老寿山听出儿子生意很忙,人一忙,说话也简单了。老寿山想儿子都同意了,多点就多点吧,免得到处去求人,麻烦。于是最后商定两万八,立下买卖字据,成交。
老寿山立马就开始工作。先是请人把旧屋拆了,然后买来红砖和石灰,请泥瓦工砌墙。砌到半人高,忽然来了一胖一瘦两个年轻人,自称是镇土地管理所的,对老寿山说,这房子违章,不能建。老寿山说了自己的情况,拿出和铁柱签的买卖字据,胖子看了,说:“这是无效合同,城市户口是不能到农村买卖宅基地的。”
当初有了武汉的城市户口,曾经让老寿山自豪不已,谁知这个让老寿山自豪了二十多年的城市户口,在农村却行不通。老寿山只好自认倒霉,在两个年轻人的协助下,找铁柱退了买房款。
这两天,老寿山一时塆前一时塆后,这里转转,那里瞄瞄,神神道道的。突然眼前一亮,他被一块种着蚕豆的田吸引住了。豆苗稀稀落落的,豆花却紫紫的开得热闹。老寿山沿着这块地走了几个来回,嘴里叨叨咕咕的不知在说什么,他知道,这是一块三类地,因为路边的大树遮挡了阳光,种什么都长不好,所以分田的时候,村里给每户强行搭配了一块。老寿山看中的这块地大约有三十平方米,刚好可以盖一间小屋。
好巧不巧,这块地恰好是内弟的。听老寿山一说,内弟倒没吭声,内弟媳妇却说:“您别看这块地不起眼,每年的收入可不少。我们不像姐夫做生意,还指望它吃饭呢。”
老寿山说:“你放心,我肯定不是白占,我会按规矩算钱。”顿了顿,又说,“这块地历来长不好庄稼,撑死一年也收不了五百元。那就按五百元算吧,二十年,我给你一万元钱。”
内弟媳妇说:“那是种小麦。明年我们打算种黄蜀葵,一年起码可以收千把元。”
“这块地不向阳,种金子都长不好。”老寿山说,“那就按一千元钱计算吧,我付两万元。”
“这多不好意思。”内弟媳妇说,“其实姐夫还是赚了。就你这身体,三十年都不够活。”
老寿山笑道:“我都虚七十了,二十年就是九十,够呛。”
内弟媳妇说:“现在九十算什么?你看我妈九十多了,还硬朗得很呢。”
“那就暂定二十年吧,”老寿山说,“活到九十岁拆房子,活不到九十岁也不退钱。”
让老寿山没想到的是,才刚刚开始砌墙,一胖一瘦的两个年轻人又来了。老寿山说难道我们在自家田里搭个小屋也犯法吗?胖子说:“没经批准的建房都是违章建筑,必须拆除。”
老寿山据理力争,胖子静静地听着,瘦子却不耐烦了,说:“这些都不是理由。屡教不改,没罚你款就算是客气了。”
房子盖不成,老寿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仍然很忙,说盖不成那就回武汉呗,哪里的黄土不埋人?老寿山不作声,沉吟半晌,悄悄地把电话挂了,又开始了塆前塆后地转悠。有人同他打招呼,他就拉着人家,向人家大倒盖房子的苦水。开始还有人敷衍着,渐渐地,人们见了他就开始绕道。
人们发现,老寿山每天必去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始祖坟,另一个是老伴的坟地。
在高大威严的始祖坟前,老寿山有时跪下磕头,有时抱拳作揖,一般都是恭敬地立在坟前,嘴里喃喃着,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只听见坟上茅草沙沙有声。
在老伴的坟地就不一样了。老寿山坐在老伴坟边的那块空地上,到底是春天了,才过几天,空地上青草如丝,间或点缀着一些不知名的细碎白花,颤颤巍巍的,像是欢迎他的到来。这本是留给他的栖息地,可如今却不知能不能回来。老寿山在上面一坐就是半天,一边同老伴说话,一边伏在老伴的坟上,细细地清理坟上的杂草,一棵一棵,一根一根,薅得如此轻柔和小心,就像那时节给老伴挠痒痒,生怕一不小心给挠疼了,抓伤了……
责任编辑/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