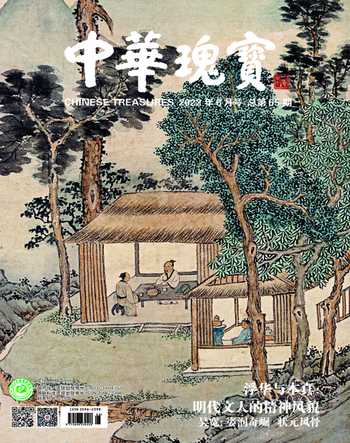经学当从注疏始
2022-06-08马银琴



《毛诗正义》作为《十三经注疏》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经典之一,也是历代士人研习《诗经》的必读书。本文希望通过对《诗经》学史的概述、《五经正义》的编撰刊行及其学术贡献的阐发,能为读者阅读《毛诗正义》提供指南。
唐前《诗经》阐释史
《诗经》在先秦时期最通行的名称是《诗》。《诗》最早是由周代仪式乐歌汇集而成的歌辞本,但同时也被用作国子教育的课本。因此,除了从西周早期就已经出现在乐官系统传承的歌辞本外,接受国子之教成长起来的公卿大夫也对这些歌辞相当熟悉。西周中期,人们开始在言语中征引乐歌的歌辞来阐发道理,如西周穆王时祭公谋父向穆王进谏,就曾引“周公文之《颂》”来阐述“先王耀德不观兵”的道理。
至春秋时代,诸侯会盟频繁发生,为《诗》的使用提供了另外一种形式,这就是外交聘问之时的“赋诗言志”。古已有之的引《诗》证事与春秋时代流行起来的“赋诗言志”,让《诗》之“义”获得了空前的关注,“《诗》《书》,义之府也”的观念由此形成。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孔子出于恢复周道的目的,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诗》三百,孔子皆弦歌之”。但是,孔子“弦歌”的教授方式并未能让《诗》继续以礼乐化的乐歌方式存在,战国之后,《诗》在儒门弟子的传承中最终走上了德义化而非礼乐化的道路。至汉朝建立,文化复兴,《诗》分四家,其中齐、鲁、韩三家被立为博士,尊为官学,“自谓子夏所传”的《毛诗》未得立,仅在河间献王刘德的推重下,小毛公毛苌被立为河间献王博士。
谶纬化的三家《诗》在汉末先后走上了衰微之路,一直在民间传承、坚守训诂本位的《毛诗》之学,经大儒郑玄的笺注后开始大行于天下。郑玄笺《诗》,虽以《毛传》为本,但其中仍有不少与《毛传》不合的解释。毛、郑诗学内容的异同,在三国时期引起了以魏国大儒王肃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反驳,由此引发了《毛诗》之学内部郑学与王学的抗衡。一直到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孔颖达受诏修撰《五经正义》,就《诗经》而言,據《毛诗》,“因《郑笺》为《正义》”。官方意识形态的介入,终于平息了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郑、王之争,形成了“论归一定,无复歧途”的唐代《诗经》学新局面。
《五经正义》的编撰刊行
编撰《五经正义》是一项庞大的学术工程,因此,孔颖达在编撰之初就确立了以前代学者义疏为底本的编撰原则,对此,他在各经正义序中都有明确的交代。《毛诗正义序》在详细列举魏晋至唐初七位最重要的义疏学者之后,特别推出刘焯与刘炫二人,赞他们“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并明确表示刘焯、刘炫二人所作“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这就是说,《毛诗正义》是以刘焯《毛诗义疏》和刘炫《毛诗述议》为底本删定而成的。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学者的证实,因为从《毛诗正义》中,仍然可以辨识出二刘旧疏、唐人补疏等不同的文本层次,也存在着所标起止分章与疏文不合等文本内部的矛盾。这可以说是《毛诗正义》编撰不精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些问题的存在,又恰恰说明了《毛诗正义》集南北朝至初唐数百年间《诗》学成就的集大成属性。
《毛诗正义》撰成之初,仅以单疏本,即只标经、注起止,不与经、注合刊的形式流传。甘肃敦煌出土的斯坦因498号《毛诗正义(大雅·民劳)》残卷,于经、注仅标起止,不出全文,经、注之起止用朱书标识,《正义》用墨书书写,由此可以看到《毛诗正义》在唐代流传时的样貌。之后,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毛诗正义》单疏本作为《五经正义》的组成部分在北宋太宗时被刊刻印行,流传渐广。
至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出于方便阅读的需要,绍兴府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司将原来单行的《毛诗传笺》与单疏本《毛诗正义》合二为一,把《毛诗正义》的疏文一段一段插入经注正文当中,形成了第一部《毛诗正义》注疏合刻本。其版式为半叶八行,故称“八行本”;其本刻于越州,又称“越州本”。
注疏合刻方便经注疏对读,更符合读者的阅读需要,于是成为经书注疏版本的主流。至南宋中期出现了把陆德明《经典释文》分散插入注疏合刻本中并附有释文内容的经注疏合刻本。其版式为半叶十行,故称“十行本”;因刻于福建建阳,又称“建刻本”或“建刻十行本”。之后,宋刻“十行本”经元、明、清三代多次翻刻、补修、重刻,作为《十三经注疏》之一,最后经阮元校勘并再次刊刻印行,成为流传至今、影响最大也最为通行的《毛诗正义》版本。
《五经正义》在唐初的撰著,本来就有统一经学内部分歧的目的。《毛诗正义》被编成之后,一直到宋代,都被用作明经取士的课本。即使在朱熹的《诗集传》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教材之后,《毛诗正义》仍然在很长的时期内被当作重要的参考书,在适应科举考试的政治需求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明代《五经大全》颁行之后,《毛诗正义》才正式退出科举的舞台。但是,《毛诗正义》“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的学术特征,至清代又一次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校勘刊行《十三经注疏》的阮元就说过:“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重刻宋版注疏总目录》)这段针对群经注疏的言论,也适合于《毛诗正义》。通过读经传注疏而知大义、明是非,本来就是经典阐释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毛诗正义》的学术贡献
《毛诗正义》的意义与价值,不仅限于具有统一思想的教科书的意义,孔颖达还通过疏解经义的学术实践,再一次强化了学术研究中“实事求是”的意义与价值。“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是《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对立《毛诗》为河间献王博士的刘德的评价,孔颖达据《毛诗》、因《郑笺》而作成的《毛诗正义》,又被阮元视为“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的优秀读本,正是因为孔颖达撰成此书是对“实事求是”精神的传承。他在面对《毛传》与《郑笺》解诗时客观存在的矛盾时,从不随意断言优劣。他一方面旁征博引、依《诗》立义,另一方面努力为《传》《笺》释义寻找证据,使之更加圆融、通透。正是这种基于事实的求是精神、严谨而包容的学术态度,才成就了该书“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的学术成就。6082ADD5-E0B6-4BED-A151-861268587491
《毛诗正义》对经学阐释十分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在疏解《毛诗序》的“六义”时,以“三体三用”的区分,消解了《毛诗序》说“诗有六义”,却只解释“风雅颂”而不涉及“赋比兴”的做法留下的矛盾与问题。《周礼》有“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与《毛诗序》“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内容相同。郑玄既注《周礼》,也笺《毛诗》,但他仅解释了“六诗”而未及“六义”。《诗经》有“风雅颂”,于是,“何诗近于比赋兴”就成为一个问题。郑玄的弟子张逸提出这个问题之后,郑玄给出的回答是:“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郑小同《郑志》)这个解释符合“赋比兴”与“风雅颂”并称“六义”的逻辑,却无法符合《诗经》的作品结构。于是,经过一番梳理与改造,在郑玄的阐释中仍然并列的“赋比兴”与“风雅颂”,就变成了孔颖达阐释体系中属于不同意义层次的“三体”与“三用”: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
“三体三用”,也有人称之为“三经三纬”。孔颖达正是看到了“六义”中“风雅颂”与“赋比兴”的不对等,才基于《毛诗序》的语义框架,兼及《诗经》篇章的实际情况,对已经发生分化的“风雅颂”与“赋比兴”做分类论说,从而消解了从“六诗”到“六义”过渡过程中出现的矛盾,让以《毛诗序》为基础的儒家诗学阐释系统真正建立起来并趋于完善。同时,孔颖达接受六朝文论的影响,把“赋比兴”明确视为诗歌的表现手法,在儒家《诗》论的框架中完成了“赋比兴”由《诗》学阐释理论向文学创作论的转变,对后世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此之外,孔颖达对中国诗歌思想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诗学思想史上“诗言志”与“诗缘情”两大命题的深度整合。在《毛诗正义序》中,他首先充分肯定了“诗”的政治功能,“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这是对传统“诗言志”观念基本内涵的继承。紧接着,孔颖达又充分肯定了“诗缘情”的合理性:“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无为自发的歌颂与怨刺,实际上都是外界环境引发内心情感波动之后的自然表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畅怀抒愤”是对诗歌抒情功能的充分肯定,“塞违从正”则是对诗歌政教讽谏功能的重申。它们原本是区别“诗缘情”与“诗言志”两大诗学命题各自不同的价值导向与追求的核心要素,而孔颖达通过“作之者”与“闻之者”的区分,就让“畅怀抒愤”与“塞违从正”之间产生了自然的关联。“诗言志”与“诗缘情”这两个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段、具有不同诗学内涵的命题因此得以相互补足,在相互融合、相辅相成中建构起了新的诗学理论,从而奠定了唐代乃至整個后世诗歌理论的基础。
马银琴,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6082ADD5-E0B6-4BED-A151-861268587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