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场”的文学性表征
——评《可可托海往事》的非虚构创作
2022-06-06王宇阔
□ 王宇阔

可可托海的冬天
董立勃是当代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多年以来他笔耕不辍,将个人的生活经验与文学想象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创作了一批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背景、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实生活的“垦荒小说”,为读者呈现出新疆独特的地域风采。2021 年9 月,董立勃携其新作《可可托海往事》再次走进读者的视野,他在该小说的创作札记中说:“这是在为可可托海立传,它的价值不仅是文学的,还应该是史学的,是一部有关可可托海的编年史。”
可可托海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在它的矿区里蕴藏着锂、铍、钽、铌、铯等多种稀有矿物,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曾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在六十年代中苏断交之际,从可可托海出口的矿石资源为中国政府偿还了三分之一的国际债务;另一方面,这些稀有的矿产资源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第一艘核潜艇的成功试航……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都有可可托海的一份贡献。
在《可可托海往事》这部长篇小说中,董立勃的写作中有意识地借鉴了非虚构的创作手法,通过再现20 世纪50 年代新疆中华儿女们在可可托海矿区为新中国建设而挥洒青春的场景,展示了可可托海在困难时期是如何扛起了为国家做贡献、为国家分忧重任的。
一、作为“记忆之场”的文学文本
可可托海是自然馈予中国的宝藏,但如果没有将这批宝藏发掘出来的人,再优渥的自然条件也无法发挥其自身的价值。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有数以万计的建设者来到可可托海矿区,他们怀揣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面对严酷的现实,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据统计,有700 多位建设者的忠骨埋葬在可可托海。他们的任务在当时被列为国家的最高机密:不能对外公开,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地图上,甚至都找不到“可可托海”这个名字,外界对它知之甚少。
到了上世纪90 年代,随着市场需求、资源储量的变化,可可托海矿务局连年亏损,这个地方便开始冷清起来。直至前几年,党中央重新加大了对新疆可可托海矿区建设的扶持力度,矿区小镇的面貌也得以焕然一新。当下,“可可托海”作为一张旅游名片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其“红色精神”的内核也开始为大众所熟知。
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关于当年拓荒的记忆,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淡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托海往事》以文学的方式为那些曾经在这片热土上奉献、牺牲的英雄们重塑了一个具有纪念碑意义的“记忆之场”,成功建构出指向“社会主义建设先驱者”的集体记忆。可可托海矿区的拓荒者,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奋图强的“见证者”,通过这部小说,读者了解了拓荒者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经历的艰苦历程。读者的阅读参与必然伴随着一种情感在场的状态——在关于可可托海矿区的集体记忆中。读者也通过这个“记忆之场”的小说文本真切地感受到建设者们那种为了理想而奉献、牺牲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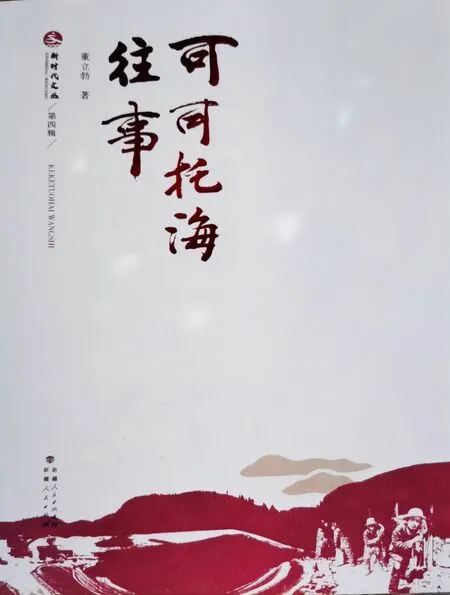
长篇小说《可可托海往事》封面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诺拉说:“记忆之场就是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这些统一体已经转变为任意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元素。”董立勃这种现实主义式的非虚构写作手法,也存在着一个象征性元素:《可可托海往事》成功地通过“见证”这一中介,将拓荒者的精神与读者的情感联结起来,成为拓荒精神的不朽象征。
“记忆之场”是包含集体记忆的场所,可可托海矿区本身就是历史事件的记忆场,当历史事件被作家书写成作品后,这个作品就成了历史事件之“精神”的记忆场。这个精神的内涵始终是指向人的,是指向那些在可可托海矿区将自己全部的青春奉献给祖国建设、勇于接受挑战、不惧牺牲的拓荒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作品就如同是作家为拓荒者树立的一块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其所纪念的不仅仅是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更是那能够唤起后来者积极向上,为祖国效命的牺牲精神。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董立勃“为可可托海立传”的写作无疑是具有当代价值和历史意义的。
二、历史与人性的辩证统一
《可可托海往事》的文学性在这个“记忆之场”中是如何实现的呢?董立勃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小说是写人的命运和情感。没有人,再美的山水也是荒凉的,再富饶的矿山也是死寂的。可可托海发生的大事件,不用我写,很多人都知道。可大事件发生时,作为具体的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他们的情感变化以及命运的转折,这些大历史会忽略的东西,地方志不会记载的东西,正是我们小说家要展示的主要内容。”在他看来,文学中的“人”正是区别于现实和历史的地方,而对人物情感的叙述,以及对人物命运的书写,正是《可可托海往事》文学性的体现。
首先,就小说人物的情感而言,董立勃擅于通过“爱情的发生”来展现爱情的纯粹性,这种纯粹性的体现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同时更是符合人性逻辑的。孙惠兰和赵义勋二人因在事业上都有着强烈的追求和明确的目标,因为二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信念合拍而互生好感,但孙惠兰担心恋爱会阻碍自己在事业上的进步,坚持晚恋晚婚,拒绝了赵义勋的表白。当她看到曾经的室友张秋凤婚后的幸福生活后,她的观念开始动摇,试着主动和赵义勋相处,直到她感受到恋爱的美好时:“孙惠兰看着赵义勋,心里一阵冲动,要不是本能的羞涩阻止了她,她差一点就要在赵义勋的脸上亲一口了。”“不是孙惠兰失去了理智,实在是这种摆布太难抗拒,一下子就让她整个身体酥软了。”孙惠兰才幡然醒悟,发现对事业的追求和爱情并不矛盾,于是毅然决然地要与赵义勋结婚,这时两个青年人将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和对婚姻幸福生活的追求统一了起来。
这种爱情观还明显地体现在余明杰和冯青身上:余明杰被冯青的优秀气质所吸引,但是冯青的援疆计划只是临时性的,余明杰认为两人之间并没有未来,所以就把对冯青的爱慕压抑在心中,然而这种暗恋逐渐到了思之如狂的地步。他们在一起工作、骑马、看电影,当冯青遇到狼群的袭击时,余明杰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事后他对冯青讲,我宁愿和你一块儿被狼吃掉,也不会扔下你自己跑掉。冯青回北京的前夕,在对余明杰女友是谁的问题再三追问下,余明杰才向她袒露了自己的一片痴情,于是冯青深受感动,放弃了回大城市的机会,愿意继续留在可可托海,与他共同厮守在这片土地上,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可见,董立勃在叙述男女爱情时,把情感、人性置于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之中予以表达。

向可可托海建设者致敬(雕塑作品)
在这部小说中,董立勃对人物性格观念的刻画也充满了某种辩证意味,张秋凤与孙惠兰两姐妹性格特征的差异从一开始就有鲜明的对比:在孙惠兰看来,张秋凤在感情上过于开放,她喜欢去舞厅,喜欢参加各种娱乐活动,这些势必会影响工作。张秋凤同时与两个男人谈恋爱,孙惠兰总担心她会“犯错误”,同时也不断警示着自己要事业而不要恋爱,可见孙惠兰把个人的感情生活与工作完全割裂开来,这种偏执正是来自于她内心深处的保守观念。反观张秋凤,她并没有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和事业对立起来,她结婚后仍然获得了先进个人的荣誉,在事业上也稳步前进。孙惠兰后来正是受她的启发,才逐渐开始反思。从这个角度看,孙惠兰与张秋凤二人所呈现出的观念差异正是一体两面的,她们是互补的,表征出发展的“人性”逐渐完善的过程。
《可可托海往事》表现出来的情感之纯粹体现了董立勃所追求的“真善美”:“它不是概念化的、生硬的,它是情感原野上绽放的花朵,人性山谷里温暖的河流。”除此之外,董立勃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故事一定要有悬念,要有逻辑性,要合乎情理,却不能太平淡。”在小说《可可托海往事》中,体现在他对人物命运的极其精妙的把控。与高歌猛进的时代相比,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具有浓厚的悲剧意味,这种悲剧意味是一种结构性的文学设计。陈志远、赵义勋、孙惠兰、安怀民、柳芭、巴克拜尔、肖长峰……小说中这些人物,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牺牲的还是活着的,无论是因为个人性格的缘故还是由于历史时代的原因,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悲剧色彩。

可可托海矿区遗址
这符合文学的真实性原则:这种真实性一方面体现在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建立在人性与事件情理协调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作家创作的情感倾向上,即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对“小人物”的命运以共情和反思的方式加以审视,在宏大叙事中对个体的话语报以悲悯的情怀。正是由于这种悲剧意味,《可可托海往事》中的人物被作者刻画得栩栩如生,他们不单单是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单向传声筒,还具有了文学审美的典型性,更真实地还原出了历史场景中的人民。
三、《可可托海往事》的文学社会学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要求作家“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其实,董立勃对人物塑造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他以非虚构的文学创作手法,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在一个特殊的场域中,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理想的存在状况,讴歌了人性的美好,传达真善美,反映了人民在苦难面前永葆坚定理想和斗志的乐观姿态。这些都激励着读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各个民族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因此造就了新疆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董立勃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将新疆的风土人情展现给了世界。作家韩少功对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有这样一个看法,他认为“硬度”和“温度”在文学文本中是可以兼容的:硬度来自于作家记录历史的冷峻和理性,而温度来自于作家文学想象的柔软和激情,所以“文学既是认知世界的手段,也是让世界存在的目的。通过文学我们能够打开世界的黑洞,将背后的真理之谜揭示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可可托海往事》的文学社会学价值具有双重维度:一个是文学的,它基于文艺反映观上;另一个则是历史的:它以文学的书写建构出一个能够存放集体记忆的“记忆之场”,它既是对“可可托海矿区如何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这一事件的见证,又是新中国拓荒者、建设者奉献、牺牲、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之精神的见证。
“记忆之场”是唤起人们集体记忆发生的场所,它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对历史使命感的延续和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文学社会学家洛文塔尔强调:“文学社会学家的任务是将作者想象的人物和情境之经验与它们所产生的历史气候联系起来。他必须将主题和文体手段的私人方程转化为社会方程。”从文学社会学的视角看,董立勃的写作正是一种将个人对于可可托海的感受很好地融入到历史与时代气候的呈现。他采用的非虚构写作所形成的“文学见证”与“记忆之场”使得其个人化的文学观察转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社会关注,从而赋予了可可托海更大的社会场域,成为国家发展与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文学标本。小说的结尾处,董立勃承认,那个具有“记者”和“小说家”双重身份的“叙述者”就是“我”,也就是他自己。
半年前,一位作家不知通过什么关系了解到孙惠兰曾经在可可托海度过了整个青春岁月,就来到她家,与她连续聊了一个星期。这位作家对她表现出的敬意,让她对他不再有所保留。她甚至把从未给别人看过的、当年写的日记都拿了出来。她还给他唱了好几首王洛宾的歌。她把藏在箱子里的黑白照片,全都拿出来,足有一百多张。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吴成朋照的。她的记忆力没有减退,还能清楚地说出自己经历过的许多事情的细节。
孙惠兰问作家,什么时候能把可可托海的故事写出来。作家说,您是我采访的第五十七位可可托海人。我真的很想把可可托海的故事写出来,但不知道能不能写出来。
《可可托海往事》可以说是董立勃在近几年的文学创作上取得的重要突破。十五年前,因《白豆》闻名于世的董立勃在《小说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作家谈《我的文学路》,他在文中表达了自己的创作理想。而今天,董立勃再次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惊喜,这部长篇小说既可以被看作是他文学理想的拓展,也可以看作是他文学创作的“新的开始”——尽管董立勃先生已经65 岁,我们从《可可托海往事》中仍能看到他向“非虚构写作”转型的希望和潜能。
①董立勃:《为可可托海立传—〈可可托海往事〉创作札记》,《新疆日报》,2021 年9 月16 日,第8 版。
②王雪迎:《可可托海的秘密》,《青年时讯》,2019年6 月7 日。第12 版。
③(法)皮埃尔·诺拉著,黄艳红等译:《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76 页。
④董立勃:《为可可托海立传—〈可可托海往事〉创作札记》,《新疆日报》,2021 年9 月16 日,第8 版。
⑤董立勃:《可可托海往事》,新疆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24 页。
⑥董立勃:《可可托海往事》,新疆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29 页。
⑦董立勃:《我的文学路》,《小说评论》,2006 年第5期,第34 页。
⑧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10 月15 日,01 版04 版。
⑨贾永平:《走向小说的后台——论韩少功〈修改过程〉中的叙事哲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1 年第4期,第290 页。
⑩Leo Lowenthal: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New York:Routledge,2017,p.x.
⑪ 董立勃:《可可托海往事》,新疆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0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