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钟娜:翻译萨莉·鲁尼更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边缘
2022-05-30王佳薇
王佳薇

作者的影响
在豆瓣搜索钟娜的名字,结果很快指向萨莉·鲁尼的小说,译者名字并排列于作者之后——这是过去五年钟娜最为人熟知的身份。萨莉·鲁尼出了三本小说,钟娜也翻译完成三本。
是否喜欢,是否有时间,是钟娜决定要不要翻译一部作品的唯二标准。2017年,钟娜收到出版人彭伦发来的《聊天记录》书稿,她一边读一边翻译,觉得作者“简直是个天才”。
与后来同样流行全球的女作家费兰特相比,“鲁尼的叙事更当代了。”彭伦说。2016年底,他在爱尔兰文学基金会的建议下购买了鲁尼作品的版权,邀请钟娜作为译者。在他眼中,作者和译者年龄相仿,又都是写作者。
“她(鲁尼)对细节的筛选,语言的干净度和精准度都让人耳目一新。”钟娜说。彼时她还是纽约新学院(The New School)创意写作课程的学生,初尝英文写作,对欧美的文学生产体系兴味盎然,与《聊天记录》中的主人公弗朗西斯一样同在文学社实习。
“作为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想要进入成人世界,但是被里面灰色地带的部分困住了。弗朗西斯其实不太懂梅丽莎和尼克之间复杂的情感联结、开放关系背后的暗流。那是由成人中产阶级异性恋缔结而成。那是她、一个刚刚分手的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聊天记录》中,鲁尼描绘了一段阶级差异显著的婚外恋——21岁的女大学生弗朗西斯与三十多岁的中年演员尼克——他们一边互相吸引,一边又害怕改变,渴望固守自己所拥有的生活方式。
翻译时,钟娜觉得自己深深地与爱尔兰大学生弗朗西斯共情。那些独属于成人世界的更尖利、复杂和危险的部分,她尚未完全谙熟。
2017年初鲁尼还是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还没有“千禧一代的首位伟大小说家”、“社交媒体时代的塞林格”等标签加持,钟娜翻译得自由,没有压力。她以为《聊天记录》会像她翻译的上一本译作般寂寂无名,等待爱书人的耐心探索,却没料到,其后几年,她的毕业、工作、写作、翻译都始终很难绕开鲁尼的名字。
“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萨莉·鲁尼,那么你要小心。她的问题、她的态度、她的视角,一旦吸收就很难忘掉。你无法撤销她对你施加的影响。某种程度上,鲁尼的小说像今天的手机,前置镜头像素紧追后置镜头。然而不同的是,她的小说世界里,前置镜头没有美颜功能。你如果想要凝视自己,就必须接受自己的全部——自卑、虚荣、丑陋,甚至平庸。”钟娜说。
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
谁在阅读萨莉·鲁尼?
美国Interview杂志采访了多家纽约书店:西村书店BookBook发现很多是纽约大学的学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布鲁克林书店Greenlight说是白人女性,特别是年轻白人女性,偶尔也有年长的男性,或带着孩子进来的妈妈;曼哈頓McNally Jackson书店指出,店里最畅销的书目是《聊天记录》,其次是《正常人》,购买人群类型多样。
复旦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包慧怡曾在鲁尼新作中译本分享会上提到,鲁尼“呈现了一种样态——一个年轻人如何通过写作、叙事在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在失序中守住一些东西。而这个东西本身也许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她让我们看到她自己如何与一地鸡毛状态的不和解”。
2019年春天,钟娜在布鲁克林McNally Jackson书店与鲁尼有过一面之缘。当日,许多人慕名而来,人满为患。在那里,她见到了装扮十分布鲁克林的年轻人,“就像博比、弗朗西斯。”当然,也有穿着像梅丽莎与尼克夫妇那样的时髦中年夫妇。
连排的椅子被围得水泄不通,鲁尼坐在一张桌子后,衣着朴素却“颇带着知识分子气息”,言谈奔放、热情,却不失犀利。
《聊天记录》出版一年后,鲁尼乘胜追击,出版了第二本小说《正常人》。在书中,鲁尼将笔触聚焦一对小镇恋人:康奈尔和玛丽安在高中相爱,却因在学校的阶级位置不同而忽远忽近,关系保持着某种拉锯。
如果说《聊天记录》处理的社会关系更为复杂 ,《正常人》或许更能引起读者的共情。“当两个小镇青年通过教育来到大城市,他们之间虽然有阶级差异,但更重要的是心灵相通。他们试图长大,但还没有抵达成人阶段。而《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描绘的关系则是当这群年轻人进入30岁后不得不面对的生活。”钟娜说。“女性要面对生物钟的衰竭,男性要面对事业成就。摆在大家面前共同的问题是,是否要缔结一个家庭关系?是否要向世界证明自己有所成就?”
2021年9月,鲁尼第三本小说《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问世(中译本2022年6月出版)。新作延续了鲁尼一贯的风格,以两对男女的关系展开——小说家艾丽丝在经历过一次精神崩溃后搬到了海边小镇,开始与蓝领工人费利克斯约会;刚经历失恋的编辑助理艾琳重新开始与童年时的玩伴西蒙约会。小说一半篇幅是情节发展,一半是艾丽丝与艾琳的邮件往来。
写作本书时,正值新冠大流行暴发之初,鲁尼刚从纽约回到爱尔兰,居家隔离,专心写作。在书的结尾——当艾丽丝与艾琳一遍遍通过邮件往来探讨文明的失落与消费主义的问题之后——四人已将近一年没碰面,疫情造成城市封锁,他们不得不困守家中。他们还能否相信,一个美丽世界存在的可能?

萨莉·鲁尼
人:人物周刊 钟:钟娜
“踩在时代脉搏上”的保守转向
人:读《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时,感觉鲁尼把视角拉得更远了。
钟:所有作家可能都在试图抽离自身情况,以第三者的眼光拉远去审视自己及周围的一切。前几日我读卡夫卡的短篇集,其中一则“Description of a Struggle”(直译为“一次战斗纪实”)的开头写道,“人们穿着礼拜日的衣服在石子路上信步,庞大的天空下,不远处的群山,伸向更远处的群山。”很妙,他用简单的语气让你一下子看到生活的无聊和限制。作家得是抽离出来的人,才能看到自己深陷于一个怎样封闭的世界。我觉得鲁尼就是这样的人,哪怕处于亲密关系中,她也会随时抽身出来看什么样的元素在决定着这段关系的权力关系。
人:你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人吗?
钟:不太是,我在训练自己。说起来有点害臊,我以前不太能读懂对话背后的潜流。后来读托尔斯泰,具体内容忘记了,他写一个人物,自以为没人能看穿他,其实早就被一眼看穿。当时读到那里我最大的感受是做人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小说迫使你诚实,如果不是一个精通谎言的人,那你最好假定所有人在生活中都能看穿你,这样往往能言行一致。从这点看,小说是非常道德的。
人:翻译《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和前两本有何不同?
钟:翻第三本的时候挺不顺手的,艾丽丝与艾琳的邮件从消费主义聊到文明的灭亡,主题涉及范围广,语言更复杂些。邮件之外的情节部分语言重复性又很高,有时很枯燥。整体来说,这本在鲁尼的作品中没有很平衡,甚至是有些风险的。它有成有败,我在读的时候情感波动很大,会很喜欢某一段,也会很讨厌某一段——是在这种强烈的情感波动中翻译完的。
如果你让我给这部作品打分,我其实打不出来。最初收到全稿时,我希望它有明确的变化,有新的东西进来。翻译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鲁尼在有意识地更换技法,包括电子邮件的穿插,还有你提到的“拉远的第三人称”。她想突破,我喜欢她的野心。我们不必要求作家的每部作品都是100分,也许这本放在之后鲁尼的作品谱系里看就是一部转型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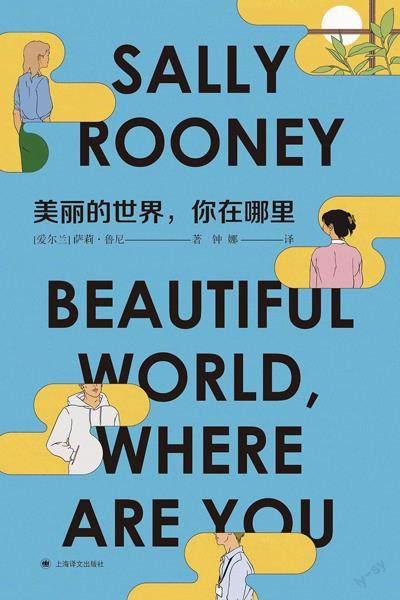
人:現在看来,新作达到你心中期待的变化了吗?
钟:不完全算。我觉得鲁尼变保守了,这不是一种批评,鲁尼仍然是一个不接受既定观念的人,她的每一个概念和生活方式都经由自己诠释。保守是说她基于目前的生活状态,对宗教、家庭和两性关系的一种保守判断。这也说明,她再一次成功地踩在了时代的脉搏上。
人:我也有相似感觉,新书中鲁尼写道,“去爱总比不去爱要好,去爱一个人总比什么人都不爱要好。”也某种程度肯定了婚姻的形式,好像流露出一种保守主义倾向。但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背后其实折射着大家对鲁尼进步性的期待?
钟:《聊天记录》里面一部分人和美国布鲁克林那群进步主义知识分子是很像的。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的崛起和《聊天记录》的出版差不多是同一时间,《聊天记录》出版后不久,我发现纽约一些本土报纸和杂志会开始提“新马克思主义青年”的概念。接下来,桑德斯在美国的大选中落败,一批新的候选人出现,但显然还没有出现改变这股浪潮方向的人。美国疫情之后进步性的思潮也受到一定影响,所以我觉得鲁尼从更激进的进步主义回到相对保守的立场也与潮流相吻合。
人:也有人认为这种转向或许是由于现实生活中鲁尼的家庭生活圆满。
钟:我不认同。有的作者过得很好,他们的作品也可以很有开创性。大家之所以对鲁尼期待更多是因为布鲁克林进步主义是充满了道德性的,鲁尼也是道德感很强的人。你看她小说里艾丽丝光是看了一眼费利克斯手机上的黄片,对方就觉得自惭形秽。所以她有价值稳妥的一面,大家自然对她期待更高。
人:鲁尼的三本书其实都是经验范围之内的书写,可是当她的个人生活趋于稳定,没有新的东西进来了,要怎么办?你会有类似担心吗?
钟:我觉得不会。人的生活永远都是充满戏剧性的,鲁尼特别擅长放大这些戏剧性,她的写作非常关注时代议题,所以它的相关性永远都在。而且,谁能保证我们的生活不会遭遇大的变动呢?
失落的人文学科,美丽世界的想象
人:鲁尼在访谈里提到,“美丽的世界”在想象中可能处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我们的政治形势、气候危机,现在的人会更强烈地感到“美丽的世界正在消逝”。在书中,我们很难不感受到一种失落感,艾琳接受过良好教育,却付不起房租;西蒙做议员顾问,却因三十多岁未组建家庭使母亲担忧。你认为这种失落具有普世意义吗?
钟:不见得完全通用。鲁尼笔下这群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从事的都是非理工科行业,那些从事科技行业、开创业公司的人用四川话说还是很“油爆爆”的,你很难从他们身上看到那种失落。我在西方媒体读到过一个概念是The Odyssey Years(奥德赛时期,指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工作与学校之间徘徊,他们推迟工作、结婚与生子,很多人经济上尚不能完全独立),年轻人漂泊不定,很难进入成年时期。他们不像他们父母那代早早成家立业,顺利找到好的工作。现在许多人文学科的学生都是负债读的研究生,他们最后得到的回报不成比例,到手的工资肯定不能买到像父母当年一样的房子。这是资源耗竭的体现。国内现在也慢慢体会到这种感受,比如,当年加入阿里巴巴创业的年轻人某种程度上无法理解现在大厂的年轻人,他们哪怕赚到钱也依然买不起房子。所以,与其说这群年轻人面临着extended adolescence(延长青春期),不如说是人文学科的年轻人在面临这种困境。
人:书中艾丽丝与艾琳关于“美丽的世界”有过一些讨论与想象,同时指出“我们是文明崩塌的最后一代”。但她们对所处环境的不认可显然和我们的语境非常不同。
钟:她们眼中“美丽的世界”是欧洲的想象,而非亚洲的。书中有句话是“世界自苏联解体后便不再美丽”。我想鲁尼大概是想说以此为节点,西方世界逐步走下坡路。过去30年,我们和鲁尼这代年轻人像两条平行的轨道,一条向上,一条向下。我们是获益于全球化的一代,外国订单愈来愈多,收获互联网红利,时代精神不断变化、向前。鲁尼她们的生活也深受全球化影响,工作机会流失、经济下行、城市衰落,这些都是肉眼可见的,最后落实到个体的生活中,或许是街边的流浪汉,或许是倒闭的快餐店,它们无可避免地成为她们认知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也许更能帮助大家理解鲁尼这代年轻人的精神困境。但整体而言,我们的成长经历是很不同的。
人:鲁尼一直警惕书籍作为商品销售的方式。《聊天记录》中,她借康奈尔之口表达了她作为畅销书作家的担忧;新作中,艾丽丝受困于畅销书作家带来的名利,在海边休养时,她写信给艾琳说自己不再阅读当代小说,那些作家她太熟悉了——周末来柏林,接受几家杂志的采访,再用自己的MacBook写些漂亮的“真实生活”。鲁尼对当代小说的批评,你同意吗?
钟:欧美出版业的生产体系整体非常规模化和产业化,很多是造星运动。他们执着于第一本小说,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品牌,作者要有辨识度,要将自己放置于市场上打量。现在美国很多年轻作家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比如语言非常强劲,或是议题新鲜,或在文体上进行实验,但有些被市场推出来后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整个行业太心急了,媒体好评有时是一种贬值和捧杀。
人:你认为媒体对鲁尼的关注是一种捧杀?
钟:她出版前两本书时媒体的关注比较自然,只是后来出现了很多衍生品:名流的加入、围绕鲁尼的评论、她拒绝以色列出版社翻译她第三部小说的邀请等等,这些行为使她成了一个文化名人。我们对她及其作品产生了同等兴趣,这是对同代作家才会产生的情感。尤其这次新书出版,欧美出版社做了一系列鲁尼的周边来营销,过度营销之下,鲁尼的作品被扁平化为一个符号,阅读它们代表着你是一个会对某些问题有深入思考,并能对自身反讽的人。这可能是作家自己不愿见到的。
人: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钟:鲁尼出圈是因为影视剧改编,电视剧选的又都是俊男美女,这本身就非常上镜。她的作品本身有极强的影视化潜力,她变成这么复杂的一个现象也与此有关。另外她写的都是亲密关系,性与爱她写得很好,某种程度上,这些描写和言情小说很像。鲁尼还是在营造浪漫,她没有反浪漫。真正反浪漫的小说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从头到尾都在讽刺把生活浪漫化、把爱情浪漫化,但鲁尼是在把友谊浪漫化、把爱情浪漫化。她会制造禁忌,深谙言情套路,知道怎么让你小鹿乱撞。大家为什么喜欢霸道总裁文和穿越文?因为有权力差,哪怕你穿越回去做皇帝的妃子,拥有现代知识技能的你还是可以左右皇帝的决策。
当各种元素被推到一定的极致,就成了一种言情。鲁尼对情感关系的描写是很小言的,尤其是她对性爱场面的描写都很直白,没有进行特别文学化的处理。她的目的是文学的,通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判断人物处在怎样的情感状态,但她本身的处理方式没有门槛,每个人读了之后都可以进入,她不会像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那样用色彩和高度艺术化的手段来写性。
人:说到性描写,新作中鲁尼的性描写和之前很不一样,太密了,变得不够神秘。
钟:我也不喜欢。我觉得她呈现的页面时间和性实际发生的物理时间过于接近,有些色情化。但我发现国外很多书评还是很喜欢,都在夸赞她的性描写。《纽约客》的小说专栏登载过《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一部分,节选的就是艾琳与西蒙的电话性爱。
人:她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似乎都不是世俗意义的强者,他们帅气、受欢迎,但也有瑕疵。
钟:男性都不强势的原因是女性都很強势,如果要制造权力关系,一方强一方弱更容易发生故事,最后达成浪漫的和解。新作中我比较惊讶的是艾丽丝与费利克斯这对,费利克斯不弱势,他身上有危险气息,有自己的原则,不会像西蒙那样一味地接受,所以我们才会为艾丽丝担心。我觉得这是鲁尼的一个突破,她尝试写了一个相对平等的关系。
人:有意思的是,她的书评价还挺两极的,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会认为矫情,絮絮叨叨,像肥皂剧。
钟:有些读者认为鲁尼小说主人公聊的东西和他们的生活是脱节的,他们也没做什么,只是纠结一些情情爱爱。但淡豹和陈以侃的评价很有趣,他们把鲁尼的小说当童话读,已经越过了对作品的这种批判,把它当作予人慰藉的童话,有点类似于读金庸的武侠小说。
我其实认为鲁尼一开始是很真诚地想要写这些东西,并且希望通过写作改变点什么。但我后来觉得,她未必能通过她的作品完成这些想法。她擅长写作,但对写作取得的效果不开心,就像小说里艾丽丝提到的,她很厌恶最后得到的一切。鲁尼是个很拧巴的人,她没完成同自己的和解,同时,她又是一个绝对忠于自己的人。
我记得鲁尼最近在一篇访谈里谈到,小说里的事件可能是假的,但所有情感经历都是真的。她的作品其实和自小说(Autofiction)很有亲缘关系,她非常喜欢那些作家,比如《房间里的母亲》作者希拉·海蒂(Sheila Heti),《成为母亲》的作者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尽管她自己写的是更加传统的小说,但其中有着私人小说的血脉以及一个非常自然主义的文学观——她一定要写自己生活中的这些东西,并且用忠实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但这也是我不同意她创作观的地方,如果想用你的小说去改变世界,你当然要去改变你小说中的世界,你不能通过忠实地描述现实世界来改变现实生活,你肯定要有纵身一跃。所以你看,新作中她谈到文明的灭亡、社交媒体和消费主义,但人物并没有和这些东西发生任何碰撞。鲁尼是个聪明人,她看到了世界终将变得越来越差,她承认了这一点,然后放弃了。如果真的抵抗消费主义,小说里的人物至少要和它们有互动,但是鲁尼小说里的人物仅仅是在便利店看到了包装很好的食品后发出一段痛苦的感慨,她痛苦地接受了。所以从小说层面,她没有真正去处理这个主题。大家之所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革命性是因为他用行动获得了生命的变革性,然后他忠实地写出来了,而鲁尼的生活里并没有这种变革性,她生活在一个相对平稳发达的西方世界,所以她的野心和她获得的材料以及处理材料的方式之间是有落差的。

写作者,译者
人:你身边的人如何评价鲁尼?
钟:我身边没有特别喜欢她的人,那种读完特别激动的,没有。可能因为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是少数族裔写作者,大家有很强烈的身份意识,会对白人浓度过高的作品有某种戒备意识,但这不代表大家对她的作品没有共鸣,只是不会像白人读者那么热情。不过无论喜不喜欢,大家都承认鲁尼写得好。
人:做自我介绍时,你总说自己是“中英写作者,文学译者”。大家认识你更多是来自于你翻译的作品,这会是困扰吗?
钟:人是被她的行动定义的,我在写作上花的精力和时间更多,我首先是一个写作者,然后才是译者。只是翻译的成果更早地被大家看见了。大家怎么定义都好,能被认识已经是一件奇特的事情。
人:写作时,对于语言的选择基于哪些考虑?作家李翊云在一次访谈中曾提到使用英文写作时可以更自由地思考,你会有同感吗?
钟:因为生活在纽约,我自然想用英语写作和这边的东西发生联结,所以现在写作时我会更主动地选择英语。它不是母语,你的词汇量没那么多,这其实有意地把自己限制起来,有点像古人给自己设置韵脚。有时候也是一种帮助,免去英文里繁冗的干扰,只剩下最经济有效的词汇帮自己完成创作。这样一来,我反而对小说有更敏锐的感受,能衡量它的重量。
用中文写作时就像做川菜,我知道撒多少盐,随便一估计八九不离十。用英文写作像做面包,所有材料都要称重,反复学习怎么去量化后便知道如何去控制,从这方面讲更得心应手。中文离我太近,对每个词的情感和认识程度不同,某种程度上是靠直觉在写,反而没有那种抽身之后可以琢磨的冷静。
人:最开始用英文写作时,会担心自己的语言和叙事不够本土化吗?
钟:我好像没有这种困扰,英文是个很杂糅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定义为是纯英语的。我希望我写的东西在英语世界里面还没有出现过,这样我的加入才会更有意义。
人:很多跨国写作者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你的写作不够“亚裔”或“中国”,如何处理这些期待与刻板印象?
钟:这其实很難,如果你没有满足他们的期待,你就会被拒稿,你连知道他们想法的机会都不会有,没有对话的可能。另一方面,只要你的作品被接受了,那就是鼓励的信号。实际上你是通过稿子的成功接受与否来判断别人对你的反馈,所以也是种鸵鸟行为。当然编辑也不会当着你的面说“你的故事不够中国”,至少我没遇到过。但同时我能感受到如果写一些更新的叙事、他们不熟悉的内容,发表会比较困难。但是说到底,我也没有写过更符合他们想象的东西,这对我来说很难。
人:鲁尼的三本书都由你翻译,有趣的是,作为她的同行,你花了很多时间参与了她作品的再生产。
钟:是的,有趣之处在于我不仅是译者,同时也在她活跃的场域里面写,所以这个会让我更加清楚自己的位置——我非常边缘,我写的东西永远都是面对更小众的读者。这让你不去谄媚——反正写出来的东西不可能像鲁尼那样畅销,也不可能改编影视,根本没人看。但是你可以写自己的东西,而且这更让我觉得要有自己的平台,因为你不能期待主流媒体来主动支持你。你要自己创造。艾略特、伍尔芙、川端康成他们都是自己办的文学杂志或者自己开出版社,因为他们写的东西太新了,超前一个时代。当然,我不是说自己的作品多超前,但我和我身边双语创作者写的东西肯定是美国主流读者没怎么接触过的。
(实习记者倪瑜遥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