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追问如何做自己的主人
2022-05-30邓郁崔畅
邓郁 崔畅

图/受访者提供
大半生里,杨照曾担任媒体机构的总主笔和高管、出版机构制作总监、大学兼任讲师,写小说和剧本,笔耕不辍,兴趣庞杂。他回忆年轻时与同代文化人交游,常有知识占有方面的虚荣心作祟。“比来比去,最后是比有没有比别人多知道一点什么。”然而历经时代更迭,他发觉知道自己是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最重要的是必須去解释历史。”
学历史的意义、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从一开始便缠绕着他。
1980年代,在台大历史系读大四的杨照,为准备研究所(生)考试,每天在图书馆用功温书到深夜。
某天夜里,像往常一样过马路到对面等公交车的他,突然感到一片迷茫。“当时正在读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突然间脑袋里面全是芜杂的史料,眼前则是台北的车水马龙。我在想,我所读的历史跟我眼前的现实到底是什么关系?老师和书本都告诉你,学历史是为了帮助你以史为鉴,能够了解现实。真的能吗?”
他很快找到答案:我们必须要有更确切的现实感,要看清楚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在这次“心灵拷问”之前两年,杨照在图书馆遇见了1960年代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资本论》,遂将日译本跟英译本的《资本论》逐句对读,读完了三大卷。在美国求学的日子,他又对照英文本和德文本,重读了一次《资本论》。
人一天有几个小时是真正为自己而活?杨照认为,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对资本、价值、人性、剥削和阶层的诠释,在今天依然出奇地精准。他在台湾诚品讲堂开设“西方现代思想名著选读”,出版著作《资本主义浩劫时我们聆听马克思》和音频讲解,希望借由巨擘的观点和实践,带动听者省思自己对生命的选择。
在将左翼思想视为“毒蛇猛兽”的彼时的台湾,另一位学术巨匠韦伯也进入了年轻学子们的视野。他的新教伦理,关于“要追求志业(神圣召唤)”的描述,都给杨照留下了深刻印象。纵然马克思和韦伯两人在许多方面观点不一,但他们以知识与思考对抗既有的世界秩序,从不因循标准答案的态度都让杨照终生受益。在看理想平台讲述《认识现代社会的真相:韦伯60讲》时,杨照提醒:只有深切理解我们所在的环境,才能进一步去提问,该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或者有无机会凭借主观意志去改变它。
在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的驱动下,钻研了一辈子历史却苦于传统历史教育窠臼的杨照,中年时开启了一人讲中国通史的尝试。
从2007年开始,他分别在台湾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前后跨越10年。根据讲稿整理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共有13册,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目前这套书在大陆已经出版11册,剩余两册仍在修订中。
有读者把杨照比作“历史界的费曼”(费曼不仅是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在物理学的教育和普及上也有突出贡献),他讲方法论,细谈考古,重视思想史和语言哲学,做中西横向对比,如同“航拍模式”的通识课。如果说他所崇敬的钱穆是从中国史内部追寻中国历史的真相,杨照则尽量避开“刻板印象”,加入了近百年来史学界的突破性成果,如他承袭的民族史学脉络、大陆盛行的唯物史观、西方汉学和中国研究的传统、日本的东洋史研究等等。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勤劳、忠实、不轻信不妥协的二手研究整合者。在杨照的描写和阐释里,我们可以感知到“史实”是基于哪些底层逻辑发生,产生了怎样的流变。他再从考古实证反推原初,今天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为何做出如许选择。杨照不希望读者把他的说法当做终极答案,而是把他的书和节目当作一个“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提醒,多了解、少判断,讲证据、讲逻辑。
人:人民周刊 杨:杨照
“你的意义之网由自己织就”
人:不久前你接受“一条”的采访,借由马克思和韦伯的主张,提出年轻人应作为“创造者”而不是作为“打工人”存在,要努力去追求志业而非职业。你很早就走出体制,定义自己为“读书人”,希望可以鼓舞年轻人。然而有读者认为你这回说得太过“怂恿和鸡汤”,在大陆“除非家境小资,父母工作稳定收入可观”才能不去卷;甚至说你“何不食肉糜”。
杨: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设想和鼓励年轻人模仿我的这条路,我这条路是我替自己走出来的。如果这条路真的有意义,不是说“我是一个读书人”的头衔,我更多地想说我不要做一个有头衔的人,这是比较重要的。
不过说老实话,我真的有点无力感,我不太知道怎么跟这些年轻人说话。我年轻的时候,周遭也是如此的沉闷,我们想象可能到晚年都还必须不断地去斗争。可是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改变,我们可以改变,这是我所喜欢的生命状态。
我在一条说,“2亿的中国年轻人如果停止内卷,这是多么大的爆发性的力量。”可我们目睹的是,我们正打造出人类文明历史上一个极其特定的社会。我一直在思考,今天大陆的年轻人,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是哪一些力量,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处境不会改变,社会不会改变?我很希望我能够找到这个答案。
人:在大陆,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几年,他很难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上父母的努力),在一个中大型城市有一席之地。“安身而后立命”成为大多数人的首要目标。
杨:这个东西就打结了。这里出了最大的问题,不只是自我认知的问题,还有对社会的认识。你为什么认为今天的状态几年后一定是不变的?
可以问问年轻人,三年五年之内就要面对的一些社会变化。比方在较高收入行业里,最有可能被AI取代的会是什么岗位?未来医生的一些岗位就极有可能被AI取代。依靠大数据,AI可以比现在的医生做诊断的时候更准确。包括房子,如果可以租一个大一点舒服些的房子,为什么非得买房子?
人:有稳定性的考虑,也有为孩子教育等方面的考量。
杨:老一辈的人那么在意房子,新一代的人在意小孩的教育、落户。你不觉得,应该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们可以体会该如何去看待这些事情?
直到今天,韦伯对我们都很有用——遇到任何问题,你应该要去质疑,而不是接受。从西方的启蒙主义到理性的发展,到它帮助欧洲快速进步,产生现代性的优势,韦伯帮助你去分析,当你跟集体、跟社会互动的时候,你的工具理性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你的价值理性或者你的信仰又是如何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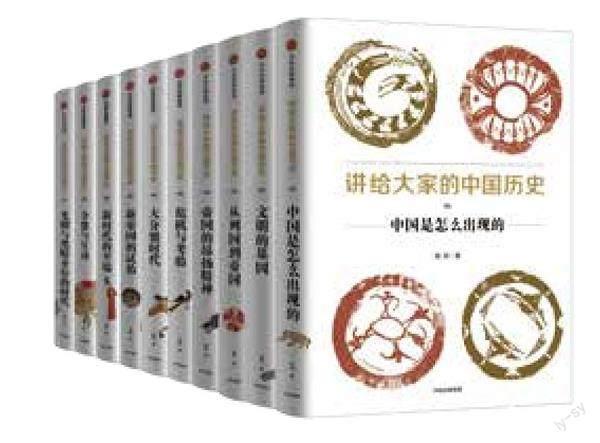
人:你也问过,作为个人,我们的自由意志做的决定占的比例到底有多高?而“被这个社会所决定,因而没有自由,就是依循着已经安排好的路线去做固定的事情”,这个成分又有多高呢?这些问题有解吗?
杨:韦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韦伯最后弄清楚了现代社会,但他像是个末世论者。他认为,我们越来越了解现代社会,就越被困陷在这个工具理性所织的网中。而马克思是持“一个社会必然要改变,不可能停留在这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必然要瓦解”的视点。
我忍不住会说,把这两个人加在一起除以二,比较接近我所认知的(他们)百年后的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会比较倾向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的系统发展到越来越完整,工具理性、金钱的数字理性已经席卷了全世界。活在这样的系统底下,工作变成目的,你越来越少自主意识。我们好像很难逆转社会变化的走向。
但就算生活里各种东西都系统化、组织化,即便在现代理性高度发展的空间里,韦伯从未预言个人意志的丧失。我们每个人仍然有编织和别人不一样的意义之网的自由。
人:那么在一个渐趋异化的社会,该如何自处?马克思和韦伯二人对异化的不同态度,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杨:当我们创造出来的外在力量,反过来统治了人,就是一种“异化”。马克思认为我们的痛苦是自我的错误认知所造成的。所以对马克思来说,异化太有用也太重要,你必须不断去寻找,到底在你的生活周遭,有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创造了异化——比如思考国家跟个人之间的关系。到最后,如果国家不退化,就变成了异化的来源。所以追到最根源就要问,什么状态下我们才是自己真正充分的主人?这就回到了康德,这是马克思非常哲学的一面。
可是韦伯没有把工具理性抬高到像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那样的程度。我们很难在现代社会里面逃离工具理性:月底拿到这份工资,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理性去分配。但韦伯告诉你,还有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永远都比工具理性重要。
回到打工人,其实也就是集体性高于个体性,你是顺应着集体的要求和目标,没有自主性。那我觉得这对于中国整体的发展是相对不利的;而且每个人能发挥的都只有真实能力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会很希望看到集体性跟个体性之间的比例做一定的调整。
人:如果说在螺丝钉的岗位上,“原创性”的工作也少的话,如何来实现你提倡的创造性?
杨: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谈创新的时候,讲到了七个面向。创新不是说在实验室里面发现了新的东西。台湾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研究机构,也没有像苹果和谷歌众多的专利,最大的长处,就是这么多年做电脑做手机,包括代工,真正把高科技每一个制作程序想得清清楚楚。像海底捞,它创新的地方在哪里?不是任何一个服务的做法,而是服务的心态。所以不要觉得打工人没有任何创新性,而是永远保持一个创新的态度来面对你的生活——我是不是非得这样活着不可。
我再问,你现在可不可以想出10种改变你跟手机之间关系的方法?很难吗?一点都不难。如果你愿意这样去做,你会发现生活里面有多少是把自己给绑死,以至于失去了自由和创新性。
人:最近有不少“‘00后整顿职场”的消息和说法(有入职新人提出不愿意加班,还有的刚入职不久发现很多东西和预期的不同,导致个人权益受损,于是迅速离职)。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这是一种自我觉醒,还是个人冲动?
杨:中国的产业升级不能靠固定僵化的工作方式来进行,一定要发挥创意。职场是需要整顿的。“00后”们刚刚进入职場,会带来一些很新鲜的东西。但不能够单纯靠消极的、表达不满的方式,也需要有长期而且是社会集体性意识配合,才有效果。但老实说,年轻人的觉醒和力量,是不是有必要对体制形成巨大冲击或者一定要展现出冲击?倒不见得。还是要一步步地推动。
如果我去挖过二里头,关于夏代我一个字也不敢写
人:除了你说的二手资料的整合,你做田野工作的经历其实不太多。如何把手头爬梳的资料、多年来华语世界的考古发现,和自己的论点结合在一起?
杨:前阵子我跟许宏老师对谈,对这些考古学人我非常尊敬。但说实话,如果我累积了更多考古的田野经验,比如说如果跟许宏老师去挖了二里头,我敢100%跟你讲,今天《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第一册里面讲夏代,我一个字也不敢写。
我的老师们给过我的东西,在我的心灵里面,我永远不会抛掉。正因为他们在学术上的严谨,我们必须把他们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传播给更多人。而我的任务是,要把考古和文献资料配合和对应,整合出一个个故事来。那些故事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大胆的论断,可是我至少有把握一点,我读过够多的考古报告,而且我的论断回到这些报告上是可以被检验的。
人:对夏商周,大家以前多认为是相继出现的朝代,但你告诉大家,原来它们曾是同时而处的部落,且因某方实力的增强,先后成为共主。这个观点并非你首次提出,但你花了几乎整整一册书来阐释。厘清这一点,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究竟有多重要?
杨:这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第一是关于中国是“一元文明”的想法(从黄帝开始产生了文明的突破和内容,然后再传到其他地方去)和“中国文明西来说”都是后来才发生的。而苏秉琦先生的论断真的太重要了,今天考古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中国的文明是满天星斗似的,在各个不同地方同时发生,然后才开始整合,从多元走向一元。它不是线性的,这个“一元”也从来没有彻底过。新石器时代那么多不同的部落在漫长的时间中彼此互动、互相竞争。夏人脱颖而出,后来商人和周人脱颖而出,虽然商人取代夏人变成了共主,夏文化却继续存在。商和周之间的关系也一样。在建构的过程中,所有这些东西慢慢进入我们所认知的中国文化。
人:这让人不免想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辨”的纲领,包括“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等,被戴季陶等人惊呼为“动摇国本”。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要捍卫中国在民族疆域和历史上的统一性,顾先生的立场后来也有所改变。对于史家而言,如何辨清时势和对抗外界的压力?
杨:我是到后来才能看清楚,我当年所受的是民族史学的教育,所以才会对钱穆先生这么熟悉,对他秉持的学术观点怀有深刻的情感。民族史学强调中国文化自身拥有强大的力量,它不只是中心性和一元性的,而且可以不断包纳外面的成分。现在我们能了解,当时很重要的危机感在于,我们会不会被西方文化吞掉?中国文化会不会消亡?民族史学可以令你有足够的信心去对抗,从而建立一个强健的中国。


钱穆。图/资料图片
但到了今天,我们还要这么担心吗?我对此有不同的评判。
当我们沿着商周一路下来,那些被民族史学家丢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把它捡回来了吗?你换个角度看中国,会发现中国的历史一点都不无聊。比如我们重讲东汉末年往后的这段历史,不需要非得讲成西晋到东晋,然后到宋齐梁陈……这当中有各种地域和民族间不同的互动,你了解到刘渊(汉赵国皇帝)、刘曜(刘渊之子,汉赵末代皇帝)、石勒(后赵国皇帝),分别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又各自在自己的文化想象上,跟北方的这些世家大族发生什么样的关系,跟佛教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我想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讲一次这些历史,为什么不把中国历史的意义解析得更多元、更有趣?
人:黄仁宇认为,身为历史学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史家的主要任务,在于将他对历史的见解和现代的读者分享。而你在讲解中国通史时,对孔子、子路,春秋的刺客等等历史人物,都有非常多的认同、同情与称道。
杨:我在每一册都有投入个人的情感,只是每一册的情感不一样而已。到我写第四册,为什么拿那么大的篇幅讲王充,那也是我个人的情感和经验,但那是负面的经验。因为王充的人生态度和想法,和我本人有太大的距离。我看到很多大陆的史学作品都把王充抬得很高,说他是中国最早的唯物主义者,具备科学精神等等。但后来我发现,你们大概都不太了解王充是谁。
对,有人看到第二册大篇幅写春秋诸子,说“没有了第一册最有特色的考古内容”,好像有失望。那我不就写成中国考古史了吗?以前通史的讲法,每一个朝代,至少开国皇帝、重要的宰相、主要的军事战争,要讲得清清楚楚。历史的范围这么广,为什么政治趋势一定是最重要?抱歉,从西周到东周,最重要的变化正是思想上的变化。如果你们去看《国史大纲》,春秋五霸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写出来,因为对钱穆来说,重点不在这里。
人:书里你多次引入内藤湖南的“近世说”。虽然这种介绍并不代表你本人的立场,但也隐含了你吸收的历史观。
杨:是。日本的东洋史(日本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里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们在社会史研究上面特别的眼光,有一部分跟中国这半个多世纪的唯物史观搭在一起,但有一部分又不太一样。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西嶋定生,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史家,具有如此的社会学的敏感,從秦到汉的社会结构像西嶋定生一样整理得这么清楚,这是很大的贡献。
而内藤湖南的贡献,是把中国从宋代以下称之为“近世史”。这个部分也很有趣,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就已经讲到,从唐到宋是中国历史阶段性的巨大改变。我们不要以为唐宋就是两个接续的朝代。你如果特别去体会、认知,宋朝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新历史元素,对应对照,就更明白唐朝是怎么一回事,宋以下元明清是怎么一回事。
人:有学者指出,在面对后来的西方近代文明的时候,宋朝的文化系统不再有接纳和消化适应的能力。
杨:杨联陞先生写过非常精彩的文章《朝代间的竞争》。民族史学在朝代竞争的看法上,其实是对宋朝最不利,也是最不公平的。当追问近代中国为什么这么弱,最容易就追到宋朝的重文轻武。其实赵匡胤是为了解决长期严重的历史问题才下定决心——不让武人治国。包括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并贯彻他的决心,以最极端的方式重用文人。
当我们说西方船坚炮利,这里就牵涉到文化的多元性或者是文化的个性。近世以下,整个中国文人文化的灿烂辉煌,放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不可思议的。比如说琴棋书画,整合佛教而形成的理学,高度美学化的文人文化,是宋朝人到达的一个高度。
我这个人喜欢替“弱势者”打抱不平。为什么写到汉代,我花那么大的篇幅写太史公?我就是非常看重《史记》跟司马迁。司马迁就是要替那些被遗忘、被冤枉、没有声音、但应该被记录下来的人说话,这是我认同的史家。
既然宋的“积弱”是代价,那么从宋朝以下的中国近世,我们得到了什么?这才是公平的说法。整个历史的视野,必须要有关联的、完整的解释。我们对国家的富强、对集体的这种重视,导致我们忽略了太多东西。
人:有媒体同行近期去美国拜访许倬云先生。报道里提到,60年前许先生怀着一份兴奋进入这新大陆(美国),盼望人类第一次用崇高的理想作为立国原则的新国家能落实人类的梦想。但是60年之后,他却目击着史学家社会学家宣告这样一个政体病入膏肓。对从事过新闻业和多年教学的你而言,目睹这么多的循环与变革,读历史是否能帮助我们对现实有所“扶正”?
杨:历史从来都不是可以直接对应现实而产生作用的,如此,定会是灾难。
在我看,学历史能够让你意识到人的行为的多样性,然后你看待人、预测人会做什么事,就会稍微小心一点。比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事情为什么会在美國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注: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约五十年前在罗伊诉韦德案中确立的基本堕胎权)为什么美国到现在不断出现可怕的枪击案,美国却管不了他们的枪支?这些都是大问题。但你只有认识了美国历史,才有资格去评论美国人发生了什么事。
许倬云老师和我都是二十几岁去美国,但他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长,我没有。我女儿14岁的时候去了德国,从此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欧洲,就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我前半生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过度放大了美国的重要性。今天人们为世界未来的这两个模式竭力争执,但是不是只有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这两个模式,是不是只有这两个模式之间的冲突?这部分的眼光可以稍微拉开一点。而欧洲经验在我后半生的重要性是越来越高的。
再回到我大四提出的那个问题。后来我想通了,我很庆幸我是学历史的。因为历史是过去人类经验的总和。不论人再怎么复杂,我们已经用这种复杂的方式过了两三千年。回到历史,我们可以找到那么多不一样的人,用不一样的方式在过生活。
比如李约瑟收集了那么多的资料,说中国古代是有科技的。那我们就要看,为什么这么多精巧的技术没有被抽象化、逻辑化,没有变成系统化的思考或者原则,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学历史,你就不会那么天真,以为人一定是如何的,一切都理所当然。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今天在面对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时做更好的准备。
(参考资料:一条《“停止内卷”,2亿中国年轻人会爆发新的高度》,施雨华《最后只有创作算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