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的日子
2022-05-30猫语猫寻
猫语猫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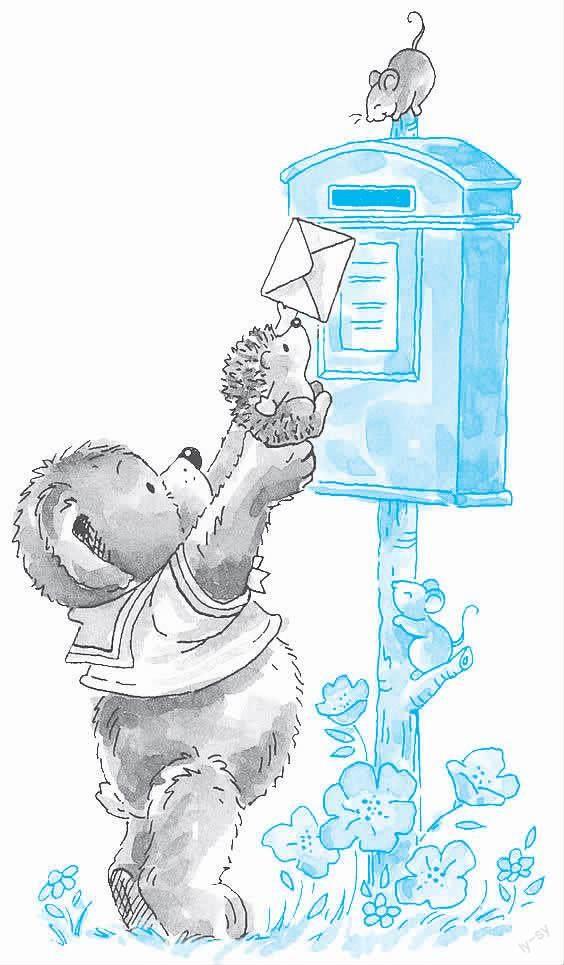
上学的时候,我常常给各种杂志社投稿,那时候有些杂志会把作者的地址和信息都登出来,方便读者写信联系,于是我成了学校收发室的常客,每天都能收到很多的信,最多一次,一天收了72封。寄来的信我都会过目,有些是分享自己的读后感的,但大多是想要交笔友的。
现在说起笔友,估计会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这应该属于80年代初那一代的记忆了。笔友这个身份对于我来说着实太美好了,我会在每天的来信里,挑出一些来回信。我一般是不会期待回音的,所以所有的回音就都成了惊喜。
这些回信一直被我收藏著了,放在家里的储物柜里。每次回家的时候,有时间我都会把我那一箱存着的信拿出来看看,有些妈妈已经看过了,以前会很在意这件事,但现在其实也都不在意了,所有的信都只是过去而已,所有过去的已经和现在的自己无关了,有些甚至连记忆都不清晰了。
这一大箱信中还夹杂着几封情书,也被妈妈看到了,妈妈还嘲笑我背着她谈恋爱,但其实我着实冤枉,有几封情书我都不记得写的人长什么样子了。上学的时候虽然我表面算得上开朗活泼,好似和谁都合得来,但其实内心认定上学的时候绝对不谈恋爱,并且已经做好毕业就离家远走的准备。
我印象最深的一封情书,起源是那时我带着班里的一帮女生读诗。我们明明是音乐班,和体育班一起是学校里学习差、爱捣乱、难管理的代表群体。每天下晚自习的时候,本应叽叽喳喳吵闹不堪的我们,竟然齐背着席慕容或者舒婷的诗往宿舍走,显得特别有文化氛围。我就因此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情书,虽说是情书,但我更愿意把它定义为诗歌交流信,他表达了对我的感觉和好奇之后,便把他喜欢的诗歌都抄在了信里,厚厚的一封,看得出写得相当地认真,但我没有回他,更没有赴他信中的约,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固执、偏执且认死理的人,后来看到他都还远远地躲着走。
那时候我的生活,也着实有趣得很。同学每次看到我收信时也会非常积极地来问问,有没有可以介绍的笔友,还会把自己想要的笔友的条件告诉我,比如字要写得好看,文笔不能太差,要男生或者女生,要是学生或者是已经工作了的……总之各种要求都有,当时我一度觉得自己可以在班里开个笔友介绍部门,专门给同学介绍笔友用。但这样的部门应该存在不了多久,因为很快班里便很少再有人写信——QQ开始普及起来了,一封封沉甸甸的信,变成了线上可以随时回复的信息。
我有仔细回想过自己写的最后一封手写信是什么内容,我着实想不起来了,但我记得我曾劝解过因为父母离异自己不知归处正处于迷茫中的高中生;我还记得我和一个远在海南的笔友约好一周写一封信给对方,不管有没有收到回信。因为海南太远了,信一寄就要走近一个月的时间,天南海北的,我们还真的按照约定,一周一封,不管有没有收到对方的信,都会寄一封信过去。后来他考上了广西的一所大学,信就慢慢地写得少了。我毕业后,也不再有固定的地址收信,他和一众笔友也均在我的世界里销声匿迹了。我想着,也许我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他的吧。
那个时候什么都慢,想要和一个人说说话,要等一周半月,在收到他的回信的时候,可能已经忘了自己之前写信时的心情,但期待来信时的心情是美好的,不像现在在意的人晚回了一会儿微信都让人觉得心焦,写信的心情也是美好的,一边看着对方的来信,一边想着对方展信时的微笑,就已经足够幸福了。小时候最想做的职业里,有邮递员,因为我觉得这是传递幸福的职业,你会看到期盼着信件的人,并把他们的期盼递到他们的手中,那份期盼比玫瑰要珍贵得多。
写信的日子是慢的,是充满期盼的,是非常纤细的,我们会记下听到的声音,闻到的花香,看到的美景,也会记下内心的细微变化和自己小小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在某一个远方,有个人想听。
(曹飞风荐自《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