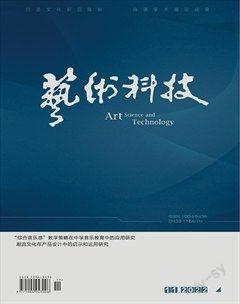论《水浒传》中的侠文化与尚武精神
2022-05-30王世丰
摘要:民间文学中的侠文化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水浒传》正是一部讴歌游侠、游民的经典之作,反映了宋元时期侠文化的泛滥和底层民众间尚武精神的风行。文章探析《水浒传》中的侠文化与尚武精神,深入分析侠的文化根源、侠士侠客的社群关系以及侠文化与尚武精神的联系。
关键词:侠文化;尚武精神;《水浒传》;宋元社会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1-0-03
《水浒传》展现了宋元时期底层社会的世态人情和文化思潮,侠文化是其重要的主题。作为一部反映江湖人的“百科全书”,《水浒传》中对江湖侠士的赞颂与对侠义精神的讴歌贯穿始终。文学创作源于社会生活,《水浒传》的侠客书写充分反映出宋元时期民间尚武之风和侠文化的流行。这种文化既有现实的民间土壤,又有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思想渊源。
1 侠文化的源流
1.1 侠的起源
《水浒传》描绘了一个游侠江湖、仗义行侠的世界,金圣叹评其所叙108位侠士“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为我国民间通俗小说一大瑰宝,其间有关侠文化的书写值得考究。
所谓“侠”,从人夹声,夹亦表相助之意,隶变后转作“侠”。《说文解字》段注云,“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侠文化在我国民间历史悠久,先秦时就有“士侠”“儒侠”的概念。汉代侠风日盛,司马迁著《史记》,亦作单独成篇的《游侠列传》。
究其根源,儒、士、侠本为一家。《韩非子》云:“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指出,“自孔子殁后……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其实,角色分野可能更早。吕思勉《秦汉史》论及,“盖当封建全盛,井田未坏之时,所谓士者,咸为其上所豢养……及封建、井田之制稍坏,诸侯大夫,亡国败家相随属……而民之有才智觊为士者顾益多。于是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由此可见,侠当为两周之际礼崩乐坏后社会阶层变迁的产物。
先秦时期,儒士亦尚武。士之六艺中,射御皆为武技,孔子本人力大能“举国门之关”。侠与儒士的区分在于职业的认定——侠不单以武为好,更以武为业,是以《韩非子·五蠹》用“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来区分。
此外,游侠一派与墨家也有重要的传承关系。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将墨家分为兼爱、游侠、名理三派。当代学者认为,“凡兼爱者必恶公敌,除害马……故墨学衍为游侠之风……自战国以至汉初,此派极盛。朱家、郭解之流,实皆墨徒也”[1]。鲁迅的《流氓的变迁》言,“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其认为梁山“强盗”与古之游侠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1.2 侠与义
关于侠的作为和品格,司马迁《游侠列传》中概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政治昏暗的年代,侠士们用个体暴力构建的法外正义模式对民众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受侮辱、受损害的个体盼望在侠士武力的介入下获得体制内无法获得的公平正义。
对于侠士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人们往往归结于“义”,相关语境下也称“侠义”。《水浒传》中,一个“义”字横贯全书,好汉们往往“义气相投”“聚义梁山”,言必称“梁山大义”;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为了兄弟“义杀阎婆惜”;朱仝“义释宋公明”,武松“义夺快活林”……可以说,水浒故事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不是“侠”,不是“武”,而是“义”。
“义”的内涵十分丰富。管仲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儒家把“义”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依据。孔子时常强调义利之辩,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中以“义”判定君子与小人的区别。《阳货》篇云:“君子义以为上。”《里仁》篇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水滸传》中,宋江为市井小民施粥舍药、置买寿木,林冲周济满牢城营的囚徒,好汉们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行为都是轻财重义的体现。
孟子进一步挖掘了“义”的价值。他提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义”是人类外在行为应遵循的准则。如果说“仁”作为人的内心情感,以爱人为主要内容,那么“义”则作为实践准则,是行为的当然之则。即使面对人身威胁,君子也当“舍生而取义”。可以说,相较于孔子,孟子的“义”在风格上与侠士之义有极大程度的趋同,其少了君子操行中的温文劝诫,化作一种大丈夫当为则为的豪迈告白。另外,后代侠士亦常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训告自勉。
由此可知,在侠的概念形成过程中,其内涵与外延越来越丰富。先秦时期的阶级变迁与诸子学派分野共同构成其社会基础,而儒家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道德观深刻影响了侠士群体的价值认同。
1.3 侠与江湖
侠士们活动的场域被称作江湖。“江湖”一词,出自《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里的“江湖”还是江河湖海的基本义。《南史·隐逸传》云:“故有入庙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归。”唐人杜牧作《遣怀》诗,亦有“落魄江湖载酒行”之句。可知,随着历史的发展,“江湖”与“庙堂”的对立愈渐明显,最终成为一种对与主流社会不相容的边缘地带的指称。
在《水浒传》中,“江湖”一词出现频率很高。第九回,林冲刺配到沧州,闻听酒店主人说起柴进大名:“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江湖上都唤作小旋风。”第十五回“三阮”抱怨王伦一伙霸占水面,吴用激他们去捉贼领赏,小七却说这样会“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可知江湖人物的影响力限于江湖本身,而江湖舆论也自有其道德评价。第二十八回,张青夫妇和武松把酒言欢,“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王学泰先生认为,江湖是游民们闯荡、奔走、觅求衣食的场所。它是与主流社会相对,受主流社会排斥、打压,却无法完全消灭的“隐性社会”。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人往往也是游民。所谓“游民”,即脱离宗法网络、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址、游荡于主流社会外的人群。古代以“四民”区别人口,谓之士农工商。宋人言,“四民百艺,朝营暮逐,各竞其力,各私其求”。游民在职业上可能是游商(如石秀),也可能为游士(如吴用),身份却不属四民之列。其日常游走于城乡间取巧牟利,甚至做些不法勾当。游民们的活动空间构成了一个无形的江湖,为“好汉”(或称“侠士”)一展身手提供了舞台。在这里,弱肉强食和快意恩仇是基本的生存规则,如孙二娘开黑店卖人肉包子,张横劫财杀人做“板刀面”,主流社会不容的暴行在江湖场域中司空见惯。宋元商业繁盛,城镇化程度较往代来说更高,大量因工商业兴起的小市镇为流动人口提供了更多生存机会,也为江湖的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
2 侠文化的社会基础
宋代重文轻武,社会意义上的“侠”往往处江湖之远,不复秦汉时期那种“关中豪杰争为交欢”的局面。这一点在《水浒传》中也有反映,如鲁达、林冲为下层军官,宋江是郓城小吏。武松出身更属微贱,赖打虎之名才获得都头身份。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宋代民间评话与侠义小说的雏形在城市空间逐渐形成。侠士们锄强扶弱、打抱不平的壮举通过话本故事广泛流传,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掌故谈资。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中原百姓遭受残酷的阶级压迫,反抗意识日渐强盛,百姓呼唤英雄人物带领他们打破黑暗现实的桎梏。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侠士揭竿而起、仗义报国的故事屡见不鲜。《水浒传》中,梁山军招安后平辽讨寇的叙事亦属此类。
已知宋江36人横行河朔的故事诞生于北宋宣和年间。罗烨《醉翁谈录》记载,南宋说话剧本已有《花和尚》《武行者》和《青面兽》等篇。南宋末年流传的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有3000余字篇幅描写宋江起义,水浒故事框架至此基本成型。
元代民族矛盾较前朝更甚,元杂剧中讴歌英雄侠士的水浒戏也日趋繁盛。全本保存至今的有《黑旋风双献功》《梁山五虎大劫牢》《王矮虎大闹东平府》等十二种。《水浒传》的成书离不开这些先期的文学基础和创作实践。其所秉持的侠义之道,与民间文化和文学创作中的侠客崇拜一脉相承。一方面,民众对铲除奸恶的期盼体现了维护公义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中所描绘的豪侠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生活,以及“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自在自足消除了阶层区分,也为饱受压迫的底层民众搭建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此外,如王学泰先生言,《水浒传》中的侠客本质上多出于游民,而游民阶层具有强烈的主动精神,虽不容于主流社会,但能吸引和裹挟广大下层民众和许多有志不逞之徒积极参与主流以外的政治实践。以梁山群体为例,他们以义为纽带的江湖伦理,将“以武犯禁”的普通游侠连接成准血缘性群落,建立起类似儒家宗法结构的军事组织。同时,行侠宗旨也由“替天行道”的公义取代了儒家“独善其身”的私德,于社会认知层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梁山群体在政治上“反贪官不反皇帝”,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暗示着庙堂逻辑在江湖中的延伸,说明侠士们面对高度成熟的封建社会,已无法在政治上撼动对手这一事实。以“杀人放火”来谋求朝廷的“招安”,手段颠覆了目的,既背离了昔日的侠义理想,又失去了体制外的自由身份,已然走到了传统侠客最后的边界。梁山群体自江湖回归庙堂的失败,进一步论证了“侠”的历史局限性[2]。
3 侠文化与尚武精神
江湖是强者为尊的世界,江湖中人行侠仗义离不开一身好武艺。《水浒传》的侠客叙事伴随着对尚武精神的推崇。有学者对《水浒全传》一书进行统计,其中“武艺”一词出现了106次,“好武艺”出现17次,“武艺精熟”出现9次,“万夫不当之勇”更出现15次之多……凡此种种,可见其浓烈的尚武之风[3]。好汉们大多不好色,不婚娶,“终日打熬气力”“刺枪使棒”,即使饮酒契阔,也要口头上“较量些枪法”。故陈洪《漫说水浒》提出,“水浒世界是个唯武是崇的世界,个人是否武艺高强是决定其生命价值的重要因素”。石麟《施耐庵与〈水浒传〉》也说,“以暴抗暴,打尽不平方太平是《水浒传》的主题思想”。
中国自古是尚武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尚武的民族。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有言,“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隋唐拓土开疆,尚武精神深植朝野,武人地位极高。文人也不免感慨,“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如李白、杜甫均曾修习剑道,岑参、高适都在边庭幕府效力。唐末藩镇割据,武人动乱,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鉴于前朝教训,宋代出台一系列政策偃武修文,但仍未根绝民间尚武之风。
《宋刑统》明文规定,“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私有禁兵器,谓甲弩、矛矟、具装等”。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太祖颁布法令禁止京都士人、百姓私蓄兵器,其后禁令更反复推行全国。翻阅宋史可见,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等多次重申禁兵。一系列禁令涉及甚广,不但杜绝军备流向民间,甚至一度连开山种田的工具刀也禁了。《宋会要辑稿·兵》载,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诏曰:“川陕路不得造着袴刀。”袴刀本是民用刀,为百姓日用生计所需,可知此类禁令已严重影响人民生产生活。与此同时,宋廷对民间习武结社极为忌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载,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仁宗诏称:“如闻淄、齐等州民间置教头,习兵仗,聚为社。自今为首处斩,余决配远恶军州牢城。”
宋朝自开国以来一直严厉管制各种民间集会,即便是民间祭祀和庙会、社会,亦在约束之列。各类宗教仪式上使用的仪仗兵器往往也犯忌讳。《宋会要辑稿·刑法》载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诏曰:“神社枪旗等严行铃辖,如有违犯,内头首取敕裁,及许陈告。”陈告即告密、告发,朝廷为求禁兵,鼓励私民相互揭发,足见约束之严。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宋代民间尚武之风始终未衰。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有臣子上奏徽宗:“江南盗贼间作,盖起于乡闾愚民无知,习学枪梃弓刀,艺之精者,从而教之,一旦纠率,惟听指呼,习以成风。”可知民间结社习武的风习未因官府纠察而消失。此外,这一时期“杆棒”的流行,亦足见社会上武风未衰。杆棒即棍棒,出门行旅时拎在手里,不但可以防身,还能挑擔行李,故民间应用极广。翻看宋元笔记小说、评话杂剧,几乎满篇都是棍棒。《水浒传》中武松以哨棒对付老虎,林冲“棒打洪教头”,亦属此风。英雄侠士们无刀可用时,仅凭一条杆棒,也能打尽世间不平。更滑稽者,《水浒传》首回,作者正是以“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来称赞太祖赵匡胤的武功。
4 结语
“侠”的由来在我国有悠久的文化传承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古代社会法制欠缺,下层百姓时受强暴凌虐,基本权益往往难以保障,因此,人们期盼和呼唤独立于体制之外的力量为民解困,主持正义,这便构成了侠客崇拜的土壤。《水浒传》是古典文学游侠传奇的集大成者,直观反映了宋元民间的尚武之风。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此类“小传统”叙事所构建的在野式文字表达,是对“广大民间的基层思想和愿望”的整理和提高,值得今人关注与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12-13.
[2] 李跃峰.侠客美学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6:43.
[3] 何求斌.浅析《水浒传》的尚武精神[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0(1):8.
作者简介:王世丰(1995—),男,陕西西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宗教美学与民间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