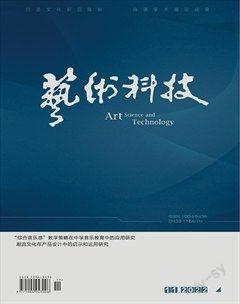论近年来国产涉案网剧中的“双探”形象设置
2022-05-30王鑫
摘要:涉案剧的探案主角形象,是观众审美理想的寄托。为了提升类型质感,近年来大量国产涉案网剧在探案主角形象的设置上采用了“双探”模式:平民探案者与警察探案者。前者是市井英雄的传承与重构,后者是体制英雄的典型代表。人物内核、形象特征与塑造方式的不同,引发了两重英雄形象的冲突,而二者最终走向和解,无疑深化了国产涉案网剧的意义建构与价值表达。文章主要对国产涉案网剧中的“双探”形象设置进行探讨,以供参考。
关键词:国产涉案网剧;“双探”;市井英雄;体制英雄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1-00-03
在作为叙事艺术的电视剧中,人物是核心,如何塑造出可亲可感可敬的人物形象,是电视剧叙事的中心问题。特定类型电视剧的人物塑造有着自身的特征,涉案剧中主角、配角与反派人物形象有特定的审美特征,而肩负探案与找出真凶任务的主角形象更承担了观众的审美理想。近年来,国产涉案剧借助网络流媒体平台获得了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类型化、精良化制作,频频获得观众好评。在《扫黑风暴》《双探》《白夜追凶》《开端》《猎罪图鉴》等涉案网剧中,为了塑造观众更认可和接受的人物形象,普遍设计了两重探案主角形象,蕴含了两种不同的想象,即警察探案英雄与平民探案英雄。警察探案英雄表现了身为共产党员与人民公仆的责任与担当,以《扫黑风暴》中的何勇为代表。而平民探案英雄是对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市井英雄的类型化改造,展现了普通人身上的人性闪光点。两种英雄的人物内核、形象特征与塑造方式存在一定的区别,构筑了国产涉案网剧中探案英雄的双重面向,丰富了剧目的类型化实践。
1 市井英雄的传承与重构
李成阳(《扫黑风暴》)、周游(《双探》)、关宏峰/关宏宇(《白夜追凶》)等人物形象是平民探案英雄的典型。平民探案英雄突出平民感与市井感,更贴合观众的人格想象,更容易为观众留下自我设想与共情的空间。这一形象在近几年才被大量塑造,凸显了新生代、网生代观众的审美诉求,丰润了区别于警察英雄的江湖叙事,表现出观众的独特类型想象,以及对作为一种社会寓言的涉案剧的书写延续。
遍观这一类英雄形象,出身市井,追求世俗与自我价值,表现出不依靠体制而选择独自追凶的精神。“出身于社会底层、相貌魁伟粗陋、语言豪爽粗俗是草莽英雄的共同表征”[1],尤其从明清时期开始,市井英雄的大量书写集中呈现了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审美追求。将涉案网剧中的平民探案英雄与古典文化中的市井英雄进行对比,二者在出身、形体特征、语言特色等方面都有相同之处。在二者的人物塑造上,创作者刻意书写了其形象中的“缺陷美”,情理之中的缺陷为人物形象增添了多彩色调和丰富层次。涉案剧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社会的武侠剧,侠客与草莽英雄形象作为一种人物原型,仍然潜在地影响了涉案剧探案形象的塑造。
当然,作为一种现代影视作品,虽以草莽英雄、俠客英雄为原型,但涉案网剧中平民探案英雄形象的塑造,为了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接受观念,更契合涉案类型的审美创造,也相应地进行了形象重构。对剧中人物内核、形象特征与塑造方式都进行了更类型化与现代化的构造。
其一,寻求创伤治愈的人物内核。随着对凶杀案件及其前因后果的呈现,创伤在涉案剧的叙事层面得以浮现,尤其集中表现在作为创伤承受者的平民形象上。揭示创伤形成的前因后果成为人物寻求治愈创伤的主要方式,也成为人物参与叙事的初始动因。例如,在《扫黑风暴》中,李成阳因为自身被陷害、师父蒙冤而立誓查清前因后果,还自己和师父一个清白。在古典文艺对市井英雄的塑造中,英雄内生的义气、豪气与打抱不平成为英雄施行正义之举的开端,更多属于一种救人者。而在涉案剧中,这一人物内核得到重构,这首先是基于现代社会对人的强调,救人的英雄被重写为自救的英雄。创伤是涉案剧的重要元素,将人物内核、行动动机和创伤勾连起来,更有利于故事的叙述,以营造涉案感。寻找之旅最后达成正义的伸张与圆满结局,既能展现人物缺陷的弥补、创伤的治愈,又表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抚慰功能”[2],呈现出独特而富有魅力的审美图景。
其二,有勇有谋有情的形象特征。继承于市井英雄,平民探案英雄的形象特征集中呈现为有勇有谋有情。有勇的一面通过凸显探案者的孔武有力与一往无前的探案决心而得以展现。为了寻找创伤真相,平民英雄一往无前,前往危险之地,不畏强权,寻找被掩埋的真相。有谋的一面则呈现为人物多重侦探技能的掌握与临危不乱的应变能力。如在欧美涉案文本中,独立于警察机构的侦探常常肩负着探案任务,掌握各种探案本领的侦探形象以智力出众闻名。而在涉案文本的本土化过程中,侦探的角色功能虽被弱化,但在平民探案英雄上仍能见到端倪。在《开端》中,拥有较强推理能力的肖鹤云与李诗情是有谋英雄的代表,他们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推导出了时间循环的真相。
其三,“寓庄于谐”的塑造方式。这一类人物形象的缺陷十分明显,如暴躁、易怒、情绪化、立场摇摆、自私等,然而这些缺陷在符合观众对市井平民想象的同时,通过创作者“寓庄于谐”的塑造方式,使人物呈现出一种真实感、生命感、现实感与崇高感。“寓庄于谐”是一种喜剧创作手法,意指以诙谐的表现形式陈述深刻的主题思想[3]。延伸到涉案剧中,指从缺陷中见出真实、从狡猾中见出正义、从平常中见出异常、从平凡中见出伟大。平民英雄形象固然有其缺陷的一面,但是在合理缺陷事实存在的基础上,展现其心态的变迁与正义感的萌发,更能表现人物庄重威严的一面。如在《开端》中,本来已经决定放弃拯救一车人的肖鹤云,受到李诗情的感染,正义感涌现,一遍又一遍进入循环,不顾自身安危也要寻找事实真相,完成剧目的意义建构。
从近年来的涉案网剧来看,平民探案英雄形象的塑造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形象塑造上初具雏形却又不免存在一些问题,如对人物内核的挖掘不够深入,人物形象的展现过于模式化,塑造方式也大量同质化,在“谐”中见“庄”有时不免显得刻意,等等。总之,对平民探案英雄的塑造,强化了涉案剧的类型光景,造就了质感独特且兼具人文情怀的优秀剧目。在网络游民时代,平民探案叙事的兴起映射了非主流群体的文化诉求,表现了赛博空间新的审美趋势。
2 体制英雄的守正与丰实
何勇(《扫黑风暴》)、张成(《开端》)、李慧炎(《双探》)等人物形象是典型的警察探案英雄形象。源发于西方的涉案类型剧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最鲜明的特色之一便是强化了警察这一形象的塑造,更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西方侦探的自主探案模式经历本土化改造,逐渐演变为对警察形象的大力塑造,开始书写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宣扬主流价值观的涉案叙事。
鲁迅有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4]。警察形象在涉案剧中的呈现及其正面价值不断被肯定,继承了自古以来中国对民族脊梁英雄的书写传统。中华民族是一个多难的民族,每有社会危难、生灵涂炭之际,总有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为了民族大义、社会公平而不断奋斗甚至不惜牺牲自我。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员、领导干部與人民公仆坚守初心,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果说继承于市井英雄的平民探案英雄以朴素世俗的价值观念引发了观众的共情,那么这些维护社会大义的警察英雄更以其崇高的人格获得了观众的崇敬。作为社会寓言的涉案剧,书写着平民在现代社会的灾难,作为社会秩序维护者的警察天然拥有维护社会正义的职责与担当,奋不顾身地寻找幕后真相,维护社会秩序。
首先,坚守人民情怀的人物内核。何勇、张成、李慧炎等警察英雄,乃至骆山河(《扫黑风暴》)这样的检察英雄,都是人民公仆,始终把人民情怀作为自身的精神追求。从这种人物内核出发,体制英雄是观众对正义、公平等理想的寄托,内植守法、护民、爱国、忠党的多重内核。在《扫黑风暴》中,绿藤市万马齐喑的社会现状引发了观众的强烈愤慨,只有听闻中央督导组到来时才给观众带来一丝宽慰,破局有望。在《开端》中,当李诗情询问张成,哪怕自己报的是假警,警察也会挺身而出吗?张成目光坚毅地说“会的,我们一定会”。可见,涉案剧叙事的本质任务是揭露黑暗,并引导大家形成对生活新的向往,有了坚守人民情怀的警察形象,剧目的社会抚慰功能自然效果更佳。体制英雄是观众审美理想的寄托。
其次,伟岸、沉着、朴实的形象特征。体制英雄的形象特征极具辨识度,在动作上表现为伟岸。出于坚守人民情怀的人物内核,体制英雄常常义不容辞地冲锋在前。《开端》里的张成明知道炸弹即将爆炸,但为了守护一车人的安危,仍然奋不顾身地扛起炸弹向桥边冲去。这一视死如归的动作设计无不让观众称赞。对比《扫黑风暴》中李成阳与何勇对同一事件的处理方式,李成阳的情绪化行为最终造成事态扩大,但何勇保持镇静,坚持向李成阳阐述其中的利害。体制英雄往往具有沉稳冷静的特征,在事情处理上也更容易从大局出发,具备宏大视野,面对突发状况也更能沉得住气。
最后,“寓谐于庄”的塑造方式。与平民探案英雄的塑造方式相反,体制英雄的塑造是于庄重的形象基层上加入诙谐的元素,增强人物形象的可看性、真实感,增加人物的可爱之处。如《开端》里的张成做事一丝不苟、神情庄重,但在剧情循环的设定下,这一特征反而呈现出一定的诙谐效果。庄重深沉的内里使人物在面对各种困境时都表现得一本正经,而在剧情的营造下,这种正襟危坐却又构成了人物的蠢萌,引发了观众的愉悦之情,同时加深了对这一人物的认识,强化了对体制英雄的敬意。
体制英雄是观众审美理想的寄托。作为社会寓言与平民灾难书写的国产涉案剧,唯有体制英雄的出场,才能完成对创伤破坏力量的审美式抚慰。在涉案类型剧的本土化过程中,体制英雄的成功塑造是最主要的经验之一,符合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对民族与社会脊梁的审美想象。当下,剧目创作应该书写更多鲜明、丰实的体制英雄形象,完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在地化表达,迎合时代与观众的需求,呈现新时代的英雄图景。
3 两种英雄的冲突与和解
平民探案英雄与警察英雄存在诸多不同,前者继承于民间广为流传的市井英雄形象,后者则是体制英雄的典型代表,二者在人物内核、形象特征与塑造方式上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直接促使二者产生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与集体的冲突、情理与法理的冲突。
3.1 个体与集体的冲突
平民探案英雄的个体属性及其探案理念,促使其成为现代游侠,更愿意只身侦查案件。处在市井中的平民,更多地受到个体观念的影响,同时,作为创伤症候的表现,封闭自我也是其基本特征。《双探》中的周游即使对案件掌握了更多线索,也不愿意向更多人尤其是警方分享自己的消息,转而孤身前往双塔镇查案。《白夜追凶》里,关宏峰隐瞒了自己的创伤经历,借助警局顾问的身份探查案件。而警察英雄则相反,其更多是作为集体的一员出现,伟光正的警察个体是警察集体的代表,更代表全体人民公仆。探案呈现出组织性和高效性,当两种形象相遇时,便会出现冲突,尤其表现为当警察邀请平民探案者合作时,后者不置可否。
3.2 情理与法理的冲突
这一层冲突是两种英雄的本质冲突。平民探案的缘起多是出于情的牵挂,如李成阳对师徒情的坚守。同时,平民探案更多秉持的是复仇逻辑,即试图绕过警察和司法,完成对凶手的“以牙还牙”式报复。复仇逻辑是民间英雄的一贯色彩,从古至今都有大量的表现,甚至能得到许多民众的追捧。以情感为导向的平民英雄往往具有一定的偏执倾向,与警察形象的稳重沉着等特征形成反差,造就了不同的探案英雄形象。
当然,两种英雄形象的追求并不必然是冲突的,逮捕罪犯的共同利益与人物内里的正义感会促使二者最终走向融合,以合作的姿态追击罪犯。在和解的过程中,平民游侠与体制英雄之间存在的个体与集体、情理与法理的冲突得以化解,二者误会消除,从而形成新的共同体,维护社会治安。在《扫黑风暴》中,李成阳正是由于何勇等人帮助其洗清诬陷之罪,才选择回归集体。集体归属感是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深层情感需求,受到创伤而被流放的个体选择与集体和解是必然之路。
平民游侠对罪犯的追击,是出于对自身创伤的治愈需求,并在寻找之旅中完成心灵的成长,最终改变个体处境,融入集体,摒弃对情的过度坚守,转向对法理的维护。体制英雄对罪犯的追击,是出于自身肩负的责任与担当,以及对社会创伤个体的关注,表现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在地化实践。平民游侠与体制英雄的和解,标志着共同体的形成,象征着个人游侠融入社会秩序,从而实现涉案剧的社会抚慰功能。
4 结语
国产涉案网剧近年来逐步走向精良化与类型化制作,获得了观众的好评。寄托了观众审美理想的探案主角,是涉案剧塑造的重心,直接决定了一部剧的意义与价值建构能否完成。为了突出类型化的质感,迎合网生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国产涉案网剧的探案主角设计颇费心思,着重塑造了形象特质区别较大的两类探案英雄:平民探案英雄与警察探案英雄。前者是中华传统市井英雄与游侠的传承,后者则是体制英雄的典型代表。二者的差异与冲突提升了涉案网剧的质感,二者的融合则深化了涉案剧的伦理与价值取向。如今的涉案剧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如何塑造出更加鲜活丰富的探案主角形象,仍然需要不断深入探索。而这种“双探”形象的设置不失为一种可供借鉴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庆振轩,车安宁.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草莽英雄形象探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4):97-104.
[2] 何美.类型、媒介和审美:近年国产悬疑网剧的破圈之道[J].当代电视,2021(4):99-102.
[3] 杨辛.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9.
[4] 鲁迅.且介亭杂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93-95.
作者简介:王鑫(1999—),男,江苏盐城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电影叙事、电影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