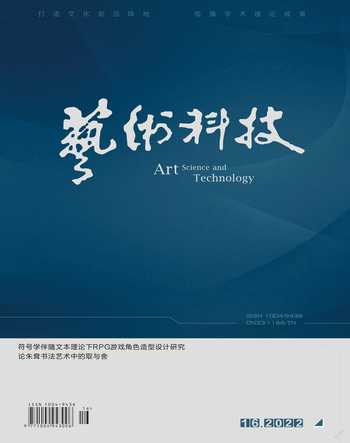《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的精神流浪分析
2022-05-30吴欢
摘要:刘震云创作了许多以平民百姓为主要人物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其中之一。在《一句顶一万句》上半部分,刘震云从话语、伦理的角度出发,描写了中国人孤独、飘零的精神状态。在混乱的家庭伦理中,主人公杨百顺面临着“说得着”和“说不着”的精神困顿,最终在失去唯一可以说得上话的养女后,正式离开延津,并且以“罗长礼”的身份继续流浪。文章以杨百顺的精神状态为切入点,摸索《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孤独意识和精神流浪。
关键词:《一句顶一万句》;精神流浪;流浪意识;杨百顺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6-0-03
杨百顺作为《一句顶一万句》上半部的主人公,虽然自孩童时起就一直居住在延津,但他深陷于精神流浪的状态。这种流浪不仅体现在杨百顺不断更换行业和住所的行为上,还表现为其精神处于孤独与虚无的状态。归根结底,杨百顺出现流浪意识的原因是他在延津生活的对话错位中逐渐失语、在家庭伦理的异化中逐渐变成边缘人等。
1 流浪意识的产生:日常话语失语与家庭伦理异化
1.1 对话错位的孤独
《一句顶一万句》展现出了对“说话”的密切关注,并且在“说话”中深入普通百姓的精神深处,探寻他们的灵魂世界。小说中出现了许多诸如“生来就爱说话”“嘴笨,不爱说”“说得着”“说不着”“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等语段。伽达默尔认为语言代表着一种世界观,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事实上,语言的不同也代表着精神世界的不同。
在小说中,杨百顺就在对话错位中生活了许久。首先,杨百顺因抽签失败只能和老杨卖豆腐,卖豆腐时需要敲鼓告知今日有多少种豆腐花样,比起敲鼓来吆喝,杨百顺更喜欢通过话语喊出来今日豆腐花样。但杨百顺又不是像吆喝豆腐那样喊出来,而是像罗长礼喊丧那样喊出来。从这里可见,杨百顺偏爱通过话语来传达自己所思。很遗憾,他的排解方式是不被认可的,杨百顺第一次自主选择的宣泄精神空虚的方式失败了,并且其他方式也都失败了:老杨会因杨百顺喊丧而嘲笑他,并且摆出大家长做派,询问“这个家到底由谁做主”;兄弟杨百利“喷空”的对象从来不是杨百顺。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杨百顺逐渐失语,他和延津镇上百姓的对话逐渐减少。作者通过乡里长短展现了“说”对杨百顺命运走向的引导性,一个“说”字,透露出浓重的中国式孤独感。
从杨百顺在延津生活的处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话错位造成的心灵壁垒下,杨百顺面对的是精神虚妄和孤独。在这种不被理解的孤独下,杨百顺的孤独感加重。作为个体的人,虽然存在于延津土地上,在物质生活上并不属于无根、无家、无父的那一类,但在精神意识上出现了无根、无家、无父的流浪感。
1.2 伦理错乱的荒诞
除了对话错位,家庭伦理话语中出现的弯弯绕绕也加剧了人物之间的疏离感。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生活逻辑下,人虽然在家中,随手可触及熟悉的物件,耳畔甚至存在父母、妻子和儿女的话语声,但内心却被无家可归的感觉牢牢拘着。老杨因杨百顺尊重罗长礼而说出家中由谁做主的问题,妻子吴香香会从吴摩西玩社火这件事绕到让吴摩西一个人去卖馒头的事情上,同样的还有因为吴摩西给逝去的老詹用竹篾编教堂而繞到催促吴摩西去卖大葱的事情上。
和老詹的孤独不同,杨百顺不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被排除在外的,种族血缘没有让他和家人更亲密,反而使其被排斥在外。在这种排斥下,他生活在夹缝中,产生了矛盾、彷徨和痛苦。例如,他因为老杨的抽签,只能放弃读书的机会,又因为岳母的逼迫,被赶出延津去寻找逃离的吴香香。杨百顺在异化的家庭伦理关系中,一直生活在无家的悲凉之中,在苍茫和无望中,他明白了自己不属于这里。杨百顺的流浪意识就产生在家庭伦理异化和悲剧冲突中。为了寻找心灵慰藉,杨百顺只能继续悲哀又洒脱地流浪。
同样,在《一句顶一万句》中,“绕”也是造成人心灵漂泊无依的一个重要因素。老裴因为蔡家的“绕”,日渐失语;杨百顺因老杨的“绕”,和父亲的关系日渐疏远,后来又由于妻子吴香香的“绕”,放弃自己所做之事。原本,老裴和杨百顺在所做事情中越来越接近个体独立,却因为各种“绕”一次次妥协。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这种“绕”存在于延津百姓的逻辑当中,注定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孤独感。
2 流浪意识的启蒙:对麻木现实的自省和宗教内核的呼唤
2.1 清醒古怪的现实体悟
“流浪实际上是一种体悟世界、面接社会然后认识其真面目的一种方式。”[1]243吴摩西一开始的出走是被迫的,他住过大通铺,睡过黄河滩,甚至两三天没有吃上饭,但是为了寻找巧玲,吴摩西还是辗转于各种火车站、汽车站之间。从一开始的新乡到后来的开封、郑州,吴摩西逐渐往人群里走,沿途看见扛大包的人群、运载货物的火车。所以在找到吴香香后,吴摩西认为“当初正是因为他们偷情,为了出门寻找他们,才丢了巧玲;接着自己才无家可归。当初丢巧玲的时候,只觉得卖老鼠药的老尤可恨;现在想来,比老尤更可恨的是他们”[2]673。
在他看到吴香香和老高两人虽然清贫但很恩爱之后,吴摩西“炸”了,他明白“就是把人杀了,也挡不住吴香香跟吴摩西不亲,跟老高亲”,而且“一个女人与人通奸之前,总有一句话打动了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吴摩西一辈子没有想出来”[2]684。所以吴摩西最后慌忙逃遁,他在这次远行中颠覆了自己曾经认为出逃的奸夫淫妇应该穷困潦倒、受人唾弃的想法。以往的杨百顺认为只要杀了人就结束了,他会因怨恨和嫉妒而想杀了父亲和弟弟,但这一次流浪让他清楚感知了死亡不是情感的结束和事件的了结,即使自己所怨恨之人都死了,自己还是孤单一人。所以,从吴摩西在火车站遇见曾经的妻子这一情节开始,吴摩西已经从被迫出逃转变为正式流浪。流浪不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逃亡,而是无穷无尽的寻觅。吴摩西在亚伯拉罕事迹的指引下,开始寻觅归属地。两段流浪的格调是不同的,杨百顺后半段的流浪显然出于心理上的需要。
2.2 摩西“出走”的宗教隐喻
吴摩西最后的出走具有宗教人文关怀的崇高感。宗教故事中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族逃离是为了反抗种族压迫,但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吴摩西的出走用以凸显“人在经验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和文学中的超越性价值”[3]103。
杨百顺在精神无依和生活没有保障的状态下遇到老詹。杨百顺希望信主可以找到事情做,老詹就给他改了名字。改了名字的杨摩西开始接受信仰——每晚住在破庙,并且听老詹传教。但是当杨摩西开始在接受信仰的破庙和维持生计的竹子社两地辗转时,即使不用回家,即使找到了生计,杨摩西也没有得到精神救赎。正如杨百顺所说,他叫百顺,但是他一点都不顺;同样,即使他叫摩西,但他并不是像摩西一样是拥有信念归属的精神活动者,他仍处于一种惶惶无依的精神漂泊中。
但是当杨摩西成为吴摩西,欲出走去宝鸡寻找老汪时,他真正觉醒了宗教意识。杨百顺遇到老詹时说,“我原来杀猪时,听你说过,信了主,就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前两件事我不糊涂,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后一个往哪儿去,这几年愁死我了”[2]335。当吴摩西在火车上与中年男子交谈时,他想清楚了自己要去宝鸡,自己叫罗长礼。小说借助了宗教隐喻,表明了穷途末路时依旧有路可走。而吴摩西在此后为自己改名罗长礼这一行为,也表示他“不再迫于生存不断被他人命名,他完成了对自我的指认”[3]105。
3 流浪意识的追溯:向死而生的孤独呼唤与远行的内在欲望
杨百顺出走的原因不单是他游离在家庭之外的孤独感以及空乏的精神生活,埋藏在灵魂深处的流浪意识也是他出走的主要原因。
3.1 生者向死者传达心意的喊丧文化
如果说杨百顺曲折的改名过程表现了他自我确认时的困惑,那么杨百顺自主选择“罗长礼”这个名字的行为则清晰显现了个人觉醒的姿态。杨百顺的生活变迁是由罗长礼的喊丧引发的。作者并没有着重描写喊丧,却让喊丧以草蛇灰线的方式延续在杨百顺的一生及其意识形态之中。在上半部的最后,吴摩西更是直接继承了“罗长礼”的名字代号。喊丧是说话的一种极端方式,一个源自民间的语言变种,它看似没有具体的对象,但却是来自心灵深处最寂寞的呼唤;它有特定的时刻、特定的环境需求,并不随时出现。对于死去的人来说,喊丧是死者故事的讲述;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喊丧会在偶然的机缘下,对人的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比如杨百顺。
杨百顺独爱喊丧,因为喊丧的“虚无、没有回应”除了代表着杨百顺孤独精神的外放之外,还让杨百顺体会到了极强的个人存在感。“‘喊丧面对死亡的个人性,其本体论意义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那是一个没有对象的呼喊,是向死的呼喊,‘喊丧发出的声调、音频、音重——那种美声似的吟唱,与现场的哀号形成深刻的区隔与歧义。由是,幸存与孤独构成一种互补关系。杨百顺着迷于罗长礼的喊丧,也是因为他从中体会到了那种孤独/幸存的经验。”[4]所以,在以死者和生者为参照时,杨百顺感受到了生命的孤独。这种孤独感来自生命,社会虽然由个人组成,但生命是独属于个人的。
在孤独感和生命力的互相交融中,杨百顺感应到了喊丧文化带给他的精神释放。他也许并未深入思考过喊丧对自己的巨大吸引力究竟源于何处,但是杨百顺在喊丧这一喜好中感受到了生与死的巨大隔阂和近在咫尺的双重体悟,对生命无与伦比的力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杨百顺的一生就在喊丧的驱动下,展开了特有的生命形态,他对生命的本质自然是懵懵懂懂,他始终在自己并未明确意识到对身体故乡的逃离和对精神故乡的追寻中缠斗。在这种缠斗中,杨百顺越来越接近自我的独立,所以杨百顺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个人流浪,并且冠以“罗长礼”之名开始了自己的精神之旅。
3.2 与生俱来的迁徙习惯
“流浪是人类自可以被稱之为人类的那一天起,就与生俱来的命运。”[1]265流浪意识更是存在于整个中华文化意识当中。自古以来,以游子、异客等为写作主体的诗歌、文章不在少数。流浪意识向来为文学艺术所青睐,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生命起源于水,人类会沿着河流、湖泊栖息,也会因为地域环境而改变栖息环境。这种迁徙状态一直存在,并且成为人类的一种习性。每一次迁徙,都伴随着一次重新扎根的过程。在迁徙之后,家带来的稳定感和舒适感构成了人类对家的整体印象,因此,家是有归属感的,流浪是漂泊无依的。
但杨百顺是相反的,从杨百顺在延津冷漠的家庭关系来看,杨百顺对家庭归属并不认可。无论是老杨组建的家庭,还是他自己组建的家庭,都满含浓重的悲剧感。因此,在社会环境和人情温暖缺失的背景下,杨百顺选择出走延津。但对杨百顺来说,由血缘组成的伦理纲常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他决定出走后,去宝鸡找了老汪。对杨百顺来说,世界之大,除了延津,就只有老汪所在的地方吸引着他。如果说是储存在灵魂深处的迁徙记忆和欲望带给杨百顺出走的冲动,那么血缘人伦则给杨百顺指明了出走的方向。
从杨百顺身上透露出来的生命孤独感来看,随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拓宽,家不仅是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居所,还是一个精神家园。余秋雨在《乡关何处》中认为,“游子是不愿意回乡的,偶尔回家也会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没完没了地想念,结果终于傻傻地问自己家乡究竟在哪里”[5]。显然,血缘伦理吸引着杨百顺对精神家园的找寻,而非家这个实体。实体的家只是精神家园的外化,有精神归属感的地方才能被叫作“家”。杨百顺一开始以为老杨的家是家,但是发现老杨是靠不住的,所以他离开了家。后来杨百顺以为,和吴香香组成的家是家,但眼见吴香香和老高相处后发现没有精神情感的家不算家,所以他开始了流浪。吴摩西在流浪中发现了自己在天地之间存在的位置,就像他喜欢喊丧一样。流浪,是他在没找到精神家园之前最佳的存在方式。
4 结语
杨百顺在出走延津之前,在一次次的改名和一次次的离家过程中逐渐明白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不在延津,于是他开始了寻找精神故乡的流浪。杨百顺流浪的背后弥漫着伦理纲常异化下,由个体精神世界空虚产生的虚无和孤独。由杨百顺的精神世界匮乏而发出的寻找精神情感寄托的呼唤,更是引导着我们思考当今社会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参考文献:
[1] 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243,265.
[2]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典藏版)[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673,684,335.
[3] 于欣琪.“出埃及”主题与中国新世纪文学的超越性面向[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0,36(1):103,105.
[4] 陈晓明.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98.
[5] 余秋雨.余秋雨自选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136.
作者简介:吴欢(1999—),女,安徽安庆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