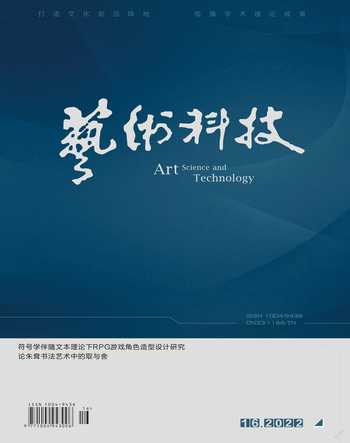古典文化语境下的动画美学意象研究
2022-05-30束铭薛骄
束铭 薛骄
摘要:在现代科技的催化下,数字技术领域推陈出新,动画的美学含义也在不断向外延展,动画艺术不再局限于影视动画中传统视听元素的简单集合,转而成为传播不同领域文化的重要媒介。动画美学意象作为独树一帜的艺术符号,对诗词意境和文学剧本都具有强大的表现力和创造力。文章以《中国唱诗班》为例,研究古典文化语境下的动画美學意向,《中国唱诗班》系列动画在原创的基础上展现了诗画一体的美学特征,实现了各种美学意象的和谐共生。
关键词:古典文化语境;动画美学意象;《中国唱诗班》
中图分类号:J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6-00-03
1 传统动画美学的创新发展
21世纪以来,文艺创作由之前侧重意识形态的传播转变为在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娱乐观众[1],原创动画历经探索、转型和发展,涌现了以《中国唱诗班》为代表的一系列优质古风动漫,既怀揣对过去经典的崇敬,也抱有对未来发展的热忱。
《中国唱诗班》又名“中国古诗词动漫”,是上海市嘉定区委宣传部投资出品的原创动画片,原为作曲家易凤林创作的音乐专辑,2015年起改编为系列动画,目前共包含《相思(上)》《元日》《游子吟》《饮湖上初晴雨后》《夜思》《咏梅》六部短篇。作品基于经典古诗词提供的历史素材,揣摩诗词背后的社会环境、人文气息及人物经历,演绎了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民间生活百态,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创作者以颇具文学性的叙事笔调描绘了一幅幅动人的情感画卷,获得了极高的关注。
新媒体时代的原创动画在技术上日趋成熟,艺术上不断融合。首先,视觉上遵循民族化风格样式。唱诗班动画的创作素材大部分来源于传统的记载,尤其是与嘉定民俗有关的背景史料,在尊重真实的基础上对诗词内容进行动画化,片中角色的样貌、服饰、发型与其所处的朝代、环境、身份大体相符。
其次,融合了当代漫画、插画的表现特征,符合年轻人的“二次元”审美。与20世纪美术片手绘为主、多种工艺共同发展的技法不同,动画生产高度工业化和产业化的当下,动画软件通俗易懂,加之外来动漫文化的冲击,促使今天的美术风格趋于多元化和类型化。
2 动画美学意象的诗性表达
王夫之说:“诗言志,但志不等于诗。”志作为人的思想感情,是可以被诗传达的,即艺术作品可以表达人的情感,但是不经加工的情感不能直接成为艺术作品。其关键点就在于艺术作品选取了意象,而在诗词中看到的意象,才是艺术表达的本体。与此同理,动画艺术所追求的意象也需要被创造,这些创造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将素材中的原型直接照搬到画面上,而是在故事素材的基础上发挥合理想象,构建一系列符合叙事环境的场景,设计符合场景逻辑的角色,赋予这些角色感情和生命,在虚拟的画面中演绎真实的情感。
唱诗班动画对意象的塑造十分成功,历史中的人物借由诗歌“活”了起来,他们丰沛的情感表达使其生动可爱、栩栩如生。
2.1 动画意象的陌生化
古诗词中的旧时生活与现代生活存在不可逾越的时空差距,动画艺术巧妙地利用陌生化手段弥补差距,实现对生命形式的再造。
其一,利用浓缩手法将冗长的历史剪辑为特定时间内的一段信息,再将信息中符合叙事逻辑的线索串联起来,形成清晰的故事段落,并确立段落之间的因果关系,构成圆满的情节冲突。诗词中所描述的社会情态、人物关系等有意义的信息得以在短时间内快速传达给观众。
其二,巧用象征手法,使原物和象征物之间产生联系。唱诗班动画中着重刻画红豆、梅树,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红豆、梅树的字面含义,不仅能够被大众理解,还能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意义。
2.2 动画意象的折射性
如果说动画艺术是映照客观事物的一面镜子,那么对写实的社会生活要有主观上的超越。大量动画作品运用拟人、拟物的手段,探索诗词中描绘的生命形式和生活空间,构造了符合常理又异于常理的美学特性。
其一,利用具象手法,以动漫造型特有的设计语言,让角色跳脱抽象的史料记载、坊间传说。唱诗班动画中的六娘、小曼、梅娘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她们所展现的肢体语言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表征,力图打破现实与梦境的界限,达到审美过程上的平衡。
其二,动画意象也充分折射出人类社会关注的哲学命题,如对自然界的认知、对人情百态的认知、对自我的认知。优秀的艺术作品善于利用画面、音乐、镜头的综合表现,揭示对问题的深层理解与反思,这是动画相比其他艺术形态在语言表达方面的显著优势。
2.3 动画意象的愉悦感
诗词如画,而动画形似戏剧,当舞台拉开帷幕,观众与角色在情绪上瞬间达成一致,开启了接受与宣泄的心理过程。动画的影像特征——动态的线条与色彩、童趣的人物与场面、奇幻的情节与包袱使这一过程带有强烈的视听刺激。作为动画作品的欣赏者,同时也是动画意象的审美主体,观众在关注故事发展和角色表演的过程中,充分调动了感知、联想、想象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具有高度的临场感。“审美感知一旦产生,审美过程便自然开始。感知领先,产生映象,然后才会吸引长久的注意力、激发激情、触动想象、获取理解”[2]。所以,无论作品的属性是喜剧与否,表演形式是否幽默诙谐,观众在审美层面的愉悦感是确定的、持续的、完整的。
3 古典文化语境下的动画美学意象群
“意象”这个词最早出自魏晋南北朝的刘勰,经过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演变,“中国文化史深受儒、道、释三家的影响,发育了若干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审美意象群,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形态,从而结晶成独特的审美范畴”[3]。沉郁是儒家文化的“仁”,飘逸是道家文化的“游”,空灵是禅宗文化的“悟”。
动画作品中的故事、角色并不停留于对历史的简单复制,也不拘泥于对古诗词的画面直译,其核心在于文化和审美的再创造。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现代动画艺术产生的时间晚于我国诗词歌赋,但是其不拘一格的表现形式高度契合古诗词意象的表达诉求。动态镜头下呈现的物的形象不仅是事物的外在造型,还是对事物进行深入探究后的胸有成竹。
3.1 沉郁:人世沧桑的深刻体验
《相思(上)》讲述了在封建礼教制约下,王初桐与六娘青梅竹马的爱情悲剧,其主体意象红豆出自王维的《红豆》,原诗是借咏物而寄思念,为眷怀友人之作。短片中的红豆被引申为代表爱情的意象符号,赠红豆、喝红豆粥、绣红豆三处情节贯穿全片。赠红豆是年幼时对相思之人的表白,喝红豆粥是少年对相思之情的寄托,绣红豆是少女待嫁他人时的不舍與伤感。
“审美体验的本质在于对自身局限的不断超越,是超出日常经验的常规,心驰神往,在生活表层上那连绵不断的因果链条的中断处深入进去,做超越时间空间的探索。”[4]创作主体借红豆完成了生活体验—审美体验—动画审美体验的过程,利用审美对象向观众发起情感对接,共同完成对生命活动的体察和还原。
南方烟雨照应着“红豆生南国”的诗词意境,全片未提及一个“悲”字,却道尽了人世沧桑。红豆作为赠予相思之人的信物,是发掘第一层生命的意象。红豆不仅是植物,还代表相思,如剧中对白,“这可不是一般的红豆,这是王维诗里的红豆”。
“红豆即相思”是多数观众既有的认知,符合审美者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是双方审美体验的高度重合。红豆粥作为相思的延伸,发掘了第二层生命意象,红豆熬成暖暖的汤水——相思虽苦但苦中有甜,以味觉关联现实生活中的苦与乐,含蓄地通过细节与观众共情,形成对美好情感的期许,是审美体验的超越。红豆手帕作为告别,发掘了第三层生命意象,少女手指被针刺破,红豆图案和着血色绣成,预示相思已经和生命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红豆这一意象完成了现实意义的突破,审美主体作为人的喜悲获得释放,实现了审美体验的再超越。故事终了,少年远走,这段痴侬之情注定没有结局,红豆的相思却依依犹在。
3.2 飘逸:精神世界的豁达超脱
对自由和美的表达是一切艺术形式的审美起点,文化对自由的表述不同,但内核高度一致。《庄子》开篇即名逍遥游:“承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康德认为:“没有自由就没有美的艺术,甚至不可能有对于它正确评价的欣赏。”[5]唱诗班动画《饮湖上初晴雨后》讲述明代才子娄坚落榜后一蹶不振,受好友邀请登船散心,众人把盏吟风月,唯有娄坚郁郁寡欢。老师徐学谟的养女小曼几次点拨使其顿悟,放下包袱重拾信心,实现了精神世界的豁达超脱。
《饮湖上初晴雨后》追求的正是精神自由的主观表达。娄坚的形象在剧中代表古代仕途不得志也不自由的一类人,在世俗评价标准的成败体系中,他们被认为是失败的。故事设定了三处调侃,逐一打破世俗评价的标准。
第一次调侃“船未漏而湿身”,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现实中未发生的坏事如何造成坏的结果,暗示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心被挫折禁锢,产生无尽的压力。
第二次调侃“才字加一捺成木”。娄坚年少成名,被称为嘉定大才子,如此赞誉在考试失败后成为负担,成为世俗的另一重桎梏——害怕再次落榜,害怕失去大环境的认同,在他人的凝视下丧失自我。“才”成为心理负担,成了没有灵气的“木”。
第三次调侃是小曼所唱南曲《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曲中有云:“端的是儒官多误身。”娄坚的失落之情达到顶点,感慨自己同样怀才不遇、饱受炎凉。此时小曼却道:“历史已有千载,状元进士有几人?”只有真正的圣贤之人才能千古留名,一时的成败不能决定人的终身价值,被世俗定义的“儒冠”往往怀才不遇,不如放下包袱,接受失败。
这三处调侃看似无礼却句句在理,娄坚的态度也从开始的无奈、尴尬、羞恼转变成结尾的释然。由此可见,意象不仅关乎外在的影像调度,还是通过创造“生命幻象”构建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契合,完成自我与外界的调和。
3.3 空灵:天地之间的无限感怀
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分析,相比儒家“沉郁”对仁的阐释、道家“飘逸”对游的阐释,禅宗“空灵”则是对悟或妙悟的观照。宗白华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源。”[6]古诗词中赞扬梅花的作品颇多,唱诗班动画《咏梅》借用北宋王安石的名句“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首尾呼应,通过对古籍内容的改编,创作了嘉定竹刻家周颢和梅娘的故事,委婉地讲述了一段文人与梅树相知相惜的情愫。
本篇剧情依然采用传统的分段叙述,梅树化为美人,清丽灵动的形象跃然纸上:文人笔下的梅花有“老人星”“孩儿面”“熊掌龟足”,却没有形容美人少艾的。周颢受师傅嘱托,要将“至美之物”刻于湘妃竹,却认为“仕女浮艳”,不愿刻画梅娘的形象。
一方面,竹刻传统题材一般以山水、花鸟、历史、戏曲为主,很少将个人情感直接外显在作品上,世人的“不解风情”暗示了古代文人审美意趣的偏好。另一方面,周颢穷其一生游历山河之间,认为至美之物必定是费尽周折、看尽大好河山之后才能寻得。最终竹面空无一物,缠绵病榻之际,意识到“至美”就是眼前人——矗立在孤岩绝境中的梅树高洁优雅,开放在属于自己的至美之境中,正如梅娘雪中烹茶自得其乐。
“万物静观皆自得”是宇宙空灵孤寂的本来状态,空不是空白,而是容纳万物的留白。竹刻和山水画的异曲同工之处也在于此,他们既能将美的事物具象化——花鸟虫鱼的妙趣、山林石涧的风骨、风霜雨雪的品格,又能将美的境界抽象化,和物象之间保持距离,保持各自不相依附的姿态。“至美之物”是融于生命的无言绝句,也是空灵和充实的对立统一。
《咏梅》深深映射出人们面对浩渺宇宙的无奈,心怀万物却言之不尽。影片将写实的景和虚幻的景交叠融合:一处是西湖十景,表现人间美景纷繁;一处是雪山梦境,暗喻生命垂危弥留。这两处虚构的情节将生与死、乐与苦、合与离的感受进行了高度的提炼,使观众主动参与到美的建构中,完成情和景的协调统一。
4 结语
艺术中的美,归根结底是根植于生活、生长在内心的,不是不经世事的空谈与自得,而是历经磨炼的智慧与勇气。我国动画前辈对影像艺术(下转第页)(上接第页)的执着追求从未停止,正如古诗词中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凝练与倾诉,她们是情与志最质朴的写照。中国原创动画再续辉煌的关键,正是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对民族情感的充分肯定。只有这样,创作者们才能赋予故事最生动的意象,观者和大众才能欣赏到优秀文化作品背后最瑰丽绚烂的篇章。
参考文献:
[1] 孙立军,孙平.文化与审美:中国动画学派的启示[M].北京:海洋出版社,2020:128.
[2] 余秋雨.观众心理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89.
[3] 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74.
[4] 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0.
[5] 康德.判断力批判[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61.
[6] 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56.
作者简介:束铭(1985—),女,江苏南京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新媒体艺术设计、影视动画。
薛骄(1999—),女,江苏南京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媒体艺术设计、视觉传达。